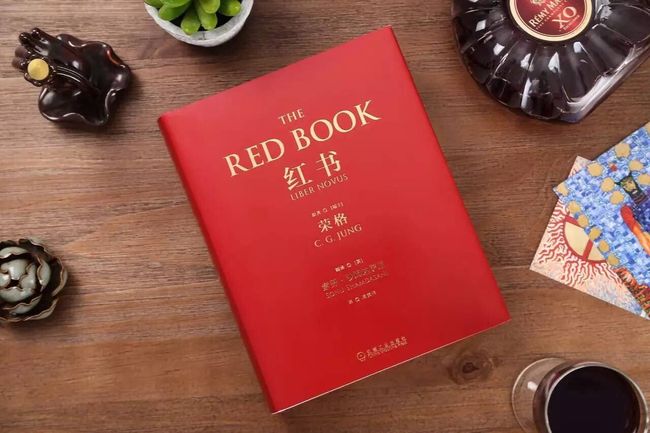前些天,有朋友让我介绍一下自己正在读的书,我说,如果世界上真的存在“天书”,大概就是卡尔·荣格的《红书》这样吧——这也许是最符合吃瓜群众们期待的回答了,人们总是愿意相信,自己无法理解的事情,是根本不可理解的。
《红书》实际上果然如大家所想象的那样不可理解么?倒也未必。只不过作为一本心理学研究专著——更准确地说是一份实验报告——没有心理学基础的读者可能需要专业解读的协助罢了。
当然这篇文不是专业解读,作为一名毫无心理学知识积累的普通读者,我不得不说读这本书是一段大开眼界的旅程,这篇文就当是拿出来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游记好了。
荣格是一个怎样的人?
即使对心理学一无所知的人也会听说过弗洛伊德的名字,如果你对弗洛伊德稍有兴趣,就一定会听到卡尔·古斯塔夫·荣格这个名字。很大程度上,荣格的知名度就是这么来的——作为弗洛伊德的传奇基友和对手——虽然这对一位同样伟大的心理学家来说并不公平,但是远离学术圈的人们显然还是对他们相爱相杀的传奇故事更感兴趣。
荣格是一名著作等身的心理学家,他的成就可以列举很长,最主要的是开创了分析心理学,提出了“集体无意识”和“原型”理论,以及和弗洛伊德一起开创了现代心理咨询与治疗的范式,两人共同建立了国际精神分析协会,并担任主席。
荣格的父亲保罗·荣格是一名乡村新教牧师。荣格的祖父老卡尔·古斯塔夫·荣格是一位著名的医生,以及共济会会员,曾有人指认他是歌德的私生子。
荣格的母亲埃米莉·普莱斯威尔克出生在一个沉浸在唯灵论的家庭里,她是弗里德迈特精神病院的一名住院患者,和丈夫的婚姻问题重重。荣格的外祖父萨穆埃尔·普莱斯威尔克是巴塞尔大学的神学家和希伯来语学者,他是提出犹太人应该有自己的祖国的先驱。
综合以上信息我们可以看到,荣格出生在一个家道中落的有宗教信仰的贵族世家,他童年的家庭生活并不幸福。
在大多数研究荣格的书中,都会首先提到一个被记录在《回忆·梦·思考》的荣格童年的梦境。在荣格4岁的时候,梦见一个在仪式中被崇拜的男性生殖器被摆放在一座地下神庙的金色王座上,他听到了母亲的声音,告诉他那是“食人怪”。荣格并不理解“食人怪”是神灵的名字还是说这个东西会吃人,但是这个梦深刻地影响了他对于神的意象。
真正使他对神的态度发生改变的是12岁时的一个梦,那是他进入巴塞尔高级中学的第一个学年,也是第一次参加圣餐仪式的年份。在梦境中,他看到神坐在巴塞尔大教堂上方的宝座上,一块巨大的粪便落下来,将教堂砸得粉碎。这个隐秘而渎神的幻想让他产生了一种如释重负的欢愉感。他感到自己在直面活生生的神(但是神却不在教堂和《圣经》里),在神的面前,他感到了孤独。
在这个梦境里,荣格意识到了父亲的缺失(这里要记得他的父亲是新教牧师)。接下来他进行了人生中第一次圣餐仪式,那种受到恩典的感受和随后而来的失落感形成了强烈对比。这些被拣选的感觉导致了他对教堂的彻底失望。在《回忆·梦·思考》中他说:“对我而言,这代表神的消失,宗教也不复存在,我再也不会去教堂了,那里没有生命,只有死亡。”
背弃了宗教信仰的荣格一生都在大量阅读。对少年荣格影响最大的是歌德(传说中的曾祖父),在《浮士德》中,荣格看到了人世间的邪恶被拟人化为魔鬼。在巴塞尔大学,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给荣格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感觉自己的第二人格和查拉图斯特拉类似。
他在母亲的纵容下,荣格开始秘密地阅读父亲的藏书,并在和父亲的探讨中不断补充给养。事实上父亲也失去了自己的信仰,日益成为一名唯物主义者。但是荣格却认为唯物论不过是一种观点而已,他更感兴趣的是神秘学。
大学时代的荣格对招魂术特别感兴趣,他的医学博士论文研究的就是海伦·普莱斯维克的降神现象。招魂术是巫师尝试使用科学的方法探索超自然力量和证明不朽灵魂的途径,现代招魂术出现在19世纪后半叶,在欧洲和美洲广泛传播。此时灵媒开始成为心理学的重要研究对象,恍惚的话语、自动书写、晶球幻视等灵媒使用的手段也开始被心理学家们使用,成为心理实验研究的首要工具。
1902年,荣格与艾玛·劳申巴赫订婚。荣格在日记里写道:“从此我不再孤独。”
《红书》是一本怎样的书?
《红书》记录了荣格从1914年到1930年间的“自我实验”——即荣格的“个体化过程”。
个体化过程是一种心理治疗方法,在于能够与幻想的人物或集体无意识的内容进行对话,并把幻想的人物和集体无意识的内容整合到意识中,那么就能重新找到在现代社会中已经遗失的神话式想象所具有的价值,从而调和时代精神(第一人格)和深度精神(第二人格)。
《红书》描绘的就是荣格的个体化过程,它呈现的是一系列的积极想象和荣格对其理解的尝试(这里的积极想象也是一种心理治疗方法,指通过自我表达的形式来吸收无意识的方法),换句话说,《红书》的主要内容就是描述荣格重新获得自己的灵魂和他如何在那个精神异化的时代克服重重困难,并把个体化当作一般心理模式进行阐述。
说白了,就是让心灵的内容自发地显现。
以此为目的,荣格在1913年12月开始了他的自我实验。实验过程是这样的:
1.在清醒的状态下刻意激发一个幻觉——灵媒的恍惚状态;
2.进入这个幻觉——这些幻觉可以被理解为一类以画面形式进行的戏剧化思考;
3.阅读幻觉——在此过程中,荣格此前进行的神话研究会产生影响,幻觉中的某些人物和概念直接来自于他阅读过的作品,而它们的形式和风格则反过来印证了他对神话和史诗世界的迷恋;
4.记录成《黑书》——《红书》的前身。
这样的过程表现在《红书》中就形成了这样的结构:
一、第一层——开篇部分
1.荣格重新找回自己的灵魂;
2.经过一系列的幻想探索;
3.1.发现自己在此之前都是在为时代的精神(第一人格)服务,特点是认同其作用和价值;
3.2.也存在一种深度精神(第二人格),它通往灵魂之物;
4.重新回到第二人格的价值观上。
二、第二层——之后的部分
1.阐述戏剧般的视觉幻想
a.遇到一系列不同背景的人物形象;
b.展开对话;
2.尝试理解;
3.转化成一般心理学概念和原理。
那么,把转化之后的“一般心理学概念和原理”抽象出来,《红书》的内容结构就会明朗了许多:
一、第一层——开篇部分
1.区辨和分析人格面具;
2.神话幻想的释放。
二、第二层——之后的部分
1.使用诠释学的方法治疗创造性幻想。
这就是“个体化过程”。这个治疗方法的理论基础很大部分建立于荣格在1916年发表的《无意识的结构》。这篇讲座论文介绍和论证了无意识的分类和无意识与“如神一般”状态、人格面具的关系,以及如何利用这些关系。
作为荣格思想的核心,《红书》不仅建立在浩如烟海的论文之上,而且建立在荣格的所有的阅读经验上,所以《红书》具有文学性并不会令人惊讶,但当我意识到它具有“如此的”文学性之后,仍然不可避免地发出了赞叹。
在研究幻想时,荣格意识到他是在研究心灵的神话创造功能。对于荣格而言,神话是力比多的象征,它们能描绘出力比多的典型活动。一个没有神话的人“就像被连根拔起一样,与过去、与自己身上延续的祖先生活、与他所处的人类社会皆失去联系。”所以,荣格选择用隐喻的方式记录自己的内在状态。
而作为一种哲学思辨,《红书》采用了对话形式——自柏拉图式对话产生以来,对话形式已经成为了西方哲学思辨的一种主导形式。和他对话的是“原始意义上的灵魂”,他将之称为“阿尼玛”——“集体无意识所看到的主体”。
当然,这个声音的在幻想中的具象随着荣格思想的变化也在不断变化。在《红书》的前身《黑书》中,为死者布道的是荣格的“自我”;在《黑书》的补充《审视》中,对死者讲话的是腓利门;而在《红书》的某些章节中,对话的对象是蛇和鸟。这些形象的不断变化,究其原因,是荣格在不断思考他对自己灵魂的三元本质的理解。
在《黑书5》的开篇部分,荣格在1916年1月16日的记录中写道:
“我将上和下绑在一起,我将神和动物绑在一起,我身上一部分是动物,另一部分是神,第三部分是人。蛇在下,人在中,神在上。蛇之外是菲勒斯,接着是地球,然后是月亮,最后是冰冷的外在空间。”
“如果我没有通过结合上下结合自己,我会分裂成三个部分:蛇——自我以这个或其他动物的形式漫无目的地行走,魔鬼般地生活在自然中,激发恐惧和渴望;人类的灵魂——永远活在你里面;天空的灵魂——与诸神居住在一起,远离你,你对其一无所知,以鸟的形式出现。三个部分相互独立。”
这大概是《红书》中蛇和鸟的意象的由来和含义。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红书》中腓利门扮演的角色类似于《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的查拉图斯特拉和《神曲》中的维吉尔。由此可见,《红书》的结构和风格受到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和《神曲》的强烈影响。但与两者不同的是,查拉图斯特拉声称神已死,《红书》描绘的则是神在灵魂的再生;虽然《神曲》和《红书》描绘的都是下地狱的过程,但是但丁利用的是一个既定的宇宙学,而荣格则尝试形成一个新的个人宇宙学。
《红书》在语言风格上深受歌德和但丁的影响。《红书》的语言风格遵循三种不同的文学语体——报告式、反思式和浪漫式,如歌德和但丁的用法相类似,三种语体在每一章交叉渗透又相互独立。此外,《红书》的每一章都是一个复调,同时又和其他章节共同形成复调。
难能可贵的是,这样的结构明显并非刻意为之,这些营养从童年开始就已经融化在了荣格的血液中。这也是我之前需要花很长的篇幅介绍荣格童年成长经历的重要原因。
荣格为什么要写《红书》?
如果要用一句话概括《红书》的主题,那么大概是——荣格整合阿尼玛的过程。整合阿尼玛的过程会带来三种效应:
1.通过吸纳无意识内容扩大意识范围;
2.逐渐减少无意识的主导影响;
3.人格的改变。
成功整合阿尼玛之后,接下来会遭遇与“超自然人格”。男性在整合阿尼玛的同时,也会获得她(阿尼玛是女性特质的灵魂)所拥有的力量,因此会不可避免地认同魔法师(公认的强大男性的原型形式)。在这个时候,他的任务是将自己与魔法师分开。于是这个人就会认识到原我——“我们身上的神”,我们整个心灵生活的起点纵横交错地根植于这一点,我们所有最高的和最深的目的都指向它。
在这里,我突然想起了荣格童年时期的一件小事。大约在10岁左右,荣格开始和自己玩一个游戏,他坐在一块石头上,问自己到底是荣格还是那块石头。他后来回忆说,“这个问题的答案一直都没弄清楚,我的疑惑伴随着一种好奇的感觉和迷人的黑暗感。”
后来有一次,他突然意识到,“刹那间我产生了一种势不可挡的印象,仿佛自己从一片乌云中浮现了出来。我立即明白了,现在我就是我自己了。”
本文首发于书入法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