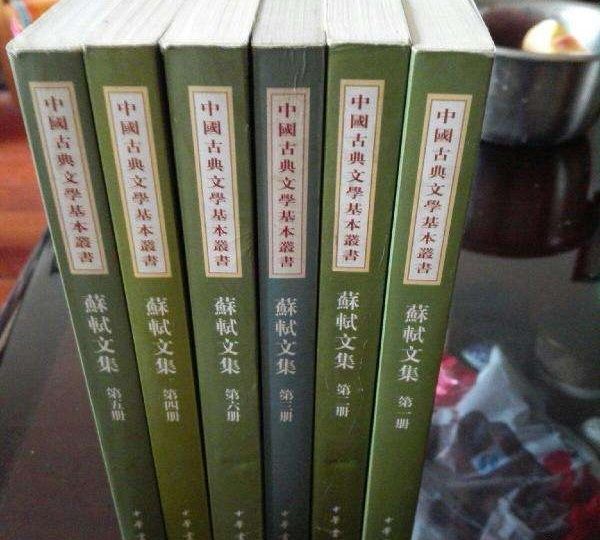巴蜀春秋之四十三
苏轼苏辙两兄弟开创的宋代蜀学到底是什么学问?
文 和运超
苏轼、苏辙兄弟是四川宋代文人士大夫最杰出的代表,两兄弟与其父苏洵在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中占了三席。可苏轼、苏辙兄弟不仅仅因为杰出的文学成就名垂青史,由他们开创的“蜀学”,与程颐、程颢兄弟的“洛学”,以及王安石的“新学”在整个宋代儒家学说形成“三足鼎立”。到南宋时期的继承者张栻、魏了翁,继续与朱熹的理学、陆九渊的心学并列。
那么,以文学见长的苏轼、苏辙兄弟的蜀学内容究竟有什么内容?他们在儒家经典方面究竟有什么独到的观点?由于绝大多数人们都只关注苏轼、苏辙的文学成就,显然在学术创造方面长期被忽视,值得被重新梳理一番。
一、苏轼、苏辙兄弟为宋代儒学代表之一
从苏洵开始,苏家父子三人早年一直在四川眉州家乡读书多年。苏洵年轻时科举多次不顺利,除了短暂游历,基本都在家教育苏轼和苏辙。
人到中年,儿子也基本成人,苏洵带苏轼、苏辙到汴京游学,拜会了文坛名宿欧阳修。对苏洵的《衡论》、《权书》、《几策》等文,认为可与贾谊、刘向相媲美,向朝廷推荐苏洵,经欧阳修的助推,苏洵的名气就传播开。
仁宗嘉祐二年(1057),苏轼、苏辙应试及第,名动开封。十年后,苏洵编写《易传》过程中病重去世,嘱咐苏轼继续完成。因此,苏轼、苏辙是宋代蜀学的开创者。
不过,要说苏轼、苏辙以博大的胸怀与杰出的学识凭空创造一种儒家学说体系,也是不科学的。他们的家乡巴蜀地区相对中原虽然较偏僻,但学术根基却十分深厚。从汉代文翁、严君平两大教育名家以来,巴蜀之地涌现的文士大多有创新精神,有扬雄这样的学术大家,有陈寿、常璩这样的史学名家,也有谯周这样纯正的经学家。
以儒学名士班固的《汉书》所记,“蜀地弟子在京师求学者之众,可与齐鲁相侔,”之后,常璩在《华阳国志》最早提出“蜀学”概念,他将巴蜀的文教事业与儒学传播联系在一起。
到唐代以后,多元文化兼容并蓄,互相成就,正是推动巴蜀文化走向繁荣的重要标志。儒释道三家都在巴蜀取得深厚的文化积淀,名家学说绵延不断。唐代众多优秀的文人士大夫,随大批北方世家大族涌入巴蜀,为当地思想的蓬勃壮大奠定了文化基因。五代十国的前蜀后蜀阶段,大量精英文士汇聚巴蜀,与南唐成为当时全国文化最繁荣的地区,儒学极为兴盛。
孟氏后蜀将《周易》、《诗经》、《尚书》、《春秋》、《周礼》、《礼记》刻于文庙石壁,田况守蜀时又补刻《仪礼》、《公羊传》和《谷梁传》,儒家经典《九经》完备,也标志巴蜀儒学的根基强大。比苏轼年长十岁的老乡吕陶(今眉山市彭山县人)在《经史阁记》总结说:“蜀学之盛冠天下而垂无穷者,其具有三:一曰文翁之石室,二曰高公之礼殿,三曰石壁之《九经》。”
稍微了解宋代文学发展脉络都知道,北宋初期崇尚南唐余音,文章以骈俪为时尚,诗词以西昆体流行。反对这种萎靡风格的正是一批文人士大夫,希望以儒家经学理念为依归,推崇言之有物,文以载道的标准。从王禹偁、石介、尹洙、范仲淹、梅尧臣、欧阳修、苏舜钦等人的作品和观点,逐步扭转宋代文化的潮流趋势。
如范仲淹和欧阳修,作为两个奠定宋代文化基础风格的大人物,范仲淹为一代名臣,在地方、朝廷、边关都有很好的成绩,是儒家出世理念的践行者。崇尚教育,推崇经典,但范仲淹倾向于“事功”一派,在南宋以后有虞允文、陈亮等人相呼应,他们都有深厚的儒学根基,但又与纯粹研习典籍的士大夫不同。
范仲淹发掘的胡瑗、李觏等人是北宋著名教育家,他重视“师道”,提倡“宗经”,以儒家经典培养能通达“六经”、悉经邦治国之术的人才。也注意兼授诸算学、医药、军事等基本技能,培养实用人才。范仲淹相比后来王安石能开创经学方面一家之言来说,更倾向于务实的才干。
而欧阳修生平在政务方面的才干不算明显,在文学、史学和经学三大领域则都有不俗的成就。只不过欧阳修的儒家经学方面,与他的史学、文学特点一样喜欢标新立异,表达不俗见解。作为一代大家,有些方面是可取的,有些方面就有点刻意,正如欧阳修主持写史,主要贯穿了他的儒家理念,不管在《新唐书》还是《新五代史》,对一些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批评都体现他的儒学宗旨。
尤其欧阳修的为人广受称赞,对有才华的同僚、后学都大力推举,像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张载、程颢、吕大钧、包拯、韩琦、文彦博、司马光等等各方面的才俊,几乎都得到过欧阳修的激赏与推荐。
可以看出,北宋文化到欧阳修开始,总体而言不是“守常”,而试图“图新”,以欧阳修为风向标,这一创新思想深深影响了王安石和苏轼。
三苏父子正以融通三教、兼采诸子的特色创立宋代蜀学。好比苏轼赠苏辙的祝寿诗《子由生日》中写:“君少与我师皇坟,旁资老聃释迦文。”经常被拿来举例说明苏轼的学术渊源以儒为宗、兼融释道。
苏轼、苏辙在宋神宗时声名最大,但这一阶段两兄弟在朝廷的实际地位并不大高。到宋哲宗元佑时期(1086—1093),朝野形成三个学术思想与政务见解相联系的派别,即以苏轼、吕陶、上官均为主的蜀派,以程颐、朱光庭、买易为主的洛派,以刘挚、梁焘、王岩叟为主的朔派。他们相互进行政治斗争,而蜀洛之争最为激烈。
南宋之初总结北宋灭亡的历史教训,清除蔡京党羽,恢复元佑时期的学术风气,对蜀派和洛派在过去朝廷方面的见解一概不追究,单单推崇他们各自在儒家学问方面的贡献,故“蜀学”与“洛学”成为宋代学术的标志。绍兴六年(1136),朝廷开始禁黜程学,被视为“伪学”,而苏轼、苏辙兄弟的蜀学从北宋到南宋前期基本都居于尊崇地位,直到南宋后期朱熹继承程颐的理学才占上风。蜀中学者李石《苏文忠集御叙跋》云:“臣窃闻之,王安石以新说行,学者尚同,如圣门一贯之说,僭也。先正文忠公苏轼首辟其说,是为元佑学人谓蜀学云。”
概括来说,苏轼、苏辙在学术上以儒家经学为根本,杂于佛道、纵横之学,他们不同于传统儒者,既是王安石新学的反对者,又是洛派理学的否定者,在宋代学术中保持独立自由的品格与巴蜀地方的学术特色。
以苏轼、苏辙为宗派领袖,以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等众多苏门弟子为成员,既经历从神宗到北宋末年大大小小的朝野纷争。同时,他们强大的文学创作影响力,基本代表了北宋中后期文坛的最高成就,即使蜀学因一定朝廷力量受到冲击,但其依附在文学思想之后进行传播,依然成为蜀学影响大量文人士大夫的一种方式。
二、苏门蜀学的内容与特色
宋代几乎公认是中华历史上文化学术的巅峰,以吴天墀等先生研究所得,虽然四川在宋代文化学术方面是一大重镇,但巴蜀文人士大夫在宋代前期的地位却不算高,从开始就颇受排斥。
四川从唐代后期开始一直与江南齐名,长期为文化、经济繁荣之地,如三苏家乡眉州,人文基础深厚,据说有一座孙家书楼建造于唐代,对眉州读书人影响很大。三苏祖上苏涣年轻时还当过盗匪,被乡里称为“白跖”,后来却开始读书学习, 在唐代宗广德二年(764)中进士,杜甫离开巴蜀前往至湖南时,还写过一首《苏大侍御访江浦赋八韵记异》诗,记录与苏涣的交游。
北宋初期,宋军入蜀颇受抵制,宋太宗登位不久发生过王小波、李顺的反抗,很多人忽视宋朝对巴蜀征税的高昂,不论北宋还是南宋,巴蜀川峡四路一直是全国交税最高的地区,这也是四川会出现“交子”的一个经济方面的原因。
另一方面,尽管有陈省华、陈尧叟、陈尧佐、陈尧咨一门父子在宋朝都算高官,非常引人瞩目。但从社会影响和文化学术方面却不突出,尤其澶渊之盟前夕,陈尧叟以来自蜀地,还建议宋真宗以迁都名义逃到四川躲避辽军,受到宰相寇准严厉批评。换句话说,除了个别状元高官,宋代前期的巴蜀文士还没有真正让人心服口服的饱学之士,只有到“三苏”父子被欧阳修这样一等一的大文豪钦佩才发生改变。
苏轼、苏辙兄弟在文学上的成就不用多说,他们在蜀学上如何融汇“博杂”的特色?
三苏融合蜀学传统的第一大特点是引入“史学”观念。蜀学一大传统是史学,因为儒家最重要的核心典籍就是《春秋》,史学是儒学根基之一。不论扬雄、陈寿、常璩等前辈,还是对“三苏”有知遇之恩的欧阳修,他们除了文学成就之外,都是重要的史学家。
尽管欧阳修后来自认为庐陵人(其老家祖籍为吉州永丰,历史上吉州为庐陵郡),但欧阳修本身是出生于四川绵州(今绵阳市),随父亲欧阳观在蜀地生活了三年,父亲过世,欧阳修才随母亲郑氏前往随州投奔叔父。
苏轼、苏辙兄弟在家乡读书较长时间,自然深受浓郁的蜀中学风熏陶,到开封参加科考以后,更受欧阳修在文学、史学方面的影响,尤其父子三人都在史论上堪称独到,三苏的论说文字几乎都是精彩华章。他们观察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的特点是更注重与寻常人的联系,扩大到对传统经典的解释更看重世俗人情方面。
苏氏蜀学的另一大特色就是充满“人情”味,这从苏洵对儒家经典的解读就开始。如《六经论》一开始就认为,礼所代表的伦理道德典范都建立在人情基础之上。“圣人始作礼也,不因其势之可以危亡困辱之者以厌服其心,而徒欲使之轻去其旧,而乐就吾法,不能也。”(见苏洵《六经论·礼论》)苏洵认为的人情,就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基本欲念,自然本性,以至于后来朱熹认为,“看老苏《六经论》,则圣人全是以术欺天下。”
苏轼继承苏洵的观点,也坚持“六经之道,惟其近于人情。”他还说:“夫圣人之为经,《礼》与《春秋》合,然后无一言之虚,而莫不可考,然尤未尝不近人情。”(苏轼《诗论》)苏辙后来也发挥这一观念,提出独到的“礼以养人为本论”,并洋洋洒洒写成一篇专文。他解释如冠礼养人之始,婚礼养人之亲,丧礼养人之孝,宾客礼养人之交,乡礼养人之本,等等,把各种礼仪都同人们的世俗生活结合,不再局限于过去抽象的儒家伦理解说。
朱熹对三苏的论述非常有意见,甚至认为蜀学比王安石的新学更加离经叛道,虽然正统宋学对蜀学带有偏激的排斥,也足以看出苏氏兄弟的蜀学对儒家的解读和切入点是非常与众不同的。
蜀学的容纳包容更体现开放性,所以第三大特色就是佛道融合。
众所周知,苏轼结交佛道非常广泛。在单纯的学术观念上,如代表性的《东坡易传》,对宇宙生成等看法,大量采纳老子说法,以老解易,如“天地一物也,阴阳一气也,或为象或为形,所在之不同,故在云者,明其一也……”包括运用水等理念,形容阴阳变化,非常有“玄”理,与朱熹等僵硬的天理说解释的确完全不同。在重要的存在论方面,苏轼看重物性自然,与庄子的观点相呼应,另一方面也与人情论相联系。
而苏辙的一些说法,更融合三教相统一,认为三教观念出于一心,有相同相通之处。他说:“老佛之道,非一家之私说也,自有天地,而有是道矣。诚以形器治天下,导之以礼乐,齐之以政刑,道行其间而民不知,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泯然不见其际而天下化,不亦周孔之遗意哉!”(见苏辙《栾城后集》)苏辙在《老子解》等著作中,也把其含义与儒家相结合来解释,往往认为与孔子孟子相一致。同时,苏轼在为苏辙写的跋文中也一再为弟弟鼓吹,认为其见解合乎先贤的真谛。
因为苏轼、苏辙是文章高手,苏轼的门生如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陈师道、李廌等无不是宋代著名文士,他们一起互相著述传播,顿时比洛学、新学门人单纯的学究水平高出不止一筹,所以,北宋后期到南宋前期,蜀学成为影响最大的学说,也进一步影响到纯正的儒家弟子。
三、苏氏蜀学的传承影响
就在仁宗时期,苏洵带苏轼、苏辙到京城开封参加科考,父子一举成名以后,随着苏轼、苏辙兄弟一流的才华,苏氏兄弟在中原打开蜀学的名号。
几乎与此同时,传统的儒家弟子如周敦颐、程颐师徒反而有前往巴蜀的经历。仁宗嘉祐元年(1056),周敦颐离开家乡湖南为官的第一次远行,就是到合州(今重庆市合川区)为判官,一共五年。在合州,周敦颐生下长子周寿,妻子陆氏过早病故。
周敦颐在巴蜀期间,为很多当地学子教授易学,尤其完成了宋代理学史上重要著作《太极图说》,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原创作品。这样一部影响深远的儒家著作,正是周敦颐在巴蜀地区吸收当地佛道兼容思想完善出来的,颇为让人诧异。
周敦颐被程颐程颢兄弟视为洛派宗师,其实并没有因为他是正统儒家士大夫,表面批评佛道思想,本质上周敦颐还是顺应时代,开宗明义“易有太极”,将阴阳与中庸,太极与无极,将儒家易学与老庄道家的许多思想都进行吸收融合。
在嘉祐五年解职回到京师路上,周敦颐与要进京述职的王安石相遇,两人都是闻名已久。之前,王安石刚向朝廷递交生平第一篇重要的万言长文《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已经提出要积极大展抱负的志愿。他也是宋代儒家标志性的人物,双方都开创一派,对儒家学说进行了透彻交流,互相都受到很多启发。
王安石之父王益,曾在四川新繁为知县,所以,王安石少年时也有随父亲入蜀生活的经历,与欧阳修近似。王安石身上的创新精神也很大,后来号称“新学”,本身王安石对佛道思想同样兼容并包,尤其他的诗文,后期离开朝廷,恬淡安静的气息更加突出。所以,宋代儒学看似各自为阵,本身基础方向却是大体一致的,只是各家都有独到见地,这才产生不同的门户之见。
周敦颐最重要的弟子程颐,二十四岁在京师讲学。神宗熙宁五年(1072),声名远播,重臣文彦博将其鸣皋镇(今洛阳市伊川县境内)的一座庄园赠送给程氏兄弟讲学,改建为伊皋书院,两兄弟前后在此讲学长达20多年。
哲宗继位后绍圣四年(1097),程颐被贬涪州(今重庆市涪陵县)进行编管。过去史学界往往认为这是程氏兄弟与苏氏兄弟之间矛盾的尖锐化,因苏轼成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以后,与程颐同为哲宗的老师。苏辙更深受高太后器重,一直做到龙图阁大学士、代理太尉,进爵开国伯。而程颐也是司马光、王岩叟等守旧人士倚重的人。哲宗亲政以后,实际对两边大臣都进行了处置,程颐就比较典型。
苏轼性格豁达,生活上不拘小节,与年轻的哲宗比较投缘,而程颐一贯比较严厉、刻板,苏轼多次批评程颐对皇帝过于苛刻,有些不近人情,造成两边矛盾加深。哲宗对程颐非常反感,后来斥责程颐“妄自尊大,在经筵多不逊。”连司马光都曾在书信里表示遗憾:“使人主不欲亲近儒生,正为此等人也。”(见《寓简》)
程颐如周敦颐一样,在涪州期间,他也完成了一部代表作《伊川易传》,就是更为严谨的义理学说形成,充满思辨性的哲学见解和儒家伦理体系初具规模,此后成为宋元明最有影响的一派学说。
程颐学说在巴蜀的流传也反过来对当地的儒学士子产生新的影响,例如张栻(今德阳市绵竹县人,为两宋之交抗金派重臣张浚之子)就深受启发,以及之后魏了翁,南宋以后的蜀学继续发扬融合包容的长处,这就是吸收洛学思想进行充实,南宋的蜀学开始具备一些思辨性的解释,像在太极、理、道、心、性、器等等概念方面,都有哲学本体论的特色。此后使南宋蜀学能够继续与程朱理学和陆九渊心学“三足鼎立”,足见蜀学独特的生命力,所以宋代由苏轼、苏辙兄弟的开创之功与铸造的蜀学特色功不可没,成为巴蜀文化中最具厚重底蕴的一大历史名片。
2019年6月
本文为作者原创,若转载请署名出处,若盗文将追究责任,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