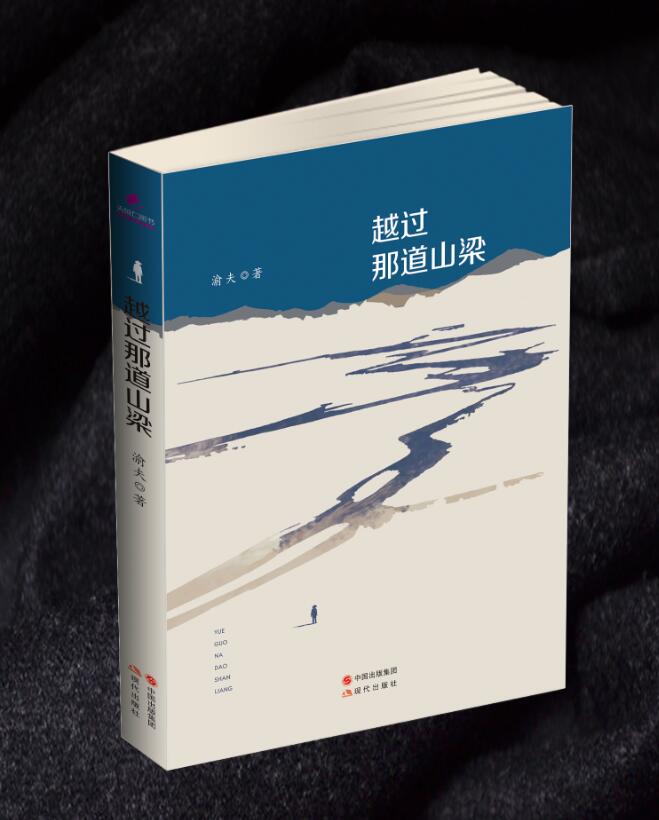(七十九)
从父亲房间里出来,李远忽然想到一些问题:面对灾难或变故,一个人的承受能力到底有多大?是不堪一击、痛不欲生?还是面对现实、笑看人生?
显然,这没有标准答案。不过在李远在看来,绝大多数人会选择后者。就像身患绝症的父亲,还有遇到挫折的自己,或许做不到泰然处之,也无法从一开始就笑看风雨,但经过一番痛苦的思索,终究还是会和现实达成和解。当然,也可以称之为妥协,微笑着向命运妥协,愉快地向生活投诚。这不是逃避,而是一种负责任的人生态度。谁能永远都做命运的强者?谁都不能。因此,不妨学一学丰子恺,学一学这位文艺大师的胸襟:“既然无处可逃,不如喜悦。既然沒有净土,不如静心。既然沒有如愿,不如释然”。
十一月一日下午十四时许,按照之前的约定,李远和田梅敲开父亲的房门。李良开早已穿戴整齐,微笑着出了门。
“爸,咱们下午去哪儿?”田梅让公公拿主意。
李良开也没客气:“就去药王山吧。今天我们一不逛街,二不参观,只有一个任务,跟在那些信徒后面,看一看人家怎么转经。”
尽管已是下午,“日光之城”拉萨的阳光依然强烈。一行三人搭车来到与布达拉宫咫尺相对的药王山西麓,看到前来转经朝拜的人还是络绎不绝。通透的阳光下,虔诚的信徒们全神贯注,默诵真言,双手合十,触额、触口、触胸,五体投地,匍匐前行……同样的动作不断重复,每一次都满脸肃穆,丝毫没有敷衍之意。
信徒俯身叩拜的这面山体,大约有两层楼高,上面密密麻麻刻着上千个色彩艳丽、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佛像。即便都不是佛教信徒,置身这样的环境里,李良开、李远和田梅还是感受到了一种庄严、神秘的氛围。三个人谁也不没有说话,生怕惊扰了虔诚朝拜的人们。
李良开面色严肃,紧靠碎石铺成的转经小路一侧,默默地跟在一位六十多岁的女子身后,用心观察看她的每一个动作。李远、田梅不知道父亲此举何意,只能尾随其后,静观其变。
这是一位骨瘦如材的女子,体格弱小,满脸皱纹,嘴里一直念念有词。李良开听不懂她在念叨什么,但注意到她的神情平静而安详。跟着转经的信徒走了个把小时,李良开觉得身体有些吃不消,胃部也隐隐作痛。田梅劝他找个地方休息一会儿,李良开不同意,说自己还能坚持。
看着妻子求助的眼神,李远微微一笑,掏出一支香烟先给自己点上,后又掏出一支递过去:“老汉,要不你也过过嘴瘾?”
“医生说了,爸爸不能抽烟!”田梅赶紧阻止,“李远,你怎么回事?爸爸的身体你又不是不知道,怎么还让他抽烟?爸,别听他的,抽烟有什么好啊,既费钱还伤身体,没一处划算的地方。”
李良开笑了笑:“二女儿,要不咱们破破例,我就抽这一支?”没等田梅答应,右手已经伸了过去。
“就是嘛,抽一支能咋的?我屋老汉以前还抽叶子烟,抽了几十年,这纸烟算个啥啊,一点劲儿也没有。”李远不管妻子反不反对,给父亲点燃了香烟。
“香,真香!”李良开猛吸了一口,“你老娘非要我戒烟,不戒就天天跟我急。我一辈子就这个爱好,戒了还真是难受。”说起抽烟这个话题,李良开来了兴趣,随意坐在一起石头上,一边吞云吐雾,一边和二儿子闲聊着。
“我和你妈搞对象那阵子,她从不反对我抽烟,还说男人抽烟才有男子汉气概。我信以为真,以为找了个好婆娘。可哪知这是烟幕弹,从结婚第二天开始,她就天天跟我念叨抽烟对身体不好,非要我戒掉。我也试着戒了好多次,每次都半途而废。这次我的胃出了毛病,她逼着我把烟戒了。老二,戒烟这滋味也太难受了,浑身上下没有一个得劲的地方。香,真香!”说话间,李良开嘴边那支香烟差不多只剩下过滤嘴。
“要不您就别戒了?”李远试探着问道。他想好了,只要父亲点头,他会努力说服母亲改变主意。毕竟,父亲来日不多,真没必要这么苦着自己。
“还是算了吧。”李良开却不同意,“好不容易戒掉了,再捡起来,我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何况,你妈也是为了我好,咱们不能图一时之快而伤了人家的心。”
“爸,您真行,说到就能做到!”田梅由衷地称赞,“不像某某人,总是说要戒烟,可从没认真戒过。”
李远哈哈大笑:“说我就说我嘛,还某某人。好好好,我向老汉学习,下一步坚决戒烟。”
三人说话间,那位六十多岁的女子也停下来歇息,正朝这边张望着。
李良开向田梅要了一瓶没开封的矿泉水,快步追了上去,用半生不熟的普通话打着招呼:“大妹子,你好。看你满头大汗的,一定渴了吧?来,喝口水。”
“劳慰您。我不口渴。”女子一张嘴,竟然是重庆万州一带的口音。
“老乡?你好你好,我是开县的,你是万县的?”多年的习惯使然,李良开仍然按以前的叫法,把万州叫做做万县。
女子点了点头,算是默认,之后指了指李远和田梅:“老乡好。那两个跟你一起的?”“我二儿子和他媳妇。”李良开点头称是。
“你几个孩子?四个儿子?还有四个孙子两个孙女?真好!大哥,你真是好福气!不像我,孤老婆子一个……”说着说着,女子的神色有些异常。
“对不起,对不起。”李良开连忙表示歉意,“我不知道你……”“也没啥。”女子擦了擦眼泪,稳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没事,都过去好几年了。谁叫我命苦啊。”
这个女子自称姓柳,来自万州城区,退休前是一家国有丝绸厂的设计师。她和丈夫晚婚晚育,三十六岁才育有一子,两口子视为心头肉,精心呵护培育。儿子是个环保主义者,大学毕业后,主动申请进藏,从事高山草地保护研究工作。四年前的初秋时节,儿子与一位云南籍援藏女大学生结婚,两人利用婚假到藏北无人区考察高山草原,遭遇车祸双双身亡。
白发人送黑发人,处理完儿子儿媳的后事,丈夫经受不住打击,留下一封遗书,从万州长江二桥跃身跳下,三天后在巫山新县城附近发现其遗体。柳姓女人本来也不想活了,但想到儿子的灵魂还在高原飘荡,需要母亲的陪伴,便变卖所有家产,到拉萨买了一套一室半的小房子定居下来。之后,每年初秋,也就是儿子儿媳遇难前后,她会一趟藏北高原,雷打不动。其余时间,每天下午沿着药王山的转经小道伏身叩拜,全程用时三到四个小时不等。
“大妹子,你这样是不是太辛苦了?”听完柳姓女子极为平静的讲述,李良开关切地问道。
“都习惯了,一点也不觉得辛苦。”柳姓女子依然很安静,“大哥,你不要小看转经,它确实能让人平静下来。说真的,作为一个失独母亲,一个失去丈夫的女人,我以前觉得我肯定活不下去了。到了西藏,尤其是天天转经,我不再那么悲伤了,甚至流泪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一切都是上天安排好的,悲伤又有什么用呢?好好为他们俩爷子和我儿媳妇活下去,别让他们在天上担心我,才是我应该做的事情。”
对失独这个说法,李良开并不陌生。因为前两天,在与二儿媳探讨二胎问题时,为了证明生二胎的必要性,田梅曾经给他看过一则微信。
这是一组拼凑痕迹较重的图片,重点是报纸上的新闻标题。第一幅是一九八五年的报纸,新闻标题为“只生一个好,政府来养老”;第二幅是一九九五年的报纸,新闻标题为“只生一个好,政府帮养老”;第三幅是二零零五年的报纸,新闻标题为“养老不能靠政府”,还加了一个感叹号。
给李良开看完这则微信,一直想生二胎的田梅讲:“爸,您看看,把这些报纸前后一对比,就会产生一个疑问,只生一个有什么好?如果意外失独,老了连个端茶送水的人可能都没有。我听说全国现在有不少失独家庭、失独夫妇,唯一的独生子女成年后意外去世,再生孩子已经来不及,配套的养老政策和社会保障又没跟上,他们的悲伤和绝望心理可想而 ,有的甚至对生活失去希望。爸,不瞒您讲,我就想再生个孩子,可李远不同意,说这不符合规定。”
当时,李良开并没意识到失独意味着什么,还劝田梅要支持丈夫,不要因小失大。可面对柳姓女子的家庭悲剧,李良开一时语塞,不知道怎么安慰对方……
(八十)
还是药王山西麓,还是那条碎石铺成的转经小路,那是那些虔诚的佛教信徒。唯一有所不同的,是李良开身边暂时没了李远和田梅的陪伴。
此刻,时针指向公元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二日七时四十五分,太阳还没出来,“日光之城”拉萨还沐浴在晨光之中。望望山上那些色彩各异的佛像,看看那些虔诚叩拜的人们,头天晚上还在担忧后事的李良开心里觉得敞亮了许多。
是啊,人活一世,草木一秋,年过百旬也好,英年早逝也罢,不过都是一个由悲到喜、悲喜交加的过程。权贵也好,平民也罢,都是哭着来到这个人间,跌跌撞撞地长大,或哭或笑面对成长中的烦恼,最后在亲人的悲泣中离开这个世界。这是人类通用的生存规律,没有特殊,鲜有例外,一切都只是时间问题。
至于比自己活得更久的亲人,牵挂又有什么用呢?一旦永远闭上双眼,这个世界的所有喧嚣与纷扰都与自己无关了,即便是最亲最爱的人,他们最终也会从痛失亲人爱人的悲伤中走出来,该笑还得笑,该乐还得乐。一个新生命的诞生会在较长时间内改变一个家庭的生活轨迹,少至七八年,多则一二十年;而一个生命离去带给同一个家庭的冲击则要小得多,最多三年,生活就会恢复正常。毕竟,无论多么重要的人去世,生活还是会沿着其固有的轨迹,一天不停地继续下去。
想明白了这些,李良开对自己的胃癌真就无所谓了。病情已然如此,活一天就是赚一天,何况自己儿孙满堂,自个儿也早已突破唐家岩李氏男丁活不过六十周岁的魔咒,个人事业上虽然说不上辉煌,但好歹也当了四十年大队和村干部,在农村来说,也算得上是光宗耀祖了。
再仔细想想,四个儿子的工作和收入都算稳定,六个孙儿孙女也一天天长大,根本不用自己操心。再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活法,就算自己活到一百岁,真正能帮衬后人的地方又有不少?少得可怜。儿孙自有儿孙福,路还得靠他们自己去走,操心也是空操心,没有多少实际意义。
就在头天晚上,李良开正准备睡觉,李远敲开父亲的房门,说有几个战友要安排吃饭,问他去不去,李良开拒绝了。自个儿不能喝酒,和这帮年轻人又没多少共同话题,去凑那个热闹干什么?与其非常尴尬地坐在那里,不如给年轻人创造一个尽兴尽情的机会。
如果说还真有放不下的,就是相濡以沫五十一载的妻子徐小芳了。平日闲聊的时候,老俩口偶尔也会谈及谁先走的问题。每一次,徐小芳都强调她希望死在丈夫前面,这样自己就不会那么悲伤和孤单。每每此时,而李良开从不表态,但内心深处十分赞同妻子的想法,男人么,就应该有点担当精神,尽可能让自己的女人开心一些。当然,他更希望与妻子共赴黄泉,这样谁都不会觉得悲伤和孤单。显然,这不大可能,除了一同遭遇突发事件和自然灾害。生死有先后,有合就有分,就算是至亲至爱的两个人,谁也不能一直陪伴另一个人,爱得再深,感情再好,总会有一个人先走一步。可是,如果自己真的先走了,妻子能挺过这一关吗?
正想着心事,李良开忽然听到背后像是有人试探着叫自己:“三表叔?您是三表叔?”
一回头,看到那位三十多岁、满脸憔悴的年轻女子,李良开惊讶得后退了一步:“小薇?你真是付小薇?你不是在深圳吗?怎么跑到拉萨来了?”
“三表叔,是我,我是小薇。”年轻女子身着防晒服,双肘双膝分别绑着轮胎胶皮一样的东西,一副转经的装扮。
“你也信这个?”李良开非常疑惑,指了指转经小路上匍匐叩拜的信徒,又指了指山上那些色彩各异的佛像。
付小薇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不上真信,就是求个心安。我的情况,您也不是不知道……”
“我知道,我知道……”李良开尴尬地笑了笑。
是的,对于付小薇这个这个表侄女的情况,李良开是知道的。如果按照城里人的说法,早在十多年前,小薇就是个“问题少女”,不自重,不自爱,自暴自弃,堕落红尘。当然,乡下人大概并不知道“问题少女”这个说法,直接把小薇之类的女子称为“鸡婆”。“鸡婆”并非李良开老家一带的叫法,而是源自东南沿海。而小薇最初的堕落,又与东南沿海毫无干系。一些女孩是到东南沿海打工后才学坏,小薇没出远门就成了被人指指点点的鸡婆。
小薇出生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长得乖巧玲珑,从小就是父母的掌上明珠。这主要得益于小薇的父亲比较开明,不那么重男轻女,甚至还更喜欢女孩一些。所以,尽管小薇还有两个学习成绩很好的哥哥,可父母还是把更多的宠爱给予了唯一的女儿。
打小起,小薇就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幸福生活。离开学校之前,她甚至没动手洗过自己的衣服。父母总讲穷养儿子富养女,两个哥哥也不多说什么,小薇更没觉得有什么不妥,心安理得地当着小公主,也多少养成了骄横霸道、我行我素的性格。这种性格,最终让小薇在初中毕业前误入歧途。
初三上学期,情窦初开的小薇不可救药地喜欢上了班里的英语科代表吴迪。先是单相思,只是默默关注着吴迪的一举一动。后来实在难忍相思之苦,小薇便用一张纸条表明心迹,结果被一心想考重点高中的吴迪婉拒。
原本这只是一段连开始都没有的感情,与失恋扯不上关系。试想,不曾彼此相恋,哪来什么失恋?可从没受过挫折的小薇却不这么认为,把吴迪的拒绝当成天大的事情,甚至有种天塌地陷的感觉。对这位骄傲的小公主来说,这何止是失恋,简直就是痛不欲生的失恋。于是,原本活泼开朗、学习成绩中等偏上的小薇变得沉默寡言,学习劲头也一落千丈,一副干啥都没意思、破罐子破摔的消极模样。
中考前一个月,小薇结识了镇上的一个小混混。同寝室的女同学提醒小薇离他远点,说这家伙儿吃喝嫖赌样样占全,不值得迷恋。小薇原本没想和他深交,听同学这么一说,她倒来了劲儿:“你该不是嫉妒我吧?那好,我偏要试试看。”
试来试去,小薇上了套,开始学喝酒,开始去镇里新开的红叶夜总会唱歌跳舞。有吃有喝还有的玩,并且不用花钱,到哪都享受公主一般的待遇,小薇很快喜欢上了这种生活方式,对学习的兴趣越来越低,先是不上晚自习,后来发展到逃课,最疯狂的时候干脆夜不归宿。班主任老师劝了几回,小薇答应得好好的,可回头依然出去胡混。学校忍无可忍,开除了她的学籍。
小薇的母亲闻讯跑到学校,哭喊着跪在校长面前求情:“再给我女儿一次机会吧。”校长也落泪了:“我也没办法啊,我得对全校几百名学生负责。”
从校长办公室出来,在学校操场上,当着父亲的面,母亲打了小薇两个耳光。小薇顿时觉得委屈,转身向镇子上跑去。父亲要追,被母亲一把抓住:“让她跑。这个砍脑壳的,她还敢不回家不成?看我不打断她脚跟。”
小薇真就没回家,而且还直接住进了红叶夜总会,先当负责倒酒、点歌的服务员,被那个小混混下药迷奸后,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做了三陪小姐,陪喝陪唱陪跳,甚至陪睡。没过多长时间,放荡不羁的小薇成了红叶夜总会第一红人,每晚点她的人很人,甚至大白天也有人开车把她接走。小薇就那么妩媚地笑着,浪荡地活着,搞臭了自己,也搞臭了家人,让父母和两个哥哥抬不起头来。
到红叶夜总会哀求女儿回家未果的那天晚上,母亲跳岩自杀。得知这个噩耗,小薇把自己关在屋里,两天没有出门。她打电话给父亲,想回家送母亲最后一程,父亲沙哑着嗓子叫她滚,能滚多远滚多远。
母亲去世一年后,借酒浇愁的父亲把自己喝死了。父亲下葬的前一天晚上,从外地赶回家的大哥让人给小薇捎话:“老爸临死前交待了,不让你回来送他,你自个儿好自为之吧。”其实,大哥只把父亲的遗言说了一半。临死前,没读多少书、已经说不出话的父亲给大儿子留了张措辞前后矛盾的纸条:“不让小薇回来送我,我没她这个女儿。你要想办法帮帮你妹妹,她不能就这么毁了。”
为父亲烧完头七,大哥和二哥到红叶夜总会找到小薇,什么也没说,先给她看了父亲的遗言。小薇泣不成声,使劲揪着自己的长发,把头往墙壁上撞。大哥上前抱住她:“妹妹,听话啊。你接下来的生活,哥来给你安排。”
大哥和二哥是父母的真正的骄傲,双双大学毕业,都有不错的工作。大哥还在南方某个省城按揭买了房子,成了家,日子越过越红火。原本,大哥想把小薇带到他所在的城市,可小薇说啥不去,因为她觉得无法面对大哥大嫂和他们的双胞胎儿子。兄妹三个商量了半天,决定请那个在北京当厨师的远房表哥帮忙,先让小薇当餐馆服务员,过后的事情以后再说。
离开家的那天,小薇跟着两个哥哥回了趟老家,看了看老屋,到父母坟前大哭了一场。在老屋跟前,大哥拿出相机:“都照张相吧。这个家,我们是再也回不来了……”
大哥的意思,小薇懂。因为自己的行为,全家人都觉得脸上无光,无法坦然面对左邻右舍异样的眼光。事实上,两个哥哥早已作出决定,老家房子不再定期花钱请人检修,而是任由风吹雨打,直到垮塌为止。换句话说,从今往后,大哥和二哥不会轻易再回老家。
(八十一)
小薇的父亲是在二零零七年夏天去世的。这一年,她十八岁。在这个年纪,别的女孩对未来充满幸福的渴望,而她则因放纵和堕落,失去了对生活的美好憧憬,除了行尸走肉般活着,一切似乎都毫无意义。
不过生活总要继续。在远房表哥的引荐下,满腹心思的小薇第一次走出连绵不绝的大山,先坐汽车,后换火车,跨越了几个省市,这个老家小镇红叶夜总会的三陪女成了京城一家川菜馆的服务员。
小薇永远都不会忘记老板娘第一次见到自己的惊愕表情和夸张声音:“多大了?十八岁?不像不像,看起来你很有女人味嘛。没结婚?没男朋友?不像不像,我是过来人,看人一看一个准儿。真没有?好吧,既然你表哥吱声了,明天上班吧,一个月只休一天。工资底薪加提成,挣多少,全看你自个儿的本事了。我可告诉你,你得好好谢谢你的表哥……”
小薇没吱声,心想这个老板娘说话怎么跟剥豆角似的。后来熟悉了,才听说老板娘来自辽宁铁岭,一个盛产二人转和笑星的“大城市”。
尽管能够感受到老板娘和饭店其他女孩的轻视,小薇还是觉得很踏实。毕竟,这里只招待吃饭喝酒的客人,不必陪酒,更没有无处不在的诱惑,不像夜总会的日子,总是让人莫名地兴奋,同时又充满混沌、飘渺或是绝望。
对于小薇来说,红叶夜总会的那段经历,简直就是一个难以醒来的噩梦,梦里没有快乐,只有强颜欢笑下的无尽耻辱。
饭店服务员这个行当并不好干,特别是像小薇这样的外地姑娘,刚开始普通话又说不好,经常被好事的顾客挑刺,诸如说话听不清、微笑不真诚、茶水温度不够,再就是上菜太慢、菜里油太多、盐太少等等,五花八门,防不胜防。
对这些挑剔的客人,老板娘不敢得罪。饭店靠的就是回头客,如果因为客人爱找茬就慢待人家,肯定是不行的。得罪不起客人,老板娘就拿服务员开刀,不管客人说的有没有道理,先把服务员批一通再说。
在这家川菜馆的回头客中,有一个叫阿胜的年轻人最爱找服务员的麻烦,不管是谁在他预订的包房里服务,都会被他为难得够呛,很多时候只有老板娘亲自出面,才能把事情摆平。
从阿胜与朋友的言谈举止中,服务员们分析他应该是一个个体户,开着一家公司,手下十多个员工,有车有房,已婚生子,也算是事业有成。
对阿胜这样挑剔的客人,有过夜总会工作经历、见识过不同男人的小薇并不怎么在意,很有点水来土挡、火来水淹的风范,不管阿胜怎么刁难,她总是以微笑应对,既不辩解,也不道歉,反正就是不接茬,最终一笑了之。
老板娘看出了点门道,阿胜再带朋友前来就餐,总会安排小薇前去服务。面对这个始终面带微笑、从不接招的秀美女孩,阿胜从最初的大呼小叫逐渐变成轻言细语,从横挑鼻子竖挑眼变为怎么看怎么顺眼,多次提出要带小薇出去玩,或去商场给她买衣服和首饰。
作为过来人,小薇知道这个男人对自己产生了兴趣,或者说他喜欢上了自己。小薇也不说破,更不表现出任何亲热的眼神或举动。她已没了谈情说爱、打情骂俏的激情,只要能把本职工作干好就行了。
事实上,风月场所的经历,让小薇对男人产生了强烈的憎恨心理,也十分认同“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这个说法。比如这个阿胜,明明是有家室的男人,还在外面拈花惹草,连个饭店的服务员也不放过。他种所谓喜欢,明摆着就是为了占有,与爱情毫无关系。这样的喜欢,不要也罢。于是,有意无意之间,小薇便在阿胜面前表现一股清高孤傲的劲头。
得不到的永远是最好的,阿胜自然也逃不过这个俗套的说法,对小薇愈加上心起来,来饭店里消费次数也明显增多。不仅如此,他还经常介绍他的一帮朋友前来就餐,并且全部直接通过小薇订餐。这对提升小薇的工作业绩大有好处,每个月的提成总会比别的服务员高出一节。
小薇依然不为所动。对于男人,对于感情,她已是心如止水。倒不是不渴望真爱,而是担心对方接受不了自己那段不光彩的经历。纸终究包不住火,捂得再紧,藏得再严,再小的秘密还是会有大白于天下的那一天,与其靠隐瞒、欺骗去获得一段感情,不如把自己彻底包裹起来,既不害人,也不伤己。
在不知内情的外人眼里,小薇委实是个漂亮的姑娘,尤其是经过风月场合的浸淫,时不时地会透露出一股媚劲。这对成熟的男人来说,多少具有一定的杀伤力。比如阿胜,还比如这家饭店的四川万源籍厨师谭小猛。
谭小猛比小薇大三岁,是父母的独子,长得人高马大,加上每天坚持健身,浑身上下全是肌肉块,显得非常健壮。看到小薇的第一眼开始,谭小猛就莫名其妙地喜欢上她。同为厨师的另一个万源老乡是个风月场的老手,委婉提醒谭小猛:“这个女孩一看就有故事,你要留个心眼,别太投入了。”谭小猛情迷心窍,断然听不出这话的深意,还以为对方是潜在的竞争对手,便采取了不屑一顾的态度,把提醒当面了耳边风,全力展开对小薇的感情攻势。
相对于阿胜的猎艳心理,尚无女友的谭小猛显得更为真诚。小薇也心动过,但她刻意掩饰了对谭小猛的好感,总是一副不冷不热、爱理不理的样子。这让谭小猛很是痛苦,却又无可奈何,只好耐着性子等着机会的到来。
转眼到了二零零八年夏天。因为北京奥运会使京城流动人口大大增加的缘故,小薇所在的川菜馆生意异常红火,阿胜带朋友来吃饭的次数也有增无减。奥运会闭幕当晚,他又订了一个包房,和一帮朋友边喝酒边看闭幕式直播。
服务员自然还是小薇。当全中国的电视屏幕被香山红叶淹没的那一刻,看到包房电视里的画面,正忙着给客人上一盘夫妻肺片的小薇仿佛被雷电击中一般,浑身抽搐,面色苍白,手中的菜盘子咣当一声掉在地上,摔得稀碎。
红叶?红叶!看到电视屏幕上飘舞的红叶,小薇想到了在家乡小镇上那个叫红叶的夜总会,想到了那段不光彩的经历,想到了被自己活活气死的父母,一分神,手中的菜盘子便掉到地上。
听到盘子着地的清脆动静,老板娘从吧台跑了出来:“小薇,你怎么回事?脸色这么差?生病了?”小薇呆立在那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阿胜没说什么,可那帮客人不干了,纷纷向老板娘发难,说这里的服务水平太差,要求大幅度打折。本来不想为难小薇的阿胜见朋友们都不高兴,其中两个还是政府官员,自己的生意有求于他们,得罪了可不好办,必须想办法予以化解。
为了生意,阿胜硬起心肠,对小薇破口大骂起来,骂得非常难听,以至于老板娘都受不了,大声回敬着对方:“我们服务不好,可以免单,你甚至可以到消协投诉我们,但请你不要骂人。服务员怎么了?服务员也是人,也有尊严,她不是你们家的佣人!就算是,现在不是旧社会,主人也不能侮辱佣人!”
阿胜喝了酒,有些醉意,上前摸了一下小薇的脸蛋:“我骂她怎么了?我还摸她呢。”紧接着,没等小薇反应过来,他又快速在小薇的胸前捏了两下,借此向老板娘示威,“我就摸她了,你能怎么的?有本事过来打我啊?!”
这一切,闻讯赶来的厨师和服务员全都看在眼里,一个个面露怒色。尤其是谭小猛,早已气得满脸通红,就等老板娘一声令下,随时准备上去揍阿胜一顿。
阿胜的轻佻举止,彻底激怒了小薇,只见她悲愤地哭喊着,一下掀翻了饭桌……小薇的举动,无形中成了一道命令,谭小猛带头冲了上去,两伙人顿时撕打在一起。
如此一来,阿胜感觉更没面子,抡起一瓶啤酒,没头没脑地朝厨师谭小猛的头上砸去。谭小猛顿时血流满面,哀号着冲回厨房,操着一把明晃晃的菜刀冲了回来,直奔阿胜而去。
眼看要出人命,小薇死死抱住谭小猛,不让他靠近阿胜。阿胜得了便宜还卖乖,照着谭小猛的鼻子就是两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