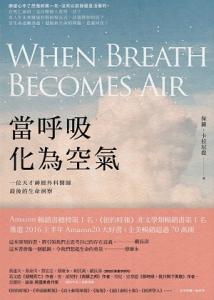拿着镊子的掘墓人
那时候的天,白天够蓝,晚上够亮。根本不需要什么天气预报,就能让每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知道,第二天能不能穿上转起来裙摆很大的裙子。只要在睡前,朝窗外看上一眼,今晚的星星满不满。
那天晚上,我没想穿裙子的事。在8岁的年纪,我就在考虑一件大事:将来我究竟是当一个艺术家,还是当一个医生。学艺,还是学医,是我在满天还有星星时想的事。事到如今,我既不是艺术家,也不是一个牛逼的医生,但是那天晚上想的事,正用另一种形式也存在着。
2008年农历的腊月二十八那天开始,对,就是大年三十前两天,在我放弃成为艺术家已经2年后,我开始憎恨所有的医生。这一切仅仅在3个半小时内就发生完毕。白天的大部分时间,我们都还沉浸在购置年货的兴奋中,谋划着来年,花掉这一年的积蓄,去买些好穿的,好吃的,就像我们所有人的平生一样,在生活中生活着。事情发生的时候,我正在把新购置的衣服扣子补一遍线,偶尔抬头看看可爱的狗,看看幸福的家人,像绝大数人一样,以为“死亡”是个极其遥远的事儿。
直到现在,当我看到城市里有120救护车经过,我都深深的为它的速度担忧。那种不知道什么牌子的标准中巴车型,在高速路上开到车都有点飘起来,速度仍然令人堪忧。我一直没有想通,为什么所有的国家和城市,在医院配备的都是这种标准救护车,在它的马力上这么草率。它担负的是与死神赛跑的重大责任,技能却只能达到载老年人出游的指数。
面对一个已经极度呼吸困难,身体呈现癫痫症状,伴随呼吸暂停情况的急救病人,我所得到的并不是救死扶伤,白衣天使的感受,没有急切的医护人员从四面八方跑来协助你卸载病人,没有急促小跑的医师对病患进行如书中所提到的呼吸辅助、心脏复苏,没有一个老练的医师总指挥下令“病人血压下降,注射1.2毫克肾上腺素”,没有电击心脏复苏,什么都没有。凌晨1点的医院,了无人烟,当我们自己急切的冲进急救室,掌握我们生死大权的,是一个漫不经心的医生,和一个不肯放下正在给另一个磕碰病人的换药护士。他们对我们的哭喊漠不关心,不紧不慢的告知我们“别喊叫”,5分钟,多么重要的5分钟过后,缓缓的走过来,用手电照了照眼睛,终于用了书里描述到的那种最低级的呼吸辅助器——两根细细的管子,微微的插在鼻孔前端,然后用标准的方言说“这都死了么。”
在我看到圆睁的眼睛旁边,那两道仍然还水润的泪痕时,我庆幸我没有偏激的认为他们是另一种杀人凶手,即便他们多么如此的相像。如此这般,还有许多。我突然觉得,把生命交到另一个人的手上,我,是多么的信任,他,需要多么深的感同身受才行。
医学,不该只是某一群人的事,日常医护和急救,也不该仅仅依赖另一群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急需,可是大多数人都像那晚缝扣子的我一样,觉得这一切还遥遥无期呢。
没有人是罪有应得
两天后的除夕那天,当我站在墓碑前,捧着一盒尘埃,看着四周到处都是燃烧的烟雾,我才意识到,医生不仅仅能够救死扶伤,他们还负责颁发死亡通行证。只是手续太快,我甚至没有一场好好的告别。我不能原谅他们的冷漠,我觉得他们应当罪有应得。
多年来我大量阅读医书,靠自己的力量照看剩余的家人。直到遇见这本书——《当呼吸化为空气》才让我终于有了感同身受的谅解。
强大的对生死探索的求知欲,让保罗从研究形而上的哲学文学,转而从事医师,他想远离物质主义的无谓与无聊,远离自高自大的小家子气,他通过脑神经外科医师,直接进入事情的核心,站在生死对抗的边界,背负道德与责任的重业,去寻找超越的可能。
上天似乎因为肯定他这份勇气,给了他癌症,赐给他找到答案,超越可能的唯一路径。但当保罗真正的与死对视时,才发现死亡,无从辨识,只有一片空白。即便是医师自己,也同样会被冷漠对待,也同样有各种对死的茫然。
当死亡降临,就意味着与你所有相关的人,事,梦想,物质,全都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第一次总是充满敬意的,医师的第一刀也是充满敬意的。开始时,都会像保罗,对“爱他们很难”感到愤怒,然后就像武侠小说中修炼奇世绝学的高手一样,一日一夜的重复练功,最终练就成一个冷面高手。大体解剖重复到一定数量,量变开始质变,最终将充满敬意,严肃而纯真的医学生,都化为冷面、傲慢的医师。
我们的生活,充满了无休止的重复,我们每天在固定的时间醒来,按固定的步骤梳洗,坐同样的车,见同样的人,做同样的事,说固定的腔调,就连性爱都以固定的流程进行。重复让我们麻木,重复让我们冷面傲慢,各个患上外科医师的脸盲症,所有人在我们眼中都模糊不清,全都一个样;所有人也都失去了对人性,对情本身的关照。偶然乍现的“绝对人性”赋予解剖下大体性格、感情,才会剧烈涌上愧疚之心,这就像生活中偶然的醒悟。它总是涌上心头,转瞬就去。
很多麻木冷面的人,就像解剖大体的医学生一样,本该具有性格、感情、喜好的肉体,在他们眼里被肢解成神经、组织、肌肉絮。我们也时常不自觉的,将生活肢解成上班、工作、回家,我们有时是主动不去赋予它灵魂,因为一旦赋予它灵魂,追究其意义,就会出现羞愧,进入短暂的“反省时刻”。
我们都该向大体、向生活致歉,不是因为自己亵渎,而是因为我们常常是“没有感觉”。
所谓人之常情,大抵就是任何人都不能总是高尚。
曾经对患者充满感觉的保罗也会变成,在一场紧迫的抢救病人失败后,心里惦记的却是抢救前没吃的午餐——冰淇淋三明治。急速丧失的道德感,将他的良心淹没。在生死边缘,他成了麻木的掘墓人。或许,真正的“将心比心“,只有落在能让你有情感产生的人身上,才能开启开关。医学院同学罗莉撞车后抢救无效死亡,成了震动保罗的开关,羞耻、仇恨、愤怒,所有切身感受令他几乎成了托尔斯泰笔下的样板医师——专注疾病的例行治疗,错失人的重要性。甚至面对那些不听从他诊断忠告的人犯病时,心中也会冒出“他罪有应得”的想法。
可是,没有人该是罪有应得的。
“爱他们很难”
“从起先常常来,天天来,一天两次。然后隔天来,然后只有周末来。
再过几个月或几年,造访者越来越少,可能只有生日和节日
最后家人会搬走,尽可能搬远一点。
因为爱他们很难”
死亡,让个体孤独。却对外界有了巨大的凝聚力,所有人都开始乌泱泱地向你靠拢,病榻之前开始络绎不绝,所有仇恨,怨憎,都化为一句“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可偏偏最该享受这一切关爱的人,所有的感官都渐渐被病痛塞满,没有精力顾及这些。而且你病的时间越长,这种凝聚力越弱。
久病床前无孝子,久病塌上也无善人。爱一个有经久累年病痛的人,是很艰难的。
除了费力的照顾,应对各种症状的突发应急,以及因为长期患病越来越愤怒和挑剔的病人以外,还要牺牲。以牺牲我们的人生为代价,所有的时光和精力、对自己人生的规划,全都要牺牲。我们就像医师,背负了另一个人的十字架。我们就像西藏的密宗上师,背负了另一个人的所有业障。没有几个人可以坚持到底。
病人一个人的病业,通常就像一个坏死的、会传染的细胞,会蔓延至家庭的每一个角落,影响家庭的每一个成员。只有绝对冷漠的人,才能全身逃脱。
我们本该并肩作战,却在持久战中屡遭背叛。
保罗与自己最后的主治医师艾玛,许多的病患家庭与他的主治医师,在与病痛抗争的战役中,自然而然的就会形成联盟,成为一个战壕的战友。但在战争中,我们都有权利放弃,有权利撤退,有权利投降。最丑陋的是什么?面对这场生死之战,有些人选择的是满口仁义的背叛,在医师与病痛抗争时,背后却被战友——病患家属狠狠插上一刀。
你能想象,面对久病至亲的抢救,有些家属最想听到医生说的是“放弃治疗”。
手术室前,病床前人性的阴暗面,面对死神,有人会选择跟着魔鬼肆意游荡
。
灵魂摆渡人,生命中转站
病房里的医师就像阎罗判官,手中的病例就是我们的生死薄。被他盯上那一刻起,我们所有当初欲望的人设,就此蒸发。也因而,医师的重担难以想像,行医就是背起另一个人的十字架,细微之间,都是生死大事。
书中对手术的细节描述,让我想到一首因果诗:
“预知世上刀兵劫,但听屠门夜半声”。
就像餐厅的后厨,肉体在这里是可以宰割的“鱼肉”,各种锋利的锯齿切割向来害怕受伤的肉体,血压随时会上升,也随时会下降,为了防止出血随时会增加,医师常常需要动用止血钳,钳住我们皮肉之下纤细的血管,有时则是电烤,让手术室里飘荡着烤肉店的味道。手术中,心脏会骤停,呼吸会暂停。。。。。。
隔着一道门,门外的人们无从得知感同身受,门里那个失去知觉,本该掌控生命的人更无从得知。
平时我们总觉得自己站在自己生命舞台的中央,但是当你进入医院,这个更为古老本能的世界,除了病人,所有人在病人眼里都是无所不能的超人,唯独自己孤独的、微弱的。这里的剧情,在输液滴管的每一滴下落时都可能是一次剧情转折,检测仪器的每一声鸣响后,都隐藏着危机四伏,这里上演的全是希腊式悲剧。主人公是医师和病患,观众是家属,导演是命运,它最擅长的恰恰又是“出其不意的无常”,结果时好时坏。
医师看病人,通常都是人最脆弱、最神圣、也最私密的时候,医院就好像生命中转站,我们从这里诞生,在这里续命,也在这里彻底的离开。
灌满生命长河的鲜血,这当中我们与医师同浮同沉,流浪生死,而医师就是生命的摆渡人。我们一同在这里,医师耗尽所能,带领我们到达对岸,这是渡河的唯一方法。
生下就跨坐在坟上
“有一天我们出生,有一天我们将死。同一天,同一秒钟。生下就跨坐在坟上,光闪亮了一下,然后再度回到黑夜。”
——塞缪尔贝克特
人人都求好死好活。
他们急于成长,然后又哀叹失去的童年;他们以健康换取金钱,不久后又想用金钱恢复健康。他们对未来焦虑不已,却又无视现在的幸福。因此,他们既不活在当下,也不活在未来。
他们活着仿佛从来不会死亡;临死前,又仿佛他们从未活过。
当你强壮而健康的时候,从来不会想到疾病会降临;
但它就像闪电一般,会突然来到你身上。
当你与世间俗物纠缠不已的时候,从来不会想到死亡会降临,
但它就像迅雷一般,轰的你头昏眼花。
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你未知生,焉知死,但你未知死,又焉知生。
生命就是“一瞬”,太短而无法过多考量。一呼一吸之间,就全都发生完毕。
而欲望就像在干枯的深渊里钓鱼,再怎么努力都不能尽合你意。算天算地算尽从前,算不出生死会在哪一天。
生活中的我们,是活得很模糊的。有欲望,有目标,眼耳鼻舌身意都被欲望盖住。生病时,却是我们感官最清醒的时刻,对疼痛越发敏感,对离别越发恐惧。当你所有的注意力,从外面收回,只需观照自己的时候,才发现感知能力的恢复,才发现最简单的“还能醒来就是活着”,就像保罗第一次躺进病房时——“感到无比的清醒”。
病痛的感受环环相扣,牵一发而动全身,仿佛身处漫天飞雪的孤岛上的空房间,无论你如何翻江倒海,而可描述可察觉的词汇与症状却非常有限。天地间,只剩下你的医师,像命运一样主宰了我们的全部。
以物易物的健康交易
到底哪一种抢救措施更好?
有时,只有书中所说的“靠判断”
原来除了决定午饭吃什么,哪一支口红颜色,有一天我们还需要躺在床榻上,决定哪一种治疗方案,决定自己的生死大事!
但是面对生死大事,仅靠经验?知识?就足够了吗?
医学从来就不是纯碎的科学,医学从来就是:偶尔治愈,常常缓解,总能安慰。大多数时候,我们需要医学的辅助,却不该迷信医生。
正如保罗描述的医院一样,人是一个复杂的小宇宙,临床经验只是另一种统计学,变数是不够精准的仪器、医生的能力和心情、还有复杂的人体构成。
在另一本医学类书籍《医生的修炼》中描述过一个案例,病人在第二根肋骨处中弹,当医生预备取出子弹时,却在中弹的位置,怎么也找不到子弹,只好先止血包扎,待第二天在详细拍片找到子弹的位置。结果第二天,病人一切正常,不疼不难受,在胸腔拍片,也没有发现子弹的痕迹。医生太费解了,病人却觉得自己没什么问题,嚷着要出院。出院后,医生因着医德,电话联系病人再次回来,并进行全身的检查,结果在患者的屁股与大腿连接的肌肉缝隙里,找到了从肋骨射入的子弹。
医院里最常见的道德思考,通常不是“要生”,或“要死”,而是“怎样活才是真正地活”。
因为任何医疗救治,任何!都伴随着伤害和潜在的危机。有时候存活,是建立在一种牺牲交换上,完全是一种以物易物的世界。
以视力下降,换取降低脑出血机率;
以对肝脏的不可回转损伤,换取血压的暂时正常;
以对内脏的不可逆转损伤,和对其他良好细胞的共同消除,换取阻止癌细胞的继续长。。。。。。
你必须选择代价,来换取活着的机会。
时时心怀罪恶,对死亡充满仪式
可能正如保罗在化疗时所想,圣经中所说的原罪,并非“时时抱着罪恶感”。
也许上帝真正想传达的是,善——是个终极目标,我们凡人永远,或者很难时刻保持觉醒,做到完全符合标准。我们有善的概念,但我们不能像主一样时时做到。所以我们理应时刻鞭策自己:
“嗯,如果我还不够善,那我仍然会犯错,我应当抱着仍有罪恶感前行”。
佛教也有相通的理论,时常听人说,觉得自己求佛不应,供养却没有得到佛经上描述的福报。佛陀他老人家明明已说明,在种种好处之前,皆有一句“若善男子善女人。。。。。。”《十善业道经》中记录了标准,一不杀生。 二不偷盗。 三不邪淫。 四不妄言。 五不绮语。 六不两舌。 七不恶口。八不悭贪。 九不嗔恚。 十不邪见。
生命的意义不是逃避受苦,达尔文和尼采都认为:生物体的决定性特征是它的奋斗。时常有不易,生命的存在主义才具意义。
经历死亡的人,和操纵生死的人,都应该面对死亡,充满仪式感。
我们为活着创造了太多的仪式和节日,我们也该为死亡,多倾注些仪式感。电影《入殓师》中小林最精彩的那场入殓仪式,充满敬重的跪坐在遗体身边,擦洗、按摩、梳妆,就是对尸体生前人性的承认与尊重,对死亡的尊重。影片中人妖青年、舍下幼女去世的母亲、带着无数吻痕寿终正寝的老爷爷,在各式各样的死别中,小林用一场一场与死的仪式,告诉我们:
不惧死,才能更好地生。没错,向死而生。
另一部影片《震荡效应》中威尔史密斯扮演的尸检医师,对死的仪式,又是另一种敬畏。每次尸检前,他都会像尸体还活着时一样,温和的对尸体微笑,绅士的握住死者的手,对它说:
“每个人都在说你不好,我知道不是。但我需要你的帮助,我们一起向他们证明。”
每一个死亡的肉体,都不仅仅是一个躯体,每一个肉体上的痕迹,都诉说着这个人一生的故事片段,而尸检医师要做的就是细细的阅读,然后把片段拼凑起来。
一切盲目的顺从皆是迷信
癌症晚期的诊断结果,让保罗陷入焦虑。痛快的结果,通常不会令人焦虑。没有未来,断送过去,只有无边无际的当下,才真让人忧郁。
知道你会立刻死,你会接受,告诉你还有确定的十年,你会做很多的梦想计划与安排,两年你会充分体验亲情。但若只知道“情况好转”,背负不确定的存活曲线,“一次只活一天”的日子,对人毫无帮助。这一天的生命,我究竟该安排些什么?当真是不知死活的活着。
人在独自面对死亡时,就会开始对所有科学产生怀疑,寻求更高的帮助。对于身患重病的人来说,也许最想听的不是医理、诊疗结果。他更想寻求获得的是神迹、神谕,那些能让人奋起的求生希望。
面临死亡,面临一切令你沮丧的信息,人很容易发现科学的盲点, 转而寻求信仰的力量,但是求而不得,又使得我们无法坚定不移。抱着半信半疑,患得患失的心情,孤独的走向正确答案。
我们获得了正确答案的方向,但对核对答案却基本不可能。最后,受每个人视力波长、生命宽度的影响,每个人都只能看到真理的一部分。乞丐看到一部分,富人看到一部分,医生看到一部分,病人看到一部分,男人看到一部分,女人看到一部分。而全部的真理,是人与人之间因缘和合的结果,在现有理论中,它貌似只存在于高于这一切的地方,我们无从得到完整的答案。
科学的根据是可复制性,是制造出来的客观现象。这个领域,科学的能力强大,但是却解释不了许多围绕人的“神迹”。人、主观、无法预测、第六感、意念、有爱。。。。。。这些都是无法具象描述的能力。
医师作为形上学的仲裁者,人的死亡究竟是不是另一个轮回的开始。奥坎的剃刀将信仰者从迷信干净的隔离。这个唯名论者,反对实在论,若没有实在的逻辑证据,则直接选择简单明了的。神的存在没有证明,因此信神不理智。
然而你不信神,不寻求信仰帮助,又好像是等于认同人死灯灭,化为虚无。相对于宇宙,我们简直只存在了一刹那。我们抛弃信仰,相当于爱、恨、意义也一并遭到放逐。如果我们认定科学不能证实神,就等于科学不能证实生命意义。生命本身要是没了意义,那所有的存在主义主张都毫无重量可言了。
向死而生,生死不易
佛经上对生的痛苦认为,新生儿,怀胎十月犹如胎狱。
母亲喝口冷水,胎儿就犹如置身寒冰地狱,母亲吃口热的,又宛如葬身火海。这是受身的必经之路,就像大病之后会失去一些记忆,这场胎狱,会令我们忘记过去,新身成命。出生时,在狭隘的“生路”中,骨头被挤压变形的痛苦,皮肤从温暖羊水中出来,初次接触充满细菌的空气时,带来的刺痛。我们现在都已一无所知。
而死的痛苦,大多数人只能想象。等你知道的时候,也意味结束,再无法对人宣讲。心梗患者的死亡。从双臂、背部酸痛开始,呼吸困难,大量的脱水可以浸透一个羽绒枕头后,还能浸湿床褥,心脏在骤停之前,人会浑身猛烈抽搐,眼睛圆睁,最后仿佛用尽全部力气,吸取这个世间最后一口空气,就再不会呼出。一吸没有呼,一去就再也不回。
出生时,有鲜血,死亡时,也有鲜血。生里有死,死中有生。
在地球的任何地方,死亡都会找到我们。人们来了又离开,忙忙碌碌,乐于享受,却不肯提一个死字,避讳跟它所有相关的内容。一旦被死亡出其不意的抓住,立刻就毫无准备,任由情绪如狂风暴雨般征服,伤心欲绝垂头丧气,怒不可遏。
有些人走向偏锋,把死亡当成一种荣耀,自我结束生命,他们相信死亡是美丽的,是对于生活抑郁的解脱。但不管是因恐惧而拒绝正视死亡,还是将死亡浪漫化,我们都是视死如儿戏。
死亡既不会令人沮丧,也不会令人兴奋,它就是草长马发情——生命的事实。
人自无边无感的宇宙中随机浮现起,遍是一个孤独的存在。死亡的事实令人不安,然而我们也没有别的方式可活。向死而生吧,知道我们最终的结局,带着这份孤独去活,会比一无所知,活得更为珍惜些。
布朗的《医者的信仰》中提到:
“当初以怎样的奋斗与痛楚来到世间,我们不清楚可是要离开世间,通常不是件容易事。”
佛经上说,世间有六道,六道中唯属人身难得。
我一直想不明白得人身为何比升天道还难,也许,它难就难在
你来也不容易,去也不容易。
最后的话
生命就像空中闪电,极速冲下山脊,匆匆消逝。
生命的真相是没有永远,一切是无常。
我们不知道死亡在哪儿等待着我们,就让我们处处等待,时时准备。
不然,当生命之光出现时
你做了哪些事,足以证明你并未虚度人生?
作者:良木火烈的焦尾
微博@良木火烈的焦尾,分享我的生活
微信公众号:jiaowei108 更多文章,秘密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