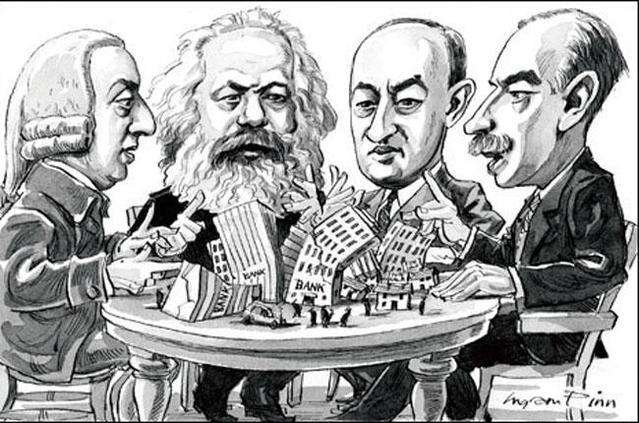这个学期,我在课余时间内重读了亚当·斯密的著作《道德情操论》,相较于第一次阅读此书(那时,我正读高三),因为此次的时间更加充裕,而且伴随着阅读做了很多笔记,所以有了许多之前未得到的细节的体验和思考。
《道德情操论》是亚当·斯密一生最引以为豪的作品之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期,他仍旧在修订此书,并且尝试添加新的内容和内涵。但是,和《国富论》一样,《道德情操论》中的语句常常为很长的拥有丰富修辞和重叠逻辑的句子,这也就导致了我第一个阅读此书的巨大的障碍。好在本学期重读此书,这些障碍明显的变小了很多,也因此得到更好的了解了这本堪称经典的巨著的内容。
人的同理心
“同理心”在很多的译本中被翻译成“同情感”,但是因为《道德情操论》中也有多处频繁提及一般意义上的“同情”,所以常会混淆,我还是喜欢第一次所看的此书的译本中“同理心”的译法,而不爱采用最近流行的谢宗林先生的译本中的译法。
在《道德情操论》中,亚当·斯密将我们的一切涉及到他人的道德观点的根源都归结到了我们的“同理心”。而这部分实在是全书最为精彩的部分了。“同理心”即当我们评价一个人的行为和处境时,我们会尝试“换位思考”,根据我们在他的处境下会感受到的情感以及做出的反应来评价他的行为,以此为基础,我们的整个道德才可能被建立。因为正是这个同理心让我们定义了什么行为应该被憎恨、什么行为应该被支持、什么时候会悲伤、什么时候会快乐等等。毕竟,我们的道德应该是一种对于一般意义上的现实的评价,而不应该仅仅是对于我们自己的遭遇的反射。
这种同理心的精妙之处(也同时被许多评论家认为是不可靠之处)在于他完全建立在我们的“想象”之上。举例来说,当一个同学丢失了自己的自行车时,我们可能会为他感到难过,也即产生了“同情心”,而当另一个同学亲人过世的时候,我们也会感受到类似的同情,而实际上“同学丢了自行车”和“同学的亲人过世”两件事情本身对我们个人并不会有任何的影响,甚至于,如果同学不告诉我们这个消息,我们都不会知道。但是,当我们知道了这个消息,我们的同理心却自然地让我们想象如果是自己的自行车丢了或者亲人过世,我们会产生怎样的感受。于是,我们就有了上述的悲伤的感受乃至于同情。而上述这种形成的机制本质上都只是基于我们的“想象”而已。
但是,这种同理心的理论的最精妙在于,上述这种“想象”的结果是基于我们全部的生活的经验乃至于我们所接触的整个社会的一切知识的。一个容易被理解的例子是,如果一个人从小到大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没有和他发生过任何的情感上的联系,那么当他听到自己的同学父亲去世的消息时,他的同理心使他可能感受到的“同学此时感受到的痛苦”显然就比另外一个和父亲关系很好的同学所感受的同样的同理情感要弱的多。所以,这种个人的全部经验和知识与同理心的结合产生的对于道德观念的影响就是,前者可能会比起后者更加模式亲情在道德观中的作用。这种解释是完全符合我们的生活经验的了,而且也非常的简练。也正因为这些优点,关于“同理心”的论述也称为了《道德情操论》全书前半部分的核心。
而上述的例子实际上也引出了“行为的合宜感”这一话题。当我们遭遇一种不幸的事故,便有一种希望得到别人的同情的期望,实际上这是因为我们在感觉到负面的情绪的时候,希望别人的同理心也会产生类似的心灵上的效果,从而支持我们的行为的“合宜性”,即是恰当而且程度适宜的。可是,因为每个人的评价别人的标准都是源自于同理心,所以,“合宜感”的程度在不同的评价者看来也可能会有很大出入。当你遭遇亲人去世时,在一个孤儿和一个在温馨家庭中成长起来的两位朋友面前表现出同样程度的悲痛的感受,那么后者可能认为你的悲伤是恰当的,悲伤的程度是他的同理心可以达到的,于是他真诚的同情你甚至于产生类似的感受;而在前者看来,你的行为却可能被认为夸张乃至于轻浮的,于是在他的立场上,此时你的行为的“合宜感”就远远不如前者了。所以,“合宜感”的一个关键是“行为的程度”,这也是为什么当一个朋友失恋后,我们可能会同情他的遭遇,但如果他整日沉浸其中而不恢复,则就很难再得到我们的尊重了,因为他的行为的程度让他的行为在我们道德评价的标准中已经失去了可贵的“合宜”的品质了。
但是,基于“同理心”,我们的道德体系,乃至于各种不同类型的美德的标准是如何产生的,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却没有细致的说明,相较于他在“论同情的快感”和“可亲的美德”等可能更偏离于主要内容的部分下了大的功夫论述,这样的产生过程的论述的缺失可以说是一个不易被忽略的不足了。对于“同理心”至于不同美德的产生的关系,我愿阐述一些个人的看法:
“同理心”和“公平和正义的美德”:因为我们道德本身追求一种我们的同理心可以达到的感受,认为对应于这样的感受下的行为和相应的评价才是正当的,而我们每个人都不愿意无辜地被剥夺利益,所以我们的利己的天性让我们希望我们受到的利益与我们的付出至少是相符的,而不是亏损的;也让我们不希望我们受到的痛苦哪怕有一点不是因为我们自己造成的过错。由此,我们追求在我们的自身上践行一种“所为”与“所得”相对应的道德标准。而经由同理心的推广,当这种关系映射到不同的个体的行为和所得利益的时候,自然就产生了关于“公平和正义”的美德的雏形;
“同理心”和“节制”的美德:我们都自然的希望别人的感受与行为”相适宜“,我们厌恶我们的同理心所难以达到的感受(不恰当的说,一个对家人没有感情的人可能会对别人失去亲人后的剧烈的痛苦产生反感),一如亚当·斯密所说:“我们讨厌那种捶胸顿足、呼天喊地的悲伤,憎恶那种不假修饰,一味以长吁短叹以及死缠烂打的悲叹恸哭要求我们的同情的悲伤”;类似的,我们也会反感别人的会被我们视为浮夸的快乐的情绪(除了同理心之外,这之中还有“嫉妒”这种特别的情绪的作用)。正是因为这种绝大部分以“同理心”产生我们的情绪和对行为的评价的体系,我们总是会赞赏那些在悲伤和快乐时表现出来的情绪都略微低于真实情绪的人,毕竟当我们的“同理心”让我们感受到的悲伤和快乐甚于当事人时,我们并不会对他感到反感,但是如果“同理心”让我们产生的情绪达不到当事人表现出来的程度时,就可能让我们对当事人产生负面的评价。由此,这种对于“行为和情绪合宜”以及“同理心可以恰当达成‘同感’”的追求,都让我们形成了对于“节制”这种性格的赞赏,并进一步将其视为一种独立的美德;
“同理心”和“仁慈”的美德:关于“同理心”和“仁慈”的美德的关系仿佛较难以说明,因为我们是否有一种“希望更多人可以在某种情况下感受到我所会感受到的情绪”的期望似乎并不是特别清楚的一件事。但是,如果我们承认这种倾向的存在,那么,“仁慈”这种美德产生的后果显然是让更多人有机会感受到正面情况下的良好的感受,由此,也便建立在了“同理心”的对个人情感的推广的基础上了;
除了上述三种美德之外,还有其他的美德,他们的出现,他们之所以成为美德,无一例外都和我们的“同理心”相关,并且根本地产生于“我们有同理心”这个条件之下,只不过这种关系有的显而易见,有的更难说明而已。但是,如果我们细致地考虑这些美德产生的细节和性质,会发现其中仍旧有很多需要推敲之处,亚当·斯密将这些内容的论述放在了“美德的性质”一部分中,而这也会在本文的后半部分中体现。
何种行为应当被鼓励
“道德”常被定义为“定义行为合宜与不合宜的规范”,无论是对于个体而言还是一个更大的集体(无论它是宗教抑或是世俗的),这样的规范都是显然必要的。当我们谈论道德的作用,一个重要的话题就是何种行为应当被鼓励,而何种行为则不应当被鼓励乃至于被禁止。亚当·斯密斯在他的所有著作中都表现了一种在“宗教”与“非宗教”之间徘徊的态度,在《道德情操论》的著就中亦然。他主张“自然女神“应当是我们行为的最初的定义者”,但为了让他的语言更具有可以精确分析的可能,他又主张“人的情感或者心里的感受,是各种行为产生的根源,也是品评整个行为善恶必须依赖的基础”,由此声明应该从“引起行为的原因”和“它所意图的目的或者倾向倾向产生的后果来考量他”。由此,他认为他的关于“行为合宜”的说明是前所未有的精确了。
我第二次读完此书后,当我综合考虑《道德情操论》中定义的“道德人”和《国富论》中的“理性人”,我意外地发现可以很好地将两者分别表现的“同情心”和“利己心”统一起来。依据后者而言,个体总是倾向于鼓励可以使自己获利或者倾向于让自己获利的他人的行为,可是,一如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论述的一样,当个体聚合起来,成为了一个社会体,两者的利益却往往不一致乃至于相反。于是,如果我们承认“感受决定行为并且是品评行为的基础”,那么也就产生了这样的状况:在个体(特别是会因为其他个体的某个行为获益或者受害的那一个)和整个社会的视角来看,同样的行为便可能产生完全相反的属性——应当被社会/某个个体鼓励,但是同时应当被某个个体/社会不鼓励。这样的结论显然是和现实的情景相符合的,但是他却解决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他一方面承认社会的有机的性质和一种常被洛克先生称为“拟人的有意识”的自身的利益相关的属性,从而避免了坠入类似于霍布斯先生的“机械唯物主义”那样的宏观上统一“国家”和“个体”,却让二者在微观行为上处处对立的困境;另一方面,当我们承认个人对于更大集体的原子性作用,但是是一种微观上无序的状态(如果不受约束的话,出于上述的对“何种行为会被鼓励”的定义,个体则显然会做出相互抵制乃至于伤害的行为),也就承认了一种更大的集体的存在的必要,以及他的拟人化的“价值标准”的重要价值。而这也和“社会契约论”中社会形成的路径的解释不谋而合了。
更具有现实意义的是,当我们承认上述的推理,那么,类似于“政府总是为了人民好”此类的说法也便可以被轻松证伪了。这倒不是因为一个更大集体的利益总是从损害组成它的个人的利益中得来的,而是因为组成它的个人本身的利益就是不统一乃至于互相抵触的,否则,这样一个集体也就没有了存在的必要了。所以,当从这个集体(可以是国家、政党、社团或者宗教组织等)的视角来判断”何种行为应当被鼓励“时,它总是出自他的一种拟人化的”情感“,而它和一个单独个人的情感倾向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完全微乎其微的。由此,当部分个体让渡自己的权力,从而促进集体的效率时,前述的这种”拟人化的情感“也越来越被接受了别人让渡了的权力的一部个体所决定了,由此,阶级也就产生了,所有的集体也就面临了成为阶级利益的工具的危险了。现实中的无数社会伦理和社会经济秩序难题也就由这个根本原因中产生了。
人的美德的性质
当我们谈论人的美德,我们究竟在谈论什么?“美德”之于我们,究竟是依赖于什么样的形成和界定机制?遵守所处政体的法律、符合亲人邻人的意愿、纯粹地追求个人身体的享乐并避免痛苦,这些往往被一部分信仰为“行为规范”的来源。亚当·斯密斯在《道德情操论》中却主张我们首先应该认识到,上述的所有“规范”都应该源自于对一种道德观的运用或者总结(他称之为“形成一种概括性原则”)。斯密斯主张应该对人的“美德”进行分类,其中有刚毅的美德、仁慈的美德、节制的美德和公平与正义的美德等,而最后一种美德应当是最重要和根本的一种美德。可是即便有了这样进一步的分类,当我们谈论“道德观”,却不得不面临许多不同的理论:
美德在于行为的合宜:历史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芝诺(斯多葛派的创始人,该派早期许多观点受他影响很大)的对于美德性质的说明都被亚当·斯密总结为“认为美德的性质在于行为的合宜感”;
美德在于审慎:伊壁鸠鲁和亚里斯迪布斯等早期哲学家的观点常常强调人的美德在于对自己的行为的审慎的考虑的充分,而这种品质本身也就是一种美德的具体体现;
美德在于慈善:一如亚当·斯密的老师哈奇逊博士等人的声明那样,一个人远不可能被称为有充分的美德的,如果他没有做出或者没有倾向作出体现了慈善的性质的行为,由此,人的美德性质自然的应该被归纳于“慈善”上。
亚当·斯密详细地分析了上述的三种说法, 并且认为“其他的任何关于美德性质的理论都无一例外的可以被归纳到这三种理论中”。对于第一种观点,它历来在西方的哲学界影响最大,亚当·斯密的想法仿佛也最接近这种理论。可是,当我们深入细节,人的美德究竟在于一种“对于行为合宜标准的准确知晓”还是“习惯于行使合宜的行为”呢?柏拉图似乎是主张前者的,而亚里士多德则明显主张美德不应该是一种知识,而应该是一种习性,因为一个再明晓大义的人,当他受到一种恶劣的习惯影响时,他也不会总是可以做出可以被称为符合了任何一种美德的行为的。但是,柏拉图却认为这种反例恰恰说明了那个人他对于“行为合宜”的知识的不够,“有利于自己”显然不应当被在任何情况在被当成“行为合宜”的唯一标准,而“符合自己的习惯”也同样不具有这样一种尊贵的资格。亚当·斯密也没有旗帜鲜明的站着某一位先哲的身边。而我则认为,亚里士多德的主张显然更有说服力,当我们考虑柏拉图的说法的细节,他的那种“人只会选择自己认为最合宜的行为”的假设和“个人的行为不满足任何一种道德”的说法自然给出了“当人做出不合乎任何美德的恶行时,说明他的对于行为合宜的理解不够”的推理,这种说法仿佛很难逃出被认为是一种因果颠倒的诡辩的嫌疑。
除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芝诺和早期的斯多葛派的哲学家认为“人的行为的圆满正直构成了美德的全部要求,而前者的关键在于选择一种顺其自然的始终如一的生活”。这样的说法实在和中国的老庄的思想有很多的契合的有趣之处。但是,另一个关键的需要说明的困难是,从宗教上,这样的说法可是视为对于上帝安排的服从,基于一种“我总是处于全能的神认为我最适合处于的位置”的信仰,但是当我们使用非宗教的视角,特别是对于部分信仰“人之初,性本恶”的中国人来说,这样的说法就显然没有任何的说服力了。毕竟,“道法自然”之于中国人的吸引力绝对不在于那样合乎美德的要求,而是在于一种更高层次的虚无的对宇宙的观点。
至于“美德的性质在于审慎”的理论,尤其是伊壁鸠鲁的理论,是被亚当·斯密最为抨击的,而且也是最不容易被中国人所接受的一种了。当我们把人的快乐和痛苦全部归结人的身体的享乐和痛苦,而认为心灵的感受只是前者的一种附属,来自于“对过去的身体的快乐或者痛苦的回忆”或者“对于未来可能的身体的快乐或者痛苦的想象”,那么,就很难的不让我们成为一个纯粹的享乐主义者,即使这一个派别常常认为,出于节制的美德,以及对未来的更大的快乐的期望,人们可能会倾向于放弃当前的快乐,而换取未来的更大的快乐。可是,将人的美德的性质建立在这样一种纯粹的算计之上,却使得人们对于美德的敬畏感降低了很多。于是,这样的对于美德的性质的解释却显然会让人们倾向于怀疑美德的高贵,与美德自身想要促进的方向完全相反。在亚当·斯密的宗教化的观点看来,这样的一种矛盾显然是不会在“自然女神”的精妙设计中所被允许的。另一方面,从一个更为普遍的观点来看,伊壁鸠鲁等人的观点使得我们的亲人、朋友、国家和教派的利益成为了我们的道德观所不会去关注的成分,而这显然使得我们每个人都称为了一个无不狭隘的利己主义者,当一种对于美德的解释自然导致这样的结果时,它显然很难成为多数人所接受的选择了。
至于包括亚当·斯密的老师哈奇逊博士在内许多更接近现代的哲学家主张的“美德之本在于慈善”的观点,我认为是中国人和一切更加看重集体主义的民族所更愿意承认的。毕竟,当一个行为的行使不但有利于行为人自己,而且有利于其他人,乃至于对行为人自己有害但是有利于其他人的时候,这个行为显然会倾向于被我们认为是符合美德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论述的美德的性质之前,《道德情操论》中专辟了两章去叙述“赞许对于行为的作用”和“效用对于行为的作用”,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尽管利他行为更有可能被认为是符合道德的,但是当一个人企图得到他人的赞许或者成为一个“值得被他人赞许的人”时他也可能会做出同样的行为,亦或者当他从审慎的计算得到了这样的行为可以获得更大的“效用”时,他也是可能做出同样的行为的。这也是为什么人们可能会为了虚荣去罕见的牺牲自己的利益(比如借高利贷来为自己装点门面),也解释了一个忠诚的军人,为什么会奋不顾身地放弃自己的生命来去争取一个可能对于国家来说非常微不足道的利益,而这个行为随着这位军人的对于国家利益的看重的增强而越来越可能,因为在那时,他对于“个人生命”和“国家利益”的效用的评价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最终,亚当·斯密也没有给出一种可以如同上述三种理论一样可以被高度概括的他自己关于美德性质的观点,但是既然他论证了一切相关的理论都可以被归纳至这样的三种观点中,那么他自己也不应该成为一个例外了。显然的,他是比较倾向于基于“行为的合宜”的理论的。由此,当我们讨论美德时,我们有了一种可以将我们的身体和心灵、个体和集体的利益与感受以及自己和他人的情感都无一例外的考虑进去的“道德观”的理论。但是,虽然亚当·斯密嘲讽“追求让一切仿佛都可以像数学定理一样简洁的怪癖”,但是他的没有被概括的零散的而且并不完善的这样的一种观点,也难以让我们就此信服。仿佛意识到了这样的缺陷,在之后的发言中,亚当·斯密甚至试图从语义学上说明“道德观”这样的概念“存在的基础并不牢靠”的有点虚无化的观点,这实在让我不免有一点失望。
总而言之,关于美德的性质这一部分,亚当·斯密显然给出了一种逻辑完整,而且充分考虑了前人哲学思想的个人阐述,但是他毕竟没有如同他的之前的论述一样给出一种概括化的归纳,并且辅以具有对比意义的实例进行说明,不得不说是本书的一个遗憾。但这也只是在很轻微的程度上削弱这一部分的伟大的价值而已。
当我于数日前看完《道德情操论》,我才发现,一本40万字左右的著作平时大概只需要我10小时的时间阅读,但这次却花了我大半学期的时间,并且记了十多页的笔记。可是,当我从那些略显晦涩的长句中抽离出来,我会开始思考这种阅读的意义。我们的道德观和伦理意识显然不会因为一本书而改变,何况这本书中也没有给出任何方法论的内容。但是,一如我们的自然科学研究是为了解释“为什么”而不是直接教导“如何做”,这种的对于人的道德的细节的讨论可以让我们更加了解我们一直赖以生存在自己处于的位置上的心灵和情感的产生与运行的机制。可以了解这种本来是“难以解释”和“它是这样,只因为它就应当是这样”但又十分重要的机制,这难道不是一种最大的幸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