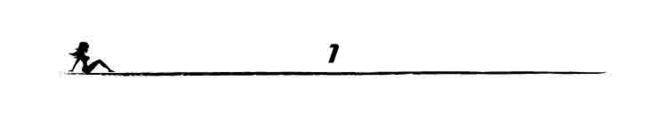文/柳青陵
三、更添香(上)
扬州自古便是名动天下的仙都乐土,那里的水,是胭脂染红的;那里姑娘的脸颊,是美酒映红的。瘦西湖旁边妓馆鳞次,湖中画舫灯船不计其数,有多少公侯名士、侠客浪人在此传歌唤月、醉卧不归!
这许多妓馆,以杏花楼最为风光,这是因为,“天下第一名妓”七巧正是杏花楼的头牌。此女名唤七巧,是因她风流婉约、能歌善舞,且才思敏捷、精通音画,乃是难得一见的奇女子。为了一亲芳泽,不知有多少人一掷万金,却不得其门而入,甚至有许多王孙公子,为她倾家荡产,落拓半生。
有了这么一个活招牌,杏花楼的宋嬷嬷自然欢喜,恨不得七巧能化身为六,一天十二个时辰,轮番不停表演。这天夜里,七巧略觉身体不适,向宋嬷嬷告了假,回了添香阁休息。宋嬷嬷只得苦着一张脸,出去对客人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解释,又十分不舍地把客人的钱如数退回,只求那些慕名而来的人,别上火砸场子。
多数客人悻悻离去,但有少数仍不肯走,挽起衣袖,就准备砸场,大有见不到七巧不罢休的架势。此时,一直坐在角落的一位客人站起来,用极其方正的声音说道:“别做这些无赖之举。”那些人仰头看看那位客人,都噤声不敢再言,灰溜溜出了杏花楼。
宋嬷嬷立时换了一副笑脸,故作娇态走到那人身边,挤眉弄眼地道谢:“多谢大侠出手相助,宋姬感激不尽。”宋嬷嬷年轻时候,也是美人,如今徐娘半老,风韵犹存,卖弄起风情来,也颇为动人。
那人只作不见,豁地向后退了两步,道:“六扇门总捕头阿鲁迪巴,改日再来拜会七巧姑娘。”宋嬷嬷吓了一跳,急忙问:“总捕大人,我只是开了一家小店,规规矩矩做生意,七巧也是本分姑娘,怎会惊动您的大驾?”
阿鲁迪巴憨直一笑,对宋嬷嬷拱手为礼:“事关公务,恕我不能告之。”说完,阿鲁迪巴告辞离去,留下宋嬷嬷一人,急成了热锅上的蚂蚁。
七巧站在添香阁上,望着阿鲁迪巴远去的背影,精致绝美的脸上露出淡淡的笑容。她其实没病,只是得知六扇门总捕要来,不想见装病避开而已。从十八岁挂牌以来,她在杏花楼已经度过四年光阴,见过无数客人,阿鲁迪巴是她唯一不想见的人。她不想与阿鲁迪巴纠缠,因为他是一个极其难缠的人。
曾经,阿鲁迪巴奉皇命追缉入皇宫行窃的侠盗米罗,便锲而不舍追了米罗大半年,最后,米罗被他追得实在心烦,只得又潜入皇宫,摸走皇帝头冠上新换的玉翡翠,并留下一封书信,威胁皇帝叫阿鲁迪巴停止追缉他,否则就要皇帝的命。皇帝自然立刻下令,米罗这才算是松了一口气。
所以,七巧对阿鲁迪巴,是敬鬼神而远之,能不见,则不见。
七巧轻声叹气,开始对镜卸妆。菱花镜里,有一张出奇妩媚的脸。浓厚的脂粉,掩盖不住她细长的蛾眉,柔软的双唇,还有,那双无论谁也不能忽略的明澄秋波,以及左眼下面动人的美人痣。
这副面具,似乎戴得太久了,有时候,她自己也分不清,镜里的人是谁。四年来,她迎来送往,敷衍所有来这里的人,但她,记住了一个人,说永不能忘,也不为过。
那人是——名动天下的赏金猎人——公子。
记得那天,她画了梅花妆,眉间的梅花衬出她楚楚动人的风韵,秀雅无比。他就那样走了进来,半旧的衣衫带着雨雾的湿气,清冷的脸上有疏离的冷漠,却是风姿绝秀,飘逸出尘。
那时正有人弹琴,七巧一见到他,便按音律清歌唱了一曲元好问的《骤雨打新荷》:
“绿叶阴浓,遍池塘水阁,偏趁凉多。海榴初绽,妖艳喷香罗。老燕携雏弄语,有高柳鸣蝉相和。骤雨过,珍珠乱糁,打遍新荷。人生有几,念良辰美景,一梦初过,穷通前定,何用苦张罗?命友邀宾玩赏,对芳樽浅酌低歌。且酩酊,任他两轮日月,来往如梭。”
他听完,便轻轻击掌赞道:“七巧姑娘好婉转清丽的嗓子!”接着,他丢出一个包袱,说:“今夜,我包下杏花楼。”此话一出,自然有人不服,但当他打开那包袱,所有的人都愣住了。那包袱中,俱是珠宝,珍珠玛瑙、翡翠琉璃、珊瑚白玉,让人目不暇接。
“你是何人,别仗势有钱就了不起!”有人不服气叫出来。
“我是公子。”
只是简单的四个字,就叫人闭了口,纷纷退走。待人散尽,他才对七巧说:“我慕姑娘之名,特来与姑娘斗斗文才!”
七巧嫣然而笑:“公子才华过人,妾自知不如。”
他淡然一笑:“姑娘,何必过谦!”
“那好,妾恭敬不如从命。”七巧欣然答应,她其实对这位名动天下的公子,也十分好奇,如今他找上门,自然不会错过机会,“请公子出题。”这时,早有略通文墨的姐妹围了上来,凝神静待他出题。
“客随主便,还请姑娘先出才是。”
七巧接过一个姐妹递上来的笔墨,铺开一张纸,片刻就写好了题目。只见上面写道:九张机,以‘雨’贯穿全词,一人一段。他看了那纸,立刻赞叹:“姑娘书法遒丽温润,又隐隐透出一股刚烈之气,实在难得!”
七巧说了声“谬赞”,提笔又写道:“一张机,谢桥寒雨自翻飞,霜清夜永愁难寐。滴滴点点,落成春恨,言誓待郎归。”
他看了,提笔续道:“两张机,晓来初雾露微晞,依依别绪萦相系。一场风雨,音书绝断,何日可逢伊?”七巧见了他的书法,也赞叹出声:“公子书法飘逸淡雅,与公子的气度相得益彰。”
说完,七巧又续道:“三张机,情浓有恨上心儿,春衫薄泪人憔悴。忽忽雨骤,透湿罗帕,君可记芳菲?”
他立时再续:“四张机,无言脉脉意成灰,半醒半醉残天白。斜风细雨,万丝千缕,都化苦相思!”七巧接着续下:“五张机,朱颜镜里问归期,幽幽冷雨波光媚。兰泽花好,暗香浮动,还蹙俏眉儿。”
他紧接着续:“六张机,孤衾单枕总因痴,愁心未有相怜计。燕山夜雨,似烟似梦,相对看涟漪。”七巧再续道:“七张机,南亭忆雨抱情丝,织成香锦裁罗绮。缠缠绕绕,绵绵密密,君且作寒衣。”
而后他续:“八张机,西风弄影夜阑时,怕听雨敲芭蕉碎。秋林烟聚,秋霜涩冷,无眠怨多时。”七巧作结:“九张机,雨残花落只堪悲,素衣敛尽红妆色。惟将春意,深藏曲水,不怕尔归迟。”
两人作完,一番品评,他澹然说道:“姑娘起得太哀怨了些。”七巧也道:“我等飘萍之人,只得作出如此哀音。请公子出下题。”
他立时请旁观的姑娘拿了本韵书上来,又请其中一人随便翻出一页,指出四个字,以此作韵,成一首五律。一位姑娘翻出韵来,乃是“八庚”的“城、清、惊、声”,他走到琴旁,随意坐下,轻挑琴弦,唱道:
“关山烽火在,长夜宿孤城。
残堠经霜重,衰翎沐露清。
金戈奔电冷,铁马驭风惊。
四野边庭寂,夷歌起一声。”
七巧听得入神,待他停了琴音许久才回过神,略有些怅然道:“公子以气驭琴,琴声已入化境,令人陶醉。此歌豪迈慷慨,又带悲凉之意,当真使人热血沸腾,不禁要为之一哭。”
他起身让出位置,七巧随即坐下,低眉思索片刻,唱道:
“梧桐遮晓月,别泪是倾城。
长忆冰心恨,空留玉叶清。
拈花花相似,沉梦梦还惊。
曲径通幽处,疏林沁雨声。”
唱毕,七巧立刻便说:“公子见笑了,妾只惯作伤春闺怨之调,比不得公子雄壮之音。妾之琴艺浅薄,有辱公子尊听。”
他微微一笑,不做声,就琴艺来说,七巧的琴音固然回旋动听,却比他逊了半筹。“姑娘,你若能以心命指,以指驱弦,弦随指使,指自心施,琴艺当可精进。”他随即指出七巧弹琴之不足,听得七巧频频点头。
“妾有几张丹青,还请公子移驾添香阁,指点一二。”七巧只觉与他相谈甚欢,越发想再多谈些时候。但,方才还兴致正浓的他,突然面色一变,匆匆向七巧道别:“姑娘,我还有事,就此别过。”
说着,他将桌上那张写着《九张机》的纸抄在手中,一闪身不见了踪影。
此后,七巧便再没见过他。公子,凭空从江湖消失,没人知道他去了何处。
一阵夜风吹来,打断了七巧的思绪,她挑亮烛火,一边吟,一边提笔写道:
“往事只堪哀。春阑意,难相记。恨鱼雁难来,思君明月开。
看闲佳客老,流光晓。雨林台,此景绕心怀,灵犀空自埋。”
七巧本是心性极高之人,她原以为世上无人能与她在文才上一较长短,但公子惊鸿一般出现,一番短暂交谈,叫她佩服至极,引为知音。此时,她想起公子踪迹渺渺,也许再无机缘相见,便忍不住写下一阕《醉垂鞭》,以抒心怀。
烛火轻轻跳动,映照出七巧卸妆后的容颜:她依旧妩媚动人,但眉宇之间,却显出浓烈的英气,竟不似女子。
“无聊,竟作如此颓废的词!”门外响起一个带着浓浓嘲讽语调的声音。七巧立刻从桌上供养的一瓶牡丹摘下几片花瓣,左手手掌平推,以掌风震开房门,右手紧跟着一甩,那几片娇艳的花瓣刹那间就带着强劲的破空之声,凌厉地飞向门外。
“你果真无聊透顶!”门口站着一个满脸桀骜的青年,他手中把玩着一对判官笔,笔尖上正串着几片牡丹花瓣,很不悦地看着七巧,“摘叶飞花的绝顶武功,被你当作伤害同伴的游戏!”
七巧满不在乎地说:“我这点微末伎俩,若能伤害你,可也算是奇异至极的事情。”
“我看你是在杏花楼呆久了,忘记了一些该做的事情。”桀骜青年冷冷提醒七巧,“主公说了,被阿鲁迪巴盯上十分麻烦,你要尽快摆脱他。”
“摆脱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七巧似乎有些气恼,只淡淡应了桀骜青年一句,便不再说话。桀骜青年冷哼一声道:“若不是太了解你,我立即就去告诉主公,你叛变了。”
“迪斯马斯克,你管好你自己就行了!”七巧也冷哼一声回道。
迪斯马斯克突然仰天大笑:“真好笑,你的个性也该改改了,别那么阴阳怪气的。”
七巧也笑起来:“恐怕那个人是你吧。”
“摆脱不了阿鲁迪巴,便杀了他。”迪斯马斯克收起笑容,冷酷地说,“主公就快举事,不能让他查出什么。”“正好,这里我也住腻了,是时候换个地方。”七巧也收了笑,“不反对我在这里解决他吧?”
“随便你,别误了主公的事。”迪斯马斯克说着,一闪身就跳下了添香阁,隐没在茫茫夜色中。七巧展颜一笑,摘下几片牡丹花瓣,在手中揉搓一阵,挥手打出,只见那几片花瓣碎开,轻飘飘地落到桌上,排成四个字:阿布罗狄。
此时,若有人看到桌上的四个字,而他又有幸看过《武林宝鉴》,一定会惊跳起来。这个名字,曾是轰动江湖的煞星,每一个听到他名字的人,都为之变色。他拥有一个更震慑的绰号——牡丹杀手,这是与公子齐名的名号。他们做的营生类似,但有所不同的是,遇到公子的人,不会死在他的手上,而遇到牡丹杀手的人,都会死在他的手里。而且,那些被杀的人,在心脏的地方都会插着一朵娇艳的牡丹,显得十分诡异。他比公子更神秘,根本没人见过他的真面目,有传说,他是耄耋老人,又有传说,他是二八佳人,还有传说,他是面目森冷的中年人,但几乎没人知道,已经消失四年的牡丹杀手,变成了杏花楼的七巧。
阿布罗狄有些自嘲地笑,有时候,他自己也不相信,这样的生活,他一过就是四年。只是,不相信是一回事,他绝不后悔当初的选择。别人是怎样,他不知道,他只知道,从他们相对而笑开始,他选择把生命交付给他,成为他的死士。他不介意易容成女人,在杏花楼迎来送往卖艺侍人,因为,这样可以以最快最安全的方式,筹集资金,亦可搜集江湖情报,为他举事做准备。
无论是谁,只要妨碍到他,他就不会客气。这几年修心养性的日子,是时候结束了。
目录|上一章|下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