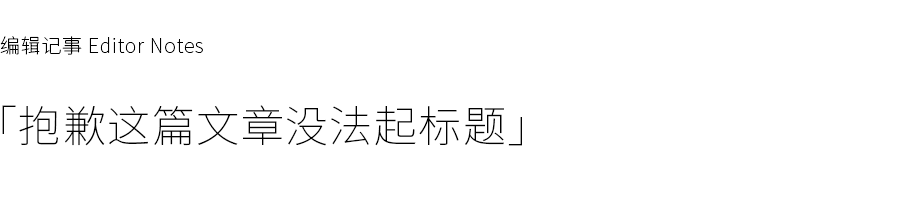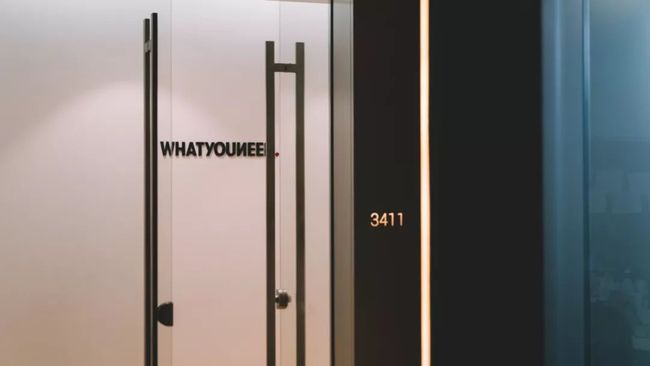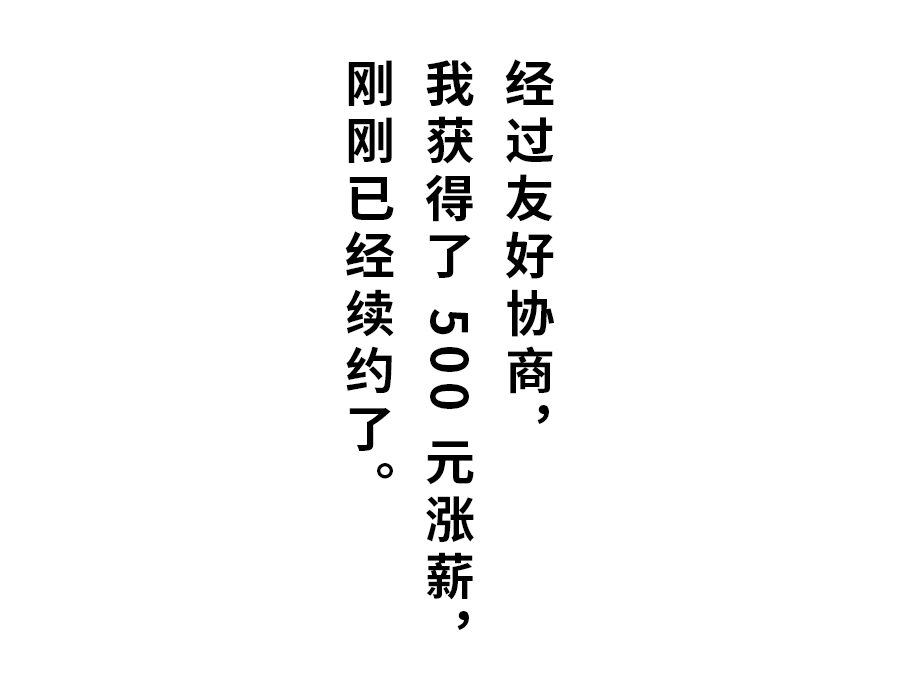在WhatYouNeed离职之前,我做了一件事。
晚上好,我是编辑 Acher。
一直以来,我很想做一件事,那就是跟大家讲讲 WhatYouNeed 的工作日常,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个公众号总是要在深夜十二点左右才推送”,“编辑们都不用休息的吗”之类的问题。
可以说,今天的文章就是一个答案。
但是,这篇答案里面也藏了很多,平时我们绝对不会分享的东西。欢迎你进行探索发现。
前两天和朋友打电话,得知她要开始度假了,准备去濑户内海晒半个月阳光。
她的工作,是运营一个关于环保的公众号,职位是主编。这个职位好听是好听,但她的手下没人,是一个光杆司令。
作为同行,我有些同情她。
我问:“那你边玩还要边更新公众号,不就玩得很不开心?”
我猜,她应该在电话那边翻了个白眼。因为她说:“我干嘛要更新?我休假的时候才不工作呢。”
我愣住了,这突破了我的认知。
因为这样的度假方式,和我的主编兼老板 Blake 完全不一样。他已经四年没有休息过了。
倒不是四年没有睡觉,而是我认识他的这四年来,他没有哪一天是可以被称为“休息日”的。
虽然,我们已有了数十人的采编团队,但每一篇文章发布前,主编和完美主义者双料身份的 Blake 都参与了审核选题、跟进采写、改稿、按下发布键。
即使是没有的那一天,这个步骤也在继续:审核选题、跟进采写、改稿、决定不按下发布键。
所以,如果公众号某天不更新了,他也没有在休息。
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工作是,就算今天拿了 10万 + ,明天睁开眼也依旧要从 0 开始。
我也做过一段时间的主编,只不过负责的是另外一个公众号。
我深知一位文字工作者的工作日常,比起生理压力,更让人难受的是心理压力。
任何时刻,即使定稿了,也无法躲避各种突然出现的闪念:
“文章这么改会更好。”
“这一段有点说不过去。”
“这个标题不够吸引人。”
这里的任何一句话,都有可能促使我在吃宵夜的途中抽离,匆匆找个安静的地方,再打开手机热点,抽出电脑开始改稿。
上一秒还和朋友开着各种无底线的玩笑,下一秒就对着电脑回忆原生家庭给自己带来的伤害,这大概算是公众号职业技能的基础要求。
我认可这样的工作方式。因为我们相信任何一篇文章,只有被我们充分讨论了之后,才会变得更好。
但是代价也很磨人。
所以做了一段时间后我接受不了(KPI 无法完成),也就卸任了。
无论在被紫光充盈的东南亚迪厅里,还是在被和风建筑包裹的京都酒店里。时刻从生活中抽离,然后投入工作,已经成为他的习惯。
唯一一次可以被称为“度假”的经历,是他去年国庆去了一周纽约。
在那次旅程中,他在一家面对着时代广场的酒店开了一间房。
然后,躺在床上审核「晚安日历」总共 75000字的文案。
昨天晚上,我问他:“你有没有发现你一天的时间里全是工作,没有生活,你不难受吗?”
他说:“工作就是我的生活。”
这个答案让我停下来思考了一会儿,但总感觉少了点人文关怀。比起这个答案,我其实自己心里已经有一个答案了。
他其实是有一套专属自己的,感受生活的方案。
凌晨时分,今天的推送发完了,他一般会做一件事——在朋友圈里无差别点赞。
逢人就点,就连实习生给自己的中学生弟弟拉票的朋友圈也不放过。
那并不意味着他喜欢你的朋友圈,更像是一种宣告仪式——表达“我忙完了,我终于可以刷今天的朋友圈了。”
和点赞朋友圈类似的,还有吃宵夜这件事。
天河区的吴系茶餐厅是 Blake 的不二选择。
翻了两页菜谱,他就会说:“今晚就简单的吃点吧。”然后点一例烧鹅、一锅汤、四五碟小炒、菠萝油和甜品。
四个人吃,八人份的菜,是和 Blake 吃宵夜的标配。
他也没有吃很多,半碗糖水,两块烧鹅就停筷了。对于他来说,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吃了。
忙碌的人可能都有这样的体会,在深夜里的许多行动,只是为了补偿每天日程里的空白。
很难说这是他找到了自己平衡工作和生活的方法,更多的是,他不太愿意真的活成一个没有生活的人。
写到这里,我又听到了 Blake 在会议室里开怀大笑了。
回头看了看会议室里的屏幕,显示的是某个项目的启动策划。这里面根本没有笑点,或者这件事情就不值得开怀大笑。
但他在开会、加班时,总是大笑的。
又比如说,他总会第一时间买到最新发布的耳机、电脑、手机、平板、手表和各类电子产品。
并在第一次使用的时候,眼睛睁大并惊呼:“天啊,这个东西真的太好用了/太好玩了/太好听了/太能提高我的生产效率。”
说实话,用某品牌第一代耳机的我,并感受不到它的第二代的音质有什么不同。但他会特意跟我视频通话:“新出的第二代耳机真的太好了,音质进步太多了!”
看起来有点小题大做,但在我看来,在忙碌的缝隙中主动发现身边事物的一点点进步和优点,也是一种生活情趣吧。
而现在的每一个晚上十一点,编辑部几乎都还在加班。但加班的现实,并没有阻挡他像巫婆一样的大笑,以及我们兴奋的心情。
以至于,凌晨来办公室倒垃圾的保洁阿姨也会忍不住问:“为啥你们加班这么晚还这么开心啊?”
“苦中作乐,就是很多人最擅长的快乐啊。” 这是我在心里给出的回答。
说到这里,有必要再次解释一下,我写这篇文章的初衷了。
我是编辑田心。
因为我最近遇到了工作上的困境。
作为一个靠写文章谋生的人,从今年夏天开始,我的创作灵感就少得可怜。选题会上,其他编辑都讨论得很开心,只有我呆在会议室的角落,默不作声。
但是 KPI 不会忘记我。
因为长期没有产出,HR 带着红彤彤的警告通知,跟我再次说明问题的严重性。
于是,每晚下班,我躺在家里的沙发上,琢磨自己到底能不能继续在这个行业呆下去。
其实 7 月 1 日,就是我合约到期的时间。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或许这就是我离开这个行业的时候了。我甚至还向我妈说了这个问题,说了我想辞职,停下来休息一段时间。
我妈说了一句话:“休息就休息吧,你从幼儿园到现在,都没有停下来过。”
没有选题,没有方向,在最惨的时候,我下意识地在身边找一个比自己更惨的人。
而记录 Blake 的生活,似乎让我找到了答案。
最近,在我们未发布的程序测试页面里,Blake 悄悄地回答了一个匿名问题,“遇到哪一件事情最让你崩溃?”
他的回答是:“无法预测我崩溃的时间这件事,最让我崩溃。”
我无法确切地把这句看起来和心理有关的话,和他高强度的工作结合上关系。
但在当下,我看到的是一个比我更“惨”的影子。
所以,我也想把我妈和我说的那一句话,发给他:“休息就休息吧,你从幼儿园到现在,都没有停下来过。”
对了,讲回我“准备离职”的事情。
实话说,在挂了我和我妈说了我要辞职的电话后的那段时间,是我在公司难得轻松的一段时间。
倒不是“我走了,你们自己忙去吧”的心态,而是我把自己从工作焦虑里暂时脱离了。
同样是坐在出租屋里的沙发,我的状态改变了。我不再自怨自艾,而是在审视自己的工作状态。
我问了自己一个问题:“假设我离开这家公司、这个行业,那我的状态会变好吗?”最后得出的答案,是否定的。
如果我在没有真正直面问题的情况下就选择逃避,那我可能永远都无法解决问题。
Blake 找我聊了一次,这个老是在埋头不作声的老板,依然有关注到我。
我最后还是决定留下来,我还能行,我还能比之前做的更好。
在和我妈的第二次通话,我就说:
“我不走了,我要续约了。”
好了
我做的一件事情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