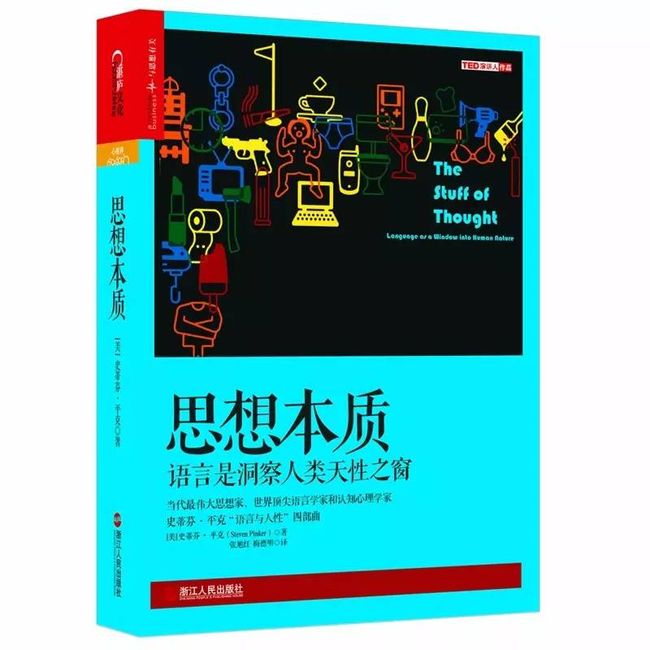- 2.21音频接口
姓学名生
硬件工程
模拟音频接口:传输直观容易实现,但会出现失真、不稳定的特点。TRS接口、XLR卡侬头、RCA莲花头。数字音频接口:AES/EBU物理接口、S/PDIF接口、同轴接口、光纤接口。平衡接口:使用两个通道分别传送电压等大反向的信号。接收端将这两组信号相减,从而获得高质量模拟信号。TRS接口、XLR卡农头。非平衡接口:信号线和地线组成。抗干扰能力弱。TS接口、RCA莲花头。TRS(大三芯):Tip(尖)、
- 存储 单元
姓学名生
其他
存储单元:只能存储一位数据的电路。寄存器:存储一组数据的存储电路。静态存储单元:只要不切断供电电源,静态存储单元的状态会一直保持下去。(锁存器,触发器)。动态存储单元:利用电容的电荷存储效应来存储数据,由于电容的充放电需要一定时间,因而它的工作速度低于静态存储单元。而且,电容上存储的电荷会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泄露,必须定期进行“刷新”。寄存器:由一组触发器组成,由n个触发器组成的寄存器可以存储一组n
- 51蓝牙+红外遥控小车
姓学名生
单片机蓝牙
51蓝牙+红外遥控小车模块:51最小系统l289n驱动模块杜邦线车模18650锂电池蓝牙模块HC-06红外接收器(用开发板上面的就!可!)红外遥控器(用开发板上的就!可!)手机一部(安装好蓝牙串口APP)工具:剪刀,万用表,螺丝刀,胶布,什么杂七杂八的。l298nENA:控制IN1IN2ENB:控制IN3IN4IN1IN2IN3IN4:分别控制OUT1OUT2OUT3OUT412V输入口:接3节3
- RocketMQ介绍与应用场景
我心向阳iu
#RocketMQJava面试知识点精讲java-rocketmqrocketmqjava
文章目录1.RocketMQ介绍1.1RocketMQ介绍1.2MQ的主要应用场景1.3MQ的应用场景举例1、限流削峰1、任务异步处理。3、应用程序解耦合4、日志收集:1.4消息队列技术选型对比1.3.1主流消息队列优缺点比较1.RocketMQ介绍1.1RocketMQ介绍RocketMQ是阿里开源的一款非常优秀中间件产品,脱胎于阿里的另一款队列技术MetaQ,后捐赠给Apache基金会作为一款
- whl下载网址
白白+懒懒
pythonpandaspillowconda
whl下载网址https://pypi.tuna.tsinghua.edu.cn/simple/在网址后加上相应的包名就可以下载相应的whl
- flutter 解决 Running Gradle task ”assembleDebug“
赖某
Flutterflutterandroidstudio
前提时间:2020-08-0100:00:00AndroidStudio配置好模拟器运行的时候在RunningGradletask”assembleDebug“始终不会变化flutterdoctor的环境基本没有问题照着官网,去配置flutter,环境变量等,然后执行命令flutterdoctor#它会检查插件SDK等环境,尽量保证无打叉这时候在AndroidStudio的考虑下,因为照着flut
- com.mongodb.MongoSocketOpenException: Exception opening socket
Mizon�
mongodb
application.yml换成application.properties,MongoAutoConfiguration上的@ConfigurationProperties识别不了yml
- 视频的上传,转码与展示的过程
小子武
java视频上传视频转码
本文是记录自己学习过程的,不适合直接拿来用的业务需求及场景后台基于springboot的微服务框架,页面是vue用户可以选择一个视频上传的管理页面,新增时,用户可以选择上传封面图片或者不选择上传封面图片(此时要根据视频的格式决定是从视频中截图或者展示默认图片)页面效果先不展示了,涉及的信息比较多这里贴的是视频转码功能部分,我从网上找的代码又根据自己的需要又改的,很佩服写这段代码的人真的很厉害(侵删
- elementui树状菜单tree_Java + Element-UI 实现简单的树形菜单
weixin_39682301
一、简单入门级树形菜单实现(纯后台逻辑)1、简介(1)开发环境IDEA+JDK1.8+mysql1.8SpringBoot2.2.6+mybatis-plus此处仅后台开发(返回json数据),前台页面展示后续会讲解。(2)数据表如下,仅供参考,可以添加修改时间、创建时间、逻辑删除等字段。DROPDATABASEIFEXISTStest;CREATEDATABASEtest;USEtest;/*用
- table多行表头合并 vue_vue elementUI table 自定义表头和行合并
weixin_39540704
table多行表头合并vue
最近项目中做表格比较多,对element表格的使用,只需要传递进去数据,然后写死表头即可渲染。但现实中应用中,如果写死表头,并且每个组件中写自己的表格,不仅浪费时间而且消耗性能。这个时候需要动态渲染表头。而官方例子都是写死表头,那么为了满足项目需求,只能自己来研究一下。1、自定义表头代码如下,其实就是分了两部分,表格主数据是在TableData对象中,表头的数据保存在headerDatas,hea
- AI写代码工具Claude:惊悚小说创作的意外热潮与全球用户偏好差异
前端
近年来,人工智能在各个领域的应用日新月异,其中AI代码生成器的兴起更是为开发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效率提升。Anthropic最近发布的一份Claude使用报告,基于百万级用户数据,揭示了这款强大的AI模型的广泛应用,以及不同语言用户对其偏好差异的惊人发现。报告的核心发现之一,便是中文用户对使用Claude创作惊悚小说的强烈偏好,这一现象引发了广泛关注。这篇文章将深入探讨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并对比分析
- 不拆MongoDB解决MongoSocketOpenException: Exception opening socket
zhutoutoutousan
mongodb数据库javaspringboot
问题起源玩JavaSpringBoot全栈项目带有MongoDB,在springboot/src/main/resources/application.properties里边定义了mongodb的database和url,在springboot项目起的时候报错com.mongodb.MongoSocketOpenException:Exceptionopeningsocketatcom.mong
- android+ffmpeg库使用教程,适用于Android的ffmpeg(使用教程:“ ffmpeg和Android.mk”)...
OF COURSE想当然
我正在尝试为Android编译ffmpeg。我已经找到了关于该主题的几篇文章,但似乎都没有。如果尝试构建ffmpeg,它会发布在[1]上。是否有人使用这些教程成功编译了ffmpeg?我不确定如何实现步骤4到5。STEP4:配置...步骤5:CD到您的NDK根目录,键入makeTARGET_ARCH=armAPP=ffmpeg-org在我看来,按照第5步的教程中的说明构建类似的应用程序需要一些先前的
- java导出word poi_Java使用POI根据模板导出Word
张林威
java导出wordpoi
最近从新写了一下根据Word模板导出Word。注意:Word只包含表格和段落,不使用表格布局。图片样式也保留,但是预先需要知道图片的资源ID。删除多余模块时,有顶部对不齐的问题。可能还存在其他细节问题。首先模板样式:下面是导出来的Word:下面贴上代码:packagecom.acgist.word;importjava.io.File;importjava.io.FileInputStream;i
- android obb在哪,未解决:Android 使用obb步骤
渔舟晚之
androidobb在哪
1.通过unity导出包含obb的工程。2.按照google官方给定的obb命名方式,已经存放路径进行操作Obb方式:https://developer.android.com/google/play/expansion-files命名方式:[main|patch]。。.obbeg:main.314159.com.example.app.obb2.1存放路径Sd\Android\obb\packa
- 《人工智能新质生产力:GDP增长的未来引擎,究竟能贡献多少?》
人工智能深度学习
在当今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人工智能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代表,正以前所未有的态势冲击着全球经济格局,其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备受关注。从全球视角来看,诸多研究和专家观点都对人工智能的经济贡献给出了积极预测。普华永道曾在2017年发布报告指出,到2030年,人工智能的发展将带动全球GDP增长14%,相当于15.7万亿美元。莫干山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朱嘉明认为,当前人工智能对全球GDP的平均影响约为0.1%,
- 2025春招,Spring 面试题汇总
springjava面试
大家好,我是V哥。2025年金三银四春招马上进入白热化,兄弟们在即将到来的假期,除了吃喝欢乐过新年,想年后跳槽升职的兄弟也要做好充分的准备,要相信,机会永远只留给有准备的人。以下是一份2025年春招Spring面试题汇总,送给大家,关于Java基础相关的请移步V哥上一篇文章《【长文收藏】2025备战金三银四Java大厂面试题》:Spring基础部分一、Spring基础1.什么是Spring框架?答
- 首个“非遗版春节”怎么过?扫描全能王发起新春扫描活动
人工智能算法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春节凝结了华夏民族数千年来的家国情感和历史底蕴,近期,“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面对首个世界“非遗版”春节,合合信息旗下扫描全能王发起了“扫描全能王春节还能这样用”新春扫描活动,用户可“花式”扫描与新春相关的“记忆符号”,助力“非遗”元素传承。春节是中华民间艺术的集中体现,围绕着辞旧迎新、团圆和
- Android Studio中使用FFmpeg动态库
Getnway
AndroidFFmpegNDKandroidffmpegandroidstudio动态库
使用FFmpeg动态库本文借鉴最简单的基于FFmpeg的移动端例子:AndroidHelloWorld,并介绍在AndroidStudio中的实现。项目地址:https://github.com/Getnway/FFmpegDemo本文介绍的是用NDK编译动态库,并在AndroidStudio中调用的步骤。准备项目需要有FFmpeg的动态库,如下文件(版本可以不同)。FFmpeg动态库编译参考Li
- chatgpt赋能python:Python怎么打包成APK
vacvefito
ChatGptpythonchatgpt开发语言计算机
Python怎么打包成APK如果你是一位有10年Python编程经验的工程师,并且想要将自己的Python应用程序打包成APK,那么你来对地方了。本文将会介绍如何使用Python来打包成APK,以及在不同平台上的一些注意事项。在阅读本文之后,你应该可以顺利地将自己的Python应用程序打包成APK了。什么是Python的APKAPK是AndroidPackage的缩写,它是Android系统中的一
- ffmpeg学习六:avcodec_open2函数源码分析
阳光玻璃杯
ffmpegffmpeg源码codecopen
上一节我们尝试分析了avformat_open_input函数的源码,这个函数的虽然比较复杂,但是它基本是围绕着创建和初始化一些数据结构来展开的,比如,avformat_open_input函数会创建和初始化AVFormatContext,AVClass,AVOption,URLContext,URLProtocol,AVInputFormat,AVStream等数据结构,这些数据结构的关系如下:
- eclipse的书签快捷键插件-Quickmarks plugin
springleft
eclipseduplicatesdocumentationkeyboardpluginsfile
eclipse编辑器增强工具之书签工具:插件主页:http://eclipse-tools.sourceforge.net/quickmarks/OverallQuickmarksareWorkspaceglobalbydefault,butyoucanchangethattohaveoneSetofQuickmarksperProject,FolderorDocument.AQuickmarkr
- deepin分享-Linux & Windows 双系统时间不一致解决方案
deepin
在双系统环境中(如Windows和Linux),时间同步问题是一个常见的困扰。Windows和Linux对系统时间的处理方式不同,这可能导致时间显示不一致。本文将介绍两种解决方法,帮助你解决Linux和Windows双系统时间不一致的问题。问题背景Windows操作系统直接将CMOS时间(硬件时钟)视为本地时间,不根据时区进行转换。每次调整系统时区或修改时间时,Windows会直接修改CMOS时间
- 【檀越剑指大厂--RocketMQ】RocketMQ运维篇
Kwan的解忧杂货铺@新空间代码工作室
s总檀越剑指大厂java-rocketmqrocketmq运维
欢迎来到我的博客,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您见面!希望您在这里可以感受到一份轻松愉快的氛围,不仅可以获得有趣的内容和知识,也可以畅所欲言、分享您的想法和见解。推荐:kuan的首页,持续学习,不断总结,共同进步,活到老学到老导航檀越剑指大厂系列:全面总结java核心技术点,如集合,jvm,并发编程redis,kafka,Spring,微服务,Netty等常用开发工具系列:罗列常用的开发工具,如IDEA,M
- 【C语言的数组指针,指针数组及数组与指针的区别】
afool�♂️
c语言开发语言
C语言的数组指针,指针数组及数组与指针的区别目录C语言的数组指针,指针数组及数组与指针的区别一、数组和指针的区别二、数组指针三、指针数组四、题总结一、数组和指针的区别老师常念叨数组名是首元素的地址,charp[3]=“abc”;数组名p是数组p的首元素a的地址,若想取到后面的值便增加偏移量就好可以得到,指针好像也是保存的地址,然后通过该增加偏移量获取后面的值。看似好像两个真像是一对“兄弟”。但是仔
- 鸿蒙UI主线程任务调度原理介绍及最佳实践
harmonyos
课程简介本课程是【HarmonyOSTechTalk】的第18课。本次交流重点围绕鸿蒙UI展开。其中,主线程在整个应用的任务处理中占据关键地位,其任务调度机制更是核心要点。开发者可通过子线程向主线程抛任务的方式,有效避免主线程阻塞,提升整体性能。而状态驱动UI更新则是一种推荐的高效模式,它依据应用状态的变化精准触发UI刷新,避免不必要的更新操作。深入理解并运用鸿蒙UI主线程任务调度机制,开发者能够
- ArkUI原生页面滑动性能分析优化实践
harmonyos
课程简介本课程是【HarmonyOSTechTalk】的第20课。本次交流核心为ArkUI原生页面的滑动性能相关内容。从HarmonyOS渲染原理切入,这是理解页面呈现与滑动效果的根基。深入剖析应用滑动性能问题的分析思路,为开发者提供排查问题的有效方法。详细阐述针对典型性能问题的优化手段,涵盖代码优化、资源管理等多方面。开发者通过此次交流,能够精准把握ArkUI原生页面滑动性能的关键要点,提升性能
- 小红书获取笔记详情API接口的开发、应用与收益。
前端后端运维数据挖掘api
一、开发基础(一)技术选型在开发小红书获取笔记详情API接口时,后端语言可选用Python搭配Django框架。Django具有强大的路由系统、数据库管理功能以及内置的安全机制,能极大提高开发效率。数据库方面,MySQL以其稳定性和广泛的应用场景成为不错选择,可高效存储笔记的各类信息,包括文字内容、图片链接、点赞数、评论数等。(二)接口设计请求方式:采用HTTPGET请求,通过在URL中携带笔记的
- HarmonyOS Next Developer Beta5 8月尝鲜版版本说明
harmonyos
课程简介本课程是【HarmonyOSTechTalk】的第13课。本次主要围绕HarmonyOSNEXT的DeveloperBeta5-8月尝鲜版展开介绍。HarmonyOSNEXT代表着鸿蒙系统的未来发展方向,此次的DeveloperBeta5版本尤为值得关注。版本配套涵盖了一系列的开发工具和文档,为开发者提供全面支持。新增特性方面,可能会有新的功能模块或技术优化,为系统带来新的活力。变更特性则
- DevEcoStudio性能工具集介绍
harmonyos
课程简介本课程是【HarmonyOSTechTalk】的第15课。本次交流聚焦于IDE性能工具集这一关键开发辅助资源。该工具集涵盖多方面重要功能,性能检测可精准定位应用运行中可能存在的效率瓶颈与问题所在;性能分析则深入挖掘问题根源,剖析各类性能数据背后的关联与原因;而性能指导依据专业知识与经验提供最佳解决方案。开发者借助这一强大的IDE性能工具集,能在鸿蒙应用开发过程中显著提升性能优化分析效率,有
- sql统计相同项个数并按名次显示
朱辉辉33
javaoracle
现在有如下这样一个表:
A表
ID Name time
------------------------------
0001 aaa 2006-11-18
0002 ccc 2006-11-18
0003 eee 2006-11-18
0004 aaa 2006-11-18
0005 eee 2006-11-18
0004 aaa 2006-11-18
0002 ccc 20
- Android+Jquery Mobile学习系列-目录
白糖_
JQuery Mobile
最近在研究学习基于Android的移动应用开发,准备给家里人做一个应用程序用用。向公司手机移动团队咨询了下,觉得使用Android的WebView上手最快,因为WebView等于是一个内置浏览器,可以基于html页面开发,不用去学习Android自带的七七八八的控件。然后加上Jquery mobile的样式渲染和事件等,就能非常方便的做动态应用了。
从现在起,往后一段时间,我打算
- 如何给线程池命名
daysinsun
线程池
在系统运行后,在线程快照里总是看到线程池的名字为pool-xx,这样导致很不好定位,怎么给线程池一个有意义的名字呢。参照ThreadPoolExecutor类的ThreadFactory,自己实现ThreadFactory接口,重写newThread方法即可。参考代码如下:
public class Named
- IE 中"HTML Parsing Error:Unable to modify the parent container element before the
周凡杨
html解析errorreadyState
错误: IE 中"HTML Parsing Error:Unable to modify the parent container element before the child element is closed"
现象: 同事之间几个IE 测试情况下,有的报这个错,有的不报。经查询资料后,可归纳以下原因。
- java上传
g21121
java
我们在做web项目中通常会遇到上传文件的情况,用struts等框架的会直接用的自带的标签和组件,今天说的是利用servlet来完成上传。
我们这里利用到commons-fileupload组件,相关jar包可以取apache官网下载:http://commons.apache.org/
下面是servlet的代码:
//定义一个磁盘文件工厂
DiskFileItemFactory fact
- SpringMVC配置学习
510888780
springmvc
spring MVC配置详解
现在主流的Web MVC框架除了Struts这个主力 外,其次就是Spring MVC了,因此这也是作为一名程序员需要掌握的主流框架,框架选择多了,应对多变的需求和业务时,可实行的方案自然就多了。不过要想灵活运用Spring MVC来应对大多数的Web开发,就必须要掌握它的配置及原理。
一、Spring MVC环境搭建:(Spring 2.5.6 + Hi
- spring mvc-jfreeChart 柱图(1)
布衣凌宇
jfreechart
第一步:下载jfreeChart包,注意是jfreeChart文件lib目录下的,jcommon-1.0.23.jar和jfreechart-1.0.19.jar两个包即可;
第二步:配置web.xml;
web.xml代码如下
<servlet>
<servlet-name>jfreechart</servlet-nam
- 我的spring学习笔记13-容器扩展点之PropertyPlaceholderConfigurer
aijuans
Spring3
PropertyPlaceholderConfigurer是个bean工厂后置处理器的实现,也就是BeanFactoryPostProcessor接口的一个实现。关于BeanFactoryPostProcessor和BeanPostProcessor类似。我会在其他地方介绍。PropertyPlaceholderConfigurer可以将上下文(配置文件)中的属性值放在另一个单独的标准java P
- java 线程池使用 Runnable&Callable&Future
antlove
javathreadRunnablecallablefuture
1. 创建线程池
ExecutorService executorService = Executors.newCachedThreadPool();
2. 执行一次线程,调用Runnable接口实现
Future<?> future = executorService.submit(new DefaultRunnable());
System.out.prin
- XML语法元素结构的总结
百合不是茶
xml树结构
1.XML介绍1969年 gml (主要目的是要在不同的机器进行通信的数据规范)1985年 sgml standard generralized markup language1993年 html(www网)1998年 xml 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
- 改变eclipse编码格式
bijian1013
eclipse编码格式
1.改变整个工作空间的编码格式
改变整个工作空间的编码格式,这样以后新建的文件也是新设置的编码格式。
Eclipse->window->preferences->General->workspace-
- javascript中return的设计缺陷
bijian1013
JavaScriptAngularJS
代码1:
<script>
var gisService = (function(window)
{
return
{
name:function ()
{
alert(1);
}
};
})(this);
gisService.name();
&l
- 【持久化框架MyBatis3八】Spring集成MyBatis3
bit1129
Mybatis3
pom.xml配置
Maven的pom中主要包括:
MyBatis
MyBatis-Spring
Spring
MySQL-Connector-Java
Druid
applicationContext.xml配置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
- java web项目启动时自动加载自定义properties文件
bitray
javaWeb监听器相对路径
创建一个类
public class ContextInitListener implements ServletContextListener
使得该类成为一个监听器。用于监听整个容器生命周期的,主要是初始化和销毁的。
类创建后要在web.xml配置文件中增加一个简单的监听器配置,即刚才我们定义的类。
<listener>
<des
- 用nginx区分文件大小做出不同响应
ronin47
昨晚和前21v的同事聊天,说到我离职后一些技术上的更新。其中有个给某大客户(游戏下载类)的特殊需求设计,因为文件大小差距很大——估计是大版本和补丁的区别——又走的是同一个域名,而squid在响应比较大的文件时,尤其是初次下载的时候,性能比较差,所以拆成两组服务器,squid服务于较小的文件,通过pull方式从peer层获取,nginx服务于较大的文件,通过push方式由peer层分发同步。外部发布
- java-67-扑克牌的顺子.从扑克牌中随机抽5张牌,判断是不是一个顺子,即这5张牌是不是连续的.2-10为数字本身,A为1,J为11,Q为12,K为13,而大
bylijinnan
java
package com.ljn.base;
import java.util.Arrays;
import java.util.Random;
public class ContinuousPoker {
/**
* Q67 扑克牌的顺子 从扑克牌中随机抽5张牌,判断是不是一个顺子,即这5张牌是不是连续的。
* 2-10为数字本身,A为1,J为1
- 翟鸿燊老师语录
ccii
翟鸿燊
一、国学应用智慧TAT之亮剑精神A
1. 角色就是人格
就像你一回家的时候,你一进屋里面,你已经是儿子,是姑娘啦,给老爸老妈倒怀水吧,你还觉得你是老总呢?还拿派呢?就像今天一样,你们往这儿一坐,你们之间是什么,同学,是朋友。
还有下属最忌讳的就是领导向他询问情况的时候,什么我不知道,我不清楚,该你知道的你凭什么不知道
- [光速与宇宙]进行光速飞行的一些问题
comsci
问题
在人类整体进入宇宙时代,即将开展深空宇宙探索之前,我有几个猜想想告诉大家
仅仅是猜想。。。未经官方证实
1:要在宇宙中进行光速飞行,必须首先获得宇宙中的航行通行证,而这个航行通行证并不是我们平常认为的那种带钢印的证书,是什么呢? 下面我来告诉
- oracle undo解析
cwqcwqmax9
oracle
oracle undo解析2012-09-24 09:02:01 我来说两句 作者:虫师收藏 我要投稿
Undo是干嘛用的? &nb
- java中各种集合的详细介绍
dashuaifu
java集合
一,java中各种集合的关系图 Collection 接口的接口 对象的集合 ├ List 子接口 &n
- 卸载windows服务的方法
dcj3sjt126com
windowsservice
卸载Windows服务的方法
在Windows中,有一类程序称为服务,在操作系统内核加载完成后就开始加载。这里程序往往运行在操作系统的底层,因此资源占用比较大、执行效率比较高,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杀毒软件。但是一旦因为特殊原因不能正确卸载这些程序了,其加载在Windows内的服务就不容易删除了。即便是删除注册表中的相 应项目,虽然不启动了,但是系统中仍然存在此项服务,只是没有加载而已。如果安装其他
- Warning: The Copy Bundle Resources build phase contains this target's Info.plist
dcj3sjt126com
iosxcode
http://developer.apple.com/iphone/library/qa/qa2009/qa1649.html
Excerpt:
You are getting this warning because you probably added your Info.plist file to your Copy Bundle
- 2014之C++学习笔记(一)
Etwo
C++EtwoEtwoiterator迭代器
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写博客了,可能大家已经淡忘了Etwo这个人的存在,这一年多以来,本人从事了AS的相关开发工作,但最近一段时间,AS在天朝的没落,相信有很多码农也都清楚,现在的页游基本上达到饱和,手机上的游戏基本被unity3D与cocos占据,AS基本没有容身之处。so。。。最近我并不打算直接转型
- js跨越获取数据问题记录
haifengwuch
jsonpjsonAjax
js的跨越问题,普通的ajax无法获取服务器返回的值。
第一种解决方案,通过getson,后台配合方式,实现。
Java后台代码:
protected void doPost(HttpServletRequest req, HttpServletResponse resp)
throws ServletException, IOException {
String ca
- 蓝色jQuery导航条
ini
JavaScripthtmljqueryWebhtml5
效果体验:http://keleyi.com/keleyi/phtml/jqtexiao/39.htmHTML文件代码:
<!DOCTYPE html>
<html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head>
<title>jQuery鼠标悬停上下滑动导航条 - 柯乐义<
- linux部署jdk,tomcat,mysql
kerryg
jdktomcatlinuxmysql
1、安装java环境jdk:
一般系统都会默认自带的JDK,但是不太好用,都会卸载了,然后重新安装。
1.1)、卸载:
(rpm -qa :查询已经安装哪些软件包;
rmp -q 软件包:查询指定包是否已
- DOMContentLoaded VS onload VS onreadystatechange
mutongwu
jqueryjs
1. DOMContentLoaded 在页面html、script、style加载完毕即可触发,无需等待所有资源(image/iframe)加载完毕。(IE9+)
2. onload是最早支持的事件,要求所有资源加载完毕触发。
3. onreadystatechange 开始在IE引入,后来其它浏览器也有一定的实现。涉及以下 document , applet, embed, fra
- sql批量插入数据
qifeifei
批量插入
hi,
自己在做工程的时候,遇到批量插入数据的数据修复场景。我的思路是在插入前准备一个临时表,临时表的整理就看当时的选择条件了,临时表就是要插入的数据集,最后再批量插入到数据库中。
WITH tempT AS (
SELECT
item_id AS combo_id,
item_id,
now() AS create_date
FROM
a
- log4j打印日志文件 如何实现相对路径到 项目工程下
thinkfreer
Weblog4j应用服务器日志
最近为了实现统计一个网站的访问量,记录用户的登录信息,以方便站长实时了解自己网站的访问情况,选择了Apache 的log4j,但是在选择相对路径那块 卡主了,X度了好多方法(其实大多都是一样的内用,还一个字都不差的),都没有能解决问题,无奈搞了2天终于解决了,与大家分享一下
需求:
用户登录该网站时,把用户的登录名,ip,时间。统计到一个txt文档里,以方便其他系统调用此txt。项目名
- linux下mysql-5.6.23.tar.gz安装与配置
笑我痴狂
mysqllinuxunix
1.卸载系统默认的mysql
[root@localhost ~]# rpm -qa | grep mysql
mysql-libs-5.1.66-2.el6_3.x86_64
mysql-devel-5.1.66-2.el6_3.x86_64
mysql-5.1.66-2.el6_3.x86_64
[root@localhost ~]# rpm -e mysql-libs-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