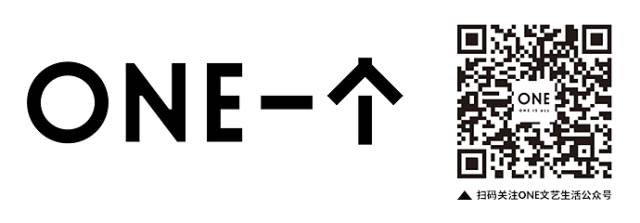没有人有源源不断的热情和温柔 | ONE能音乐
只是在选择的路口,选择了真心以待。
在职场摸爬滚打一年的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只要甩锅能力好,职场命运就会长寿。当一个莫名其妙的屎盆子扣在我头上时,没有人愿意为我说一句公道话。辞职后我买了去杭州的机票,在一个吃知了的仲夏天。
我订了鼓楼旁边的一家民宿,站在前台一边办理入住一边从口袋摸出纸巾拧鼻涕。飞机机舱里的温度有些凉,落地后取了行李走出自动玻璃门时,一股热浪朝我扑来,忍不住打了几个喷嚏。好不容易把行李挪上二楼,关上房门即刻瘫在床上摆着大字睡着了。
醒来的时候头昏脑胀,一摸额头感觉情况不妙便下楼打车去了医院。待护士固定好输液针头,拿出手机摆拍了个楚楚可怜的照片po上朋友圈,饱含心机地加了个定位。凌晨2点,因为流感盛行输液室还是有不少人。朋友圈没睡的人也不少,15分钟已经有了10个赞,列表里几个在杭州的朋友评论说“你来杭州了?有空一起吃饭啊。”我当然知道“有空吃饭”跟“下次一起”通常代表着“不了了之”,但这种客套还得是配合着演下去,否则就是不近人情。
只有张小茹给我发了消息。
这是一则语音信息,声音平静中带着殷切,语音里传来呼呼的风声,应该是不舍得开空调的司机摇下了车窗。她说她正好在附近,现在过来找我。我感到有些意外,毕竟我们已经有好些年没见过面了。对话框里的聊天记录,也仅有这则语音赤裸裸孤单单地躺在那儿。我把手机放在大腿上,做贼心虚似的单手飞快地打字回复婉拒她的好意。人很奇怪,见惯了流于形式的问候,面对真挚的关怀时竟然会感到手足无措。
张小茹还是来了,一身棉质的绿底白花背心伞裙,黑色浓密的过肩直发,还是一副普通顺从的备胎脸,手上提着两碗生滚粥。她揭开盖子贴心地放在我椅子右边扶手上,她笑说她刚下班还没吃晚餐。我小心翼翼抬起右手撇了上面一层粘着葱花的粥皮送入口中,难为张小茹在这个城市能找到如此地道的粤式生滚粥。
肚子里有了热气,精神也慢慢恢复了起来,我开始打听她这几年过得如何。她说在剧组跑龙套,寥寥数语一笔带过,我也没再问。吊完药水已经凌晨三点多,张小茹把我送回住处,自己打车回去。她说接下来两天也没事,可以带我逛逛。张小茹走后,我洗了个热水澡,因为生病忍着没开空调。我躺在床上,精神抖擞得像在田野里撒欢奔跑的小母鸡,脑子里有马达似的切换着回忆画面。
张小茹是我高中三年最好的朋友,上了大学后便渐渐断了联系。距离并不是所有感情淡了的替罪羊,是我们不愿意承认,其中有一方对这段关系没那么在乎罢了。记得那时候的课间十分钟,我都要跑到楼下最西边的教室找张小茹一起上洗手间。我们一起住校,一起去三楼饭堂吃早餐,去一楼饭堂吃午晚餐。每年冬天,张小茹总是帮我到水房打热水。我也总是隔三差五溜到她寝室,跟她挤一在张床蒙上被子讲悄悄话。我跟她讲我的男友,我的情敌,以及我的梦想。张小茹学习成绩一般,而我几乎不花什么力气也能在前十名稳住。我是家长眼中的机灵小孩,所以张小茹的父母很喜欢我去她家做客,但我其实没怎么想过要带带张小茹。我那时候除了上课只顾得上谈恋爱,张小茹需要配合我说一个个夜不归宿的谎。她是我的金钟罩铁布衫。
张小茹是不早恋的,整个高中她都像我随时待命的侍卫,给我打掩护,帮我出谋划策。她做过最叛逆的事,就是瞒着所有人填了一个外省的志愿。于是大学四年,她在长沙,我在广州。至于后来怎么去了杭州,不得而知。一开始我们还会互通电话,直到后来我身边出现了第二个“张小茹”。
对我来说,侍卫只要好用,就不论是谁了。
再睁开眼发现已经是日上三竿,我是被张小茹叫醒的,打开门时我看见她上半身倚着门说叫了你好久了。她扬了扬手里的菜,说:“走,去我那,做饭给你吃。然后下午我们去逛逛西湖,晚上吃完饭早点回来休息。”
张小茹住在青山路,公寓的名字就叫做青山公寓,离我那不远。她一边掏钥匙拧门锁一边对我说,这栋公寓里住的都是些小演员。因为大家经常外出拍戏,所以有可能三四个人拼租一个一居室。张小茹买了大棚反季节毛竹鲜笋,滚刀切块码在盘子里。咸肉切成两指长一指宽的小块,与新鲜的猪腿肉一起放入冷水锅里开火焯水。竹笋无需汆烫,与肉块一起放入砂锅,小火煨上。我双手插进洗菜盆,轻轻揉搓棕黑色的绍兴梅干菜。我发现碗架旁有只玻璃烟灰缸,可是张小茹并不抽烟。我发现我一点也不了解张小茹,她喜欢吃什么、不喜欢吃什么、喜欢怎样的男生、梦想是什么?一概不知。记忆里她总是安静地听着,对于自己惜字如金,又或者是她知道我根本并不关心她喜欢什么。她也许早就看穿了我的自私和刻薄。
吃过饭后我们打车去了湖滨路,张小茹做的本帮菜有模有样,腌笃鲜汤白味鲜,梅干菜蒸扣肉醇厚咸香。就连食欲不振的我也多吃了半碗饭,坐在后座忍不住打饱嗝。西湖风景区很大,也很美,还能看见松鼠在树梢上窜来窜去。旁边还有雷峰塔,搭公交几个站还能直达灵隐寺。就在我们决定去四季青淘便宜衣服的时候,张小茹接到剧组的电话,需要马上到剧组接个活儿。是什么活儿她没说,也不好撇下我走掉,于是我们一起打了车过去。
影视城门口下车后,走了一段路才到达剧组。立刻有人迎出来向我俩打了招呼,这个人我也认识,是高中屈指一算的帅哥顾一帆。这么一来所有事情都能对得上号了,我记得顾一帆也报的湖南的大学。我看向张小茹,她本能地躲开了我的视线。顾一帆是剧组执行导演,没等我们坐下就叫了她过去说戏。然后张小茹换上了女一号的衣服,走了出来。片场被清走了大部分的人,在场的人都刻意地假装没看见她,她也假装没看见任何人,赤着脚闷声躺在道具床上。我突然明白过来,张小茹是个裸替。
我看见男演员覆在她身上扯开她的衣服,手臂有意无意地在她胸脯上蹭来蹭去。本来这种划水的戏,两三条就能拍好的,硬是拍了七八条。有个女演员一边捧着玻璃碗里切好的西瓜瓤,一边用牙签戳着往顾一帆嘴里喂,两个人的胳膊像浇了蜜似的黏在一起。几个男生在交头接耳,听不见说什么,但看神情就不见得是什么高尚的内容。我看得很难受,从包里掏出烟点上,烟雾熏得眼睛有些发疼。
等我抽完了两支烟,这段戏还是没能过。不知怎地我脑子一热站起来,冲过去拽过男演员的衬衫,伸手就是一个耳光。我气得说不出话来,张小茹赶紧过来拉住我。顾一帆也跑了过来,质问我在做什么。我冲他喊,你他妈给我闭嘴!然后转头向男演员骂道:“演戏和做人你两样都不及格!”
最后张小茹还是坚持把戏拍好了才走,顾一帆给她现结的工资。她身边没一个好东西,也包括我。
我坐在车里,难过得不知道该说什么。反而她安慰我:“别人露脸,我露身体,其实说不上谁更吃亏。世间大多数的工作,不正是帮别人去完成那些别人不愿意做的吗?替身演员不应该是一个让人难过的职业。”
我问她:“那顾一帆呢?值得吗?”
张小茹沉默了一会儿说,感情是没办法选择的,如果可以,那叫交换。
我说张小茹你完全能演一个完整的角色。她摇摇头说,你不懂这一行。剧组选角时,通常我会在第一轮就会被刷下来。在知道你好不好用之前,通常只能判断你好不好看,每个人都会拿着筛子度量你的价值。
当晚张小茹带我去了楼外楼吃饭,她说今天拿的钱比平时多好几倍呢,请你吃一顿好的。从片场出来,她还是这样保持着笑容,仿佛她的温柔永远都挥霍不完。张小茹点了一桌的菜,眼角余光却不停地往放在一边的手机望去。女人的直觉告诉我,她在等谁的消息。她往我碗里夹糖醋排骨和茶香鸡鸡腿,却突然红了眼眶。她低头看着桌沿,像烈日下暴烤过的柳树嫩枝。
她说:“其实如果不是因为你,顾一帆根本不会注意到我。我们是初中同学,初二那会儿我们分到同一个班,我就坐在他的右前方。为了想多看他一眼,经常绕着远路回家,只为了能跟他同走一段路。可就算这样,直到初中毕业,他还是没跟我说过一句话。后来我认识了你,顾一帆和陈阳是好朋友,而你跟陈阳在谈恋爱。而这些,我都从未对你坦白。” 我不知道怎样安慰张小茹,只是说了几句表示理解却无关痛痒的话。我该对她的心有城府生气吗?就算是当时她告诉了我,我难道不会在心里嘲笑她不自量力?
吃完饭后我们在饭店门口分别,我没回民宿,而是去见了顾一帆。晚上十点半,我在青山公寓楼下看着顾一帆拿着一束黄色玫瑰,熟练地找到电梯走了进去。夏天的夜晚还是相当烦闷,我在楼下站立了一会儿,便掏出手机打车回去。洗完澡出来时,我拿起手机刷朋友圈,我看见张小茹发了一张图片。是一束玫瑰在暖光落地灯下的娇媚姿态,配文是“和你平淡似水,才可千杯不醉。”顾一帆在底下评论了两颗红心。
我很快离开了杭州,张小茹送我到萧山机场。在安检口,我用力抱了抱她,拍了拍她瘦瘦的肩膀。看到她幸福的样子,我心里也释怀了不少。
在回程的机舱里,我突然想起以前在电台做的一期节目。“想象一下,如果你现在最好的朋友突然消失了,你会怎么样?”我们可能都有过这样一个朋友,你们一起逃课,一起压马路,安慰对方失恋,一起坐在天台喝酒……那段时间你们什么都可以分享,一起笑一起哭,见过你身边换了又换的恋人。
后来你们疏远了,也许因为学业、工作、婚姻。再后来,你们加了微信也不知道要开口说什么,各自身边又有了新的好友。从此你们分别跟新的好友分享生活,朋友圈里对方合照里越来越多陌生人。你知道她身边已经有了新的人可以互相取暖。
岁月像高山,翻过去了,青春再也不回来。每一份友谊都需要善待,相互的关心和陪伴。我一直认为张小茹跟我做朋友,是我用光环笼罩着她。到最后我才发现,是我用刀子在她身上放血来维持自己丑陋的虚荣感。也许这样根本就称不上友谊。没有人有源源不断的热情和温柔,只是在选择的路口,选择了真心以待。
我很幸运,当我回头时,张小茹还依然留在身边。而我也尝试着去为她做点什么,去弥补这些年不称职的友谊。再一起肩并肩走向未来,友谊地久天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