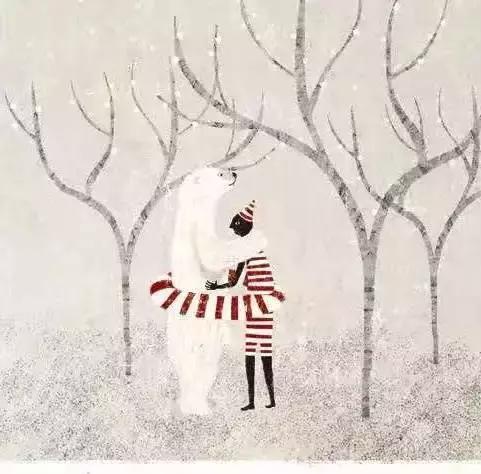有时会觉得自己很奇葩,不像一个正常人。
8月份困在西宁不知道去哪儿时,听客栈的一位朋友说,格尔木值得去,我没做太多的了解,从青海湖回来的第二天就坐火车去了。那是一辆直达拉萨的火车,在车上听着广播想,下一站去西藏好了。
但我在格尔木的两天,因为觉得很多景点拼车太贵,且只够下车拍照的时间,就哪都没去,在客栈里写文章和小城里闲逛。想去西藏,查手机发现,拉萨连续一周都有雨,再加上别人说感冒期间不易进藏,放弃。
到其他地方的火车都没票。我听说格尔木有到敦煌的长途汽车,就乘公交去了汽车站,原来就在客栈的附近。在那里我看到一个叫大柴旦的地方,是西北大环线上的一站,就去那里吧,完全是随机决定的。
客车穿越漫漫荒野,经过察尔汗盐湖,我看到了黑乎乎淤泥般的盐碱地,偶尔看到的白色不是雪花,是盐。接着几个小时看到的全是戈壁、荒野和沙漠。黑乎乎的山,几百公里不见一棵树,也不见村庄。
快到大柴旦时才出现一片绿洲,湖水泛着绿,很是新奇。
大柴旦是方圆百里唯一的行政区,但更像一个普通的小镇。这里没有公交,没有高楼,只有几条简单的街道,一个商业步行街和一所中学。路边很多清真拉面馆和宾馆,绿化带里流淌着人工水,远处全是荒山和戈壁。
我住的是50元一晚的床位,整个客栈只有我一个客人。老板和对面卖凉皮的女孩是闺蜜,她还在旁边开了一家服装店,前后忙活,却没一个员工。见我不想包车去景点,老板说邻居阿姨的山地自行车可以租给我骑。
二十元一天随便骑,不要押金。
我欣然租下,在西北荒野里骑行还是挺有意思的。我去了翡翠湖,十七公里需要一个小时左右。我迎着风在柏油路上飞驰,路边很多化工厂(盐场),除此之外都是荒野,一点庄家都没有。
然后变成了土路,坑坑洼洼,有车驶过会扬起尘土。我骑得十分费力,在野地里撒了泡尿。
骑了很久,我看到小路的尽头是一片湖泊,很多车驶向那里。小路旁长满了野草,泛着黄,与远处的戈壁和蓝天连成一片,挺美的,停车拍照。又骑了一会才看到翡翠湖,在那里聚集了很多人,走近了才发现是一个个盐水湖。
我还是喜欢淡水湖多一些,比如青海湖。朋友说,翡翠湖用无人机航拍挺美的,天空下波光粼粼,像一块块绿宝石。
这时我才发现车子坏了,前胎没气了,明明来的时候刚打好的气。我有种不祥的预感,已经无心看景了,想这十几里路该怎么回去?看到前面有人经营沙地摩托,便问有没有打气筒。
他正在修摩托,抬头看了我一眼,我以为他不会理我,在很多景区,你不买东西,别人是不愿意理你的,他只是淡淡说了一句,你等下,然后招呼同伴骑沙地摩托去别处取来。我想给他点打气费,他挥挥手继续修摩托。
这让我想起在客栈租车时,他们没要押金,没要身份证。我问车子有锁吗?她说,放心,这地方没人会偷车的。所谓民风淳朴便是如此吧。
打气效果不理想,车胎像软柿子一样,硬不起来。肯定是不能骑了,我不能把车子丢在这里,也不能硬骑回去,弄坏别人的车子可不好,就想趁着天亮推回去。我想过要搭车,可周围都是小轿车,没好意思开口问。
手机导航显示需要走三个多小时的路程,预计晚上九点能赶回去吧,按照西北的日落时间,那时天才刚刚黑而已。我便推着原路返回。路上没有一个骑车的人,各种私家车驶过,我一次次地回头张望,希望能搭个皮卡或者小货车回去,一直没遇到。
走了很久才来到那条土路上。我继续回头张望还是没有遇到适合搭的车(可能是我没勇气去问吧)。我抬头看见远方的工厂烟囱和城镇,安慰自己很快就到了。
我闷着头继续往前走,仿佛走了很久,看导航距离却没减少太多。路边哪有什么美景呀,都是沙地和落满灰尘的旱草,对荒野的好奇心随着路的漫长而变得煎熬。
一路上我都在想——该怎么给这个奇葩的经历赋予意义呢?
这个世界上,恐怕只有我这样奇葩的人才这样做吧。别人可能会直接丢掉车,大不了赔些钱,或者花钱叫个拖车什么的,或者会去搭车,管它私家车还是什么车,打开后备箱总能塞进去吧,脸皮厚一些就行。
我习惯了用最笨拙和低效的方式处理一些事情,就像在城市里,能走路就不想坐车。我想到了很多,我的小镇,我的家庭,我的父亲,我的性格,以及我在北京的生活。有些成长的痕迹始终伴随着你,甚至深入骨髓。
我在第一本书里写了一篇《父亲的行李包》,其中几段写道:
儿子提着父亲的行李包走在大街上,没走多远,行李包的提手就断了,“这包不能再用了”儿子抱怨,他想回租房把自己的包给父亲换上,被父亲拉住,说不用,然后父亲就捡起脚下的一根白色的塑料绳子要系上。
儿子站在那里有点生气,那个行李包此刻如此碍眼。
父亲还是固执地说没事,“我自己拿着就行,你别管了。”
当无法说服父亲后,儿子只好把抱起行李包往前走,那根白色的绳子让他很不舒服,于是便扯了下来,却被父亲捡起,放在了口袋里。他就这样抱着父亲的行李包,在别人异样的目光下,挤公交、坐地铁。也许,他所谓的异样目光,不是来自别人,而是他内心深处的自卑感……
那个“儿子”就是我。在我的身上有着太多父辈的痕迹。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我第一次去麦当劳、肯德基是在二十多岁;二十五六岁才第一次进影院,第一次看3D电影,去晚了,满座位找眼镜,以为会放在那里,却不小心摸到别人的鞋上。他说找什么呢,我说3D眼镜,他说眼镜在门口领呀。
而那时我已经在北京生活了几年。
然后我又想起了很多事情——睡过好几天 的火车站、熬过深夜一个人的高铁站,还躺过一晚的xxx广场……原来都那么得相似。
我做过很多看上去奇葩的事情,它们都带着成长留下的痕迹。如果非要寻找意义的话,那这应是我作为小镇青年的人生体验吧,更是我写作的真实素材。
睡火车站那次,算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主动的逃离。济南退学后,我对未来十分迷茫,为了不成为一个农民,为了摆脱命运的束缚,我深夜偷偷逃出了那个村庄,坐汽车去隔壁城市,再坐火车跑到了苏州。
我没有钱,没有被褥,在火车站售票厅的地板上睡了好几天,想着该如何在这里活下去。如果在一座城市的深夜无家可归,无处可去,也不想去住酒店,更不在乎体面,火车站是最好的去处。
那里有很多熬夜等车的人,流浪者,拾荒者,不愿回家的中学生,闲逛的恋人,还有失眠夜行者。没人觉得你怪异,哪怕你睡在广场的空地上,都没什么。到后来养成了习惯,遇到深夜无法回家时,我常常去火车站去凑合一夜,天亮再回去。
当然,现在的高铁站已经不具备这种功能了,有些城市的高铁站建在荒芜人烟的郊外,到了晚上没什么车,车站关了,商店关了,保安也睡觉了,两个人影都没有。因为我待过一晚,所以才深有体会,那天晚上只有我和一只流浪猫没有离开。(《猫的流浪者》中有写)
睡xxx这事,也挺酷的。那天东北的读者来北京培训,顺便约我见一面。我从燕郊倒了好几次车就去了,逛逛后海,吃吃饭,又到西单和xxx溜达一圈,已经是晚上十点,那时通往燕郊的班车早没了。
我不想打车,也没这个习惯。
送走东北朋友,想到一位重庆的朋友曾说,她有一个心愿,就是来冬天的北京看升旗。我在北京这么多年了,都没看过一次。于是我就以想看升旗的名义在xxx睡一夜。
这地方应该去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之 一了。
一点都不孤单,广场上有很多人在熬夜看升旗,三五成群,而且装备齐全,或坐着聊天或睡成一片。我没有睡垫,也没买,直接枕着背包躺在了广场上,石砖上残留白天的温度,十分惬意,除了满地的蟑螂到处爬。
断断续续睡了一会儿,到天快亮的时候,更多的人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一样,几千,几万,甚至十万人我都相信。黑压压的一片,挤满了各个位置,都等待着升旗的那刻。
人真的太多了,只能看天空和旗杆了。
很快,奏乐和升旗结束,我看了看人海的背影,就走了,去坐最早的地铁去国贸倒车。可能对我来说,只是想熬过这一夜吧。
你看,多奇葩,熬了一夜都没多看几分钟广场。
西北的天渐渐黑了,我终于走出了翡翠湖的土路,来到了宽阔的柏油路上,走过很多个白色的工厂,远处城镇的上空笼罩着黄色的光。导航显示,还要走一个小时。
黑暗中,我终于看到有皮卡和三轮车飞快驶过,还没来得及犹豫要不要拦下搭车,已经远去了。我推着坏掉的自行车继续走,路灯很多都没亮,在黑夜里沿着路边前行,但能看到远方的光。
回到客栈的时候,已经快十点了,知道我是一路推回来了,惊呆了客栈老板和卖凉皮的姑娘。老板开玩笑说,你直接把她的车子丢了好了,旁边的车主阿姨嘿嘿地笑,很多钱买的呢,并对我说:“你应该搭个有车兜的车回来,这里人都很好说话的。 ”
然后,阿姨把车子放在路边,和两位姑娘像孩子般玩起了踢脚游戏。
我洗洗就睡了,居然一点都不疲惫。后来我想,下次一定要学会搭车呀,人总是要打开自己的,就像几天后,我在兰州第一次坐了飞机,原来经济舱打折时挺便宜的,原来我并不会晕机,也没有高空恐惧。
一切都是那么的平常,自然。
而我的家人,这辈子还没坐过飞机,我的奶奶、我的母亲,还从未走出菏泽之外的城市。你要尊重你的来处,尊重你的自卑和土气,这个世界有很多不同,但一切又不是那么绝对,去遇见不同的自己吧。
我依然在路上,在下一站等你,听你讲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