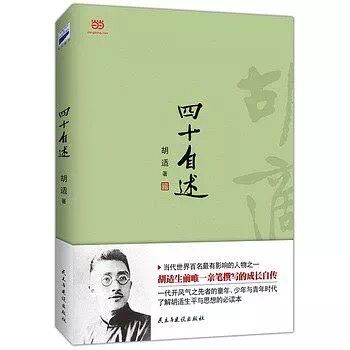2019年2月24日 星期日 天气晴
民国是一个群星璀璨,大师辈出的时代,胡适就是里面一颗闪亮的星。他是现代中国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和哲学家,同时也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他一生共获得过35个博士学位,其中1个为他攻读的哲学博士,其他34个为多个大学的名誉博士,这与他一直担任驻美大使有关,不过他本人也算学富五车。
《四十自述》是他撰写的一本自传。他一直很提倡撰写自传,因为他觉得中国最缺乏传记文学。而他原本想将自己四十年的生活分为留学以前、留学期间、归国以后三个阶段,结果因为种种原因只完成了第一阶段的六章。他谦虚地把自己的传记比作为抛砖引玉里的那块“砖”,他希望自己那些对于少年时代琐碎的描叙,能够引发那些在社会上做出过一番事业的人能够记载他们的生活,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
传记文学是让我们能够快速了解一个人的思想,一个时代思想的文学体裁,不管撰写者生在哪个年代,书本的翻阅间他便鲜活地跃然纸上。通过阅读,就等于同他们成为了朋友,近距离地感受他们的人生智慧,以他们为旗帜,避免走弯路,让这份智慧之光始终照耀在自己前进的路上。
当我展开这本《四十自述》时,仿佛能看到胡适如朋友一般笑盈盈地在我对面坐下,准备将他的故事向我娓娓道来。
我的朋友(请允许我这么称呼)原名嗣靡,学堂名为胡洪,徽州绩溪人,曾经在上海澄衷学堂读书。那时严复翻译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译本,一问世就引起了社会的巨大反响,“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风行一时。恰逢他想起个表字,他二哥就从这八个字里挑选了一个“适”字,又因着几个哥哥的字都是什么之,就用了“适之”两字,后来发表文章常用“胡适”作笔名,直到去美国留学,就正式使用了“胡适”这个名字。
他的自述是从他母亲的订婚开始的。他的母亲与父亲年龄悬殊,相差三十岁;身份悬殊,一个是做官的,一个是农家女;文化教育悬殊,一个是学者,一个是目不识丁。原本貌似毫无交集的两个人却因缘结合在了一起,由此十七岁的母亲嫁给他父亲做了填房,成了一个大家庭里的家长。
我们常常都说一个人的性格以及成就都离不开他的原生家庭。
朋友的外祖父虽然家庭贫穷,但是性格坚毅,吃苦耐劳,从而造就了他母亲的容忍禀赋。而正是这种禀赋使得她在接下去的二十多年里在这个没有家主的大家庭里支撑着。
朋友早慧,父亲在世时每天用红筏方块教他认字,三岁不到,已经识得八百字,父亲过世时才三岁零八个月。
父亲过世后,母亲就成了慈母兼任严父。对于他不仅仅有读书的要求,更是教会了他做人的道理。
母亲家教甚为严格,但是她从来不会在别人面前骂朋友一句,打他一下,只会对他望一眼,朋友看见母亲严厉眼光就吓住了。母亲总是在天还没有亮就开始把他唤醒进行晨训。会对他说前一天做错了什么事,说错了什么话,要他认错。把她对父亲所知道的一切告诉他,希望他将来能踏上父亲的脚步,在他母亲眼里父亲是最善良最伟大的人。试想现在你看到的那些熊孩子的家长,要么是任其所为,借口孩子还小;要么就在公共场合打骂孩子,两厢一比较,孰高孰低境界差距立即显现。
朋友的母亲用善良和容忍教会他“世间最可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世界上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所以,朋友他待人接物和气得令人如沐春风,他一生中总是笑容满面的。他曾经在《容忍与自由》中写道:“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还要重要”。
有一次朋友因为说话轻薄被母亲罚跪,跪着哭泣时用手擦眼泪,眼睛进了细菌,得了一年多眼病总也治不好,母亲又悔又急,听说用舌头舔可以治好,便真的用舌头舔朋友的眼睛。
母亲同时也是他的严师。教导他一定要好好勤敏学习,唯有行为好,学业科考成功,才能使她们二老增光。朋友三岁多时就进入了家乡学堂,每天上课平均时间为十二个小时,一直在学堂里读了九年。母亲从不让他与一般儿童游戏,更是多倍于一般学生学费给老师,让他们逐字教学,一定要解释清楚每字每句。死板的文言文字便转化成了白话,上课变得有趣生动,学习自然就比其他同学自主性强多了,这大概也是之后为白话文的推行潜移默化奠定了基础。
朋友的父亲是一个经学家,遵循的是程朱理学思想,他最初的启蒙,就是父亲编写的《原学》和《学为人诗》,当时因为年纪小,虽然熟背了并不了解说的是什么,但是他总是父亲的儿子,父亲是遗留了理学家风的,有趣的是家里的那些女眷却是极信神佛的。自后也是学习《孝经》、《小学》、四书五经,接受传统儒家思想的教育。在十一二岁时读了范缜的《神灭论》和司马光的《资治通签》,“因果论”和“形灭神散”的观点让他的思想有了极大的转变,成为了无神论者。
我们看过的书,从中懂得的知识和道理可能不是立即体现它的作用,但是它已经储备在你大脑中,某一天需要时你就能随时提取。朋友曾说:“读书要博,中国人所谓开卷有益,原也是这个道理,博不仅仅为了参考,也是为了做人。”读书能够帮助你审视自己,从而更好地走余下的路,路有宽窄,选择在人。
朋友在十二岁时,带着慈母的关爱,一点点用功的习惯,和一点点爱怀疑的头脑去了上海。他先后在四个学堂读书,第一个学堂为梅溪学堂,课程只有国文、算学和英文,老师授课使用的是上海话,分班标准为国文程度。最初被分到程度较低的五班,读了一个多月后已经勉强会说上海话,因为纠正了老师的典故引用,被老师赏识连升四班,最终又凭借自己的努力进入了头班。那时他开始读梁启超一派人的著作,也因为一些观点的变化离开了学校。
第二所澄衷学堂课程更加多元化,除了国文、英文和算学,还有物理、化学、博物图画等课程。他离开第一所学堂时英文和算学并不好,于是常常在宿舍熄灯后起来演习算学问题,自己买了代数书补习,那时因为睡眠不足,两只耳朵有一阵子全聋,而后才渐渐康复。他年年考第一,一年连升四班。在此期间,他深受梁启超的影响,特别是对于“新民”的论调,要改造中国的民族,要把老大的病夫民族改造成一个新鲜活泼的民族。朋友总说梁先生的文字是带有热度的,笔锋常带情感,每每读完,总是激发起他满腔热血,同时也因为梁先生对西方民族美德的赞誉而看了更多西方文学的书。他的英文和算学基础都是在那里打下的。那时学校管理严格,对于考试要求也高,学校办事人能了解到每个学生的功课和品行。
从以上两个学堂的读书经历,我们不仅能看到朋友他自我读书十分刻苦,学校对于他的影响也是深远的。韩愈说:“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学习成绩固然重要,但是人的格局,人生观的建立,老师是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
第三所学堂中国公堂,是由日本回国的留学生创办的,学校的教职员和学生中有不少革命党人,是上海第一家用普通话授课的学校。朋友又学会了普通话,还跟着四川同学学了一口四川话。当时大多数人都被要求剪去小辫,朋友却被大家认为将来是要做学问的,大家都很爱护他,所以也不劝他参加革命。
同寝室的同学办了一个白话的旬报,叫做《竞业旬报》,大家感觉“普通国语”是有需要的,能够统一中国的语言,而朋友也开始在那个报纸上投了第一篇白话文。朋友觉得自己文字的长处就是明白清楚,短处则是浅显,他觉得做文字必须要叫人懂得,那是他的宗旨。这不由让人想起了白居易,写的是诗要让妇孺都能通晓,朋友也是读过不少白居易诗的。
年少时我们读过的书就像一颗种子埋在土壤里,这些种子有了一定的条件作用后便会生根发芽。几十期的《竞业旬报》,给了朋友一个发表思想和整理思想的机会,还给了他一年多白话文的训练。七八年后,白话文这件工具使他能够在中国文学革命运动里做了一个开路的工人。
在中国公学学习了三年后,学堂掀起了一次大风潮,很多学生退学出来,又自行成立了一个中国新公学,朋友也进入了新公学读书。因为家庭经济每况愈下,虽然年仅十七岁,还是在新学堂里担任了英文老师一职。因为肯负责任,肯下苦功去预备功课,所以在一年的教学中还教出几位杰出的学生。他那时虽不大能说英国话,却喜欢分析文法的结构,尤其喜欢拿中国文法来作比较,非得把字字句句的文法都弄得清清楚楚为止。
新公堂最终由于经费拮据解散了,那时前途茫茫,不敢回家,跟着一帮子失意的革命党朋友堕落了,整天赌博喝酒,当然因为没钱,赌博也只是谁输了请客吃饭。有一次喝得酩酊大醉,被抓到巡捕房,次日回家照镜子看见一身惨相的自己,想起“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诗句,心里万分懊丧,觉得对不起慈母,至此精神上有了重大转机,决定去考留美官费。
人不怕走错路,怕就怕走错了还不能悬崖勒马,所以人需要常常审视自己,才能将自己从歧路拉回正道。
这时候朋友的同学和族叔给了他经济上的支援,筹了他北上的路费,他先精心闭门读书两个月。到了北京,又在二哥朋友的厚待下借住在女师大校舍里学习了一个月,更得指点读旧书,于是从《十三经注疏》开始读了汉儒的经学。
朋友之间的交往不在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有些人可能不会在你身边吹捧你,顺应你,但是在你有难的时候他会第一个来帮助你,危难之中才能见真情。
正因为朋友他自己面临过经济的困顿,之后只要有人向他寻求帮助,他就慷慨解囊,并且不造成别人的思想负担。林语堂在美国哈佛留学时学费短了,写信给朋友求助,朋友一下子汇了一千美元,还故意说是工资预支,等学成后要去北大任教。哈佛毕业后,林语堂又去德国莱比锡大学读书,又跟朋友预支了一千美元。等他归国后如约到北大任教,找到校长致谢时才知道学校并没有给他寄钱,而是朋友个人为他出资的。朋友还曾经资助过沈从文、季羡林、李敖等一众才子。狂傲的李敖谁都敢骂,唯有说到朋友时赞誉他的人格高人一等。
他的朋友上至总统、主席,下至企枱、司厨、贩夫、走卒、担菜、卖浆……“我的朋友胡适之”曾经是许多人的口头禅,无论相识与否,文人雅士、社会贤达多引以为荣。他的名望之高、人缘之好、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四十自述》前五章分别是九年的家乡教育、从拜神到无神、在上海(一)、(二)、我怎样到外国去。而第六章被命名为“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他何谓要称被逼呢?
那时他归属于清华在美国留学生,在中国的留学生成立了一个“文学科学研究院”,成立当年把“中国文学的问题”作为论题,而他的题目是《如何可使我国文言易于教授》,起初思考的还是如何改良文言文的教授方法,如何使汉文容易教授。他共提出了四个方法:第一条是注重讲解古书,这是他幼年学习古文最有力的方法;第二条是主张字源学;第三条是讲求文法;第四条是要讲标点符号。
那年夏天他开始认为“白话是活文字,古文是半死的文字”。同学中常常讨论中国文学的问题,继而转移到中国文字问题。有一个守旧的同学不承认中国古文是半死或者全死的文字。因为同学的反驳,朋友不能不仔细思量自己的立场,在这个过程中倒是让他渐渐更坚持了自己的看法,于是中国文字必须要有一场革命的想法在心里产生。
起初“文学革命”的口号只是乱谈出来的,而后有了更深的觉悟,深深觉得“中国今日需要的文字革命就是用白话替代古文的革命,是用活的工具替代死的工具的革命”。坚定自己的想法后,他尝试着去说服同学,并且说有了具体的方案,就是用白话文作文,作诗,作戏曲。
后来由于同学发生了一个事故,双方诗文往来,朋友用白话文作诗,同学却不同意他的观点,认为小说能用白话,诗文不行,彼此来来回回写了多次对论。因为同学的反对,让他更坚定了实验白话诗的决心。
爱因斯坦说过:“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莫过于有几个头脑和心地都很正直的朋友。”同学间对于各自见解不同的辩论力争正是彼此友谊的体现,能有如此志同道合的朋友也是人生一大幸事啊!所以对同学他从来只有感激,没有怨言。
在各种逼迫下,他决定给自己写的白话诗出一个集子,就叫《尝试集》。他深信实验主义思想“一切学理都只是一种假设,必须要证实了才可算是真理”。
之后,他写信给陈独秀,提出了八个“文学革命”的条件,不到一个月,又写一篇《文学改良刍议》。八个条件为:须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陈独秀是赞成这个观点的,于是得了一个坚强的革命家做宣传者、推行者,不久就成就了一个有力的大运动了。
这八个条件如今看来也是具有现实意义,值得文学创作中借鉴的。现在那些所谓的鸡汤文都是些无病呻吟的毒鸡汤、励志文不少都是造假的!人还是脚踏实地,写点实事求是的东西为好。
此时朋友的自述已经结束了,合上书,我仿佛还能看见他那张笑眯眯的脸。一个伟大人物的诞生从来不是偶然的,自小家庭的教育是基础,后天的自身努力则是成功的直接因素。他的父母不仅教导他好好读书也教育他好好做人,而他始终都是一个认真、勤勉且追求真理的人,对于自己的思想上更是不断有新的追求与完善,而他交往的一干朋友对他的帮助也是让他受益无穷的。他对朋友的批评从不生气,认为如果他的朋友能从中有所收获,他也是满意的。
我还知道朋友另外一件事,就是他对妻子的不离不弃,作为留美归国博士,没有放弃母亲为他定的十五年的小脚妻子。他受的家教和多年教育让他明白:不能伤害一个等待自己多年,又用心照顾自己母亲的人。这位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就这样一脚踏进了旧式婚姻,娶了一位小脚夫人,这被称为民国“七大奇事之一”。蒋公是这样评价他的:新文化中的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今天是他逝世五十七年的纪念日,像这样一位宽厚的朋友,伟大的思想者,必定会在历史的长河里烁烁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