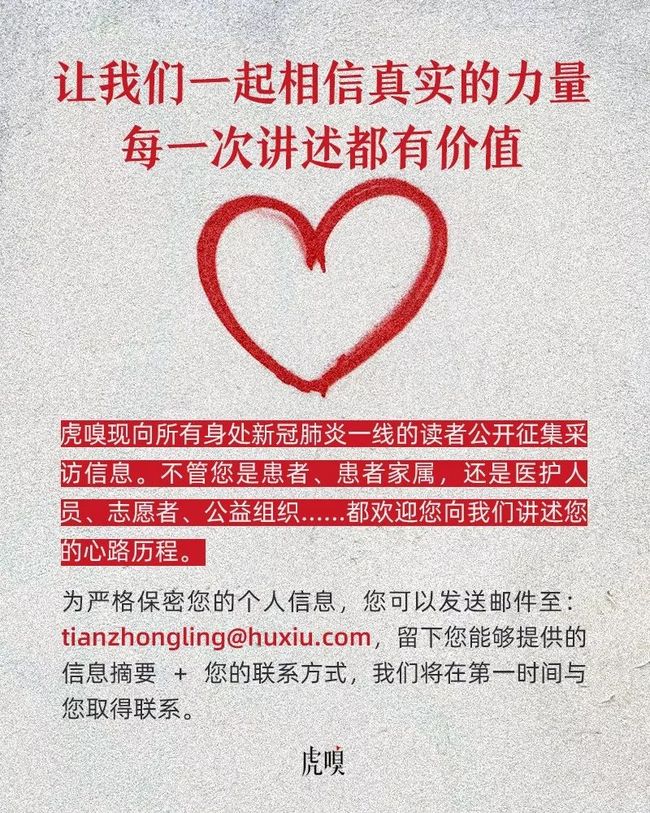作者|刘晨,常芳菲,胡展嘉,六九,南陆,孙鸣远,宇多田,曾欢,庄伟宏Odin,昭晰
图片|虎嗅
在一场引发全球关注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阴影笼罩下,我们迎来了庚子鼠年。
这个春节,因为疫情,让我们有了特别的牵挂,我们牵挂武汉,牵挂湖北,牵挂在抗疫第一线的每一个医护人员。这个春节,我们放弃了拜年、串亲,我们自觉戴上了口罩,我们让父母也戴上了口罩。这个春节,我们为某些地方政府不作为、晚作为痛心疾首,我们为湖北红十字会不发放物资而出离愤怒,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感人的个体的故事。
我们心系武汉和湖北的同时,也心系广袤大地上其他省市县乡村的疫情——他们是怎么过这个春节的,他们是重视还是轻视了这次的疫情,他们对疫情的讨论又是怎样的,他们又是怎么自我防护的?
于是,春节回乡、散布在全国各地大江南北的虎嗅编辑们,成为撒在中国地图上的一个个镜头,记录着每天暴增的疫情病例冰冷数字下的一个个散落的温情。
我们走在祖国的大地上,在这个疫情笼罩的春节,我们既关心着身边的大事小情,也心系着武汉和湖北,我们心连心。
我们相信,这是我们唯一力所能及的。
我们相信,我们终将打赢这场抗疫战。
我们相信,我们很快将在这个春天里相见。
我们相信,“你的心并不是粗砺荒漠的一片,那光明的一隅,会永远充满了温情地留给世上无助的弱者。”
武汉加油!中国加油!
以下内容按作者姓氏(包括笔名、化名)字母顺序排列,但我们想把目前正在湖北孝感前线抗疫的同事刘晨放在第一个——
每咳嗽一次,我都会自我怀疑一次
文|刘晨,湖北孝感
直到现在,每咳嗽一次,我都会自我怀疑一次。
1月20日中午,我从汉口站下了车。出于前期在北京接受的讯息以及对此次疫情的担心,回武汉的全程,我都没有摘下口罩。但彼时的车厢里,戴口罩的人数不足30%,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列车快驶到汉口站了,才将包内的口罩拿出来。从汉口站出来,我强烈的感受是,如网上所说,全中国人都在担心武汉,而武汉人似乎还有一些不以为然。汉口站的广场至少有一半人依然没有戴上口罩,出租车司机也没有。
当天下午我约了大学室友见面,她从青山过来,我提醒她带好口罩出门,她给我的回答是:我十分坦然地出了门。
当天,我离开武汉的家,回到了孝感老家。
回到孝感的第二天,钟南山院士说新冠病毒确认有人传人现象的视频就开始广泛传播,早上我在家附近的药店开了点中药,那个时候就是疯抢口罩的开始。
那时的我还随时出门,也会忘戴口罩。随着各种朋友圈关于此次事件的传播,各种真假虚实信息漫天飞的时候,我开始越来越关注自己和家人的状态,叮嘱他们出门戴好口罩。
拿完中药回到家后直到今天,我一共出过两次门。我们小区据说已经出现了2例确诊病例,武汉的家旁边市场也出现了确诊案例,感觉疫情越来越靠近的时刻,自己也会变得揪心起来。
小区5天前开始严格限制出入,进出测体温,4天前不让车驶出了,前天(1月31日)接到通知,整个市区的菜场关闭,全市只留一两个地方用于采购生活所需物资。
不过,最难过的是,这两天看到的新闻说很多人国内国外帮忙募集的物资不知去向的时候,看到武汉非四大医院做护士的朋友防护服的时候——他们在朋友圈说自己的防护服还不如寿衣,并且医院下令让他们删除朋友圈——是真的心疼,且无可奈何。对于红十字会,我们除了愤怒也不知道能表达什么了。
大家正常对武汉人、武汉外来车辆做例行检查,我个人认为都是应该的,我们看到一些可能有点歧视意味的段子,偶尔自己也会转发。
但我不太能理解那些在武汉封城前连夜赶着跑出武汉的那批人,尤其是发着烧还吃退烧药躲避检查、有疑似症状的人,对这批人我其实是有一点点谴责态度的,起码你要保证自己是健康的不是嘛。
目前我每天还会偶有咳嗽,每咳一声,我爸就会跑进房里来,给我递杯水,然后说:你这搞得蛮吓人。我偶尔也会担心自己是不是真的有什么,但希望自己平安吧。
我想回北京,想回到虎嗅大家庭,但现实不允许。我自己的乐观估计是3月份,但目前这种情况,感觉有点悬,我哥昨天嘲笑我说5月能回都算好的。
让人回想起17年前的北京
文|常芳菲,北京
不会有人想到17年后,北京街头人与人之间又开始自觉保持3米以上的距离。快递员、外卖员一律不许进入小区,街道办的志愿者坐在马路牙子上,戴着红袖箍,手里拿着登记表,紧紧盯着每个拖着行李、满面倦容的人。
17年前,非典爆发的时刻,我正在升初中的当口,对一个小学毕业生来说,空中课堂的内容可听可不听,没作业可领,升学考试也只考语数外,倍感轻松。唯一令我感到不安的时刻,是听说小区里有一家三口同时感染了SARS,被送到小汤山医院隔离,几天之后,就听说“人都没了”。
若干年后,我在书里看到了这场战役的残酷:
那你们怎么区分清洁区和污染区?朱继红沉默了一会儿,慢慢举起手,在胸口指了一下:“在这儿。”
17年之后,肺炎形势严峻的信号断续从各种社交媒体、外媒上发出,而官方辟谣的声明掷地有声、紧随其后。真正让普通老百姓重视起来的,仍然是钟南山接受央视采访中,明确会“人传人”的信息。一夜之间,人人都戴上了口罩。
早就习惯了北京一过年就变作空城,今年尤为萧索。最初的几天,雾霾严重,天一黑,整个城市笼罩在不可见的浓雾中。所有大型商超都缩短了营业时间,只留一个门出入。上午10点开门,就有老年人排队等在门口抢购蔬菜。超市不得不在一进门的地方就贴上通知,上面写着:本店蔬菜水果供应充足。
但这依然不能阻挡大家囤货的热情。便民菜场里,大白菜已经接近5元一斤,也就是说一棵白菜很可能超过30元,依然供不应求。
饭店是相反的一番景象。我走到街角的涮肉馆,服务员站在五菱宏光后面,卖蔬菜和水果,价钱只要市场的一半。突然停业,他们说只能尽量止损。
同样被抢购一空的还有各种消杀用品,从75%医用酒精到84消毒液、免洗凝露、滴露都被卖空。
大年三十,我走到社区的药店想要买医用酒精,店员立刻拿出售罄的通知,跟我说:“这才来买,心真大。”不死心又去了超市,刚走到生活用品区,身后的阿姨一把推开我,一个箭步冲上前去,然后和我一起面对着空荡荡的货架。讪讪地自言自语:哦,卖没了啊。
北京确诊人数几乎每四到五小时就会滚动更新一次。焦虑情绪和感染人数一样,不断增长。大年初二的时候,有一份确诊人员所在的小区名单在各个微信群流传,其中包括我家附近的一个社区。我第一时间询问了保安、住户,都说没有人被带走隔离,也不会封闭小区。
一个在三甲医院当护士的姐姐,已经取消了春节休假。医院辟出了房间用作院前体温筛查,重新开放发热门诊。因为不在定点医院的名单上,家人为她松了一口气。但如果感染人数增多,他们随时可能作为后备医院启用。“这话你就别告诉我妈。”她说。
街边依然挂着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标语。往年的除夕和初五,多少能听到几声爆竹响,今年却一声都没有听到。
而这个年,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开端,就这样安静地过去了。
我爸妈比我还重视这场疫情
文|胡展嘉,天津
1月23日,买了从北京南站回天津的动车,半小时后,刚到天津南站,就看到我爸我妈两人戴着N95口罩站在车站外,全副武装。
当时车站还有很多人没有戴口罩,其实我当时也没意识到情况会那么严重,我对象开车送我去北京南站时,口罩都没戴,我也是临走前一天才买了一副3M口罩(现在想想,略微有些后怕)。
在路上,我爸又去老百姓大药房买了9个N95,当时价格已经是19元1个,接着又去菜市场买了一大堆青菜,说接下来几天可能没办法出门,菜市场也会关门,就靠这些过冬了。
大年初二,因为我们家人、亲戚都没去过武汉,也没有发热、发烧病例,所以我爸早上5点多就开始起来捣鼓,做了一大桌子菜,准备宴请亲戚、朋友,结果他们陆陆续续打电话、发微信说,今年就不要聚了,看到新闻说有好几起聚集性病例,保险起见,就都没有来。
我爸做的菜,蒸碗,这只是部分,还有很多.……
春节期间,我家电视机基本固定在央视13套新闻频道,晚上六点半就调到湖北卫视,实时关注着武汉疫情的最新进展;在饭桌上,家人讨论的也是新型冠状病毒,新增多少例了?死亡人数多少了?有没有出来防疫措施……每天面对的都是这些信息,搞得我也有点儿恐慌。
回想起2003年SARS期间,就记得我妈囤了很多无碘盐,家里每天一股醋熏的味道,当时年纪还小,面对这一切更多是好奇,还为延迟开学沾沾自喜。17年过去了,再次经历类似的事情,作为亲历者,虽然不在湖北,不在一线,但仍然会觉得离死亡很近,感受到生命的脆弱,以及面对逝去、消亡的无力感。
在全世界被疫情阴霾笼罩的时候,我又重温了不知看了几遍的《伪装者》,最后大结局,明楼在天台上给明台说的话依然让人动容:我们都在黑暗里摸索,前方的道路越黑暗,我们内心就越渴望光明。
最后喊个口号,振奋一下人心吧:武汉加油!中国加油!世界加油!
冰天雪地里,很多东西都在消融
文|六九,黑龙江哈尔滨
我到家的时候,我妈问我有没有口罩,掏出来一堆口罩塞给我。这些都是雾霾天她单位下发的保障品,所以我比较庆幸自己在这个时期不用费口舌嘱咐家里人戴口罩。
受气候影响,东北人春节聚会基本都是由一个室内到另一个室内。即使这样,路上的行人依然少了很多。
东北人有家里囤冬储白菜的习惯,虽然我家很多年不囤了,不过面对本次疫情依然不用太为食材发愁,阳台是天然冰箱,可以存下很多吃的。
家庭、朋友聚会取消,除了饭店以外,遭受毁灭性打击的恐怕是东北的洗浴行业,毕竟泡在池子里太利于病毒传播了。
前年开始,哈尔滨市内春节期间禁止燃放烟花,去年除夕一直都有零星的炮声,今年是彻底安静了。前几天好像有一篇论点是“因为烟花爆竹被禁了,所以有不明病毒引发传染病的流行”的文章很火,
还好微信删得快,不然支援武汉的可能就是烟花爆竹了。
我爸身体不好,一直在家待着不太出门。春节期间突然发热,事后证明只是普通感冒。家里人如临大敌,频繁给他测量体温,我爸不许我进入他的房间,我妈每次给他测完体温都很紧张地过来问我怎么办,果然,恐惧是有它的土壤的。
因为没怎么出门,所以也没拍什么照片,回到北京以后倒是在路上拍了一些:
路边有很多摆摊买蔬菜的,一问大多都是饭店老板,春节之前他们会囤一波食材,以备朋友家庭聚餐、年夜饭使用。疫情之下他们不得不卖卖食材来减少损失,市民又有买菜需求,大受欢迎。
上图中远远的街边还插着家门口公园“新春文化节”的宣传小旗。我离开北京的时候这个文化节还在搭建中,回去时活动已经主动取消了。红火的店面和无人的街道的错位很有科幻感,仿佛前一秒这里还有人在干活,下一秒就都消失了,烤串都来不及收。
我走了这条公园的路无数次,从来没有注意到过有科比的宣传物料堆在路边。四五个堆在那里,好像什么都还没发生。
与口罩和电视相伴的春节
文|南陆,四川成都
在从北京回成都的路上,我们一直念叨着要买个口罩,但是一再错过。
出发的前一天下午,我才从公司开年会的地方返回北京,第一件事是把家里的猫送去寄养中心,然后回来打包收拾行李。心里有个念想“需要买几个口罩”,但是潜意识里,这又不是最紧急的事情。那时根据舆论传播的信息,疫情在武汉很严重,北京毕竟远离武汉。这时是1月19日。
第二天一早出发,整个人都昏昏沉沉,到了登机口还在打瞌睡。后来我想起来,航站楼的便利店应该是有卖口罩的,可是实在懒得找。下午到达成都,一路上也没有看见几个人戴口罩。20日晚,家附近的中心公园依旧热闹非凡。
不过,就在20日~21日的24小时里,关于疫情的最新进展越来越多,情况也越来越严重。即便如此,家里的老人也泰然自若。21日晚,岳母不顾全家人的反对,坚持要带小朋友出去饭后散步,小朋友倒是很高兴,把中心公园的滑梯都滑了一遍,因为没有多少人和他抢了。
一锤定音的时刻来了。伴随着疫情的发展越来越严重,成都市当地媒体也开始劝告市民在家过年,连大熊猫基地都决定关门谢客了。22日居委会前来家访,听说我们来自北京,做个登记离开了。家人终于达成共识,除了下楼倒垃圾,基本不再出门,就在家过年。23日武汉封城的消息,让家里老人也接受了现在大自然比家里更危险的事实。
留守在家并未影响家宴的丰盛,附近的永辉超市提供到家服务,中间叫了两次配送到家,除了蔬菜还要了一大叠口罩。配送速度很快,但是有一次配送小哥没有戴口罩。后来听说,小区根据成都市规定,在原有垃圾收集站(点)增了设专门垃圾收集容器,用于收集废弃口罩。进入小区的外来人员会将一次性口罩即时丢弃。
小区内设置的口罩回收点
如果说这一次疫情和非典有什么区别,那就是非典时外卖还没有出生,移动互联网也没有今天这样发达,不会一人一部手机追剧。但是疫情也让开机率连年下降的电视行业找回来一些尊严。家里的电视几乎是整天开着。一家人看着电视里热热闹闹的春节晚会,才感觉找回一些新年的气氛。唯一不和谐的是,晚上会听到大街上有救护车拉着警笛声,呼啸而过。
硬核河南的真相
文|孙鸣远,河南许昌
今年“回家过年”可谓是魔幻旅程。
在即将乘车回家过年之时,收到不久前一起吃饭的朋友发来“噩耗”——他前一阵见过的朋友去过武汉且已经发烧了。消息传来之时是凌晨3点,辗转反侧几个小时后,想法由一开始的“没啥事,这种概率不会发生在我身上”,变成了“万一不幸传染了病毒,回家过年会害了亲戚朋友”。
于是次日一早告诉家人暂不回家,等那位去过武汉的朋友复诊结果出来后再做决定。
还好,大年三十当天复诊消息出来了,确定只是“普通感冒”。随后立即驱车900公里,在春晚即将开始前一刻赶到了家。当我一边跟父母讲述着此次疫情的严重性时,手机弹出的祝福信息中却夹杂着很多不熟悉的头像——
“你们河南真厉害!”
“你们河南太硬核了!”
“我都想搬到河南住了。”
……
好多朋友纷纷发来了“贺电”,夸赞河南此次疫情做出的快速有效的手段。其实当时我不怎么了解是什么情况,只是在社交媒体中零零碎碎看到了一些关于河南此次的“雷厉风行”和“无情”,不过总觉得似乎有些夸张,应该实际情况不至于此。
然而当我真正走上街头时,才发现网友们所言非虚。
在城市里,小区几乎都只保留一个出入口,由多位保安以及居委会人员把守,登记在册的人员可以自由出入,但每次都需要测量体温和记录,外部人员不得入内;车辆管控更是严格,外部车辆不得进入,小区内原有车辆出入也会严格登记。即便是规模较小的小区,也会有人在门口严格把控。
而对于周边的村庄来说,就更夸张了。
每个村头都用拖拉机或者汽车堵一半的路,另一半摆上桌子,对出入人员严格把控。所有车辆不得自由出入,外部进不来,里面出不去,人员的往来也需要自己登记和测体温,一般来说如果不是村中长住人口,是不可能进去的,即便村里有其他的缺口,也会用车辆或者土堆封上。
有些地方由于是类似城中村的模式,很难封死所有出入口,就将整个外部全部封禁,只留一到两个出口。
话说回来,这些措施的执行是自上而下的,也就是政府下达的命令,真正让每个命令执行到位的,让人们意识到问题严重的,是“传播力”。
近几年所有行业都在讲“下沉市场”,从消极角度看,是这部分市场还未开发足够,潜力很大;从积极角度看,是这部分市场看似“固若金汤”,但实际上由于这部分人群的特点,内部“消化能力”极强,也就是信息的传播速度非常快,流量效应就意味着利益。
比如在我们这个三四线小城市,人口流动相对较小,居委会和小区内部很多人都互相认识,所以疫情的危险和防治很快就能在一个小群体内部传开,而城市人口结构的相对稳定,社交媒体例如微信等工具的传播速度也是难以想象的,城市中任意一个群体的消息发出,不出半个小时,整个城市的工作、家庭、爱好者等多个聊天群会快速遍布最新消息。
河南是个农业大省,大多数城市都处在这种结构类型中,人们的关系网和结构类型,让各类信息的传播速度超乎想象。此次疫情防治,先是政府反应及时,然后是人们了解及时,迅速配合要求和执行措施,并且通过社交媒体快速传播正确的疫情信息,让绝大多数人认识到严重性,从每个个体做起,从而影响身边的人。甚至笔者在外面烟酒店购买杂物时,老板用两辆电动车横拉了一条绳子,大家交易通过喊的,老板进去拿货物和二维码,出来让顾客扫码提货,整个过程保持在通风的大街上,不能踏入店门一步。
笔者在走访村落时,发现其实村民们一点都不慌乱,家家摆起几桌麻将和酒席,十分热闹,而他们地里有菜,屋里有肉,哪怕是断电,他们都不觉得是什么大事,甚至还有些悠然自得。
无法上前线,我用科技报道尽绵薄之力
文|宇多田,山东潍坊
1月20日回老家的火车上,我还没有戴口罩,也不会料到武汉新冠病毒会在这未来10天内给整个中国舆论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是一名跑科技口的记者,总是固执地“蹲守”着一些特别的行业。但无论如何,我都身在媒体圈,我能在这十几天里,清楚看地到自己的媒体同行以及朋友们到底在做些什么,也能感受到真正的媒体在这个历史特殊节点上的行动力,没有因为自身力量日渐衰微而让人失望。
当看到财新副主编高昱老师在朋友圈发了他们因前线所见所闻而产生的费解与无奈时,我心底当时那种惭愧和羞愧感,真的是像病毒一样,从脚底蔓延扩散至头顶:我啃着苹果躺在沙发上过大年,我作为记者,还什么也没做。
有朋友劝我说,跑科技口的凑什么热闹呢?但我觉得,倘若以往一些被人吹捧甚高的技术,在这种最最需要它们来贡献力量的时刻发挥不了作用,那么这些技术的商业价值也大不到哪儿去。
一方面,1月22钟南山院士确认了病毒“人传人”的可能性,而春运正值返乡最高峰,病毒携带者早就散落在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如果找到这些人,我们平时因“隐私”而批判的行踪数据与各个卡口的人脸数据,恰恰是最能派上用场的。
另一方面,医疗设备供应商与生产特殊医疗资源的制造业,也势必将在这场浩大的救援运动中,成为当下和未来最难以被忽视的国家科技创新力。
这都是科技正在发挥的作用,也是我作为记者——相比前线作战记者——所能贡献的最最微不足道的力量:报道出来,让更多人看到和选择相信科技的力量。
在山东老家,大年三十前一天,我在“蹭蹭”写稿,我爸妈没多说,只是在一旁给我加油鼓劲,默默给我“端茶倒水”,默默去买了口罩,还每天在家庭群和姐妹群担任喇叭功能,由头是“孩子在媒体,知道这次疫情有多猛烈”。对了,他们还默默在互联网公司发起的捐助平台上捐了钱。
我爸说,我们都是善良的人,但也没什么大本事,只力所能及保护好家人就行了。
初三,因为怕疫情后续会影响甚至封堵“北上”的铁路班次,我决定提前返回北京。由于“恐慌”似乎开始席卷且下沉到全国各个城市的大小社区,我爸对于网上“北京泡面都被哄抢”的谣言深信不疑,硬塞给我一堆泡面和馒头。
我拖着沉重的大箱子,接受了火车站的红外体温检测,目睹了整个车站无一人不佩戴口罩,等候大厅人不少,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安静的奇特景象。甚至大家彼此因为不愿意靠得太近而彼此礼让起来,让我完成了一次平生最井然有序的火车旅程。
但让人担心的情况并不是没有。
由于口罩供应极度紧张,很多人都戴的是不合格的棉质口罩与防晒口罩,甚至于,我看到不少小孩佩戴的都是卡通棉质口罩,即使被父母用绑带紧紧缠了好几圈。这不由让我想到近几天来关于“感染病例开始出现低龄化”的多起报道。
回北京路上,我妈一直不放心我,甚至在微信上多次表示过几天要北上来看我。她一直埋怨我总是“没大没小”,自己不是医生,对病毒还没个谱,还老跑出去,“害人害己”。
“你把你自己保护好,就是对疫情最大的贡献。” 她叮嘱我千万别出门,饿了就吃那好不容易驮到北京的几大袋馒头“充饥”。
“你别来,就是对我媒体事业的支持。返乡高峰病毒传播更广,最容易中枪。”我有样学样。
“那你要好好的,我们就会好好的。”
1月31日,我没再出门。但是又打开了电脑,用自己的方式开始了新一轮战斗。
每个瞬间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文|曾欢,新疆乌鲁木齐
1月19日从公司年会在河北怀来的现场往回赶的路上,我们的车上播放着 Marshmello 的音乐,沿途的风景疯狂倒退,我们带着对触手可及假期的期待往前疾驶。关于冠状病毒的消息零星出现在手机弹窗上,停留在时间的真空,没有人意识到这已经是“安全区”正在缩小的提示。
19日,无论是在我出发的首都机场,还是到达的地窝堡机场,没人戴口罩,也没有专人量体温。4个小时的飞行之后,凌晨一点的到达口,挤着接孩子的父母、等朋友的年轻人,一切都是往常的样子。
20日,我有家人过生日,我们相约在了一个KTV庆祝,现在看来,那是我这次春节假期最远也是停留最久的一次“旅游”。那天很多公司都还没正式放假,但大中午的,KTV还是有很多顾客。随后,我们去了乌鲁木齐核心商圈的商场,各种春节大促正在进行,一层奢侈品店也并不冷清。在商场喝咖啡的时候,我听到一个男孩子在跟他的朋友说起疫情,“你知道武汉那边……”寥寥几句,语气像在说很遥远的事情。
很快,我就知道这件事并不遥远了。有一个发小在武汉读医学博士,比我先回乌,几天来一直在发小群里热切地约大家一起聚会地时间和地点,可突然有一天就没说话了,再次出现,说警察上门来登记调查了,需要全家隔离观察,每日上报,他们全家正在进行消毒,不知未来几天会怎么样。
街上,戴口罩的人突然增多了,连最爱说“没事,我们这里没有”的父亲也乖乖戴上了口罩,不往外跑了。最戏剧性的情节发生在1月23日,早上我去药房买口罩,药房还存货满满,当日新疆宣布首例确诊病例后,家人再去药房,口罩全部售空。我们去过的商场,已是空无一人。
每个瞬间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1月26日,我奉命跑腿出小区买菜,提着社区菜店最后的存货,我险些回不了家。社区的工作人员守卫在小区门口,除了录过人脸识别的小区常住居民,其他均不可进入小区。我打电话叫来父亲,送来身份证,也因被视为“走亲访友”,不许入内,直到我调出行程单证明我不是当日回家的,才被允许进入,并被反复嘱咐,不许再出小区。有非本地居民但房子买在我们小区的几个大哥被拦在了门口,看样子也是开车出去买趟年货就回不去了的,他们情绪激动:“那现在是让我们买机票回北京么?!”“你跟我发火没用,中午才出的通知,就是这么规定的。”后来他们怎么处理的,我不知道。
假期就快结束,我和我的另一个发小,在同一个小区,至今还没见面,我们相约在地库大喊几声,就当是见面了。
乌鲁木齐的大地上还有层不算薄的积雪,这成了小区居民在室外最后的娱乐希望,昨天我看见那边的窗外出现了一个雪人,今天我看见这边的窗外有两个孩子拉着爬犁找了一个小坡来来回回地滑,已经整整滑了一个下午。
爆辣鸡炒、丸子汤、椒麻鸡、扁豆面旗子,我们下次再见了。
日本的口罩被抢购一空
文|庄伟宏Odin,日本大阪
我在香港远程办公,所以新年没有回乡的需要,趁着春节假期去了日本关西一带游玩。
尽管我们在旅途中已收到武汉肺炎爆发的消息,也有亲戚朋友托我们从日本买口罩回来。不过,由于我们身处远离武汉2000公里的日本,并没有太在意疫情,所以不但没戴口罩,也没有急着买口罩回国。
有的药妆店因为被抢购一空而不得不限购:每人5个
但很快,在远离武汉2000 公里以上、仅有2个输入型确诊病例的日本,也像如临大敌一样了,很多药妆店的口罩被一抢而空。
我不知道日本人看见香港人和内地人这样紧张,会不会觉得我们小题大做,也不清楚有关方面会否觉得这样会造成恐慌。然而,我理解“过度恐慌”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但即使十次“过度恐慌”所带来的副作用,可能也不及一次“掉以轻心”所带来的坏后果。
抱最大希望,尽最大努力,做最坏打算,持最好心态。最终,在我准备回国之时,默默地戴上了口罩。
乡下的春节:小世界的坏消息和大世界的坏消息交叠在一起
文|昭晰,山东临沂
今年去乡下看望奶奶。
我们到家那天刚好是爷爷去世一年的日子。爷爷去世前的几年,耳朵就很不好,需要我们把音量提到最高,对着他的耳朵喊,才能听清。奶奶的耳朵一切正常,有时会充当他的传声筒。
今年奶奶的耳朵也不行了。虽然疫情成了今年亲戚们谈天的主要内容,但能被她听到、听懂的寥寥无几。
离开家的前一天,我问奶奶,知不知道现在很严重的那种病毒。她说不知道。
我才发现,一位老人,在她自己孤独的视角里,可能根本没明白,为什么往年热闹的年夜饭,今年一下那么冷清;为什么今年小辈们拜年的频率,明显下降;为什么每个人明明围坐在她周围,却都紧盯手机,屏幕上是一幅幅红色深浅不一的中国地图。
她更清楚的,是隔壁那户人家42岁的儿子,腊月二十八回家当天脑溢血死亡,依村里的习俗,丧事不能跨农历新年,所以匆匆办完了本该持续半个月的礼仪。死亡在北方乡村的冬天并不鲜见,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噩耗对一位老人的冲击依然强烈。
今年,小世界的坏消息和大世界的坏消息环相交叠,又是一个冬天。
乡下电压不稳,网络不通顺,也没有暖气,我缩手缩脚地不停刷新网页,断断续续获取疫情信息。
看着确诊数字一点点上涨,深深知道数字背后都是活生生的人。面对这些数字,有痛心,有失落,有愤怒。看着各家媒体的记者朋友们奔赴前线也好,后方采访也好,一篇篇地写,一篇篇地提供消息,我却什么都做不了,心急如焚。
或许和多数人一样,我的焦虑情绪在大年三十晚上达到了顶峰。没法继续看春晚的我本想早些休息,但却一直看着疫情信息直到深夜。凌晨,我看到了一条征集心理咨询师的信息,这是我本科学习的专业,也认识很多专业人士,我发动了自己能接触到的所有心理方面的资源,对接到凌晨三四点。
暂时不能履行记者使命的我,终于提供了一点点自己力所能及的帮助。至此,心安片刻。
提前返京后,恢复网络的我终于可以开始做选题了。如果大家有关注的疫情话题或疫情相关线索,都欢迎联系我。(见下图)
让我们一起相信真实的力量,每一次讲述都有价值。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