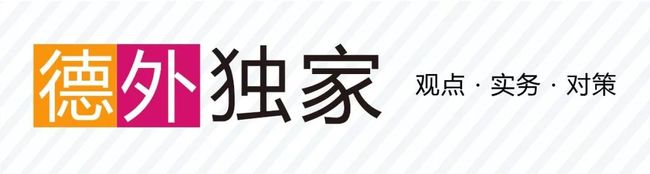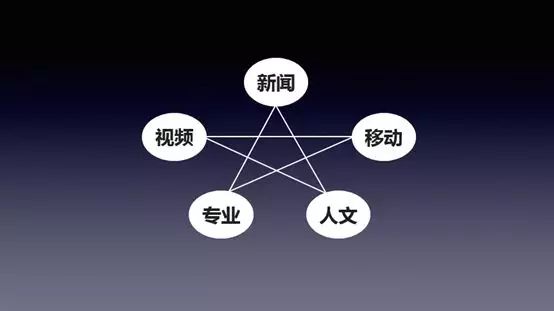原创:彭远文德外5号
2019-11-27 20:00:00
编者按:
在“中国电视融合峰会—短视频生态圈”上,作为主题演讲嘉宾上台的新京报"我们视频"副总经理彭远文,刚一开口就直言很紧张,表示“我们做报纸的人来做视频,特别外行”,但从效果来看,这份紧张似乎有些多虑。
"我们视频"自2016年9月上线至今,发展非常迅速,已成为传统媒体向新媒体转型的一个标杆,在《CTR-快手媒体号综合榜》里排在第六位,超过了地方广电媒体号“快乐大本营”。此外,它还在《CTR-快手媒体号热搜榜单》中排名第二,截至2019年10月份累计109次登上快手热搜,可以说是自带“热搜体质”,一举一动牵引着网友的注意力。
那么,从报纸转行而来的"我们视频"是如何从众多视频产品中杀出重围的?
图注:新京报"我们视频"副总经理彭远文
很早之前,我们给自己定的目标就是要做中国最大、最有影响力的移动端新闻视频生产者。大约是在三年前,当时我们的小团队一共有20到30人,大家经过一下午的“头脑风暴”,想出来了几十个关键词,再把不算最核心的词一个个擦除,最终留下五个关键词,到现在都没变:
图注:新京报"我们视频"做移动端新闻视频的五大关键词:新闻、移动、视频、专业和人文
这五个关键词里,最重要的是“新闻”。我们的定位是做新闻视频,因为新京报最擅长的就是新闻,转型目标实际上是把自己最擅长的部分来做一个视频化的处理。其次是“移动”,即针对的渠道是移动端,因为现在大家看手机的时间越来越多,“受众往哪个方向跑,我们也要朝哪个方向去”。然后是“视频”,从团队成立的第一天,我就定下了一个规矩,做图文是没有稿费的,只有生产视频才能拿稿费。至于“专业”、“人文”,我们强调要把人的价值放在最高位置,尊重生命,作为媒体来讲,这点特别重要。今天我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媒体,尤其是报纸,在转型时可能会面临的几个疑问和解答。
有必要做“全能记者”吗?
报纸这几年有个词频繁出现,即“全能记者”,在我看来这是有问题的。现在媒体的日子不好过,尤其做新闻视频更是费力不讨好,所以仍在高投入做新闻类视频的媒体并不太多。我经常听到“反正到了现场,除了文字报道,顺便把图片拍一拍,拿回来就得了”,什么意思呢?其实是说媒体希望尽可能充分利用现有人手,榨取到更多的剩余价值。当媒体的原有业务做不下去,裁员又比较困难时,就把人员分流转岗去做视频,导致很多视频行业从业者并没有相关基础,这或许是大家在转型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最实际的问题。
问题首先体现在做视频的技能门槛上。十多年前,我在央视工作,在新闻评论部干了两年后,老师对我的评价仍是“你的视频语言还没有入门”。这说明视频语言的门槛非常高,给没经过培训的人一台摄像机,他就能去拍视频了吗?这就像在大街上随便抓一个人,给他一个录音笔让他去写稿子一样,并不现实,所以“全能记者”的提法隐含着对专业门槛的忽视。另一个问题是考核管理,比如说安排一个文字报道记者去做视频,他首先不会把视频视为最优先的工作,若是做出来不合格又会在心理上备受打击,而视频部门的人又该如何跨部门指挥记者?内部沟通的成本将非常高。
出于这些原因,我们从一开始就没有强调做复合型人才,我们只强调一点,就是做视频。一件事情只有全身心地投入才可能做好,如果团队成员的内心不情愿、技能不熟练,还是兼职队伍,怎么可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胜出?所以我个人认为,纸媒转型做视频时最大的一个坑就是“全能记者”。但也许站在一个更高的位置来看,我的观点是错的。
传统电视与移动端有何区别?
在推动传统媒体和互联网融合的过程中,大家可能都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传统电视新闻的节目哪怕放到网上去也并没有人看,对此我个人的看法是需要重新认识栏目、演播室和播出标准。
栏目是传统电视的产物,跟报纸填版面一样,电视在有效时间里的内容也是由诸多栏目拼在一起,以前这种模式行得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电视频道是垄断资源,观众不看也得看。但当这些东西放到网上去之后,消费者的要求就会高很多。这几年大致也可以看出来,几乎没有新闻类栏目在移动互联网端保有影响力。
演播室的功能也该从移动端的视角去看待,它的价值并没有那么大。长久以来,演播室实际上是节约成本的一个做法,比起去现场拍视频更为经济。为什么电视台的主播颜值都会比较高?因为只有一个人在那说半天,内容也不是好玩的脱口秀,观众会觉得唯有看一个颜值赏心悦目的人,还堪忍受。
在播出标准这方面,以前一般更看重视频的画质,而不是内容,实际上更重要的是视频里有多少真正有效的信息。现在的新闻短视频使用了大量的监控视频、网友提供视频等素材,但它的价值可能胜过我们拿很贵的摄像机拍摄的内容。
UGC时代,记者还要到现场吗?
现在做新闻和十年前做新闻大不相同了,其中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几乎所有的重要现场都能找到事发瞬间的画面,比如重庆公交车坠桥事件,公交内部的车载镜头画面最后都被公布了出来。以前的新闻事件中,如果记者没有到达现场,媒体就无法获取具体画面。而在今天,这甚至已经不是一个问题。因此,UGC(用户生成内容)视频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是做新闻类视频时绝对不能放过的素材。
但与此同时,媒体要坚信快速到达现场仍然是不二法宝。过去数年来做新闻的经历让团队培养起了这种意识,例如在江苏响水爆炸案发生后4个小时,我们的记者就已经到达事发地点,在现场待了一个通宵,期间持续不断地生产内容。另一个例子是斯里兰卡恐袭案发生时,我们第二天就到了现场,及时参与到事件后续的报道中。
"我们视频"的“快”,体现在又准又快,因为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自媒体或UGC的很多内容在未经过核实求证时,机构媒体是不敢转载的,但我们的内容他们就敢转,这说明我们只需要在符合新闻规范的操作方式里面做到最快。此外,我们的视频也是有增量的,比如说更全面、更好的叙事手法等等。将发自现场的专业内容和UGC内容结合在一起的持续报道,是"我们视频"在做新闻时的核心竞争力。
"我们视频"的优势在哪里?
面对互联网的碎片化特性和信息过载的现况,我也时常思考,我们的优势在哪里?一个直观却又分外重要的优势是,跟自媒体比,我们人多。做新闻首先需要媒体资质,这在整个市场上都是稀缺的,因为现在真正去做社会新闻、突发新闻的媒体越来越少了。
最开始"我们视频"的定位是在一个非常窄的新闻领域,主要就是做社会新闻和突发新闻。一个实例是今年6月,一个女子在街头遭男子凶残踢打的视频在网络上广泛流传,关注度极高,当时我们投入了非常多的人力去做挖掘和采访,最终发现事件的发生地是在大连,是全国首家核实地点的媒体。而在做起来两三年之后,我们也会开始把做新闻的范围慢慢拓展。
另外,新京报社也在大力推动视频表达的全部门、全领域覆盖,促进视频报道部门与现有内容团队的深度融合。内部会有选题沟通机制,每天的选题共享,而"我们视频"在外面获得的采访资源、采访对象也会跟所有部门分享。目前“我们视频”新闻短视频日产量已达100条,新闻直播日均超过1场,产量远远领先于国内其他传统机构媒体,也已占到约三分之一的新京报采编总量,而这一比例还在继续扩大。
另一个优势是专业性,这体现在生产新闻时有一整套的规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把新闻理解为工厂的一条流水线,我们能以工业化的流程生产来保证产品的质量。从这个视角来看,视频其实并不是什么新媒体,反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传统媒体,因为我们在用最传统的方式生产新闻,包括到现场、求证、采访、核实的方方面面,内容在上线之前还要通过“三审三校”,这都是对新闻可信度和质量的尊重。
在保证内容准确的同时,我们也一定会考虑到移动端视频的特性,比如移动端是最不友好的一个观看场景,受众可能是走路的时候看,可能是在地铁上面看,这意味着声音是听不清的,所以我们全程都要有字幕,而由于屏幕大小有限,字幕必须够大才能够看清楚,这反过来又对文字的精炼程度提出了要求。
媒体该如何与平台合作?
近几年传统媒体渐渐失去了自己的平台,比如报纸看的人少了,而媒体如果想从头打造一个APP平台也很困难,因为要跟今日头条、快手、抖音这样的平台竞争,只有一些重量级选手可以入场。这就意味着大部分媒体只能选择做好内容生产,同时跟平台合作。
"我们视频"选择的短视频平台,主要提供了两种价值:一是人物类报道的主要内容来源,二是新闻视频的分发平台。在拍摄人物故事时,通过短视频平台可能一两天就能把以前半年的工作完成,因为当事人可能已经自己发布了几百条短视频,我们很轻松就能完成对素材的梳理整合。目前,"我们视频"新闻短视频的日产量已经达到100条,新闻直播日均超过1场,产量领先于国内其他传统机构媒体;从传播效果来看,截至2019年11月,“我们视频”在新京报以及旗下平台、腾讯、微博、快手等渠道的日均播放量超过2亿次,其微博MCN矩阵的日均阅读量达到1亿次。
在与平台合作时,营收也是一个不得不谈的问题。许多新闻平台在逼迫传统媒体成为廉价甚至是免费的内容提供者,这并不正常。理想的平台会针对内容付给媒体一定的版权费用,或直接提供完整的广告经营权。平台需要有合理的商业模式,足够的流量,来支撑媒体账号拓展受众,在提升整体的品牌效应的同时,也有利于商业变现。
编者按:
作者:新京报"我们视频"副总经理彭远文
整理:苟于清
转载引用声明:
请原文转载或不加修改地引用文中数据、结论及数据说明,并注明来源。除此之外的任何自行加工与解读均不代表CTR观点,对由此产生的不良影响,CTR保留诉诸法律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