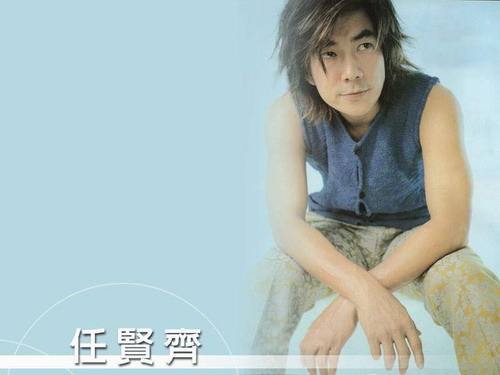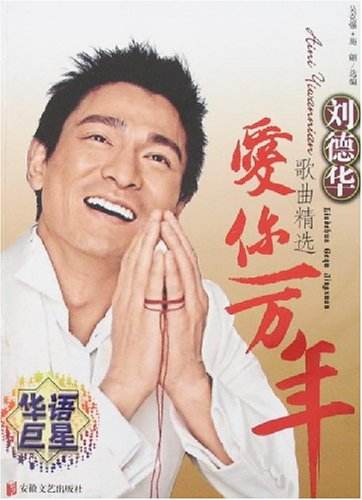一
2019年4月24日,夜,0:51,成都。
下午下班回家路上,在地铁车厢里猛然听到别人手机里放的《浪花一朵朵》,任贤齐的歌。他的歌最为火爆应该就在2002年前后,那时我还读着初中。像他唱的《兄弟》《死不了》等等歌曲,就如同陈小春、郑伊健他们饰演的《古惑仔》系列电影一样,被正处于叛逆期的我们疯狂追捧。
在故乡那座县城里,但凡跟我们年龄相差不太大的初高中生,还有一些辍学少年,都热衷于把自己想象成电影中的模样。平常打招呼,一句“跟谁混的”,总感觉要比其他的问候高级很多。我们不齿于比较彼此的学习成绩,在我们的“江湖”里,比的是义气,比的是豪气。成绩是书呆子才会去比较的。
留长发,穿宽松的工装裤、牛仔裤,无袖牛仔马甲,牛仔裤上还得有三五条从前皮带环连接到后皮带环的银色铁链子,走起路来,晃里晃荡的,简直拉风的很。有条件的再在裤腰里别个寻呼机,呼叫铃声一响,夸张地拿出寻呼机望一望,然后快速跑到校园中的小卖店,在拨通对方的座机后,声调极高地来一声“喂,找兄弟什么事?”
感觉威风无比。
那时候家在县城中的女同学们穿着的干净,整洁,自然看起来比许多农家女孩子更加耐看一些。男同学们正值情窦初开的年纪,虽不懂爱情的真正含义,但说起话来,张口闭口爱你一万年,那写在花花绿绿信纸上的情书,看起来辞藻华丽,文采飞扬,每一句写得看起来比谁都真诚。
男同学们嘴上说着兄弟为大,情义为大,学着周润发《英雄本色》《纵横四海》等电影中的声调和场景,前呼后拥,时刻准备着为兄弟两肋插刀。转眼间,就因为女同学主动说的一句话,屁颠屁颠地跑到女同学身边,巴不得挨的再近一些,一副忠诚奴仆、情圣花痴的模样。更有甚者还以女同学使唤他、让他为其跑腿为荣。
一个班里拢共学生四五十人,女同学占不到二分之一,其中耐看的、稍活络点的也就寥寥数人。与这几个公认的“梦中情人”搭话嬉笑多了,自然也就会引起其他人的不满。久而久之,兄弟翻脸,心生间隙,甚至“反目成仇”的自然也不在少数。
“单挑还是帮挑?”矛盾多了,火药味也十足。
古惑仔为大家提供了那么鲜活的样本和剧情,大家也不可能只用“嘴炮”一决高下。况且,只吵吵不动手,那是娘们才会干的事儿。男同学们普遍认为,没有哪个漂亮女同学会喜欢看起来没有一点男人味的男人。
只是青春叛逆的年龄,凡事冲动不计后果,动起手来也没个轻重。那时,许多男同学床头或者床底都藏着砖块、踩断的拖把柄、钢管甚至砍刀、菜刀。当然,那些看起来杀伤力大的家伙,一般都是属于“带头大哥”“扛把子”们的——在他们看来,这是身份的象征。
一般约架的很少在本班内出现,大致都是在不同班级、同校跨年纪,或者跨学校之间产生的,一般也鲜有人会“单挑”、都热衷于选择“帮挑”,人多力量大,“单挑”主要是怕吃亏。而“帮挑”,少则双方五六人,多则数十人。若是约架的过程中没有谈拢,争锋相对,或者缺少社会上的这个“哥”,那个“哥”的调停,便会开始扭打开来。一番混乱下来,人多势众、占据上风的欢呼雀跃,处于下风的则悻悻离去,心里想着怎么“复仇”。
当然,也有颇具戏剧性的,约架之前,又是下挑战书,又是饮血誓盟,等双方来开阵仗,正准备大干一场,不知从哪儿来了个比双方带头大哥还厉害的“扛把子”。
“今天就给我X哥个面子,你们握个手,吃个饭,以后就都是我兄弟了,都跟着我混。”语气容不得商量。
“扛把子”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那面子必须得给啊。于是,双方带头大哥握手言和。随后一众人浩浩荡荡的开进街边的“酒家”。待数十人占满狭小的店面,带头大哥扯大嗓门喊道“老板,先每人下一碗面片,每桌割一斤卤肉,然后来一扎啤酒。”
都是长身体的时候,大家肚子里都不免缺少油水,面片还没上桌呢,桌上的卤肉已经被消灭见底,甚至盘中配料大葱也被吃的一干二净。可是谁在乎呢?俗话说,多个朋友多条路,有兄弟走遍天下,无兄弟寸步难行。
乒呤嗙啷一阵,脚底下的空酒瓶慢慢就多了起来。店内烟雾缭绕,推杯换盏,行拳猜酒,就像是谁家娶媳妇儿摆宴席似的,好不热闹。
“扛把子”和带头大哥们自然要文雅一些,待餐桌上面片以外的几个菜肴也吃的差不多了后,便结伴走到邻桌,相约敬酒。
“大家都是兄弟,以后有事情就找哥,我罩着你们。”言毕,将杯中啤酒一饮而尽。临了还将杯子翻转过来,在空中抖抖,以示诚意。
看此情景,众兄弟们也毫不含糊,纷纷起身,咕咚咕咚一饮而尽。
许多饭店老板对中学生这样的行为见怪不怪,也不会多说什么。待饭店快要打烊时,店老板走到“扛把子”所在的那桌,告知马上就要打烊了。
“扛把子”毕竟是见过大世面的人,是绝不跟一个普通的店老板计较的。店老板话音刚落,便招呼兄弟们结账离店,说完自顾自地走出了店门,带头大哥们紧随其后。剩下几个动作缓慢的,留在店里你五十他二十的凑钱结账,但即便如此,没有一人面露不悦,兄弟嘛。这世上,兄弟最重要。
再说回约架,也有刹不住车的。我曾亲眼见过,拿起砖块就往人家头上拍的,拍到头上的瞬间,鲜血就直冒出来,滋在了宿舍白墙一溜儿。场面有点血腥。
还有一个比我长两三届的学长,号称“菜刀哥”,口袋里时常揣着一柄菜刀,每回到宿舍,稍有不开心,便摸出菜刀向宿舍门甩去,菜刀直楞楞的插在门背后的三合板上,若不是门正面包裹着铁皮,宿舍门早被砍出了大洞。另外,一些社会上的“带头大哥”们来校园滋事,被学校体育老师和高年级学生围追着在校园里打,被打得不省人事的事例也不在少数。
每年学校在进行年度总结时,会特地邀请县公安局或辖区派出所的民警们来开展预防青少年暴力犯罪的讲座,许多案例都是发生县城中或者周边,像打群架被人砍断胳膊,误伤致人死亡,少年街头抢劫等,每年都会新增一些事例。教训满满,但对处于青春期的男同学们来说,这就像是听说书似的,往往左耳进右耳出,听完就完了,没人从心底意识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
案例警示教育开展完没多久,大家便又在下了晚自习课后,三五成群的钻进录像厅、网吧,重温古惑仔打遍铜锣湾,周润发纵横四海的美梦。
因为年轻,许多人都觉得浑身都是热血。
二
按当时的标准,老贺绝对算得上是我兄弟。作为一路相伴走来的发小,我们从学校一年级开始,一直到初中都在同一个班级,学习成绩也不相上下。
老贺和我最大的不同,就是他比较“潮”,喜欢潮流前卫的人和事物,尤其对刘德华、周润发、谢霆锋等明星很是喜爱。他有一个专门的笔记本,里面贴着从海报、明信片上剪下来明星照片,每一页都写着明星的名字、籍贯、生日等等信息,有些还写着从别的地方摘抄下来的一些格言。
老贺梳着一头类似谢霆锋的发型,其中的分线很是分明,“头可断,发型不可乱”是他的口头禅,因为精于打理,他的发质看起来显得饱满而富有光泽。他喜欢唱歌,在我们进行英语早自习的时候,他在唱歌,在我们晚自习的时候,他仍在唱歌。他唱的歌曲多半是那时最为流行的,让人惊奇的是,他能将歌声的音量恰当的控制在邻座漂亮女同学模糊听到与听不到之间。显得十分神秘。
老贺对未来充满着想象,充满着希望,经常幻想畅谈着外面的世界和未来的光辉岁月。
我们和班里的男同学们一样,正值青春,自然也免不了追随班级中的带头大哥,但毕竟我们是农家子弟,家中寒苦倒也知道几分,要说生性顽劣那倒谈不上。只是我们过往多年区居于深邃的山坳,就像笼中鸟儿,一到了外面的世界,忍不住感叹“哇,城市原来如此精彩”。于是内心起了波澜,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开始变得不安分起来。
我们跟班级中的带头大哥厮混往往选在周末。从周五晚开始钻游戏厅、钻网吧、录像厅,一直持续到周日的下午。从小惯于听家中父母的话,除了学习几乎找不出第二样喜好,但自跟了带头大哥厮混,仿佛世界为我们打开了另外的一扇窗。
我和父亲的隔阂也是那个时候开始产生的。父亲每每语重心长地教诲和提醒,在那时的我看来,教条又束缚,剥夺了我太多的自由和快乐。我慢慢变得不愿和父亲说话,有些事情只是私下跟母亲说。父亲也看出了端倪,和我说一些话的时候变得格外小心起来。实际上,我也深知父亲的爱意,只是有时在谈论和面对起一些事情来,往往又说不到一起,不欢而散。
等县城中的娱乐场所混得时间长了,新奇感快要消散殆尽,我们认为,我们的人生不应该拘谨于此。那时网络兴起没多久,网络上、故事中,呈现和描述的世界简直精彩纷呈,光是看看,就诱惑力十足,我们就像是面对一盘冒着热气、香味四溢的精美菜肴的饥饿少年,对县城以外的精彩垂涎不已。于是,在那年深秋的某个下午,一场外逃计划在被某个同伴提起时,顺理成章、而又迅速地达成了一致。
具体的计划是这样的:我们先各自回家,从家里带一些换洗的衣物,顺便“拿点”钱,然后在约定时间返回县城的指定地点。待人员齐整后,乘坐大巴去往省城,再从省城坐火车抵达上海。
我们的目的简单又明了——去闯荡上海滩,待事业有成之时,荣归故里。
我们听某个男同学绘声绘色地讲,他一个亲戚家的哥哥在上海的某个餐厅工作,月薪高达2000多块。这更加坚定了我们前往上海,打拼天下的信念。
出逃计划定在一个工作日。那天,上午的课程结束后,在其他同学们纷纷跑向食堂的时候,我们从校门里跑了出去,准备按计划各自回家。
但是就在我去上厕所的功夫,等我出来时,我已找不到老贺了。我返回学校宿舍,搜寻了一番无果后,料想他应该以为我已经去了车站,肯定是去车站找我了。之后,我便独自前往车站。在车站,我一直等到汽车发动,也没有等来老贺。
秋季的天气已然寒冷了下来,我蜷缩在座位上,看着车窗外渐渐向后飞驰而去的树木、河流和远处的群山,西北高原深秋土黄色的色调看起来有些单调和衰败,我的心情复杂而沉重。
班车前排上方位置悬挂的电视中,正播放着周润发当红的碟片,但我却没有丝毫兴致观看。我想到自这次走后,或许,久久不能回家,心中竟然有一丝悲戚。
回到家时,已近黄昏。我推门进去,看到祖母正在火炉上做着晚饭。看到我站在她眼前,她稍稍迟疑了片刻,显得有些惊奇,继而,问我肚子饿不饿。
直到吃过晚饭,祖母也没有问及我此番突然回家的缘由。反倒是父亲看到我,在同样惊奇之后,再三询问我,我回答说天气冷了,学校的宿舍太凉了,请假回来拿些暖和的衣物。
第二天,我的心情矛盾而又复杂,我没有再说太多的话,生怕哪一句暴露了我们的计划。当再次想到此番一去,定是不混出个模样誓不回乡,心里徒增了许多悲壮。我一反常态地搜罗了祖母、父亲母亲待洗的外套,花了一下午的时间全部手搓了干净。
吃过晚饭后,便一个人坐在院子里,思考该如何从父亲手中“拿点”钱。父母忙于收拾刚从地里挖回的土豆,顾不上关注我郁郁寡欢的状态。
但祖母却像是看出了我的愁绪,她走到我的身旁,对我说“心里有啥事,你跟奶奶说吧。受了啥委屈,也跟我说。要是实在不行,这书我们不读了,你回来,我养着你。”
祖母不说话则以,这一说话,让我的神经绷不住了,眼泪瞬间就沿着我的脸颊流了下来。
我说了句没事。简单安慰了祖母之后,返回房间开始睡觉。
几乎一夜无眠。
第二天我背着些厚实的衣服,坐上了回县城的班车。一路上,车内循环播放着一首叫《走出喜马拉雅》的歌。
“雪域的山,山山水水
雅鲁藏布江,你一路欢唱
带我满心的渴望送向何方
带我满心的渴望送向何方
......”
歌声婉转悠扬,意境辽远,就好像是司机知道我即将离家乡而去。歌词句句入心,很合我的内心和境遇。
但是,到达县城之后,我在约定的地点整整等了一个下午,我还是没等到老贺他们。时值黄昏,我不得不沮丧地回到学校。事实上,除了学校,我无处可去。单枪匹马闯上海滩?我可没那么大的勇气。
如我所料,我最终在学校也没有等到他们。我心中肯定,他们已弃我而去了。遥想着有朝一日他们荣归故里,我心中甚至有些怨恨起来。
“我——呸——”这算什么兄弟!我朝地上吐了口浓痰。
外逃计划中的另外两个同伴也陆续回到学校,只有带头大哥和老贺不见踪影。显然,他俩单飞了,他俩无情地抛弃了我们。
我们在向班主任老师提交了深刻的检查书后,重新坐回了课堂。而少了带头大哥的招呼、吆喝,我们的小帮派圈子很快瓦解了。我也没有心思再去组织、聚拢。
没有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我也不确定他们是否果真去了上海。
不过,我的脑海里还时常浮现出上海繁荣街道上某个知名夜总会里的场景——富贾权贵、觥筹交错、夜夜笙歌,尤其芳龄舞女的模样楚楚动人,惹人怜爱,我觉得比我们班里的女同学要耐看多了。
我闯荡天下的梦想,就那样在那个深秋,因兄弟们的“背叛”抛弃而破灭了。
三
再见到老贺是大概在两个月以后。
某一天,小我一届的一个男学生来找我,告诉我有人在学校外的渔场里等我。
我不知所以,起初担心这又是哪个“冤家”在设圈套,但任凭脑汁搜尽,怎么也想不起来,究竟是得罪了哪一拨人。为了壮胆,便约了两个同乡结伴而去。结果,在那废弃数年的渔场里看到了老贺。我心情复杂,正准备如何挖苦他。反倒被他抢了话语先机。
“有没有吃的?我快饿死了,我都两天没有吃饭了。”老贺这话说出后,把我惊呆了,同去的几人也面面相觑,但老贺说话的神情又显得非常真诚。这让我觉得有些滑稽。
他身上穿着最新潮的牛仔裤,脚下一双皮鞋锃亮闪耀,上身穿一件时髦的套头卫衣,看派头一点都不像是吃不起饭的样子。
但我还是陪着老贺一起悄悄回到了宿舍。在我给他泡了一袋方便面后,他等不及滚烫的开水变凉下来,就吸溜着把搪瓷缸子里的面条全部吃完了,而后又一遍吹气,一边大口地把汤喝了个干净。
看到这个情景,我才真正相信,他说的饿了两天原来是真的。
听老贺说,他和带头大哥在外的过程中闹掰了。他不知道带头大哥现在身在何处。
在我们纷纷严格执行出逃计划第一步——各自回家的那天,老贺和带头大哥等不及我出来,便提前走到了县城的街道。之后从县城里找了辆出租车,约定以往返四百块钱的价格乘车直驱家乡。等老贺到家后,发现家里一个人都没有。但这并不要紧,他知道他家的钱放在哪里。他打开他父母放钱的箱子,从里面拿出1万元现金揣在了身上。
那些年,他的父亲靠贩卖沙金挣下了不少钱,乡邻们都知道他家生活比较富裕。拿了钱后,老贺想到父母发现后,肯定以为家里招贼了,便又在箱子边上留下一张字条,上面写了些类似“儿子不孝,养育之恩今后再报”的话。然后,同带头大哥一道钻进了出租车,原路折返回县城。到达县城后,便直奔省城火车站。
他俩先到了上海,在待了一两周后,又游历了江苏等地。后来返回上海后,带头大哥告诉他,自己需要去会见一个朋友,这事关他们能否在上海立足的重大问题。之后便留下他一人,不知所踪。
老贺等待了许多日,但始终不见大哥踪影,而自己身上的钱已经被花的差不多了,找工作又不顺利,置身于异乡城市,举目无亲,便想到了回家。无奈地是,当想回来,才发现自己身上甚至连买张火车票的钱都没有了。
老贺说,当他们从县城出发之时,带头大哥提出为防止钱财丢失,两人无路可退,便约定由俩人共同保管那1万块钱。出于对兄弟的信任,带头大哥揣了8000元,剩下的2000老贺揣在了身上。
后来带头大哥一去不回后,老贺的经济状况已不允许他再在外面晃荡,他想到找一份差事糊口。于是,他又相继给两家职业中介机构各交了200块钱的职介费。中介推荐工作的时候,说的天花乱坠,但等老贺真正去工作场所时,才发现,中介口中的工作场所就是个街头苍蝇馆子,而工作内容就是些洗碗、传菜工之类的活计。这与老贺的心理预期差距太大。没干满一天,老贺便直接离开了。
“端盘子我在互助的县城都可以端,为什么还要跑到大上海?!”老贺受不了那被人使唤来使唤去的“鸟气”。
接下来,没过几天,老贺便支撑不下去了。他心里已经打定了回乡的主意,哪怕回去遭人唾骂,那也必须回去。
苦于身上只剩几十块钱,实在没办法,他就先到了上海的火车站。他想碰碰运气,在车站广场搜寻有没有家乡出来的老乡,“哪怕是借点钱,回家了想办法再还他也行啊”。后来,还真碰到了一个具有相同乡音的人,说明来意后,这个老乡给老贺指了条明路。而老贺把身上剩余的五十多块钱拿出二十作为酬谢。与此同时,同乡告知老贺,他出门在外遇到了困难,并留给老贺一个银行卡号,叫老贺回去后无论如何也得给他想办法凑个200块钱打到那个卡号里。同乡说,他已经有两年多时间没回家了。
同乡给老贺指的明路就是让老贺混杂在给旅客提前送行李上车的人群中,等进了车站,上了车,先找个地方躲起来。等到列车查验票的时候,再提前进到厕所里,躲着不出来。真方法真管用。靠着这样的方法,老贺从上海一路提心吊胆的回到了省城。
真是遇上好人了。老贺说。老贺对那个同乡的评价让我们确信他遇上了好人。但至于那200块钱,老贺是实在没法给他转过去。
“曾经都是天下人负我,而今我不得已负于天下人。”老贺要了一根烟,点燃后,站在宿舍的窗户前感慨道。
我不知怎样搭话。我以为只有在经历了老贺那样具有传奇色彩的事情后,才能发出这样的感慨。但还没等到烟抽完,老贺便开始向我打听起班里女同学的近况。
我知道他说的是谁,便问了一句:不想去班里看看她吗?
老贺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脸和身上的衣服,反问道“就这样灰头土脸地去吗?”
我无言以对。
老贺最终没能见上心爱的女同学一眼。他那时候大概没想到以后他再也没机会看那女同学一眼。
他在那个下午从学校出走。没过多久,学校的一纸通报将他开除了。
一个月后,我回乡的间隙,看到了他的父亲,愁容满面,憔悴不堪。那个时候老贺因害怕家人的责备还躲在外面不敢回去。
我劝说他的父亲,再给老贺找一所其他学校,继续让他读书。他父亲摇摇头,失望地说,不读了,说啥也不让他读了。
随后几年,初中肄业的老贺,不是在家帮忙干地里的农活,就是外出奔波务工的路上。
我高中快毕业的那年,有一天,老贺来学校找我们,告知我们要出去打工,来跟我们辞行。我约了几个关系要好的同学,一起在县城的某个旅馆中一饮而醉。次日,在我们回学校的路上,老贺踏上了前去江苏打工的路程。
之后的几年时光,我一直在继续我的求学之路,而老贺已娶妻生子,单立门户。
在他结婚那年的那个春节,我们喝了许多酒,说着曾经在校园中的往事,情到深处,老贺说,可惜啊,再也回不去了。
往后的几年日子,我与老贺见面的机会更少。我参加工作后,有一年,偶然在村中碰到了他,寒暄了几句后,老贺便问起我的收入。我告知后,老贺说,真好啊。那时,他的发型还是没有变,只是脸上看起来已不再光滑,眼神在我看他时,有些恍惚游离。
自从初中分别,往后至今的十几年时间里,我和老贺总共相见过五六次,每次相聚,他必定酩酊大醉。醉意来袭,老贺不停地、反复跟我谈起初中的那段时光,有时,也会抱怨农活太累,生活不易。他的美好记忆在那年那个深秋戛然而止,而我还在波折前行,因后续缺乏共同的生活经历,我鲜少在他面前谈及我的学业和我的工作,一是担心他无法体会我的心境,二是怕他心里会有更大的落差。
属于我们的共同记忆在初中三年级那年,永远定格。
在人生的道路上,有些时候,我会不由地回想起以往的那些时光。青春年少,一念之间,世界便给了我们两种截然不同的道路和运途。
为他惋惜,为自己庆幸。
或许,曾经的“江湖”现今仍在,只是,那些“古惑仔”兄弟们早已散落东西,或许如意,或许失意。
而那些漂亮的女同学们,许多已为人母,大概她们是不会想到,曾经那么多男同学,视她们为心中女神,理想伴侣。
那么想牵绊左右,终此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