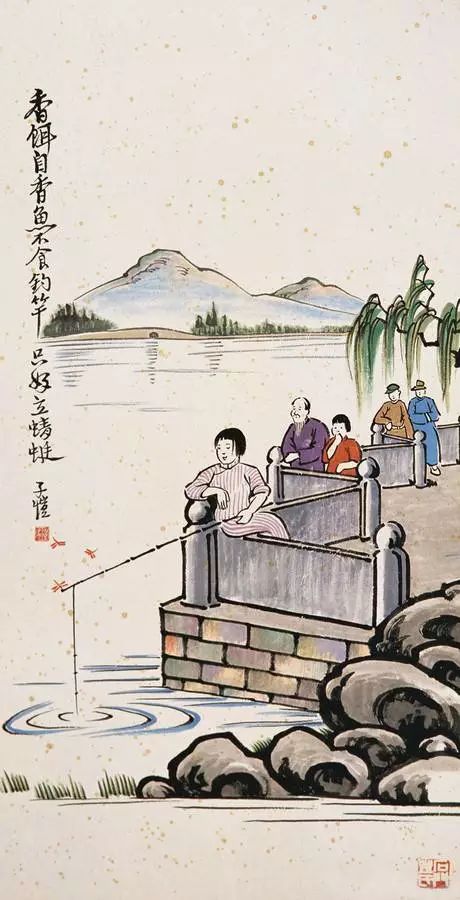一、我的大学
我的大学是在扬州师范学院度过的。在走向杏坛的过程中,我其实经历了一些中文系学生都有的苦痛,那就是我必须从诗意的文学走向虽有诗意但毕竟是严谨而科学的语文教学。对一个做着强烈的作家梦的人来说,这种选择是很痛苦的。幸好,我对当一名语文教师同样有着强烈的冲动。
我在大学时代就有着一手抓住文学一手抓住教育的野心。我坚信自己在成为一个优秀的语文教师的同时也能成为一个出色的作家。
在我的教学法老师中,有一位是当代著名的语文教育理论家,他就是顾黄初先生。顾先生默默耕耘在大学教授们大都不愿意问津的领域,很让我们钦佩。
在教育见习阶段,顾黄初先生为我们选择了扬州中学。省扬中是一所海内名校。顾先生有意让我们在扬州中学这样一所名校内感受教育的神圣与崇高。他还请扬州中学校长郑万钟先生为我们作了报告。郑万钟是我们的校友。他是语文教坛上最早将“红学理论”移植到中学语文教学与科研里的名师,在中学语文教学的领域里独树一帜。郑万钟对我们中文系学生的影响是很大的。
见习结束后,我对大学同学开了一节《狂人日记》课。那一天顾黄初先生、教学法组王乃森老师、梅尚筠老师都去听我讲课。讲课结束后,三位老师异口同声地夸奖我,认为我就在当时也都可以算是一个出色的语文教师。王乃森老师则在我的毕业纪念册上写下“你怀瑾握瑜,相信将来定能遂凌云之志”的话。我终生都不会忘记我的老师对我的鼓励。
四年级下学期,我到江苏省兴化中学实习。兴化中学校长、语文特级教师柳印生得顾黄初先生真传也颇多,他和顾黄初先生一样,很看重教后记和教后感的写作。柳先生亲自指导了我的教育实习。现在想来,在从事教育工作的起始阶段,与别人相比,我实在幸福得有点奢侈。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有幸遇上这些名家的。
二、乡间那一盏优美的台灯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母校江苏省兴化县唐刘中学执教。那是在一九八六年。那时候,在一个乡村中学,还很难找到一个中文本科生。在我的老师、唐刘中学校长孔沁梅先生的强烈要求下,教育局将我分配到了这所中学。我一回到母校就担任了高三语文的教学工作。
大学一毕业就执教高三,对我来说,实在是一种极大的考验。但一年的高三教学,使我对高中全套教材有了全面的掌握。在教学中,我最能让学生服膺的是,课本中要求背诵的课文,我自己从头至尾一字不错地背诵给学生听。而教材中的每一篇文言文,无论长短,我都一字不错地全部背出来。我的备课也和很多教师不同,我几乎不带教案上课。教案上的内容,我全都非常深刻地印在脑海中。
我非常怀念那一段特殊的日子。如果不是那个教师青黄不接的时代,一个普通的应届大学毕业生是不会那么快地找到自己在教学中的位置和那种成功感的。同样,没有那段日子,我也很难培养起语文教学上的大眼光。也是在那一段日子,我深深地领悟到,一个语文教师,最要紧的是他必须在从事教学的最初阶段能深切地了解他整个教育生涯中需要哪些东西。
但在我开始从事语文教学的年代,语文教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应试教学的影响,使语文科研出现了很多功利性的东西,有的东西甚至背离了语文教学的本质。标准化考试又使语文的人文性惨遭面目全非的重创。我同样清醒地知道,我的高三语文教学其实离语文教学艺术还很远很远。
一九九○年,我从家乡兴化调到盐城工作。这时候,我觉得我已经有了一定的教学经验积累,我于是开始了教研论文的写作。
写作动机源于一次公开课。
那是县里的一次青年语文教师优质课比赛。执教课文是初中第五册书上的《赵将括母》。我在大赛中得了第一名。
我在参赛前其实对自己很没有信心。因为谁都知道,初中语文教学更讲究教法。用高三那套应付标准化考试的做法一点用处也没有。
对于公开课,现在还有很多人提出质疑与批评,这很没有道理。作为一种公开性的教学活动,它确实让很多教师投入了比平常多得多的精力与兴奋。这让很多人都觉得公开课有点做假。但是我认为,正因为投入了很多的精力,正因为精神高度集中而又异常兴奋,公开课才更能将平常无法感受到的一些最细腻的感觉全都调动出来。一次公开课所获得的感受与心得,会成为此后教学与科研中的丰厚的养料。一次公开课就是一次提高的过程。公开课其实是杏坛的奥赛。
我此后又有很多机会执教公开课。每一次都能获得很多感悟与教训。正是这些感受的日益积累,使我的科研论文写作日益正常化,成为我生活中的一种必需。我就这样在盐城乡间那一盏优美的台灯下开始了我的科研之旅。
现在,在我写作很多年以后,我很想告诉我的同行们,教学科研中,不能以阅读别人的文章形成的一些肤浅感觉作为出发点,而应该以自己的教学实践为出发点。同样,在写作中,也不能光是援引别人教学实践中的某些经验,而应当从自身的教学实践中提炼感觉。只有这样的文章才是真文章,也只有这样的教师才能有科研上的大气象。
还有一点,语文教师的写作不能带有太大的功利性。写作是一种需要,是一种表达自己的愿望。违背了这一原则,那么势必出现一种令人遗憾的写作偏向。这一点,我在《语文教师的写作偏向》(《语文学习》2000年第12期)里已经说得非常清楚。偏向一旦形成,语文科研的写作就再也不会有任何生命力。
此外,有一点,我觉得有必要提醒我的同行。很多年轻的同行开始写作时,总想贪大,想在一篇文章中将很多方面的内容都扛起来,有的甚至一开始就想形成某些写作内容的系统性。这其实是不可能的。写作的自觉意识与敏感是要在写了很多文章之后才能形成的。只有在一定的写作经验与感觉的基础上,才能扛得起重大的题材。
写作中还要注意针对性的阅读。光是读几本杂志是远远不够的,要读教育名家的著作。(但我又认为对名家们的著述不宜读之过早。一个语文教师,他的最初的阅读,还应该是鲜活的文学作品。这一阶段很为很重要,它对构建语文教师的语言大厦起着很大的作用。大学时代的阅读与这个时期的阅读完全是两种不同的阅读。科研阶段的阅读,主要着眼于语言的感觉以及独特视角的寻找。这里有一个学与思的问题。再有,当代文学是生生不息的源头活水,一个语文教师对当代文学缺少在场的观察与感受,是不可能感觉到汉语言的丰富多彩与新鲜活泼的。作为一个语文教师,我们应该清醒地感受到,信息时代的语言也是以很快的速度在发展着的。)阅读文学名著与教育名著并能很好的吸收,这才是一个语文教师的看家本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功底。
阅读还应该广博。叶圣陶、于漪、顾黄初、钱梦龙、魏书生、陈钟梁等名家,乃至于其他一些名气不是很响的特级教师们的的论著都有一读再读的价值。而在我的阅读中,像苏霍姆林斯基、凯洛夫、赞可夫、布鲁纳、威廉·格拉塞、沙塔洛夫等教坛巨擘的著作我都没有放过,这些人是真正的教育财富。
三、写作是一种需要
一九九五年我发表了第一篇小说作品。从此一发而不可收,陆陆续续写下了近百万字的文学作品。和很多作家一样,我的写作是从阅读先锋作家开始的。九十年代的文学比起八十年代来,虽然没有了那种热度,但是这个时期的文学显得更加成熟。我的小说创作一开始就带上了先锋的印记,但我不像先锋作家一样回避现实。我在很多作品里写人们在现实中的无奈与在欲望面前的挣扎。同时,正因为我是从阅读起步的,我对当下文坛的熟稔程度就非一般人可比。这为我文学批评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很多人说我是一个边缘人,双栖的。但我比其他人更了解自己,我其实是三栖的。我在教学科研之外,在写小说之外,最近,又在评论圈子里有了自己的声音。我一九九三年发表的评论作家王朔的文论作品《这一朵美丽的罂粟花》在二○○一年被《中华文学选刊》推为当代评论王朔的主要论点之一。也是在这一年,继长篇纪实文学《重塑生命》出版后,我的评论出现了一种崭新的意象,《花城》、《青春》等几家很有影响的刊物相继发表了我四篇文学评论。二○○二年,我应著名作家李洱邀请,为《莽原》杂志主持“对话”栏目,与活跃在当代文坛的名家新秀进行深度对话,全面展示一个作家的创作成绩与文学理念。我的对话富有极强的在场性,对作家的提问也颇具挑战意味,受到读者的好评。最近我先后完成了与毕飞宇、叶兆言、刁斗和红柯的对话。
我曾有好长时间的迷惘,觉得自己好像是不务正业的。但是,我后来渐渐地发现,随着我对文学的投入,我对学生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我的课堂教学再也没有了教书匠们的那种冬烘先生的味道,取而代之的是鲜活的课堂语言与师生间亲密无间的合作。而更让我觉得欣慰的是,我的科研写作因有文学这一基础,眼界更加开阔,视角更加独到,文风更加活泼,深为一些教学杂志编辑与语文同行喜爱。最近,我又应《作文与考试》杂志之邀,主持该刊的“时文赏读”专栏。写作到了这一境界以后,我觉得,表达就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
而更加令我欣慰的是,我去年执教的一个基础较差的班级,却出现了一些非常喜欢作文的学生。2001年年底在江苏省首届高中生作文大赛中,这个班有一个学生获得了三等奖。这个获奖学生在面对学校与社会的发问时,兴奋地说:我是受了姜老师的影响才喜欢写作的。
我为自己能这样去影响一个人感到高兴。同样,我也领悟到一点,语文教学与研究要注入生命的活力与文学的活力那才是真正的教研,语文只有注入了文学的活水才是一种大语文。
我因此想对我的语文同行们说几句心里话:
文字是一种奇妙的东西。但它绝不像将军手下的士兵一样可以任何时候招之即来。对一个语文教师而言,文字的感觉有时显得很残酷。因为是文字决定着你是一个教书匠还是一个高明的教育大家。
对后一种类型的人而言,写作是一种需要。但是千万别把自己会写作当作一种特长。写作说穿了只是一个语文教师必备的技艺。在我们的身边,很多写作者的内心都很容易萌动一种陌生的欲望与丑恶。其实,写作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越来越成为自己的事了。文坛上的个人话语与私人化写作足可说明这一问题。一个语文教师,千万不要认为自己掌握了某种话语权势。否则,你会因此娇惯自己而抱怨环境,整天怨天尤人最终导致才华尽失。
一个人想要取得教育上的成功,光是有一点才华是不行的,你还必须学会与环境相容。这不是什么妥协与不妥协的问题。我们就生存在这样一个环境里。我们如果无法改变环境,那么我们就只能适应环境。与环境相谐,注意与身边的同志搞好关系,像于漪老师那样,手中总要拿着两根尺子,一把尺子量自己的短处与不足,一把尺子量别人的长处与优点,实在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所以,无论在什么场合,我对我写作的评价总是很平常。我认为这是我个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或者就像语文前辈范守纲先生对我说过的,写作其实只是自己的一种需要,是一次人生的总结,是思想的一次自我梳理。
教育是培养巨人的事业。我时时提醒自己:当我们的学生成为巨人的时候,我们自己千万不能成为矮子。
也许,这就是我选择写作的最根本的动机。
四、与高万祥共事
一九九七年,我的四万多字的中篇小说《逃离一座城市》发表,也是在这一年,我因为对乡村教育环境的绝望而开始走向城市。我到过宁波、珠海、无锡。大多是在私立学校里像一个打工仔一样很辛酸地生存着。直到二○○○年七月,我才像在沙漠里发现绿洲一样发现了张家港高级中学。这所学校的校长、著名语文特级教师高万祥先生聘我为该校教师并让我出任教科室副主任。
我非常感谢高万祥先生,是他让我进一步地走进了一种大教育的人文环境里。
我是二○○○年夏天加盟张家港高级中学的。在这里,我有幸遇上了像高万祥这样的在省内外都非常知名的语文特级教师。通过他,我又认识了朱永新、于漪、袁振国、范守纲、李镇西、任小艾等著名专家与杏坛名流并与他们成为很好的文友。在高万祥先生的提议与帮助下,学校又请北大教授、著名作家曹文轩担任我的指导教师,指导我的文学教育课题。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谈过智力背景的问题,我觉得,这种背景不独对学生而言,对教师而言,身边的名师也是自己成长的良好的智力背景。在这所学校,在走进高万祥苦心经营的“语文沙龙”以后,我更深切地感到这种智力背景对一个真正的教师是必不可少的。
高万祥校长对我的写作采取了一种少见的宽容与支持。他不但鼓励我写作,而且某种意义上讲他还是我的真正的文友与书友。我们的文字之交很深,我们的文章里有着某种共同的精神。他自己的书,一定要让我先行看过,他才交付出版;在他的指导下,我们还曾合作写过一本关于语文教学方面的书;我写的书,他精心收藏着,爱护备至。他在买得好书时,总不会忘了替我带上一册。我加入江苏省作家协会的时候,他说务必要在学校行政简报上加上这一条新闻。他还说,如果有一天你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我要发动全校为你庆贺。但高万祥先生对我要求比较高,他希望我向叶圣陶、李镇西等人学习,将文学与教育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他认为,我的《重塑生命》已经在这方面作了一次很成功的尝试。他很想将张家港高级中学办成春晖中学那样的名校,他的手下则有一大批语文名师。在世纪之交,他觉得教育应该是一种能够寄托神圣梦想的必要的乌托邦。
2001年9月,我到上海参加于漪老师从教五十周年纪念活动。在上海期间,我有幸与《语文学习》的老主编范守纲先生作了一席长谈。那一天,范守老与我谈得较多的是他在半个世纪中与叶老的交往。他告诉我,叶老对自己一生有一个总评:为人平平,为文平平。
范老一再鼓励我要以叶老等前辈大师为榜样,争取以自己的文学写作与科研成绩在当代中学语文教坛上独树一帜。他还劝诫我,无论发展到什么境界,都要像叶老那样,有一颗可贵的平常心。叶老作为一代教育大家,作为一个卓有成效的文学大师,他对自己的评价也只不过是那样的八个字,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又何德何能?
我如醍醐灌顶一般地在刹那间想到了很多很多。
而在于漪从教五十周年的纪念会上,聆听了于漪老师的讲演后,我于热泪盈眶之余更是惶愧不已。前辈大家那种风范,确实鲜有人能够企及。
至此,我真切地感觉,在进入张家港高级中学这样一所学校后,我的教研空间进入到了一种阔大高远的境界。
我为此感到特别幸福。而这种幸福,我觉得是因为身边有着像高万祥这样的语文特级教师才获得的。
如今的我,不敢说已经很有成就了。作为一个语文教师,作为一个真正走进文学写作与小说研究的作家和评论家,虽然有时候觉得抓住了文学与教育两个世界,但是,我又清醒地知道,离语文教学的最高境界,我还有着很远很远的距离。
但我坚信,我会牢牢地抓住这两个美丽的世界,走向一个真正的语文教师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