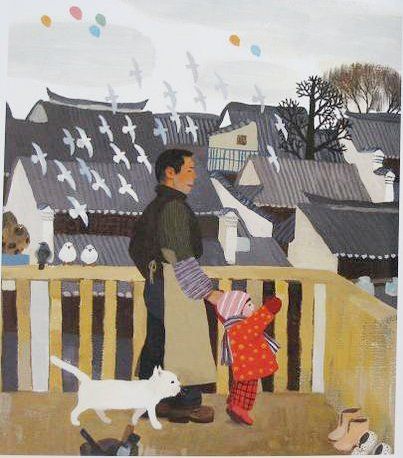- 当你的梦想与现实碰撞的时候
洋娃娃的甜品屋
对于一个忙碌的早晨,今晨就是一个星期一,是一个超级忙碌的早晨,家庭里没有什么可以吃的东西了,基本都是我不能接受的东西,比如炒米饭啊,比如方便面啊,但是今晨确实没办法,家里只有一包超级大的方便面,于是这个就成为早餐主角了。这一方方便面拯救一个家庭的早餐,而且长时间我也是不做方便面,孩子们一般情况下是吃不到方便面的,我认为这个东西不健康,对于孩子增长没有好处,于是我家一年都吃不上一顿方便面的,只有是外
- 2022-09-14
L玲珑剔透
中原焦点团队龙玲坚持原创分享第1197天(2022.9.14星期三晴)早晨依旧是五点四十的铃声,起来洗漱,收拾好之后,抓紧时间把阳台上的花浇一遍水,已经六点十几分了,就赶紧出门奔学校了。今天学校的早餐有炒米,只是不太好吃,好久没吃了,我还是吃了半碗米饭,还有一个白水鸡蛋,一碗玉米糁粥。吃完到班里,学生刚来一部分,安排他们去打扫清洁区,还有几个在班里打扫卫生。现在的孩子在家都没干过活,扫地都不会,还
- 给女儿的第1185封信 李白读完了
用书信书写父亲
田园:宝贝女儿好!你的关键词:上午下午课间、与爸跳绳二百、午间旅行箱推、快旋刺激不停、为爸手套捏脚、还得捂紧口罩、镜前蹦床欢笑、爸在地跳比高、课后不吃先作、急看哈利波特、洗漱妈读李白、激昂慷慨有趣、晨读手机录像、姜枣水喝爸端。哥哥关键词:午餐象棋半局、园拉爸推旅箱、休息无法正常、加班画写抄报、问爸可否合作、文字爸代抄写、网课用心听讲、课后作业积极、晚餐鸡蛋炒米、听课达芬奇传、饭后哈利波特、洗漱爸读
- 2022-2-13晨间日记
黄殿财
今天是什么日子起床:八点半就寝:三点天气:晴天心情:良好纪念日:还有二天元宵节叫我起床的不是闹钟是梦想自觉起床的年度目标及关键点:睡在床上想挣钱不干咋想都眠然劳动还要勤思考生活才能品味高本月重要成果:顺利完成了还个单,今天早上八点起床,先要了老板的电话,找修理工修车,搞了半天,老表有生意了,又外出了,我上停车场大门口,要了一份炒米饭,先吃饱再说。千里去做官,为了吃和穿!今日三只青蛙/番茄钟成功日志
- 2022-11-20
青溪慕兮
小区管控期间的一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排队做核酸。接下来才开启一天的生活。做早餐的食材,汤圆。将就着吃,特殊时期吗。吃完早餐后,我在阳台洗衣服,孩子在书房写作业。客厅成了我家大神的天下,他悠闲的坐在沙发上,摆好姿势,拿着手机开始玩,开启休假模式。他只有在听见孩子走出书房的声音时,才比较收敛的放下手机,来到阳台,假装在晒太阳。午饭:米饭,牛肉卷和白菜烩一锅,炒土豆丝。晚饭:鸡蛋炒米饭。
- 【日记星球第90篇】——充实的居家生活
神秘园的简书
2020年2月26日星期三(阴)图片发自App最近几天进入忙碌状态,网上办公之余,今天继续收拾书房几个整理箱,终于把书柜抽屉接近填满,为了每个抽屉必须留有余地还要重新调整一下。很多文件资料还没时间分类取舍。感恩爱人每天做那么好吃的饭菜,想少吃都忍不住。中午又做了香喷喷的炒米饭和萝卜汤,还有花生米凉拌海带,让我总是边吃边赞。午休醒来水果时间,吃了一个可爱的小橙子,按照新方法切掉两边后直接用手剥开,果
- 幸福花园
杨依琳Linda
就在这时,一个比蒂蒂尔高过一头的台子,突然出现了!上面还出现了!狗,面包和糖!就连蒂蒂尔的妹妹米蒂尔也出现在了台上!最肥胖的幸福:“来吧,和我们一同吃着点心蛋糕,烧烤,热干面,炒米,寿司,披萨,排骨和红烧肉吧!和我们一同庆祝这不散的宴席吧。”米蒂尔:“哥哥,你就不要那么固执了吧,这些吃的,真的很好吃,你也上来吃吃看,吃完你就知道了,你就知道你一吃你就停不下来了,因为实在是太美味了,比我们在家吃的好
- 没去买火腿,他不理我了
慢慢存钱
昨晚下班后老公去理发了,而在他理发回来之前,我也是带孩子出去刚回来。他回来就做饭,我说有中午剩下的米饭,他说:“给你个机会,去买根火腿吧。”我直接就说,不去!他说,那你吃啥,我说有中午剩下的豆角和蒜苔再一起炒炒,还有鸡蛋汤,配米饭或者做成蛋炒饭也行。之后不知道怎么的就生气了,准备炒米饭,他生气的说,就这样吧,米饭啥也不放了,别跟我说话了!我一听,我还生气了呢,要不是跟公婆住一起,不愿意让他们跟着着
- 2019-04-02
雨弄风
预约羽毛球2个小时,外面下着雨,影响了打羽毛球的心情,因为雨点打在室内羽毛球室的顶棚上,顶棚是一层铁皮,故而声音很大,有些位置还漏雨呢。11个人打2个场地,几乎没有什么休息时间,感觉还行吧,赢多输少。回家后喝了1小瓶LEObeer,一点点炒米饭,感觉还行吧。但晚上很久也睡不着,也许是之前喝了一瓶能量饮料,也许是太累了,身体的一种机能反应吧。中午和晚上看了2遍欢乐喜剧人第5季20190331,第一个
- 腊肠鸡蛋炒米饭,腊肠味道香醇,整盘饭都散发着腊肠的香味
遇见yh
刚刚做了一盘腊肠鸡蛋炒米饭,腊肠味道鲜美,整盘饭都散发着腊肠的香味。腊肠许多人都喜欢吃,对于吃腊肠这件事,对于喜欢吃腊肠的人来说,早已经成了一种难以割舍的习惯了。【过年做腊肠】每年过年前,一般人家都有自己制作腊肠的习惯。以前的人家从年初开始,家里都会养一头猪,等到快过年了,就高高兴兴地杀年猪过年。为了储存的方便,就会用猪肉做一些腊肠保存起来,腊肠一般不加淀粉,所以它很容易贮存。晾干的腊肠可以放好几
- 好饿啊嗯嗯
安桐都维
好饿呀,感觉自己都快饿死了,这大半夜的,肚子咕咕叫,好想吃东西啊。想吃红烧肉,排骨,再来三碗米饭了。好想点外卖,来份炒米粉,然后放点辣椒。再来羊肉汤,早点吃完早点睡觉,明天其他工地要开工了啊。一会儿就去下单。
- 翁婿对话
大海姐姐
两个不会做饭男人的对话主人公:岳父女婿一、炒米饭(中午)岳父:今儿她们娘俩不在家,咱俩中午吃什么?女婿:炒米饭吧。岳父:你会炒米饭吗?女婿:不会岳父:咱俩一起炒吧女婿:好的岳父:你说锅里放多少油合适?女婿:放多少都行吧,我也不知道啊。岳父:放葱花吗?女婿:放点儿吧岳父:放酱油吗?女婿:不知道啊岳父:放吧,可能会好吃些。于是俩人手忙脚乱的开始炒米饭。最后还放了点儿水,炒米饭成了稀饭。岳父:炒的有点儿
- 四人去内蒙古旅游5天4夜有适合全家人的旅游路线推荐吗?
旅游博主嘉尔
内蒙古旅游攻略:四人五天领略草原风光,深入感受蒙古族文化之美!一直以来,心中对内蒙古的向往如火如荼。听闻这片草原上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与丰富的蒙古族文化,我和伴侣决定展开一场浪漫的内蒙古之旅。四个人,五天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踏上这段梦幻旅程吧!小西:17769487331(长按复制、添加导游薇信、免费咨询)【吃】内蒙古的特色美食令人心驰神往。早晨,我们品尝到了传统的奶茶和炒米糕,清香扑鼻,给了我们满满
- 儿时乡村的寒冬腊月
xczxyt
小时候的我们凡是到了寒冬腊月,就天天数着指头盼年,对年总有一种独特的情怀,虽有些久远,但那记忆却刻在内心深处无法抹去。回眸儿时过年,心里便会暖暖的,它是一年中最开心和幸福的日子,可以美美地享受一番平时难得一见的油荤,也能吃上汤圆、爆米花、炒米糖和一些糖食、饼干,可以穿上漂亮的灯芯绒新衣,蓝卡其布缝的裤子,穿上母亲一针一线做的布鞋,还能得到父亲奖励的压岁钱,用长辈发的过年钱去买鞭炮。一年中所有美好的
- 壁纸:高清美图
苹果高清壁纸
防迷路-点击上方蓝色字(苹果高清壁纸)-右上角找到【…】立刻设我为星标/置顶每天17:30准时营业公众号:苹果高清壁纸请记住翻开手机,查收壁纸礼物版权声明:图文无关,发布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意图。若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络,咱们将及时删去,小时读《板桥家书》:“天寒冰冻时暮,穷亲戚朋友到门,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佐以酱姜一小碟,最是暖老温贫之具”,觉得很亲切。郑板桥是兴化
- 给女儿的第324封信 让姥爷闹心的几瓶酒
用书信书写父亲
田园:宝贝女儿好!你的关键词:陪爸一中接妈、一百数过未出、炫耀和爸互动、大声雨涵快看、和哥留宿姥家、早上爸接绘画、路问何时归家、今夜你有爸妈。哥哥关键词:送妈归来迟哭、跆拳家水魔方、晚去姥家吃睡、缠爸陪玩攻击、爸问午餐吃嘛、面条击败炒米、下午独自宅家、继续自我战斗。爸爸关键词:摩托幸福百里、一中芹家三地、两孩姥家低效、有家安置重要、早起卫哥十三、非暴关键两听、送妻岳丈好酒、货币对比解惑、谈话三方利
- 第二阶段第2天
梦已启航
HAIO五一长假的第二天,单位组织去露营️,一大早起来给孩子和老公做了鸡腿和炒米饭,吃完后老公把我们送到了单位。八点左右我们就出发了!大约两个小时的路程,我们就到了朱雀国家森林公园。当车开始进山的时候,小丫头就看着窗外的风景,边欣赏风景,边感慨好美呀!一会看到了鸡,一会看到只鸟,一会又看到樱花树,嘴上感慨着,妈妈,这是我第一次进山露营,好开心啊!开心喜悦的心情全都体现在脸上!今天是五一,进山的人很
- 家里有剩饭倒掉又可惜怎么办?那就做一份色香味俱全的番茄炒米饭吧
吃播长沙
食材:米饭、番茄、鸡蛋、火腿肠、玉米粒、洋葱、香葱、酱油、糖、五香粉1.备齐材料2.番茄洗净切丁,洋葱去皮洗净切丁,香肠洗净切丁,鸡蛋打散3.砂锅加入适量的油,煎熟鸡蛋,将鸡蛋推至边上,爆香五香粉和洋葱丁4.加入玉米粒、番茄丁翻炒5.加入香肠翻炒,最后加入米饭炒匀6.加入盐、糖、少许味极鲜酱油、香葱调味
- 儿子,你慢慢炒
知叶茶室
儿子想吃炒米,就指导他采购了食材自己做。买来火腿肠之后,儿子开始剥皮,切片。建议他切成自己喜欢的形状就好。他先切成了片状,之后,想切成小丁,征求我的意见。再次告诉他,尽自己的喜好来。他就细致地切起来。我帮他把炒菜的锅洗净,开火蒸干水分备用,然后,就离开了,叮嘱,需要我时叫我。正在喝茶,儿子过来,表示自己都切完,准备好了,接下来怎么办。我估计接下来,仅仅用嘴巴解决不了,就陪着儿子到了厨房。小家伙开火
- 177:外婆的炒米
爱琴海湾
图片发自App微友小云妈妈做的炒米非常好吃,曾被儿子誉为天下第一好吃炒米。记得那是一个下午,一个朋友送了我两袋炒米和一袋盐水豆。回到家,儿子撕开牛皮纸袋,抓了一把炒米,吧咂吧咂,吃完连声称赞。于是我也抓了一把尝尝,松脆、咸香,顿时打开了每一个味蕾的记忆,记忆里小脚外婆的炒米总是能喂饱我肚子里的馋虫。每年暑假,外婆总会挑着担子到我家来,扁担的一头挂着衣物和扫把(汪村不产竹子,外婆所在的正冲盛产竹子,
- 安昌古镇~腊月风情
蘑菇小资
安昌古镇是绍兴的一个千年历史的著名江南水乡古镇,每年元旦古镇举办的腊月风情节成了古镇的品牌活动,热闹非凡,处处可见鲁迅笔下浓浓的乡土人情。安昌土制的风腊肠,绍兴麻鸭、扯白糖风干鱼、蜜仁糕、绍兴香糕、酒香月饼、桂花香糕、桂花炒米糕、鱼肉皮子馄饨、重酥烧饼、松子糕、煎酥鱼、奶油小攀、响玲、香糕等等许多叫不上名字的小吃,让人垂涎欲滴。舌尖上的中国曾拍摄的安昌仁昌酱油作坊就在安昌镇内,一起去安昌打酱油吧!
- 2022-02-21
小陈冲冲冲
日期:2022.2.21今日收获:吃到了炒米粉,发现贡茶的芝芝莓莓挺好喝的,和朋友一起购物,吃到了一家一元icecream今日需要注意的改进之处:需要充足的钱,提前做好预算今日工作/学习是否完成:没有完成任务,还有视频课没有看完有什么关于提高效率的想法:专注,学就好好学,玩就好好玩有什么奇奇怪怪的想法:今天逛宜家发现,虽然有些东西几块钱,像是杯子,有些东西三四十,在当时身处环境购物比在网上购物对于
- 水乡之恋:炒炒米
小刺猬乖乖
【原创作品】【侵权必究】小时候炸炒米还算比较常见,吃过炸炒米的人自然不少。但要说到炒炒米,见过吃过的人恐怕就不多了。长这么大我所知道会炒炒米的只有一位,是小时候我们庄上的一位老奶奶,恰巧也是我们家的邻居。印象中出了我们庄我从来没见过炒炒米,更没吃过,也没听说过哪里还有人会炒。那时庄上几乎所有大人都喊那位奶奶“茂奶奶”,他们自己家孙辈则习惯于喊她“太太”。【侵权必究】茂奶奶个头不高,走起路来脚步碎,
- 菜米油盐那些事5
逸琼
今天早晨,早早起来给孩子做饭,炒米饭和鸡蛋汤,鸡蛋汤里加了胡萝卜香菇海带和豆腐,还有一丁点粉条,是不是很有创意?反正孩子吃的很多,米饭也吃了些最后说如果炒米时加点肠更好。中午做了麻辣烫,内容也很丰富,在上次用西红柿和火腿肠做锅底的基础上加了一点八角。然后煮香菇丸子豆腐土豆等最后加上油麦菜菠菜和香菜,出锅后放麻酱。当然了还热了一个包子一个馒头,结果我两都吃麻辣烫,那两样剩下。下午,孩子说身体不适,让
- 0905学玩两不误
kytee
今天虽然是周末,小马同学还是很早就起来读英语,是第一个打卡的,阅读了20分钟。我则起来准备早饭,今天用了一碗胡萝卜丁+一碗香肠丁+三个鸡蛋一起炒的米饭,又煮了一个玉米,感觉最近炒米饭炒出感觉了,哈哈,虽然重复,但熟能生巧可能也是有点儿那个意思,对于配料和火候等的把握逐渐找到点儿感觉。想来做饭炒菜和做研究搞开发是类似的,首先要有兴趣,自己如果能主动投入时间去钻研和多做尝试,就能不断积累经验和提升水平
- 中秋拜月
芽儿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中秋,却没有什么节日的气氛,一个是因为疫情肆虐,正处于人心惶惶的时刻,另一个是这几年各种传统节日都似乎过的越来越没有氛围了。晚餐是炒米粉,炖牛肉和虾,跟平常差不多的样子。并没有什么太大节日的感觉,敬了老公一杯饮料,说一句中秋快乐,就算过了节了。小时候的过节似乎更有气氛,也许跟那时候物质生活比较匮乏有关,总在节日的时候会有好吃的。也行是那时候年龄小,小孩子容易被过节气氛带动。记得小时
- 五月初五系龙舟节啊,阿妈她叫我去睇龙船
亦泪yilei
氹氹转啊菊花园炒米饼糯米糯米团五月初五系龙舟节啊阿妈她叫我去睇龙船我唔去睇我要睇鸡仔鸡仔大我拎去卖卖得几多钱卖咗几多只呀我有只风车仔佢转得好好睇睇佢氹氹转呀菊花园睇佢氹氹转呀氹氹转又转这是一首我们小时候经常听的儿歌,今天是端午节,情不自禁就想唱这首歌了,想唱就唱要唱的响亮。一大早吃了个自己包的粽子,心情难得很欢乐。可惜今年端午不能跟自己爸妈过,虽然经常见,但是节假日总是更想见。待会要跟ZB一家人去
- 2023-05-13
敖夜的码字日记
今天又是划水的一天。没有构思小说。也没有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算是摆烂吧。不过心情倒是挺轻松的。平时构思点子和剧情,精神内耗挺严重的。昨晚熬夜看了一宿的老三国。大概六点多睡觉。醒来已经是下午七点多了。醒来后点了一碗新疆炒米粉,感觉没有之前点的好吃。一边吃着一边看今天的LOL比赛。就这样,一天又要过去了。想起今天的日更还没有完成。于是又来水一下字数。没有什么想写的,只能发一下无意义的文字凑下字数。就这
- 7.7记录每一天
月光下的筱儿
7.7支教今天,是每周支教下乡的日子早晨听课两节评课一节通过听课,交流我感受到了大家的进步我也学到了很多虽然早晨忙碌内心却是充实的感恩……亲子篇每天为了这小吃货的肚子我也是绞尽脑汁早餐~三明治、鸡蛋、豆浆午餐~炒米饭~~(补充营蛋白)晚餐~鸡翅~薯条(买的新厨具做的,效果不错,不用油,健康饮食,值得拥有)不过,时间少了,颜色不太好看。11:35支教评课结束12:05到家12:40饭菜上桌然后看着探
- 至亲的话
以黔
回家快两个星期了,我每天做饭,洗衣服,收拾东西房间我爸都没看到,今天我下午做炒米粉,做完没收拾,碗没洗,我爸回来说的我一文不值,我的确是,我懒得拖地,懒得做饭,懒得起床,懒得学习,我只是做的事,他没看见,在他这里,我就是好吃懒做,不收拾家里,不洗碗做饭,只会顶嘴,只会摆烂的人。我是摆烂了,我该振作起来吧!我该积极一点面向生活。
- github中多个平台共存
jackyrong
github
在个人电脑上,如何分别链接比如oschina,github等库呢,一般教程之列的,默认
ssh链接一个托管的而已,下面讲解如何放两个文件
1) 设置用户名和邮件地址
$ git config --global user.name "xx"
$ git config --global user.email "
[email protected]"
- ip地址与整数的相互转换(javascript)
alxw4616
JavaScript
//IP转成整型
function ip2int(ip){
var num = 0;
ip = ip.split(".");
num = Number(ip[0]) * 256 * 256 * 256 + Number(ip[1]) * 256 * 256 + Number(ip[2]) * 256 + Number(ip[3]);
n
- 读书笔记-jquey+数据库+css
chengxuyuancsdn
htmljqueryoracle
1、grouping ,group by rollup, GROUP BY GROUPING SETS区别
2、$("#totalTable tbody>tr td:nth-child(" + i + ")").css({"width":tdWidth, "margin":"0px", &q
- javaSE javaEE javaME == API下载
Array_06
java
oracle下载各种API文档: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java/embedded/javame/embed-me/documentation/javame-embedded-apis-2181154.html
JavaSE文档:
http://docs.oracle.com/javase/8/docs/api/
JavaEE文档:
ht
- shiro入门学习
cugfy
javaWeb框架
声明本文只适合初学者,本人也是刚接触而已,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小有收获,特来分享下希望和大家互相交流学习。
首先配置我们的web.xml代码如下,固定格式,记死就成
<filter>
<filter-name>shiroFilter</filter-name>
&nbs
- Array添加删除方法
357029540
js
刚才做项目前台删除数组的固定下标值时,删除得不是很完整,所以在网上查了下,发现一个不错的方法,也提供给需要的同学。
//给数组添加删除
Array.prototype.del = function(n){
- navigation bar 更改颜色
张亚雄
IO
今天郁闷了一下午,就因为objective-c默认语言是英文,我写的中文全是一些乱七八糟的样子,到不是乱码,但是,前两个自字是粗体,后两个字正常体,这可郁闷死我了,问了问大牛,人家告诉我说更改一下字体就好啦,比如改成黑体,哇塞,茅塞顿开。
翻书看,发现,书上有介绍怎么更改表格中文字字体的,代码如下
- unicode转换成中文
adminjun
unicode编码转换
在Java程序中总会出现\u6b22\u8fce\u63d0\u4ea4\u5fae\u535a\u641c\u7d22\u4f7f\u7528\u53cd\u9988\uff0c\u8bf7\u76f4\u63a5这个的字符,这是unicode编码,使用时有时候不会自动转换成中文就需要自己转换了使用下面的方法转换一下即可。
/**
* unicode 转换成 中文
- 一站式 Java Web 框架 firefly
aijuans
Java Web
Firefly是一个高性能一站式Web框架。 涵盖了web开发的主要技术栈。 包含Template engine、IOC、MVC framework、HTTP Server、Common tools、Log、Json parser等模块。
firefly-2.0_07修复了模版压缩对javascript单行注释的影响,并新增了自定义错误页面功能。
更新日志:
增加自定义系统错误页面功能
- 设计模式——单例模式
ayaoxinchao
设计模式
定义
Java中单例模式定义:“一个类有且仅有一个实例,并且自行实例化向整个系统提供。”
分析
从定义中可以看出单例的要点有三个:一是某个类只能有一个实例;二是必须自行创建这个实例;三是必须自行向系统提供这个实例。
&nb
- Javascript 多浏览器兼容性问题及解决方案
BigBird2012
JavaScript
不论是网站应用还是学习js,大家很注重ie与firefox等浏览器的兼容性问题,毕竟这两中浏览器是占了绝大多数。
一、document.formName.item(”itemName”) 问题
问题说明:IE下,可以使用 document.formName.item(”itemName”) 或 document.formName.elements ["elementName&quo
- JUnit-4.11使用报java.lang.NoClassDefFoundError: org/hamcrest/SelfDescribing错误
bijian1013
junit4.11单元测试
下载了最新的JUnit版本,是4.11,结果尝试使用发现总是报java.lang.NoClassDefFoundError: org/hamcrest/SelfDescribing这样的错误,上网查了一下,一般的解决方案是,换一个低一点的版本就好了。还有人说,是缺少hamcrest的包。去官网看了一下,如下发现:
- [Zookeeper学习笔记之二]Zookeeper部署脚本
bit1129
zookeeper
Zookeeper伪分布式安装脚本(此脚本在一台机器上创建Zookeeper三个进程,即创建具有三个节点的Zookeeper集群。这个脚本和zookeeper的tar包放在同一个目录下,脚本中指定的名字是zookeeper的3.4.6版本,需要根据实际情况修改):
#!/bin/bash
#!!!Change the name!!!
#The zookeepe
- 【Spark八十】Spark RDD API二
bit1129
spark
coGroup
package spark.examples.rddapi
import org.apache.spark.{SparkConf, SparkContext}
import org.apache.spark.SparkContext._
object CoGroupTest_05 {
def main(args: Array[String]) {
v
- Linux中编译apache服务器modules文件夹缺少模块(.so)的问题
ronin47
modules
在modules目录中只有httpd.exp,那些so文件呢?
我尝试在fedora core 3中安装apache 2. 当我解压了apache 2.0.54后使用configure工具并且加入了 --enable-so 或者 --enable-modules=so (两个我都试过了)
去make并且make install了。我希望在/apache2/modules/目录里有各种模块,
- Java基础-克隆
BrokenDreams
java基础
Java中怎么拷贝一个对象呢?可以通过调用这个对象类型的构造器构造一个新对象,然后将要拷贝对象的属性设置到新对象里面。Java中也有另一种不通过构造器来拷贝对象的方式,这种方式称为
克隆。
Java提供了java.lang.
- 读《研磨设计模式》-代码笔记-适配器模式-Adapter
bylijinnan
java设计模式
声明: 本文只为方便我个人查阅和理解,详细的分析以及源代码请移步 原作者的博客http://chjavach.iteye.com/
package design.pattern;
/*
* 适配器模式解决的主要问题是,现有的方法接口与客户要求的方法接口不一致
* 可以这样想,我们要写这样一个类(Adapter):
* 1.这个类要符合客户的要求 ---> 那显然要
- HDR图像PS教程集锦&心得
cherishLC
PS
HDR是指高动态范围的图像,主要原理为提高图像的局部对比度。
软件有photomatix和nik hdr efex。
一、教程
叶明在知乎上的回答:
http://www.zhihu.com/question/27418267/answer/37317792
大意是修完后直方图最好是等值直方图,方法是HDR软件调一遍,再结合不透明度和蒙版细调。
二、心得
1、去除阴影部分的
- maven-3.3.3 mvn archetype 列表
crabdave
ArcheType
maven-3.3.3 mvn archetype 列表
可以参考最新的:http://repo1.maven.org/maven2/archetype-catalog.xml
[INFO] Scanning for projects...
[INFO]
- linux shell 中文件编码查看及转换方法
daizj
shell中文乱码vim文件编码
一、查看文件编码。
在打开文件的时候输入:set fileencoding
即可显示文件编码格式。
二、文件编码转换
1、在Vim中直接进行转换文件编码,比如将一个文件转换成utf-8格式
&
- MySQL--binlog日志恢复数据
dcj3sjt126com
binlog
恢复数据的重要命令如下 mysql> flush logs; 默认的日志是mysql-bin.000001,现在刷新了重新开启一个就多了一个mysql-bin.000002
- 数据库中数据表数据迁移方法
dcj3sjt126com
sql
刚开始想想好像挺麻烦的,后来找到一种方法了,就SQL中的 INSERT 语句,不过内容是现从另外的表中查出来的,其实就是 MySQL中INSERT INTO SELECT的使用
下面看看如何使用
语法:MySQL中INSERT INTO SELECT的使用
1. 语法介绍
有三张表a、b、c,现在需要从表b
- Java反转字符串
dyy_gusi
java反转字符串
前几天看见一篇文章,说使用Java能用几种方式反转一个字符串。首先要明白什么叫反转字符串,就是将一个字符串到过来啦,比如"倒过来念的是小狗"反转过来就是”狗小是的念来过倒“。接下来就把自己能想到的所有方式记录下来了。
1、第一个念头就是直接使用String类的反转方法,对不起,这样是不行的,因为Stri
- UI设计中我们为什么需要设计动效
gcq511120594
UIlinux
随着国际大品牌苹果和谷歌的引领,最近越来越多的国内公司开始关注动效设计了,越来越多的团队已经意识到动效在产品用户体验中的重要性了,更多的UI设计师们也开始投身动效设计领域。
但是说到底,我们到底为什么需要动效设计?或者说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动效?做动效设计也有段时间了,于是尝试用一些案例,从产品本身出发来说说我所思考的动效设计。
一、加强体验舒适度
嗯,就是让用户更加爽更加爽的用
- JBOSS服务部署端口冲突问题
HogwartsRow
java应用服务器jbossserverEJB3
服务端口冲突问题的解决方法,一般修改如下三个文件中的部分端口就可以了。
1、jboss5/server/default/conf/bindingservice.beans/META-INF/bindings-jboss-beans.xml
2、./server/default/deploy/jbossweb.sar/server.xml
3、.
- 第三章 Redis/SSDB+Twemproxy安装与使用
jinnianshilongnian
ssdbreidstwemproxy
目前对于互联网公司不使用Redis的很少,Redis不仅仅可以作为key-value缓存,而且提供了丰富的数据结果如set、list、map等,可以实现很多复杂的功能;但是Redis本身主要用作内存缓存,不适合做持久化存储,因此目前有如SSDB、ARDB等,还有如京东的JIMDB,它们都支持Redis协议,可以支持Redis客户端直接访问;而这些持久化存储大多数使用了如LevelDB、RocksD
- ZooKeeper原理及使用
liyonghui160com
ZooKeeper是Hadoop Ecosystem中非常重要的组件,它的主要功能是为分布式系统提供一致性协调(Coordination)服务,与之对应的Google的类似服务叫Chubby。今天这篇文章分为三个部分来介绍ZooKeeper,第一部分介绍ZooKeeper的基本原理,第二部分介绍ZooKeeper
- 程序员解决问题的60个策略
pda158
框架工作单元测试
根本的指导方针
1. 首先写代码的时候最好不要有缺陷。最好的修复方法就是让 bug 胎死腹中。
良好的单元测试
强制数据库约束
使用输入验证框架
避免未实现的“else”条件
在应用到主程序之前知道如何在孤立的情况下使用
日志
2. print 语句。往往额外输出个一两行将有助于隔离问题。
3. 切换至详细的日志记录。详细的日
- Create the Google Play Account
sillycat
Google
Create the Google Play Account
Having a Google account, pay 25$, then you get your google developer account.
References:
http://developer.android.com/distribute/googleplay/start.html
https://p
- JSP三大指令
vikingwei
jsp
JSP三大指令
一个jsp页面中,可以有0~N个指令的定义!
1. page --> 最复杂:<%@page language="java" info="xxx"...%>
* pageEncoding和contentType:
> pageEncoding: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