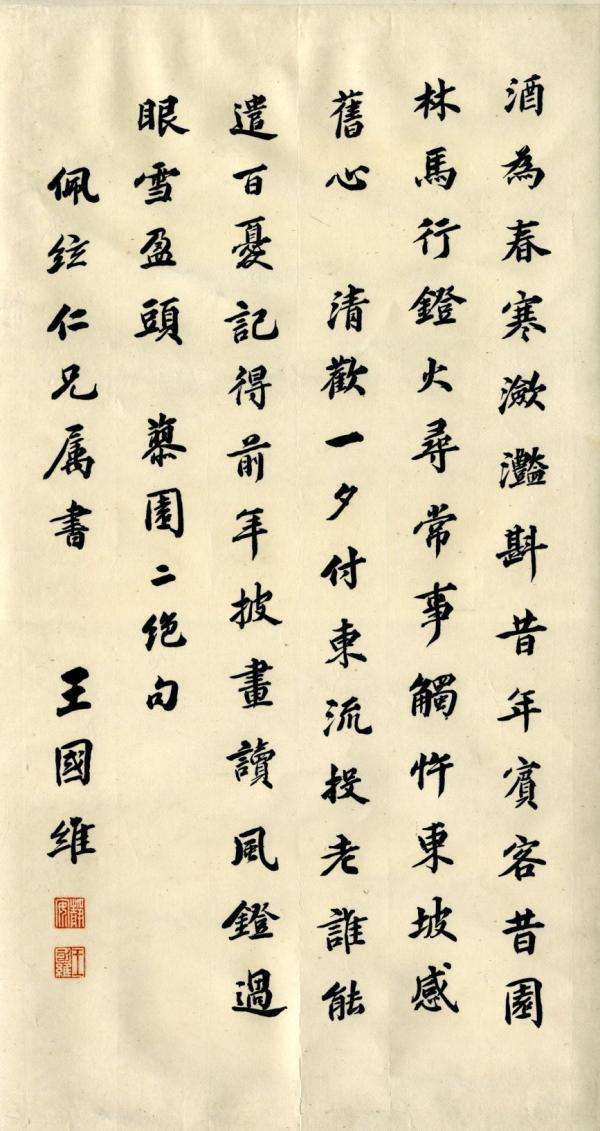他在《人间词话》中留下最广为人知的三个境界理论。古今成大事业者,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境界: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后来才知这三重境界的含义实为:
看山是山,看水是水;
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
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
梁启超赞他,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所有的学人。
郭沫若评他,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物,那好像一座崔巍的楼阁,在几千年的旧学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胡适说:王国维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
而王国维自己说:“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
因为政治家只能谋求物质利益,文学家则可以创造精神之利益。
“夫精神之与物质二者孰重?物质上利益一时之也,精神上利益永久之也”。
他身材不怎么高大,面孔也小,有点龅牙。
常着罗缎短袖马褂,后面拖一条小辫子。
不是很新潮,也不适合很古板,但很整洁。
他的物质生活随随便便,却没有一点遗老或是名流的气味。
就这样一位老先生,不知底细的人单看衣饰相貌,很可能把他当做乡下佬。
一次,日本学者桥川时雄拜访王国维,行至清华门口,留着辫子的门房问桥川时雄找谁,当被告知后,门房立刻恭敬第对他说:“你真了不起。”
桥川很是不解,问为什么,门房答:“拜访那位留辫子的先生的人,都很了不起。”
读经书,考秀才,中进士,经世致用,光宗耀祖。
这是父亲王乃誉对王国维的培养计划。
而这位开放的学人,在他的一生读书历程中,成就可不只是光宗耀祖。
他精通英文,日文,能阅读德文版哲学原著。
他是中国学者研究康德,叔本华,尼采等西方哲学家的先驱。
他写的《人间词话》《宋元戏曲史》《红楼梦评论》,是文学界的经典名著。
他的甲骨学,文字音韵训诂之学,考据学和古器物研究成果,更是当今史学界无法逾越的学术空间。
从知识结构上说,王国维真正做到了融合中西,学贯古今。
他在《国学丛刊》序中提出: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
哲学上说,大部分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
王国维是做了可爱又可信之人。
从乏味的学术问题入手揭示人生的目的和意义的怕是只有他了。
郭沫若说:“卜辞的研究,要感谢王国维。……我们要说,殷墟的发现,是新史学的开端;说王国维的功绩,是新史学的开端,那是丝毫不过分的。”
王国维认为,人的精神是有限的,每天从朝气到暮气。
所以上午宜读经典考据书,午后宜读史传,晚间宜读诗词杂记。
他这说也是这样做的。
处处严谨,不营生计,不图享受。
虽名满天下,却心无旁骛,甘于清贫。
1925年,清华本想请他做国学院院长,王国维却以不想为行政事务分心拒绝,只任导师。
故此国学院院长由吴宓以办公室主任的名义兼理。
真正生活到极致的人,一定是素与净。
他的一生,可能没有娱乐两个字。
对中国戏曲有很深的研究,却从来没有去看过戏。
有人慕名求字,他一概拒绝。
他说“这是应酬,我没兴趣。”
他不会画画,小孩子缠着他要画人,他只会画一个策杖老人或一叶扁舟。
他在学术之外的生命并不很丰富,似乎寥寥几笔就能概括完。
但他对孩子,有格外的耐心和慈爱。
时值1927年,刚过天命之年的王国维带着四重身份,离开清华研究院公事房。
坐车前往颐和园,他的终点是昆明湖。
面对动荡的时局,他淡然自若的说“我自有办法”。
在微澜的湖水前,扑通一声,不见了人。
悄无声息,仿若平常,一如他的名字——静安。
他曾写过:“社会上之习惯,杀许多善人。文学上之习惯,杀许多天才。”
伴随一封遗书的面世,王国维永别了他曾反反复复咏叹的人间。
当我们惋惜这位不善交往的国学先生时,避不开一份极其冗长的吊客名单,从中可以窥见王国维在学界的影响……
张慧剑说:“中国有三大天才皆死于水,此三人者,各可代表一千年的中国文艺史——第一个一千年是屈原,第二个一千年是李白,第三个一千年是王国维。”
鲁迅说: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
梁启超这样评价:此公治学方法,极新极密,年仅五十一岁,若再延十年,为中国学界发明,当不可限量。
老友陈寅恪为王国维写下墓志铭:
先生之论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不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久,共三光而永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