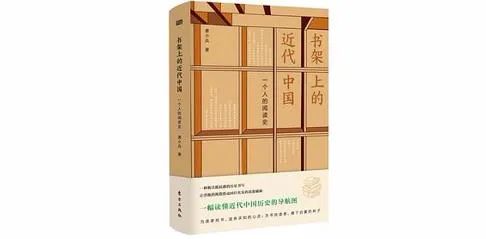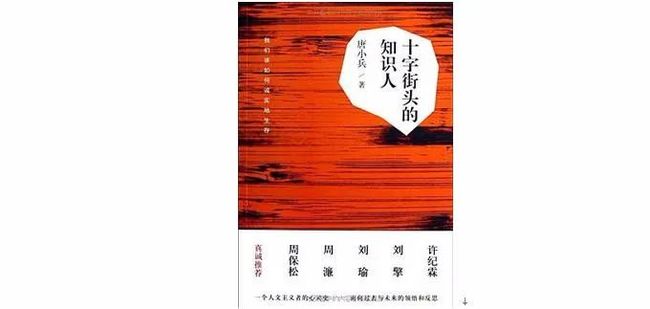知识分子凭什么自诩为“以天下为己任”的启蒙者?——评唐小兵《书架上的近代中国》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唐小兵教授,多年来,致力于晚清民国报刊史、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与20世纪中国革命等议题的研究。在最新的著作《书架上的近代中国》中,他以书评的方式纵论近代中国的历史转向,以及其中的知识分子命运,他力图把握精英与大众的关系,并重思知识分子在近代遭遇的公共信任危机。
撰文丨西闪
对我来说,好的书评就像一封推荐信,可以让我更自信地面对原著。问题是现在什么人都在写“推荐信”,值得信任的太少。学者唐小兵先生说,每个书评人都应该有一片属于自己的瓦尔登湖,用湖光映照世界。这是自我期许,少有人达到他的境界。
读唐小兵的《书架上的近代中国》,这种感受愈发强烈。在这本书中,他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理解,对知识分子命运的剖析,对精英与大众关系的把握,对地方文化生活的尊重,无不体现出一个书评人的优良素养。扪心自问,我是否达到他对书评人的要求?颇难自许。稍觉欣慰的是,他评论的书我也读过一些,故而有类似的思考,也有讨论的基础。
《书架上的近代中国》唐小兵著,东方出版社,2020年3月
01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先天不足”
中国近现代的进程既宏大又诡谲,就像暗夜里的大江,裹挟着所有人。无论大家清醒,还是懵懂,很难不让我想起著名的“历史三峡论”。在唐德刚先生看来,近现代中国必有一个穿越三峡的命运,虽说滩险流急,煎熬漫长,终有扬帆直下海阔天空的大局。真心觉得,这种带有历史终结论色彩的预言乃是一厢情愿——因为三峡过后,不确定性仍在。
记得唐小兵在《十字街头的知识人》一书里也不认可历史三峡论,但唐德刚对胡适的某些看法,他在新著里却有所肯定。而这些看法,归根结底是对以胡适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批评。其核心的指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先天不足”,导致这个群体不乏介入政治的勇气,却缺乏介入政治的能力和智慧。
《十字街头的知识人》唐小兵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12月
在新作《书架上的近代中国》里,唐小兵明显深化了这一议题。于他看来,传统士人转型为近代知识分子,这个过程本身就包含着复杂的利弊得失。在“政教合一”的传统政治中,士人是中心人物,他们不但负责正统意识形态的生产和传播,也实际从事政治活动和行政事务。而近代知识分子不一样,他们中的大部分脱胎于传统士人,却失去了从事政治和行政的空间和地位,也不再有承担正统意识形态的责任和义务。他们中的另一部分,本来就“野蛮生长”在广东、上海、四川等边缘地域,天然地具备“远庙堂,近江湖”的侠气,却又不乏士人传统浸淫而来的介入政治的壮志雄心。
唐小兵引了史家杨国强先生的一段话,我觉得很有意思。杨先生说,在传统士人蜕变为近代知识分子的过程中,“知识人与圣贤意态越离越远,与豪杰意态越趋越近”,以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近代化”与“志士化”常常叠合在一起难分彼此,在自觉、自省、富有激情的同时,又带着极端、粗鄙和暴戾的特质。
这个独特的知识阶层对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唐小兵没有明言。他只是克制地写到,要检讨20世纪中国多舛的历史和命运,不能不从反思和批判的立场多加审视这一段波澜起伏的转型。这让我不禁发问,难道知识分子的转型如此重要,足以决定一个国家的兴衰?
书中没有明确的答案。然而毫无疑问,知识分子的命运是《书架上的近代中国》主要的线索之一。沿着这条线,唐小兵的目光从晚清一直延伸到20世纪上半叶。他注意到国家认同的建构过程中知识分子的积极作用,同时也不忘提醒,这个群体的固有缺陷必然带来的消极后果。假如说,革命、启蒙、内战和阶级斗争,是中国近现代史的命运节点,那么这些节点的意义则是由知识分子来确立的。从这个角度看,把中国的命运与知识分子的命运视为互为表里的关系也不为过。
清华国学五大导师(左起: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宓)。
02
精英与民众之间的深刻矛盾
就像唐小兵在书中反复谈到的,中国知识分子既是多重危机的产物,也必然是多重任务的承担者。民族要觉醒、国家要强盛、个人要自由、阶级要“翻身”,不同的危机对应着不同的任务。问题在于,这些不同的危机在这个国家几乎连锁爆发。它们相互牵涉又相互制约,孰轻孰重,让人们难以取舍穷于应付,以至于某些理应成为共识的价值理念迄今仍未完全落地。
书中有一段文字颇能证明知识分子的窘境,它出自1912年梁启超写给袁世凯的信。信中写道:“以今日民智之稚、民德之漓,其果能产出健全之政党与否,此当别论。要之,既以共和为政体,则非多数舆论之拥护,不能成为有力之政治家,此殆不烦言而解也。善为政者,必暗中为舆论之主,而表面自居舆论之仆,夫是以能有成。”信中透出的对民众的蔑视、对舆论的曲解、对民主政治的误读,无不让我生疑:作为危机的产物,知识分子真的清楚什么是危机吗?须知梁启超是那个时代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之一。
看清危机是解决问题的前提。以梁启超为例,这个前提条件并非想象的那么容易达成。反过来,如果这个前提无法满足,知识分子凭什么还可以自诩为“以天下为己任”的启蒙者呢?唐小兵用一段精彩的文字刻画了其中的矛盾:“启蒙者需要戴上人民的面具,伪装成大众的一员,暗中引领无知而混沌的大众,从黑暗王国的洞穴里走出来。这需要他们在公共舆论中将人民无限美化和神化,也将民间和底层乌托邦化,这就刺激了中国的游民文化与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无缝对接,同时,启蒙者又时时按捺不住驯化人民和蔑视民众的隐秘心态。”细细想来,这样的启蒙,与诱劝有多大分别?
青年梁启超。
认清危机只是应对危机的第一步,必须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举国共识,也就是梁启超所谓的“公共的信条”,然而用近乎诱劝的启蒙不可能达成目的。唐小兵在多篇文章中讨论了精英与民众之间的这种深刻的矛盾。正如他所指出的,当民众成了操纵的对象,对精英的怀疑和抵触就成了普遍的情绪。他认为,民国政治从议会民主蜕变为派系纷争,再堕落为军阀割据,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知识分子的急功近利。他们无暇等待举国共识的春华秋实,动不动就想“改弦易辙弯道超车”。结果呢?他们中有不少人像传统文人那样委身权力,扮演着宾客幕僚的角色。一时间,文人主政,武夫当国,中国退回到传统政治的运作模式,从而给暴力革命埋下了伏笔。
知识分子如此偏激躁进,也难怪唐小兵会认为,现代中国的启蒙运动包含着自我瓦解甚至自我摧毁的基因。不知道他是否意识到结论的灰暗沉郁,在我看来,他对成都文化、上海文化以及广东文化的评论,为《书架上的近代中国》添上了几笔亮色。在这些研读和分析中,广东的地方知识分子、成都茶馆里的市井茶客、上海洋行里的经理人,以及活跃在江浙一带的商贾买办,共同构成了复杂多元的地方生态,抵抗着也丰富着中国近现代的叙述。
唐小兵对地方文化的评述,让我继续思考知识分子如何应对危机的命题。为什么他们在探索解决之道的时候,如此没有耐心?其中有没有一个原因是对多元复杂的现实世界缺乏理解和同情?如果没有如此觉悟,当知识分子面对家国危机的时候,会不会像大多数人处理个人生活的重大危机那样,要么怨天尤人,要么随波逐流,始终不肯诚实地评估困境,又或者彻底否定自身的价值,将如今的遭遇归咎于“业报”,把自己贬得一无是处?
唐小兵似乎提前预感到了读者的困惑。为了考察知识阶层的命运,他用了不少笔墨在具体而微的个体之上。他在梁启超、蔡元培、周作人、傅斯年等人的著述和言辞里爬梳剔抉,也从陈寅恪、吴宓、沈从文、殷海光等人的书信、日记和回忆录中追寻脉络。书中这一部分散发着体温的文字,不仅让人觉得亲切,也提醒着我这样的读者,不可把过往的一切都想得那么悲观失败。这时候我方才醒悟,作者的思考有多么周全体贴。假如把《书架上的近代中国》当作一幅思维导图,唐小兵不仅呈现了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国近现代变迁的关系,也将自己为何思考以及如何思考的过程展现了出来。
03
对自然科学知识分子考察的缺失
当然,也并非十全十美。我认为在唐小兵的思维导图里缺了一块拼图,那就是对自然科学知识分子的考察。我们老爱讲科技对一个国家如何重要,也不否认它在中国近现代进程中的重要作用,那么为什么学者们在讨论历史命运之时,不知不觉地把讨论的对象限定在人文知识分子的范围内呢?是因为生物学家、气候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数学家和医生没有在这一进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还是说他们失去了发声的机会和能力?又或者,被学者们有意无意间忽略了?
《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葛兆光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5月
正是因为想到这个问题,我对书中殷海光与林毓生的书信内容有些不以为然。他们认为电视是邪魔外道,收音机更是烦躁之源,时代的症结在于“技术肥肿,伦范消瘦”,在于科学压倒了人文,造成人类精神萎缩。而在我看来,这类精英主义的话语,恰恰应该对中国近现代的悲剧性命运负上一定的责任。
有意思的是,唐小兵把他对葛兆光的研读放在殷海光之后,巧妙地做了一次观念的“再平衡”,因为葛兆光的思想史研究正是对精英主义的反动。一本以书评为主的文集,竟然在谋篇布局上下足工夫,我很佩服。
![]()
本文为独家原创稿件,作者:西闪;编辑:徐伟;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