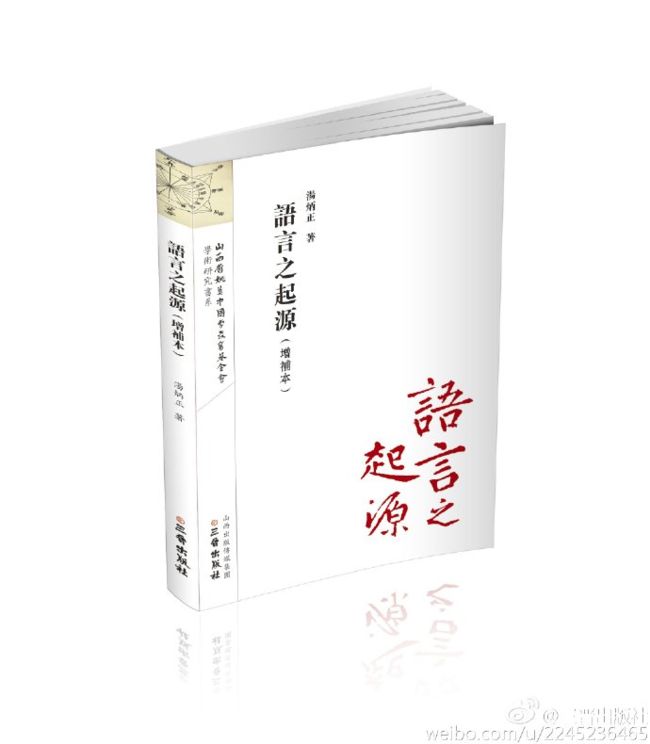《语言之起源》(增补本)編後記
汤序波
汤炳正《语言之起源》(增补本)出版
本报讯汤炳正先生学术代表作《语言之起源》(增补本)新近由三晋出版社出版。此书原版1990年由台湾贯雅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这次出版增加了三分之一的篇幅。汤先生系当代著名语言学家,20世纪30年代受业于章太炎先生之门,并担任太炎先生创办的“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小学主讲教席,学术界认为他的语言起源研究“为世人揭开了人类语言起源之谜”。
《中华读书报》( 2015年10月14日02 版)
本書係先祖父景麟公一九九〇年在臺灣貫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的《語言之起源》的“增補本”。正編凡註明出處者以及兩組附錄皆為今次新補;這個本子囊括了目前所能找到的先祖父有關“小學”的全部著述(《齊東古語摘錄》一文因篇幅過小,且先祖父晚年曾作過擴充、並撰有跋語者已不知去向,故茲未收)。在我已理董出版的景麟公書稿中,數這一部難度最大。青燈黃卷,一個字一個字地校勘,耗時三年有餘。即使如此,仍覺心中無底,深怕做得不好,一来對不住一輩子獻身學術的景麟公,二来怕有負讀書人。
景麟公生前,因出版環境的惡劣,加之所研究對象的深僻,此書原稿在內地找不到出版社,最後衹得輾轉寶島出版。這對他來說,當然是退而求其次的選擇。過去因兩岸文化交流的不對等,大陸學界很少能看到臺灣出版的書籍,最多是聞其書名而已。如四川大學前些年啟動《儒藏》編纂工程時,其《史部·儒林年譜》收先祖父所造《楊子雲年譜》一文,所用底本係一九三七年發表在無錫《論學》雜誌上的。其實,在編入《語言之起源》一書之前,先祖父已對該文作了精心補訂;未能用此定本於這部大書中,顯然是個遺憾。景麟公走後,為了使學界中人能更好地了解這方面的研究成果,我曾復製了二十餘份分赠師友同好,不言而喻,是远远不能滿足需求的。有鉴於此,我於大前年着手理董此書,並把消息公諸網上。很快著名出版人賈勤先生留言:“我是北京新世界出版社‘木鐸學刊’的編輯,我們可以出版此書。”賈先生主持的“文庫”,對國學“傳火添薪”,其氣魄與膽識令世人敬佩。書稿入選“文庫”,我幸何如之。
景麟公覃思著述而重獨創,不管是多麼深奧的課題,總能以簡練之筆出之。如關於語言起源的研究,他顛覆了中外語言學界的傳統說法,創立了自己嶄新的語源學說。完成這麼大的課題,所用的文字不過區區四萬言。何其精粹、何等才具,與那些動輒数十万字而未得要領者比,相去難以道里計。另外,對楊雄生平與其學術的研究,先祖父用力亦勤甚(一讀《〈法言〉版本紀要》即明)。他在這一領域的研究成果,至今仍因具獨特的價值而為研究者所重。
景麟公學術能取得如此的成就,小学功夫至关重要。近讀張聞玉老師賜下的《中國人學問之路》,他寫到國內“一個很有名氣的教授”來其所在大學作學術報告,“我們中途就走了,不是他講得不好,衹是小學功夫差”。又說:“傳統的學術以小學為基本功,再去發展,基本功不好,衹能在底層徘徊,不能做學問。”“研究中國學問,必須要讀得通文獻,讀懂文獻方能研究,要有這個本領,這個本事就是小學。”但在當下,說到小學,無論一般的讀書人,即使一些學者專家,恐怕也覺隔膜生疏。有人追問,為什麼新中國沒有出“國學大師”?當然這不是一兩句话能講清的事。不過,竊以為一九四九年後,薄古而厚今,教育界“全盤蘇維埃化”,高校取締小學課程,截斷小學命脈,當是個致命傷。彼時有一種觀點因意識形態的需求,被無限地放大,繼而成為主流與時尚:即漢字落後了,應實行拼音文字[if !supportFootnotes][1][endif]。甚至還創辦《文字改革》雜誌作鼓吹。最高领袖也介入,說“文字必須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 (實際上他的想法是“要消滅漢字,改用拉丁字”)。有位著名語言學家道:“簡化漢字衹是治標”、“要真正解決問題還是得搞拼音文字”。漢字都要被廢除了,“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小學還能存在嗎?世間還需要小學家來“說文解字”嗎?景麟公這一代以小學教、研為志業者,遭遇了這門學科自創立以來最為尷尬的局面(過去小學家可名列儒林,是甚受尊敬且禮遇甚隆的一類學者),被迫紛紛轉行,失去了應有的話語權,只好眼睜睜地看着西方的語言學一統天下。這對繼承學統,無疑是釜底抽薪。這樣的氛圍,怎麼能產生得出大師?什麼是國學大師,按劉夢溪先生的說法,須具有這麼兩個條件:一是通經學;一是精小學。這確為不刊之論。謝謙先生在《國學詞典》中也精闢地論證了小學與國學的關係(這是我讀到的一部很好的國學入門讀物)。早在一百多年前,章太炎先生在《論語言文字學》一文中就明確指出:“今日欲知國學,則不得不先知語言文字。此語言文字之學,古稱小學。”其前的阮元在《擬國史儒林傳序》中已有一很形象的說法:“聖人之道,譬若宮牆,文字訓詁,其門徑也。門徑苟誤,跬步皆歧,安能升堂入室乎?”今人以小學為高深莫測、艱澀如天書,就是因為我們曾經無情地拋棄小學傳統,失去認真、虔誠、敬畏、樸實的讀書之心。在古代,小學不過是啟蒙性的知識(按章學誠的說法是“童蒙所業”),读书必先识字,與待人接物、灑水掃地等一起學,沒有什麼深奥之感。如《漢書·藝文志》“小學”類小序云:“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六書”即文字學,小學始脫胎於此。現代人感到不可思議:連學者專家都弄不甚明白的學問,在古代怎麼會入初級課程中呢?其實,不獨小學,其他學科亦然。如清初顧炎武在《日知錄》卷三十《天文》說:“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if !supportFootnotes][2][endif],農夫之辭也;‘三星在天’,婦人之語也;‘月離於畢’,戍卒之作也;‘龍尾伏晨’,兒童之謠也。後世文人學士,有問之而茫然不知者矣。”單說小學,造成以上情形实乃古今語音的變遷、流轉以及字義的變化所致。以六經中的《尚書》為例,此書所收的文字不過是當時的政治報告、告示、會議記錄之類的東西。按朱自清的說法,是“官話或普通話”。即所謂的“大白話”。否則,先民何以看得明白呢。但到了唐代,連“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愈都說它“佶屈贅牙”了。這就是“語音變遷”所造成的。小學(作為一門學問)因此應運而生,其創始者一般認為即西漢末年的楊雄。
最近二十年來,為看懂景麟公的學術論著,我涉獵了些小學著作,感到這門學問並非原先想像的那樣枯燥,甚或還有點好玩。比如胡朴安《文字學常識》、張舜徽《〈說文解字〉導讀》、李孝定《汉字史话》、左民安《汉字例话》、李學勤《古文字學初階》、張大春《認得幾個字》、張聞玉《漢字解讀》、流沙河《文字偵探》,都寫得很風趣、有味。在他們的筆下,每個漢字都凝聚着一塊文化、一段歷史、一個故事。這正如劉毓慶先生在《國學概論》中說的,“沒有漢字就沒有中國文化,不懂漢字的玄妙,就不能理解中國文化,也就根本不可能走進中國文化的殿堂”。我們要想讀通古書,小學那是繞不過的。這一點是以前讀書人的共識。遠的不說,就說民國時期,如革命家陳獨秀,對小學中的文字學、聲韵學就有深入而透徹的研究。他給魏建功的信論古韵分部,見識即非同一般,好似乾嘉诸老之言。其《小學識字教本》,一九四九年被梁實秋攜之入台,易名《文字新詮》出版,風靡一時(巴蜀書社也曾出版了大陸版)。我讀他這方面的論著,衹覺得他是個純粹而出色的小學家,忘了他的世俗身份。再如錢穆先生,學歷不過中學,完全以自學成為一代大史學家。他先在小學、中學執教,後由顧頡剛推薦到大學教書。在中學任教時,學校規定除“國文”正課外,還得“兼開一課”,並自編講義。錢先生第一學年開的就是小學。過去講國學者,必首講小學,否則就成笑話。他寫的講義《文字源流》,現已被發現。觀其所論,完全是個內行。其時“小學”整體水準之高,於斯可見一斑。如關於“國家”的“國”字,他說繁體裏面是個“或”字,“或”字从“戈”,就是兵,代表主權,中間有個“口”代表人口,就是社會,“口”底下還有一橫,代表土地,這個“國”字包括了主權、領土、社會。他由此得出:“中國古人造字精妙,從中國文字學即可推出中國傳統文化之由,其深義有如此。”
小學並非荊棘榛莽之地。對這門學科素有“用”與“研”兩途。姚奠中老先生在懷念景麟公的文章中曾說:“我對文字聲韵訓詁,不重在研而重在用。如對《詩經》,我根據聲韵學家從顧亭林到江有诰的研究成果,使古詩的聲韵美從朗讀中體會出來。”張舜徽老先生在回憶錄中談及小學時也說:“於此興趣雖濃,然特視此為讀書之工具,非欲終身肆力斯道,以專門名家自期也。”絕大多數人對小學都是立足於“用”, 衹需掌握其基本知識即可。第一步可選讀幾部小學方面的權威讀本,書目不妨參攷臺灣二〇〇九年影印出版的“民國學術叢刊”。其 “第三種”收小學方面的書,約二百六十種,共一百二十冊。我們選讀其中三五種,即可知就裏。在此基礎上,再讀两三種這方面的經典性論著,就可以入門。待有相當的基礎後,景麟公此書便不當放過。这裏說句題外話,日前,某名牌大學的博導在電話裏告訴我:一次他在同系一位年長博導家裏看到案頭上放着的《語言之起源》,已被翻成“油脂麻花”狀。而且這位漢語史學科的博導在給自己歷屆研究生所開的書目中,此書永遠是必讀的。學生買不着衹有向導師借。我知道此老早年的弟子現在多已是語言學領域的一流學者。先前我總以為自己是世間讀景麟公著述最多的一个。台版所收的十三篇論文,每篇也讀了不下二十遍。現在才知道有人對此書所下的工夫,或在我之上。
在本書的理董中,父親湯世洪、母親張世雲給我許多具體的指點,使本書終於以現在的面貌問世。我是個資質低拙之人,齠年視作文為畏途,往往好不容易寫出一篇,卻滿紙錯字。記得有一次我磨蹭半天,也没寫出幾個字,鄰居一個大哥見狀,就替我作了一文。然等我抄好遞上,父親衹看了一兩段,就放下作文本,問我:“這篇作文是你寫的?”近將此事作笑話告訴內子,她說或許其中沒有錯字,爸才感到不像是出自你的“手筆”。他說不是我的“語調”。我現在近乎以硯田為生,且悠游自在,實拜父母之賜。還要感謝大姑湯俊玉與表姐朱玲,本書係據她們提供的景麟公“自存本”作為底本錄入的。上面有作者少許訂正,我皆一一迻錄。還有蔣南華先生、張聞玉先生、顧久先生,對本書提出了很好的編纂意見,他們對景麟公的拳拳盛意,常常令我感動莫名。还要特别提到力之先生,這些年我所做的每部書稿,均得到先生切實的指導。前幾年我與友人為一前輩校理手稿,先生在我们已校好的稿子裏,發現三百多個硬傷。那本書掛名我們整理,我實在是慚愧。此間,我所以還能做點事情,實因背後有一個“團隊”倾力支持,而力之先生就是團隊的靈魂人物。先生勞己逸人,對此書做了精細的對校、本校、他校、理校(因書中有些文章的寫作時間跨度過長,而作者所用的文獻版本又不盡相同。如《說文》就用了好幾個本子,先生則不嫌麻煩將所有重要的版本找來逐一核校諟正),糾正我失校處甚夥,洵是本之大幸已!景麟公當年編這部書稿時,正是簡體的天下,為了遷就時俗,凡能用簡體而又不產生歧義者,都被迫選用了簡體字。現在這套叢書要求統一使用繁體来排印,也正符合景麟公的心願,簡體怎能傳達出此書之精妙(《說文》能排成簡體)?他當年堅持以手寫體影印出版,就是有些字實在不能簡。這樣我又花了三個多月来做此事,但對有一些字是否就安妥當了,實在沒有把握,幸有力之先生為我把關。本書的文字錄入主要由劉繼學先生完成;孟騫、湯文瑞也過錄了部分文字。繼學先生是位工科大學生,但對傳統文化殊為熱愛,對景麟公的小學,尤其是聲韵學津津樂道,對其中的精妙之處領悟之深,令我欽佩。我們時常聚會,有時一談就是兩三個小時,議題多是景麟公的小學。我許其為景麟公異代知音,他也常以未能親炙景麟公而引為憾事。以上諸位親友師長,對於本書,可套用司馬遷的话,與有力焉。
湯序波
本文寫訖於二〇一一年六月十九日清晨。此刻望着天邊泛起的一抹紅暈,我忽然想到今天不正是父親節吗,在此伏頌老人家安康、長壽!並恭祝天下所有父母吉祥如意!
附言
數月前,姚奠中老先生[if !supportFootnotes][3][endif]的女兒姚力芸老師與女婿張志毅老師來黔中,尋訪老先生曾經工作生活過的地方,我全程陪同。一次,兩位垂問先祖父著作的出版情況。我說:“晚生輯校的《語言之起源》(增補本),北京一家出版社原本已決定出版(清樣都作好了),可後來說這套叢書虧了,恐已無力繼續。”兩位當即表示“山西省姚奠中國學教育基金會”可以資助出版。他們回去後,我很快便接到三晉出版社社長張繼紅先生的電話,說該社願意出版此書,具體編輯工作將由副總編輯落馥香先生負責,並表示要一起努力把它作成“精品”。峰迴路轉,令我感慨萬千。據我瞭解,僅去年該“基金會”立項支持的課題,就達十五項之多。
剛過去的2014年,在先祖父湯炳正研究史上是個大豐年。力之先生就先祖父語言文字之學發表了四篇論文,對今人理解與認識《語言之起源》一書,極具意義。我因淺陋,曾困惑當年先祖父在這方面究竟有哪些特質與表現,讓閱人無數的樸學大師太炎先生那麼賞識,以至有“為承繼絕學惟一有望之人”的期許?看了這組論文,我恍然明白:“偉大也要有人懂。”(魯迅語)現將其篇目錄於此,俾便好之諸君參閱:《語言發生的“手勢說”:兼論湯炳正先生的貢獻》(《中國文化》2014年春季號);《略論湯炳正先生<原“名”>一文之學術價值》(《貴州文史叢刊》2014年第2期);《論湯炳正先生在文字與語言關係領域中所作之貢獻》(《廣西師範大學學報》2014年第5期);《略論湯炳正先生對語言起源研究之貢獻》(《貴州師範大學學報》2014年第6期)。
2014年於我個人也是一個轉捩:離開原單位而服務於貴州師範大學歷史研究院,為該院中國古代史專業的研究生講授“《史記》研读”“《左傳》研读”的必修課,並擔任碩士生的指導教師。七十年前,先祖父曾在此歷史研究院的前身“史地系”開過《史通》等課(並作過“應當用古文經學家的治學方法研究史學”的演講)。想來冥冥之中,也許存在着某種機緣吧?
湯序波謹志
2015年1月22日(甲午年臘月初三),
恰為先祖父105歲冥诞
校稿感言:落先生乃姚門高弟,她在給我的信中說:“遙憶一九八七年春月,隨姚先生到成都開會,曾到府上拜會湯先生,相談甚歡。如今兩位先生先後西去,不勝感慨!惟有竭力做好先生著作的傳承,才無愧焉!”落先生对书稿的编辑真是尽心尽责,实实在在地做到了精益求精;而其中贡献之大,令我感佩不已。湯序波2015年5月15日补记
[if !supportFootnotes][3][endif] 波按:新近發現老先生的一篇佚文《三十年來國學界的概況和今後應由之路》(國立貴陽師範學院《教育學術》1949年四、五合刊號)。其文云:“我們可以根據語音變遷的定律,上溯初古的語音之原型,再根據語義孶衍的途軌,上泝初古語音之本義。二者互相印證,而得語源。這樣,語言學上便開了一種新的局面,而可成了古史學、人種學的一大助力(同門湯炳正兄另有專著)。”“另有專著”,即指本書所收的《語言起源之商榷》《<說文>歧讀攷源》等文。湯炳正原計劃寫專著《語源研究》的,後改以單篇發表了。
汤炳正《语言之起源》(增补本)出版
本报讯汤炳正先生学术代表作《语言之起源》(增补本)新近由三晋出版社出版。此书原版1990年由台湾贯雅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这次出版增加了三分之一的篇幅。汤先生系当代著名语言学家,20世纪30年代受业于章太炎先生之门,并担任太炎先生创办的“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小学主讲教席,学术界认为他的语言起源研究“为世人揭开了人类语言起源之谜”。
《中华读书报》( 2015年10月14日02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