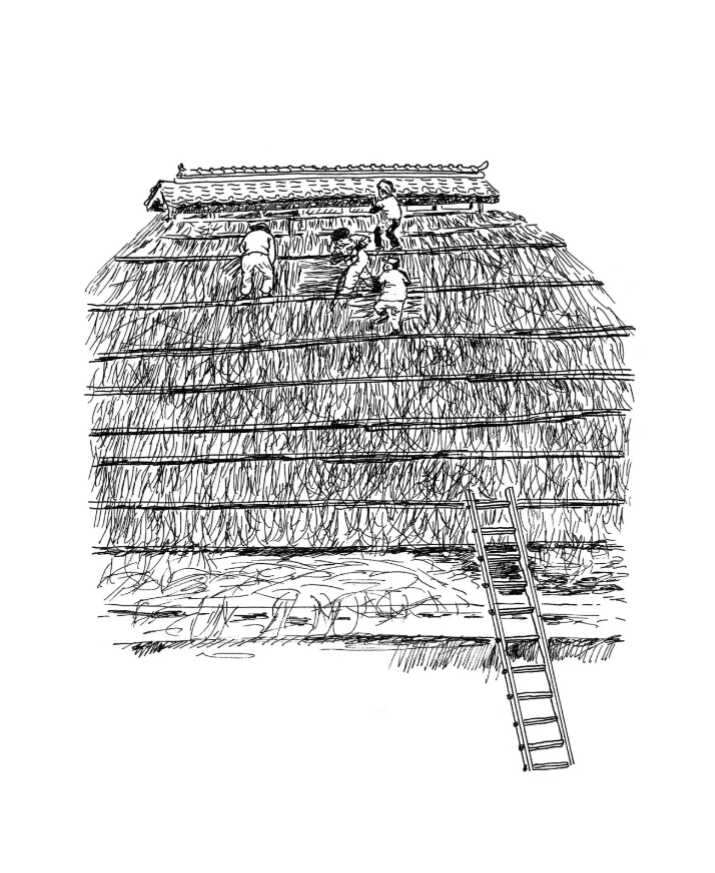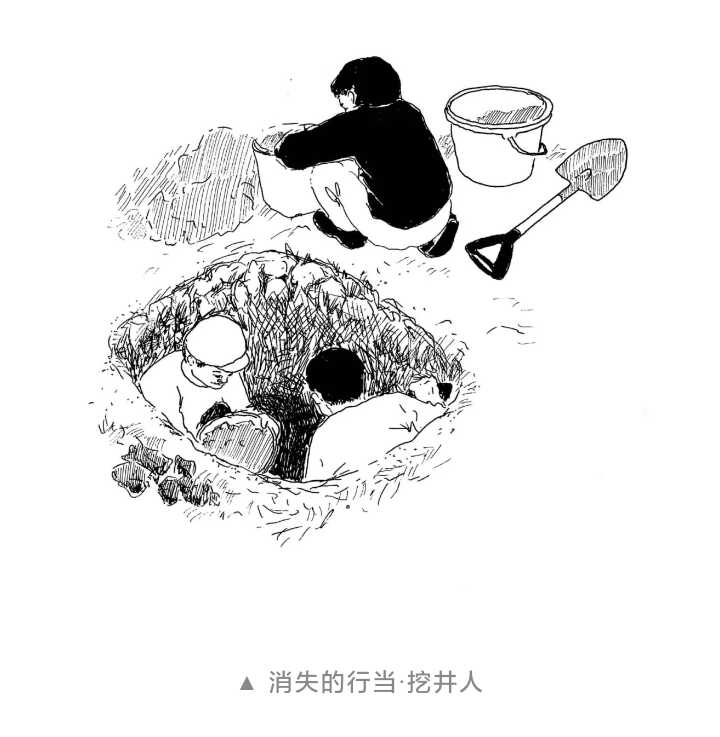- Python初识-day3:复合类型里的序列类型、映射类型和集合类型
梌
python开发语言
目录1.复合类型初识1.1列表类型(list)1.1.1列表的创建1.1.2列表的运算1.1.3列表的访问1.1.4列表的具体示例1.1.5列表的常见API1.2元组类型(tuple)1.2.1元组的创建1.2.2元组的运算1.2.3元组不可变1.2.4元组的具体示例1.2.5元组的常见API1.3字典类型(dict)1.3.1字典的创建1.3.2字典的运算1.3.3字典的访问1.3.4字典的特性
- Libevent(3)之使用教程(2)创建事件
Once-Day
#Linux实践记录#十年代码训练开发语言Clibevent
Libevent(3)之使用教程(2)创建事件Author:OnceDayDate:2025年6月29日一位热衷于Linux学习和开发的菜鸟,试图谱写一场冒险之旅,也许终点只是一场白日梦…漫漫长路,有人对你微笑过嘛…本文档翻译于:Fastportablenon-blockingnetworkprogrammingwithLibevent全系列文章可参考专栏:十年代码训练_Once-Day的博客-C
- 和二宝在一起的大宝更让人心疼
湉湉丫头
昨晚哄睡俩娃之后,我开始沐浴更衣,快洗完澡,突然听到二宝豪放的哭声。通常爸爸完全可以控制局面,我也就慢悠悠地享受着洗澡的时间,可是听着哭声一点也没减小,反而大宝也哭了起来,这时姥姥也加入了哄娃队伍,听见奶奶不太温柔地和大宝说:“你别哭啦”我极速完成所有步骤。推开门的一刹那,姥姥抱着二宝坐着,奶奶站在一旁。我能感受到二宝希望我抱抱,但我还是毅然决然地说了一句:“我得先哄大宝.”卧室里黑漆漆的没开灯,
- 2021:乐早起|遇见更好的自己|(180/365)Ⅰ如胶如漆的爱情,却被它所拆散
梦想加油站
每日语录强则易折,柔弱才会赢。——曾仕强(处事篇)导语早起已经很多年,以前早起没有固定的时间点,有的时候会四点起来,有的时候会六点起来,虽然都在“早起”,但早起的效率和质量并不如所愿。2020年09月20日开始,自己发起“在路上”早起习惯养成圈子,经过一系列实践和调整,最终把自己的早起时间点定为04:00。我发起的早起圈子,注重的是早起之后做什么,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一个适合自己的早起点。根据自己
- 《如何阅读一本书》—见感思行
亚会Jessica
见:关于全民阅读能力方面,绝大部分人大学毕业之后,仍然不具备通过阅读去提升整体认知的能力。虽然很多大学已经开设“速读”和“竞读”等课程,但多年的阅读习惯已养成,仍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感:之前一直很困惑,读了那么多书,为什么都记不住呢?回顾自己之前的阅读方式,拿到一本书之后(且更倾向不须太多思考的小说类),从头到尾的浏览一遍,然后开始下一本,过程当中的思考少的可怜。总结的来说就是,虽然自认为读了
- 《蛰伏》剧本杀复盘解析+谁是凶手+真相答案+角色剧透
VX搜_小燕子复盘
为了你获得更好的游戏体验,本文仅显示《蛰伏》剧本杀部分真相复盘,获取完整真相复盘只需两步①【微信关注公众号:集美复盘】②回复【蛰伏】即可查看获取哦﹎﹎﹎﹎﹎﹎﹎﹎﹎﹎﹎﹎﹎﹎﹎﹎﹎﹎﹎﹎﹎﹎﹎﹎﹎﹎﹎﹎﹎﹎﹎﹎﹎﹎﹎﹎﹎﹎﹎﹎1、剧本杀《蛰伏》角色介绍这里也是无数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人们,梦开始的地方!这里有人一夜暴富,有人家破人亡,有人成疯成魔。这里是法外之地,唯有权利与金钱同黑暗主宰着一切。在这
- 淘宝优惠券在哪里查看-淘宝优惠券在哪找
氧惠_飞智666999
淘宝优惠券的寻找和领取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氧惠APP(带货领导者)——是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抖客+淘客app!2023全新模式,我的直推也会放到你下面。主打:带货高补贴,深受各位带货团队长喜爱(每天出单带货几十万单)。注册即可享受高补贴+0撸+捡漏等带货新体验。送万元推广大礼包,教你如何1年做到百万团队。淘宝官方平台:在淘宝官方平台上,可以关注“淘宝优惠券”或者“淘宝联盟”等相关频道,这些频道会定期
- 天真无邪的童年
阳轩
此刻七岁半的女儿正在院子里拿着一桶泡泡水,吹得满院子都是泡泡飞。一岁九个月的小弟弟,还身着棉衣棉裤,东追西赶那满院的小泡泡,嘴里不时发出咿呀咿呀的声音。女儿嘿哈嘿哈,引逗着他的小弟弟,两个人又不是发出哈哈的笑声。在院子里给儿子洗衣服了老公,对正在给他做饭的媳妇儿说:“天真无邪的童年,孩子们玩的真幸福!”是啊,孩子们可以全身心的投入他们的娱乐活动,我们是不是也应该保存自己的一份童心,好好享受当下的生
- 自媒体怎么赚钱?做自媒体一定要掌握这些方法,月入过万一点不难
爱睡觉的木子
自媒体怎么赚钱?自媒体可以赚到钱吗?这个问题毋庸置疑,玩自媒体肯定是能够赚到钱的,而却玩的好还可以轻松月入万元。今年是自媒体火爆的一年。如果你还不抓住这个机会,你将会失掉赚钱的一次机会。靠自媒体赚钱很简单,就是利用今日头条、百度百家、企鹅自媒体、大鱼号、搜狐自媒体、一点资讯、网易自媒体等自媒体平台发布文章,平台推荐文章给用户阅读,然后用户阅读过程当中点击了广告,那么文章作者就获取相应的广告收益,这
- 三年不长 足以改变我的一生
青小桥
谨以此文献给自己。曾经以为自己的研究生三年会一切顺利,毕业后去读博,去做学问。但是现在看来,曾经以为的都没有出现。01嘻嘻哈哈,没心没肺,是我对自己最自豪的评价。一直以来,自己过的都很顺利,或者说很平凡。没心没肺的开心,应该最接近开心的本质吧!习惯了放飞自我,你总能在那条小路上看到一个穿着绿色冲锋衣的,不修边幅的连影子都很自由的女生。吃饭、睡觉、学习、玩,应该就是全部的生活了,没有厌食,也没有失眠
- 外面下雨了。我的心好乱
63abc4c0289b
不知道为什么,昨天晚上我听见外面在下雨让我心很烦躁,我准备录制我的有声书,可是,我发现那个时候,太晚了,那个时候,天天都在录制有声书,其实,自打失业了开始,我自己开始迷失自我,其实,我的心很乱的,记得,那个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老公他天天送我去车站去公司上班的时候,其实,最近,在家录制我的大神有声书,我觉得,那个时候,天天在公司上班说自己最近,看了什么电视剧,那个时候,她们光会问我孩子与我老公的事
- ls总结
黑客不黑撒
linuxls列出目录下所有文件数量http://blog.hehehehehe.cn/a/12311.htm查看统计当前目录下文件的个数,包括子目录里的。ls-lR|grep"^-"|wc-lLinux下查看某个目录下的文件、或文件夹个数用到3个命令:ls列目录、用grep过虑、再用wc统计。举例说明:1、查看统计当前目录下文件的个数ls-l|grep"^-"|wc-l2、查看统计当前目录下文件
- 热情逐渐变冷
云树滕梓祥
她一头黑色的秀发。一身潮流的衣服。走在大街上都是引人注目的存在。他便是我的表姐。我的表姐目前正在念大学。她的同学以及陌生人看到的都是他那光鲜艳丽以及他的成绩优越的外表。却从来不曾晓得他内心深处的那份孤寂。小时候爸妈因为工作忙碌原因,暑假把我送送到姑姑那里。那个时候,白天姑姑也要上班。于是表姐便在家里照看。表姐的性格非常随和,他从来不与任何人争吵。正是因为他这种性格就像他的外表以及他的成绩,在学校里
- 好好工作,不要混日子
艺龄菇凉
2018年7月27日星期五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烦恼,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快乐。有来自工作的,有来自生活的,有人内部消化,而有的人大庭广众发泄。不管是属于哪种,那都是自己的一种行为。有的人工作很认真,有些人就想着混日子。工作中是有苦有累,有时候累得趴下去直接秒睡,有时候苦得话都不想说。谁不想工作少点,钱多点,并不是每个老板都是慈善机构。你今天的努力工作并不是为了老板而工作,而是自己的每一份成绩单。今天你不
- 2021-09-23
感恩学习相信小陶
感恩!六点签到4209天有时候事情就是这么神奇。只要开始了,奇迹就会发生。当你开始反思,你会意识到你在想什么,好的,或者坏的想法。接着,你会开始纠正自己不好的想法。也会把美好的感觉记住。最终做出更好的选择。所以,改变可能从每一次细小的观察开始。——对一切都充满好奇的小陶。
- 浅析PGC、UGC、OGC、KOL、公域流量、私域流量
七喜f
2019年12月5日,星期四,晴,很温暖以下是我今日份的学习任务:PGC:(Professionally-generatedContent,专业生产内容,也称PPC,Professionally-producedContent)PGC为专业生产内容,常见于个人自媒体的变现转化;UGC:(User-generatedContent,用户生产内容,也称UCC,User-createdContent)U
- Django数据库迁移
番茄码
django数据库djangooracle
在Django中进行数据库迁移的命令是`pythonmanage.pymigrate`。下面是一些常用的数据库迁移命令及其用途:1.`pythonmanage.pymakemigrations`:生成数据库迁移文件。当你修改了模型(Model)或创建了新的模型时,需要运行该命令来生成一个包含最新更改的迁移文件。2.`pythonmanage.pymigrate`:应用数据库迁移。运行该命令会将生成
- Django基础(一)———创建与启动
【本人】
PythonWebdjangopython后端
前言从这篇文章开始,我将给大家介绍Python中的一个框架Django我将从基础开始一步一步带领大家深入了解Django框架并完成实战案例一、Django是什么?Django是一个免费、开源、高级的PythonWeb框架。它的核心目标是使开发复杂的、数据库驱动的网站变得快速、简单和安全。Django遵循“Don'tRepeatYourself”的设计哲学,强调代码复用和组件化。它奉行“包含电池”的
- 年初二记事 | 手写我心DAY10
我是问夏
每年大年初二都是亲戚们到我家拜年的日子,说实话我还真没有下过厨做饭,之前都是老公的小妹妹掌勺,今年因为小妹妹坐月子,婆婆亲自掌勺了,说实话我在考虑明年的春节我要不要露一手。各位哥哥姐姐都在公司上班,上班见面平时吃饭见面,逢年过节聚会什么的也还是见面。因为工作关系彼此间相互有了矛盾,私下里也就没有什么交情了,有时候想想这也有不好的地方,原本有个空还可以聊聊天,而这样都互不来往。吃饭时总免不了喝酒,喝
- 面对家长的种种问题,怎么办?
007欢
如果你也是一线班主任那肯定遇到过抱怨孩子种种问题的家长。孩子管不下来,家长们第一时间想到的往往是告老师向班主任求助。家长向你求助你能否给予帮助或解决呢?举两个例子来聊一聊。问题一家长说:孩子在家谁的话都不听,只听老师的,我的孩子拜托老师了,一定严格要求他。这时老师怎么办?老师:1.让家长明白,孩子在家谁的话都不听在校还愿意听老师的,那肯定是家庭教育出了问题。2.家庭出现的问题不能回避,要想办法解决
- 冬雪
跳动的脉搏
冬雪冬天第一场雪,是四季老人在四季末写好的语句。它没有华丽辞藻的精心修饰;时晴、时雨、时阴,天气从不把脸色放在心里——多么任性而高傲的公主:要想吹风就刮风,要想下雪就飞雪!小河水冷,是四季进入冬季的序幕;这序幕开始了一年的归属。如果不真正理解,就无法从内心共鸣远遁秋声的阵阵歌吟。把悠闲了春夏秋三季的雪花,从时光中搀扶而出;漂得白白的,直到它慵懒地打着呼呼的鼾声,睡眼惺忪地飘向冬季。冬天的第一场雪,
- 刘燕酿制:为什么你很难再对一个人心动?
刘燕酿制保养顾问
身边单身的朋友越来越多,而且一单身就持续好几年。许多过去陷在感情的伤痛里迟迟无法自我疗愈的人,现在大多数都过着非常独立的生活。一个人上下班,一个人做饭给自己吃,周末的时候就约上三五个朋友一起吃吃饭,唱唱歌。其实这样也挺好的,真的。遥望明亮的夜空Abrightnightsky"为什么你很难再对一个人心动了?"有个女孩儿说:"大概就是觉得把心放自己这里最安全吧。"这条评论被点赞顶到了第一。这句话,一定
- 小猫咪 “伤人”之后
黑皮漫漫
感恩我可爱善良的妈妈,被小猫咪抓伤了还是最疼她,感恩妈妈对自己孩子的爱对我的爱都是那么明目张胆那么毫无保留,即使自己受到了一些伤害也毫不计较,感恩她的大度和宽容,感恩她对于我的教育和影响。事情是这样的,昨晚在楼下遇到妈妈,和我投诉说被小猫咪抓伤嘴唇出血了,我心里一惊被猫抓伤可不是什么好事情,可是好奇怪为什么会被抓到嘴唇?妈妈说是抱着猫咪的时候不小心被抓伤的,唉,真不知道是谁任性了。我回到家看到猫咪
- (已完结小说)--《佛胎女》江挽娄煦--(全文免费阅读)
小说推书
(已完结小说)--《佛胎女》江挽娄煦--(全文免费阅读)主角:江挽娄煦简介:流落缅北那年,我成了人人艳羡的佛宠,价值万金。娄煦是我的第一位恩主,他阴险,毒辣,疯魔,而我作为他的佛宠却不得不徘徊于他们两兄弟之间。可关注微信公众号【放心文楼】去回个书号【14】,即可免费阅读【佛胎女】全文!第5章我被迫的每天定时去给娄煦喂“药水儿”。他的未婚妻告诉我一天三次不能少,我得早上按时给他喂水儿。而且,得赶在早
- 明天放假啦
一方如何
一周之前上班就已经三心二意,一心只想为祖国母亲庆生。准备好明天一早闹铃,争取避免出行高峰,堵高速上太惨了。其实今年假期没有什么安排,之前还会附近景区打卡逛逛,虽然十有八九堵路上,景区也是人推人走马观花,但是还是要假期还是想出去啊。放张去年乌镇吧今年疫情最好还是不出门,乖乖在家放松享受假期吧,看看本是贺岁档的电影,逛逛县城的商场,买买物美价廉的生活用品,其实也挺好。最近挺忙的,前段时间刚说闲,现在就
- 我会想念这样的下午
小太阳阿慧
阳光透过蓝玻璃照进来。我趴在桌子上敲着键盘,耳朵里是自己喜欢听的歌,想着晚上应该去做什么饭,先熬一锅玉米糁吧,拿一个大大的红薯,甜甜软软的,削干净皮,切成块放进锅里就好了。炒什么菜呢?炒一盘胡萝卜好了,橙橙的萝卜又甜又脆,切成可爱笨拙的丁,掺着妈妈灌得腊肉炒下去,一盘菜了。再炒一盘青菜吧,昨天买的芍菜,青黄的叶子,白白的梗,洗净随便炒一下,本来一锅的青菜随着火就蔫成了一点。夏天的时候,妹妹在她用坏
- 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
安静的大海
今天和不同科室的人一起HI聊,每个人不免会抱怨自己科室某人让人崩溃的习惯。发现人人都有两面性,人人的世界观确实相差甚远,在某一些人眼中的徐爱是额,完全可以成为别人眼中的大事。因此,佛陀教导大众说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
- 网上的捡漏群可信吗?捡漏群靠什么挣钱?
测评君高省
现今的数字时代,微信成为了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社交工具。与此同时,微信捡漏群也成为了许多人赚钱的新方式。通过参与捡漏活动,人们可以获得高价值的优惠券和折扣,进而实现省钱甚至赚钱的目标。本文将介绍微信捡漏群赚钱的方法和高省APP的应用。一、微信捡漏群赚钱的方法寻找合适的捡漏群首先,你需要寻找一些合适的微信捡漏群。可以通过搜索相关的关键词或加入相关的社交群体来寻找合适的捡漏群。在选择捡漏群时,需要
- js改变表单元素的值,不会触发监听事件
LilyLaw
最近工作中遇到一个问题:监听input框的值的变化,当js改变input框的值时无法触发其监听事件。查阅资料后得知,监听事件都是监听某种操作的,如果没有发生这种操作,这个事件肯定不能被触发。比如下面的代码:+letinputbox=document.getElementById('inputbox');letval=parseInt(inputbox.value);inputbox.addEven
- 存钱才是成年人最顶级的自律
shenLan888
“钱不是花出去了,而是用另一种方式陪在你身边”。“钱不是省出来的,而是赚出来的”。这样刺激消费的鸡汤比比皆是,大多数人好像终于找到了突破口乐此不彼地喝着鸡汤来不断满足自己的物欲。我不敢认同,我觉得好好存钱,富养自己,才是正确的金钱观。这里的富养自己绝不是一般的买买买,看到喜欢的,流行的,别人有的就得买回来那种毫无节制的物欲,不管这件东西对自己来说有用还是无用的冲动性的消费;而是有计划的身心都有益的
- 关于旗正规则引擎中的MD5加密问题
何必如此
jspMD5规则加密
一般情况下,为了防止个人隐私的泄露,我们都会对用户登录密码进行加密,使数据库相应字段保存的是加密后的字符串,而非原始密码。
在旗正规则引擎中,通过外部调用,可以实现MD5的加密,具体步骤如下:
1.在对象库中选择外部调用,选择“com.flagleader.util.MD5”,在子选项中选择“com.flagleader.util.MD5.getMD5ofStr({arg1})”;
2.在规
- 【Spark101】Scala Promise/Future在Spark中的应用
bit1129
Promise
Promise和Future是Scala用于异步调用并实现结果汇集的并发原语,Scala的Future同JUC里面的Future接口含义相同,Promise理解起来就有些绕。等有时间了再仔细的研究下Promise和Future的语义以及应用场景,具体参见Scala在线文档:http://docs.scala-lang.org/sips/completed/futures-promises.html
- spark sql 访问hive数据的配置详解
daizj
spark sqlhivethriftserver
spark sql 能够通过thriftserver 访问hive数据,默认spark编译的版本是不支持访问hive,因为hive依赖比较多,因此打的包中不包含hive和thriftserver,因此需要自己下载源码进行编译,将hive,thriftserver打包进去才能够访问,详细配置步骤如下:
1、下载源码
2、下载Maven,并配置
此配置简单,就略过
- HTTP 协议通信
周凡杨
javahttpclienthttp通信
一:简介
HTTPCLIENT,通过JAVA基于HTTP协议进行点与点间的通信!
二: 代码举例
测试类:
import java
- java unix时间戳转换
g21121
java
把java时间戳转换成unix时间戳:
Timestamp appointTime=Timestamp.valueOf(new SimpleDateFormat("yyyy-MM-dd HH:mm:ss").format(new Date()))
SimpleDateFormat df = new SimpleDateFormat("yyyy-MM-dd hh:m
- web报表工具FineReport常用函数的用法总结(报表函数)
老A不折腾
web报表finereport总结
说明:本次总结中,凡是以tableName或viewName作为参数因子的。函数在调用的时候均按照先从私有数据源中查找,然后再从公有数据源中查找的顺序。
CLASS
CLASS(object):返回object对象的所属的类。
CNMONEY
CNMONEY(number,unit)返回人民币大写。
number:需要转换的数值型的数。
unit:单位,
- java jni调用c++ 代码 报错
墙头上一根草
javaC++jni
#
# A fatal error has been detected by the Java Runtime Environment:
#
# EXCEPTION_ACCESS_VIOLATION (0xc0000005) at pc=0x00000000777c3290, pid=5632, tid=6656
#
# JRE version: Java(TM) SE Ru
- Spring中事件处理de小技巧
aijuans
springSpring 教程Spring 实例Spring 入门Spring3
Spring 中提供一些Aware相关de接口,BeanFactoryAware、 ApplicationContextAware、ResourceLoaderAware、ServletContextAware等等,其中最常用到de匙ApplicationContextAware.实现ApplicationContextAwaredeBean,在Bean被初始后,将会被注入 Applicati
- linux shell ls脚本样例
annan211
linuxlinux ls源码linux 源码
#! /bin/sh -
#查找输入文件的路径
#在查找路径下寻找一个或多个原始文件或文件模式
# 查找路径由特定的环境变量所定义
#标准输出所产生的结果 通常是查找路径下找到的每个文件的第一个实体的完整路径
# 或是filename :not found 的标准错误输出。
#如果文件没有找到 则退出码为0
#否则 即为找不到的文件个数
#语法 pathfind [--
- List,Set,Map遍历方式 (收集的资源,值得看一下)
百合不是茶
listsetMap遍历方式
List特点:元素有放入顺序,元素可重复
Map特点:元素按键值对存储,无放入顺序
Set特点:元素无放入顺序,元素不可重复(注意:元素虽然无放入顺序,但是元素在set中的位置是有该元素的HashCode决定的,其位置其实是固定的)
List接口有三个实现类:LinkedList,ArrayList,Vector
LinkedList:底层基于链表实现,链表内存是散乱的,每一个元素存储本身
- 解决SimpleDateFormat的线程不安全问题的方法
bijian1013
javathread线程安全
在Java项目中,我们通常会自己写一个DateUtil类,处理日期和字符串的转换,如下所示:
public class DateUtil01 {
private SimpleDateFormat dateformat = new SimpleDateFormat("yyyy-MM-dd HH:mm:ss");
public void format(Date d
- http请求测试实例(采用fastjson解析)
bijian1013
http测试
在实际开发中,我们经常会去做http请求的开发,下面则是如何请求的单元测试小实例,仅供参考。
import java.util.HashMap;
import java.util.Map;
import org.apache.commons.httpclient.HttpClient;
import
- 【RPC框架Hessian三】Hessian 异常处理
bit1129
hessian
RPC异常处理概述
RPC异常处理指是,当客户端调用远端的服务,如果服务执行过程中发生异常,这个异常能否序列到客户端?
如果服务在执行过程中可能发生异常,那么在服务接口的声明中,就该声明该接口可能抛出的异常。
在Hessian中,服务器端发生异常,可以将异常信息从服务器端序列化到客户端,因为Exception本身是实现了Serializable的
- 【日志分析】日志分析工具
bit1129
日志分析
1. 网站日志实时分析工具 GoAccess
http://www.vpsee.com/2014/02/a-real-time-web-log-analyzer-goaccess/
2. 通过日志监控并收集 Java 应用程序性能数据(Perf4J)
http://www.ibm.com/developerworks/cn/java/j-lo-logforperf/
3.log.io
和
- nginx优化加强战斗力及遇到的坑解决
ronin47
nginx 优化
先说遇到个坑,第一个是负载问题,这个问题与架构有关,由于我设计架构多了两层,结果导致会话负载只转向一个。解决这样的问题思路有两个:一是改变负载策略,二是更改架构设计。
由于采用动静分离部署,而nginx又设计了静态,结果客户端去读nginx静态,访问量上来,页面加载很慢。解决:二者留其一。最好是保留apache服务器。
来以下优化:
- java-50-输入两棵二叉树A和B,判断树B是不是A的子结构
bylijinnan
java
思路来自:
http://zhedahht.blog.163.com/blog/static/25411174201011445550396/
import ljn.help.*;
public class HasSubtree {
/**Q50.
* 输入两棵二叉树A和B,判断树B是不是A的子结构。
例如,下图中的两棵树A和B,由于A中有一部分子树的结构和B是一
- mongoDB 备份与恢复
开窍的石头
mongDB备份与恢复
Mongodb导出与导入
1: 导入/导出可以操作的是本地的mongodb服务器,也可以是远程的.
所以,都有如下通用选项:
-h host 主机
--port port 端口
-u username 用户名
-p passwd 密码
2: mongoexport 导出json格式的文件
- [网络与通讯]椭圆轨道计算的一些问题
comsci
网络
如果按照中国古代农历的历法,现在应该是某个季节的开始,但是由于农历历法是3000年前的天文观测数据,如果按照现在的天文学记录来进行修正的话,这个季节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
也就是说,还要再等3000年。才有机会了,太阳系的行星的椭圆轨道受到外来天体的干扰,轨道次序发生了变
- 软件专利如何申请
cuiyadll
软件专利申请
软件技术可以申请软件著作权以保护软件源代码,也可以申请发明专利以保护软件流程中的步骤执行方式。专利保护的是软件解决问题的思想,而软件著作权保护的是软件代码(即软件思想的表达形式)。例如,离线传送文件,那发明专利保护是如何实现离线传送文件。基于相同的软件思想,但实现离线传送的程序代码有千千万万种,每种代码都可以享有各自的软件著作权。申请一个软件发明专利的代理费大概需要5000-8000申请发明专利可
- Android学习笔记
darrenzhu
android
1.启动一个AVD
2.命令行运行adb shell可连接到AVD,这也就是命令行客户端
3.如何启动一个程序
am start -n package name/.activityName
am start -n com.example.helloworld/.MainActivity
启动Android设置工具的命令如下所示:
# am start -
- apache虚拟机配置,本地多域名访问本地网站
dcj3sjt126com
apache
现在假定你有两个目录,一个存在于 /htdocs/a,另一个存在于 /htdocs/b 。
现在你想要在本地测试的时候访问 www.freeman.com 对应的目录是 /xampp/htdocs/freeman ,访问 www.duchengjiu.com 对应的目录是 /htdocs/duchengjiu。
1、首先修改C盘WINDOWS\system32\drivers\etc目录下的
- yii2 restful web服务[速率限制]
dcj3sjt126com
PHPyii2
速率限制
为防止滥用,你应该考虑增加速率限制到您的API。 例如,您可以限制每个用户的API的使用是在10分钟内最多100次的API调用。 如果一个用户同一个时间段内太多的请求被接收, 将返回响应状态代码 429 (这意味着过多的请求)。
要启用速率限制, [[yii\web\User::identityClass|user identity class]] 应该实现 [[yii\filter
- Hadoop2.5.2安装——单机模式
eksliang
hadoophadoop单机部署
转载请出自出处:http://eksliang.iteye.com/blog/2185414 一、概述
Hadoop有三种模式 单机模式、伪分布模式和完全分布模式,这里先简单介绍单机模式 ,默认情况下,Hadoop被配置成一个非分布式模式,独立运行JAVA进程,适合开始做调试工作。
二、下载地址
Hadoop 网址http:
- LoadMoreListView+SwipeRefreshLayout(分页下拉)基本结构
gundumw100
android
一切为了快速迭代
import java.util.ArrayList;
import org.json.JSONObject;
import android.animation.ObjectAnimator;
import android.os.Bundle;
import android.support.v4.widget.SwipeRefreshLayo
- 三道简单的前端HTML/CSS题目
ini
htmlWeb前端css题目
使用CSS为多个网页进行相同风格的布局和外观设置时,为了方便对这些网页进行修改,最好使用( )。http://hovertree.com/shortanswer/bjae/7bd72acca3206862.htm
在HTML中加入<table style=”color:red; font-size:10pt”>,此为( )。http://hovertree.com/s
- overrided方法编译错误
kane_xie
override
问题描述:
在实现类中的某一或某几个Override方法发生编译错误如下:
Name clash: The method put(String) of type XXXServiceImpl has the same erasure as put(String) of type XXXService but does not override it
当去掉@Over
- Java中使用代理IP获取网址内容(防IP被封,做数据爬虫)
mcj8089
免费代理IP代理IP数据爬虫JAVA设置代理IP爬虫封IP
推荐两个代理IP网站:
1. 全网代理IP:http://proxy.goubanjia.com/
2. 敲代码免费IP:http://ip.qiaodm.com/
Java语言有两种方式使用代理IP访问网址并获取内容,
方式一,设置System系统属性
// 设置代理IP
System.getProper
- Nodejs Express 报错之 listen EADDRINUSE
qiaolevip
每天进步一点点学习永无止境nodejs纵观千象
当你启动 nodejs服务报错:
>node app
Express server listening on port 80
events.js:85
throw er; // Unhandled 'error' event
^
Error: listen EADDRINUSE
at exports._errnoException (
- C++中三种new的用法
_荆棘鸟_
C++new
转载自:http://news.ccidnet.com/art/32855/20100713/2114025_1.html
作者: mt
其一是new operator,也叫new表达式;其二是operator new,也叫new操作符。这两个英文名称起的也太绝了,很容易搞混,那就记中文名称吧。new表达式比较常见,也最常用,例如:
string* ps = new string("
- Ruby深入研究笔记1
wudixiaotie
Ruby
module是可以定义private方法的
module MTest
def aaa
puts "aaa"
private_method
end
private
def private_method
puts "this is private_method"
end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