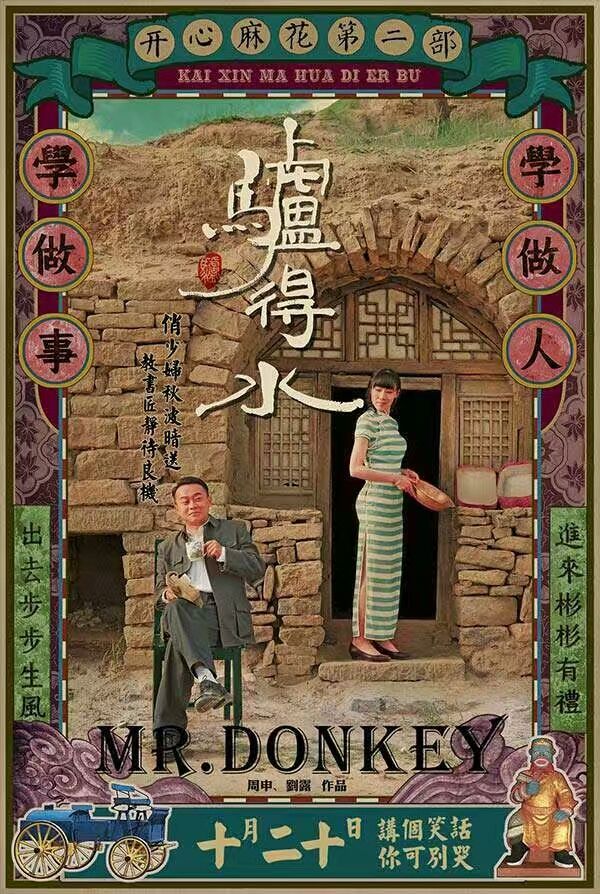- 深度学习中高斯噪声:为什么以及如何使用
小白学视觉
深度学习人工智能
点击上方“小白学视觉”,选择加"星标"或“置顶”重磅干货,第一时间送达来源:DeepHubIMBA本文约1800字,建议阅读8分钟高斯噪声是深度学习中用于为输入数据或权重添加随机性的一种技术。在数学上,高斯噪声是一种通过向输入数据添加均值为零和标准差(σ)的正态分布随机值而产生的噪声。正态分布,也称为高斯分布,是一种连续概率分布,由其概率密度函数(PDF)定义:pdf(x)=(1/(σ*sqrt(
- webstorm 推送项目到github
stephen--zhu
git前端webstorm
1.在github中建立对应仓库。webstorm会建立连接,在github中建立对应的仓库。根据提示,会执行commit,以及push。然而,webstorm默认使用的是ssh连接。push失败。因此,执行第二步,设置remotes为https格式。2.添加远程仓库https格式在为:https://github.com/lven/es6.git设置webstorm的gitRemotes为htt
- 查看代理设置Get-Item Env:https_proxy
如若123
https网络协议http
通过PowerShell来检查和设置代理环境变量。以下是对每个命令的解释以及你提供的命令的功能:###1.**获取`https_proxy`环境变量**```powershellGet-ItemEnv:https_proxy该命令会显示当前PowerShell会话中的https_proxy环境变量值。如果该环境变量没有设置,将会显示ItemNotFound错误。2.获取http_proxy环境变量
- 【NTN 卫星通信】关于卫星通信的一次访谈
一只好奇的猫2
NTN卫星通信卫星通信NTNstarlink波束覆盖
1概述 通过CSDN的途径,有个咨询公司找到我,说是有投资公司看到我的博客,希望做一次访谈,我回答了10个问题,现在发到博客上;很多观点都是自己根据经验拍的,并没有严格的计算,有兴趣的看看就好,有些问题还挺有趣的。2访谈问题以及回复1、对于一个信号发生设备,如通信基站,其理论最大信道容量(网速,bit/s)和其通信频率(Hz)、功率(W)的数学关系是什么,能否用公式表示。答复:这个问题可以直接由
- 【eMTC】eMTC 窄带以及带宽的关系
一只好奇的猫2
eMTCeMTCLTE窄带带宽
1概述 eMTC传输进行通信时,一般采用1.4M带宽,在和LTE小区联合部署时,需要将LTE的带宽分割成以1.4M带宽为粒度的单位,这个单位在协议上叫做窄带。2窄带定义3参考文献36.211
- fuadmin
jcsx
开源学习djangovue.js
fu-admin-web采用VUE3,TS开发。fu-admin-backend采用Python,Django和Django-Ninija开发。数据库支持MySql,SqlServer,Sqlite。前端采用VbenAdmin、Vue3、AntDesignVue。后端采用Python语言Django框架以及强大的DjangoNinja。支持加载动态权限菜单,多方式轻松权限控制。Vue2项目移步
- docker容器基础入门
霉逝
docker容器运维
docker容器技术基础入门文章目录docker容器技术基础入门@[toc]1.docker基本概念2.Docker的引擎的组成以及功能3.docker的架构4.docker安装、配置加速器以及常用指令4.1安装docker软件包4.2开启docker并查看状态4.3配置阿里云镜像加速器4.4docker常用命令1.docker基本概念docker是容器技术的一个前端工具,容器是内核的一项技术,d
- 什么是华强北-ChatGPT4o作答
部分分式
笔记
华强北是中国深圳市的一个著名电子市场,位于福田区。它被誉为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交易市场之一,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消费者和技术爱好者。华强北以其丰富的电子元器件、电子产品以及配件而闻名,是全球电子产业链的重要组成部分。华强北的历史背景华强北的发展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随着深圳成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电子产业迅速崛起。最初,华强北只是一个传统的小市场,出售一些基础的电子元件和零配件。然而,
- Swagger自动文档工具以及gin-swagger的使用
百川Cs
Go工程化后端golangginci/cd
什么是Swagger?Swagger是一个开源的API设计和文档工具,旨在帮助开发者更高效地设计、构建、记录和测试RESTfulAPI。它基于OpenAPI规范(前身为Swagger规范),通过自动化的方式生成交互式API文档、客户端SDK和服务端代码,从而简化了API的开发和维护工作。核心功能自动生成API文档:Swagger能够通过解析代码中的注解或配置文件,自动生成API文档,包括接口路径、
- 深入浅出 Python 函数:编写、使用与高级特性详解
田猿笔记
python开发语言函数
引言在Python编程的世界中,函数堪称构建复杂逻辑和模块化程序的基础砖石。它能够帮助程序员组织代码、避免重复,并通过封装逻辑提高代码的可读性和可维护性。本文旨在全方位解析Python函数的核心概念,包括基础定义、文档化、默认参数、可选参数、解包参数、关键字仅参数、注解、可调用性检查、函数名称获取、匿名函数(lambda表达式)、生成器以及装饰器等多种实用特性。一、函数基础与文档化defexamp
- C++三连击(升级版)问题
D20120131
c++开发语言
题目:题解&解析:这个是一种比较简单粗暴的方法,主体思想时用循环枚举标准数,再根据比例确定三个数,并加以判断是否符合标准。首先定义变量,如上,i为标准数,j用来进行与使用数字相关的循环判断操作,num1,num2,num3为结果的三个数,x,b,c分别为A,B,C,以及标记变量flag并赋值0,最后是一个a数组,用来进行与使用数字相关的循环判断操作。输入之后,用一个循环枚举标准数,再表示出三个答案
- 2021年Javascript最常见的面试题以及答案
2401_86401365
javascript原型模式开发语言
区别:||和原数据是否指向同一个对象|第一层数据为基本数据类型|原数据中包含的子对象||—|—|—|—||浅拷贝|否|不会使原数据一起改变|会使原数据一起改变||深拷贝|否|不会使原数据一起改变|不会使原数据一起改变|点击对Javscript中浅拷贝和深拷贝的探索和详解查看详解项目中实现深浅拷贝常用的方法有哪些?===========================================
- 《网络安全之多维护盾:零信任架构、加密矩阵与智能检测的交响制衡》
烁月_o9
网络服务器安全运维密码学
网络安全之多维护盾:零信任架构、加密矩阵与智能检测的交响制衡一、引言在数字化浪潮汹涌澎湃的当下,网络空间已深度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成为推动全球经济、文化交流以及科技创新的核心引擎。然而,与之相伴的是网络安全威胁的指数级增长与日益复杂化。恶意黑客攻击、数据泄露事件频发,不仅对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构成严重威胁,更对个人隐私、国家安全等诸多方面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构建一套全面、高效且
- Hibernate不是过时了么?SpringDataJpa又是什么?和Mybatis有什么区别?
芝士汉堡 ིྀིྀ
mybatishibernatespring
一、前言ps:大三下学期,拿到了一份实习。进入公司后发现用到的技术栈有SpringDataJpa\Hibernate,但对于持久层框架我只接触了Mybatis\Mybatis-Plus,所以就来学习一下SpringDataJpa。1.回顾MyBatis来自官方文档的介绍:MyBatis是一款优秀的持久层框架,它支持定制化SQL、存储过程以及高级映射。MyBatis避免了几乎所有的JDBC代码和手动
- 【数据结构】最有效的实现栈和队列的方式(C&C++语言版)
大名顶顶
数据结构数据结构c语言c++程序员计算机编程软件开发
在这个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掌握基础的数据结构知识是每个程序员必不可少的技能。本文将深入探讨栈和队列这两种线性数据结构,带你了解它们在实际编程中的应用以及如何用C/C++代码实现这些结构的核心操作。我们不仅讲解了栈的后进先出(LIFO)和队列的先进先出(FIFO)原理,还通过实例展示了如何将这两种数据结构结合起来,提升编程效率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不论你是编程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开发者,本文都将
- 移动应用开发技术 架构图
彭乙肱
移动应用相关视频讲解:AIGC和微信的辅助学习移动应用开发技术架构图移动应用开发技术架构图是移动应用程序员必备的工具之一。它展示了一个应用程序的各个部分如何相互交互,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简要介绍移动应用开发技术架构图的基本概念,并使用代码示例来说明其重要性。架构图的重要性移动应用开发技术架构图对于理解一个应用程序的整体设计和功能至关重要。它可以帮助开发人员更好地组织代码,减少代
- 简识JVM中并发垃圾回收器和多线程并行垃圾回收器的区别
天天向上杰
jvmjava算法
在JVM中,多线程并行垃圾回收器和并发垃圾回收器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垃圾回收机制,它们的主要区别在于垃圾收集线程与用户线程之间的运行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应用程序性能的影响。以下是对这两种垃圾回收器的详细比较:一、多线程并行垃圾回收器定义与特点:多线程并行垃圾回收器(如ParallelGC)利用多核CPU的优势,通过多个垃圾收集线程同时工作来提高垃圾回收的效率。这些垃圾收集线程在垃圾回收过程中是并行的,
- 前端构建工具
光影少年
前端软件构建
前端构建工具是开发现代Web应用时不可或缺的工具,用于优化代码、提升开发效率、以及实现高效的构建和部署。以下是常见的前端构建工具及其作用:1.模块打包工具Webpack特点:功能强大,插件与配置灵活。作用:将模块(JS、CSS、图片等)打包成浏览器可运行的文件。适用场景:中大型项目,需高度自定义。Vite特点:轻量、快速构建,基于ESModules。作用:适合现代框架如Vue、React,热更新速
- 几种常见的求特殊方程正整数解的方法和示例
max500600
算法算法
以下是几种常见的求特殊方程正整数解的方法和示例:一元一次方程例题:已知关于(x)的方程(mx+3=9-x)((m)为不等于(1)的整数)的解是正整数,求该方程的正整数解,并求相应(m)的值.求解步骤:首先解方程(mx+3=9-x),移项可得(mx+x=9-3),即((m+1)x=6),解得(x=\frac{6}{m+1})。因为方程解是正整数,所以(m+1)是(6)的正因数,(6)的正因数有(1)
- 使用 Railway 和 Supabase 零成本搭建 n8n 自动化平台
小二上酒8
自动化系统架构运维java开发语言
在前文使用自动化工作流聚合信息摄入和输出中,我介绍了如何在NAS提供的Docker环境安装n8n,以及n8nworkflow的使用方式。经过3个月的使用,我有了一些新的体会和尝试,重新设计了n8n的部署方案。本文将对这套新的方案进行说明,并分享数据迁移和第三方服务接入的实践。系统架构系统架构图我们所要搭建的这套服务有着如图所示的系统关系。Cloudflare:CDN和Proxy,用于加速网站访问,
- 计算机毕业设计之jsp影视推荐系统
我的微信bishe911
课程设计java开发语言mysqljsp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网络系统都趋向于智能化、系统化,影视推荐系统也不例外,但目前国内的很多行业仍使用人工管理,影视信息量也越来越庞大,人工管理显然已无法应对时代的变化,而影视推荐系统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轻松的对影视信息进行评分,既能提高用户对影视推荐的了解,又能快捷的查看影视信息,取代人工管理是必然趋势。本影视推荐系统以SSM作为框架,B/S模式以及MySql作为后台运行的数据库。本系统主要包
- Vue.js组件开发研究
清北互联木材
vue.js
摘要随着前端技术的快速发展,Vue.js以其轻量级、高性能和组件化开发的优势,在前端开发领域占据了重要地位。本研究深入探讨了Vue.js组件开发的理论基础、开发方法以及实际应用。通过系统梳理Vue.js框架的核心特性、组件化思想及Vue.js组件的基本概念,本研究为Vue.js组件开发提供了全面的理论支撑。进一步地,本研究详细介绍了Vue.js组件的设计原则、组成要素及组件之间的关系,并阐述了组件
- RTSP的URL中用户名或密码含特殊字符怎么办?
音视频牛哥
RTSP播放器大牛直播SDK实时音视频音视频rtsp播放器rtspplayerrtspurl特殊字符rtsp解析url大牛直播SDK
技术背景在RTSP的URL中,如果包含用户名、密码以及特殊字符串,一般来说,需要遵循特定的格式和处理方式:用户名和密码:RTSPURL中包含用户名和密码时,通常使用username:password@的格式放在主机地址之前。例如:rtsp://admin:
[email protected]:554/cam/realmonitor?channel=1&subtype=0,其中a
- 流媒体直播实时视频延迟时间排查和剖析:gop关键帧间隔导致延迟,流媒体和播放器缓存,B帧等导致的延迟
eguid_1
#1.4.3版本)直播延迟视频延迟直播平台播放延迟网络延迟
本章是流媒体直播实时视频延迟时间排查和剖析javaCV系列文章:javacv开发详解之1:调用本机摄像头视频javaCV开发详解之2:推流器实现,推本地摄像头视频到流媒体服务器以及摄像头录制视频功能实现(基于javaCV-FFMPEG、javaCV-openCV)javaCV开发详解之3:收流器实现,录制流媒体服务器的rtsp/rtmp视频文件(基于javaCV-FFMPEG)
- linux下nginx部署以及配置详解
由数入道
运维服务器
单台配置linux下nginx部署以及配置详解-韦邦杠-博客园(cnblogs.com)多台配置在linux系统下安装两个nginx以及启动、停止、重起-韦邦杠-博客园(cnblogs.com)
- C++学生学籍管理系统开发详解
悦闻闻
本文还有配套的精品资源,点击获取简介:学生学籍管理系统是高校或教育机构中管理学生信息的重要工具。本项目详细介绍基于C++实现该系统的关键技术和方法。从面向对象编程、数据结构的选择,到数据库操作、运算符重载、文件I/O处理、用户界面设计、异常处理,以及单元测试等,系统地覆盖了构建高效、稳定学籍管理系统的全过程。1.面向对象编程基础面向对象编程(OOP)是现代编程范式的核心,它允许开发者通过类和对象来
- 【深度学习|迁移学习】Wasserstein距离度量和跨域原型一致性损失(CPC Loss)如何计算?以及Wasserstein距离和CPC Loss结合的对抗训练示例,附代码(二)
努力学习的大大
深度学习基础深度学习迁移学习人工智能python
【深度学习|迁移学习】Wasserstein距离度量和跨域原型一致性损失(CPCLoss)如何计算?以及Wasserstein距离和CPCLoss结合的对抗训练示例,附代码(二)【深度学习|迁移学习】Wasserstein距离度量和跨域原型一致性损失(CPCLoss)如何计算?以及Wasserstein距离和CPCLoss结合的对抗训练示例,附代码(二)文章目录【深度学习|迁移学习】Wassers
- 【Python Web开发】Python Web开发知识全解析
萧鼎
python基础到进阶教程python前端开发语言
PythonWeb开发知识全解析Python是一种强大的编程语言,以其简洁和高效而闻名,尤其在Web开发领域,它有着广泛的应用。Python提供了许多功能强大且灵活的Web框架,如Flask、Django、FastAPI等,使得构建现代Web应用变得简单而高效。本文将从PythonWeb开发的基本知识入手,逐步介绍开发流程、核心技术以及如何使用Python框架构建高效、可扩展的Web应用。1.什么
- Ubuntu Server连接wifi
Young4Dream
Linuxubuntulinux运维
背景家里服务器放在客厅太吵了,准备挪到阳台,所以买了TPwifi接收器,因此需要配置wifi连接.刚开始买了TendaAx300,结果不支持服务器系统,买前还是得和客服交流交流.准备驱动安装对于windows系统来说,这款接收器是免驱的,但在linux上需要安装相应型号驱动安装完成后,使用ipa查看网卡情况,一般wl开头的就是我们的主角.配置nmcli命令是配置的主要工具,需要先安装network
- Django 日志配置实战指南
ivwdcwso
django数据库sqlitepython开发
日志是Django项目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帮助我们记录应用程序的运行状态、调试信息、错误信息等。通过合理配置日志,我们可以更好地监控和调试应用程序。本文将详细介绍如何在Django项目中实现日志文件分割、日志级别控制以及多环境日志配置,并结合最佳实践和代码示例,帮助你全面掌握Django日志的使用。1.日志级别概述Python的日志模块定义了以下日志级别(从低到高):DEBUG:详细的调试信息,
- ASM系列六 利用TreeApi 添加和移除类成员
lijingyao8206
jvm动态代理ASM字节码技术TreeAPI
同生成的做法一样,添加和移除类成员只要去修改fields和methods中的元素即可。这里我们拿一个简单的类做例子,下面这个Task类,我们来移除isNeedRemove方法,并且添加一个int 类型的addedField属性。
package asm.core;
/**
* Created by yunshen.ljy on 2015/6/
- Springmvc-权限设计
bee1314
springWebjsp
万丈高楼平地起。
权限管理对于管理系统而言已经是标配中的标配了吧,对于我等俗人更是不能免俗。同时就目前的项目状况而言,我们还不需要那么高大上的开源的解决方案,如Spring Security,Shiro。小伙伴一致决定我们还是从基本的功能迭代起来吧。
目标:
1.实现权限的管理(CRUD)
2.实现部门管理 (CRUD)
3.实现人员的管理 (CRUD)
4.实现部门和权限
- 算法竞赛入门经典(第二版)第2章习题
CrazyMizzz
c算法
2.4.1 输出技巧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int i, n;
scanf("%d", &n);
for (i = 1; i <= n; i++)
printf("%d\n", i);
return 0;
}
习题2-2 水仙花数(daffodil
- struts2中jsp自动跳转到Action
麦田的设计者
jspwebxmlstruts2自动跳转
1、在struts2的开发中,经常需要用户点击网页后就直接跳转到一个Action,执行Action里面的方法,利用mvc分层思想执行相应操作在界面上得到动态数据。毕竟用户不可能在地址栏里输入一个Action(不是专业人士)
2、<jsp:forward page="xxx.action" /> ,这个标签可以实现跳转,page的路径是相对地址,不同与jsp和j
- php 操作webservice实例
IT独行者
PHPwebservice
首先大家要简单了解了何谓webservice,接下来就做两个非常简单的例子,webservice还是逃不开server端与client端。我测试的环境为:apache2.2.11 php5.2.10做这个测试之前,要确认你的php配置文件中已经将soap扩展打开,即extension=php_soap.dll;
OK 现在我们来体验webservice
//server端 serve
- Windows下使用Vagrant安装linux系统
_wy_
windowsvagrant
准备工作:
下载安装 VirtualBox :https://www.virtualbox.org/
下载安装 Vagrant :http://www.vagrantup.com/
下载需要使用的 box :
官方提供的范例:http://files.vagrantup.com/precise32.box
还可以在 http://www.vagrantbox.es/
- 更改linux的文件拥有者及用户组(chown和chgrp)
无量
clinuxchgrpchown
本文(转)
http://blog.163.com/yanenshun@126/blog/static/128388169201203011157308/
http://ydlmlh.iteye.com/blog/1435157
一、基本使用:
使用chown命令可以修改文件或目录所属的用户:
命令
- linux下抓包工具
矮蛋蛋
linux
原文地址:
http://blog.chinaunix.net/uid-23670869-id-2610683.html
tcpdump -nn -vv -X udp port 8888
上面命令是抓取udp包、端口为8888
netstat -tln 命令是用来查看linux的端口使用情况
13 . 列出所有的网络连接
lsof -i
14. 列出所有tcp 网络连接信息
l
- 我觉得mybatis是垃圾!:“每一个用mybatis的男纸,你伤不起”
alafqq
mybatis
最近看了
每一个用mybatis的男纸,你伤不起
原文地址 :http://www.iteye.com/topic/1073938
发表一下个人看法。欢迎大神拍砖;
个人一直使用的是Ibatis框架,公司对其进行过小小的改良;
最近换了公司,要使用新的框架。听说mybatis不错;就对其进行了部分的研究;
发现多了一个mapper层;个人感觉就是个dao;
- 解决java数据交换之谜
百合不是茶
数据交换
交换两个数字的方法有以下三种 ,其中第一种最常用
/*
输出最小的一个数
*/
public class jiaohuan1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int a =4;
int b = 3;
if(a<b){
// 第一种交换方式
int tmep =
- 渐变显示
bijian1013
JavaScript
<style type="text/css">
#wxf {
FILTER: progid:DXImageTransform.Microsoft.Gradient(GradientType=0, StartColorStr=#ffffff, EndColorStr=#97FF98);
height: 25px;
}
</style>
- 探索JUnit4扩展:断言语法assertThat
bijian1013
java单元测试assertThat
一.概述
JUnit 设计的目的就是有效地抓住编程人员写代码的意图,然后快速检查他们的代码是否与他们的意图相匹配。 JUnit 发展至今,版本不停的翻新,但是所有版本都一致致力于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发现编程人员的代码意图,并且如何使得编程人员更加容易地表达他们的代码意图。JUnit 4.4 也是为了如何能够
- 【Gson三】Gson解析{"data":{"IM":["MSN","QQ","Gtalk"]}}
bit1129
gson
如何把如下简单的JSON字符串反序列化为Java的POJO对象?
{"data":{"IM":["MSN","QQ","Gtalk"]}}
下面的POJO类Model无法完成正确的解析:
import com.google.gson.Gson;
- 【Kafka九】Kafka High Level API vs. Low Level API
bit1129
kafka
1. Kafka提供了两种Consumer API
High Level Consumer API
Low Level Consumer API(Kafka诡异的称之为Simple Consumer API,实际上非常复杂)
在选用哪种Consumer API时,首先要弄清楚这两种API的工作原理,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能做的话怎么做的以及用的时候,有哪些可能的问题
- 在nginx中集成lua脚本:添加自定义Http头,封IP等
ronin47
nginx lua
Lua是一个可以嵌入到Nginx配置文件中的动态脚本语言,从而可以在Nginx请求处理的任何阶段执行各种Lua代码。刚开始我们只是用Lua 把请求路由到后端服务器,但是它对我们架构的作用超出了我们的预期。下面就讲讲我们所做的工作。 强制搜索引擎只索引mixlr.com
Google把子域名当作完全独立的网站,我们不希望爬虫抓取子域名的页面,降低我们的Page rank。
location /{
- java-归并排序
bylijinnan
java
import java.util.Arrays;
public class MergeSort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int[] a={20,1,3,8,5,9,4,25};
mergeSort(a,0,a.length-1);
System.out.println(Arrays.to
- Netty源码学习-CompositeChannelBuffer
bylijinnan
javanetty
CompositeChannelBuffer体现了Netty的“Transparent Zero Copy”
查看API(
http://docs.jboss.org/netty/3.2/api/org/jboss/netty/buffer/package-summary.html#package_description)
可以看到,所谓“Transparent Zero Copy”是通
- Android中给Activity添加返回键
hotsunshine
Activity
// this need android:minSdkVersion="11"
getActionBar().setDisplayHomeAsUpEnabled(true);
@Override
public boolean onOptionsItemSelected(MenuItem item) {
- 静态页面传参
ctrain
静态
$(document).ready(function () {
var request = {
QueryString :
function (val) {
var uri = window.location.search;
var re = new RegExp("" + val + "=([^&?]*)", &
- Windows中查找某个目录下的所有文件中包含某个字符串的命令
daizj
windows查找某个目录下的所有文件包含某个字符串
findstr可以完成这个工作。
[html]
view plain
copy
>findstr /s /i "string" *.*
上面的命令表示,当前目录以及当前目录的所有子目录下的所有文件中查找"string&qu
- 改善程序代码质量的一些技巧
dcj3sjt126com
编程PHP重构
有很多理由都能说明为什么我们应该写出清晰、可读性好的程序。最重要的一点,程序你只写一次,但以后会无数次的阅读。当你第二天回头来看你的代码 时,你就要开始阅读它了。当你把代码拿给其他人看时,他必须阅读你的代码。因此,在编写时多花一点时间,你会在阅读它时节省大量的时间。让我们看一些基本的编程技巧: 尽量保持方法简短 尽管很多人都遵
- SharedPreferences对数据的存储
dcj3sjt126com
SharedPreferences简介: &nbs
- linux复习笔记之bash shell (2) bash基础
eksliang
bashbash shell
转载请出自出处:
http://eksliang.iteye.com/blog/2104329
1.影响显示结果的语系变量(locale)
1.1locale这个命令就是查看当前系统支持多少种语系,命令使用如下:
[root@localhost shell]# locale
LANG=en_US.UTF-8
LC_CTYPE="en_US.UTF-8"
- Android零碎知识总结
gqdy365
android
1、CopyOnWriteArrayList add(E) 和remove(int index)都是对新的数组进行修改和新增。所以在多线程操作时不会出现java.util.ConcurrentModificationException错误。
所以最后得出结论:CopyOnWriteArrayList适合使用在读操作远远大于写操作的场景里,比如缓存。发生修改时候做copy,新老版本分离,保证读的高
- HoverTree.Model.ArticleSelect类的作用
hvt
Web.netC#hovertreeasp.net
ArticleSelect类在命名空间HoverTree.Model中可以认为是文章查询条件类,用于存放查询文章时的条件,例如HvtId就是文章的id。HvtIsShow就是文章的显示属性,当为-1是,该条件不产生作用,当为0时,查询不公开显示的文章,当为1时查询公开显示的文章。HvtIsHome则为是否在首页显示。HoverTree系统源码完全开放,开发环境为Visual Studio 2013
- PHP 判断是否使用代理 PHP Proxy Detector
天梯梦
proxy
1. php 类
I found this class looking for something else actually but I remembered I needed some while ago something similar and I never found one. I'm sure it will help a lot of developers who try to
- apache的math库中的回归——regression(翻译)
lvdccyb
Mathapache
这个Math库,虽然不向weka那样专业的ML库,但是用户友好,易用。
多元线性回归,协方差和相关性(皮尔逊和斯皮尔曼),分布测试(假设检验,t,卡方,G),统计。
数学库中还包含,Cholesky,LU,SVD,QR,特征根分解,真不错。
基本覆盖了:线代,统计,矩阵,
最优化理论
曲线拟合
常微分方程
遗传算法(GA),
还有3维的运算。。。
- 基础数据结构和算法十三:Undirected Graphs (2)
sunwinner
Algorithm
Design pattern for graph processing.
Since we consider a large number of graph-processing algorithms, our initial design goal is to decouple our implementations from the graph representation
- 云计算平台最重要的五项技术
sumapp
云计算云平台智城云
云计算平台最重要的五项技术
1、云服务器
云服务器提供简单高效,处理能力可弹性伸缩的计算服务,支持国内领先的云计算技术和大规模分布存储技术,使您的系统更稳定、数据更安全、传输更快速、部署更灵活。
特性
机型丰富
通过高性能服务器虚拟化为云服务器,提供丰富配置类型虚拟机,极大简化数据存储、数据库搭建、web服务器搭建等工作;
仅需要几分钟,根据CP
- 《京东技术解密》有奖试读获奖名单公布
ITeye管理员
活动
ITeye携手博文视点举办的12月技术图书有奖试读活动已圆满结束,非常感谢广大用户对本次活动的关注与参与。
12月试读活动回顾:
http://webmaster.iteye.com/blog/2164754
本次技术图书试读活动获奖名单及相应作品如下:
一等奖(两名)
Microhardest:http://microhardest.i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