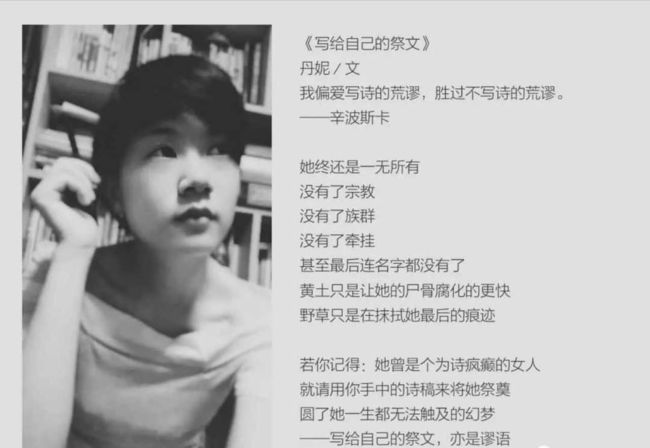这是我在上所写的第一篇读后感,上一篇收录在我的文集《文心雕玉》里的是一篇诗评,虽至今无人问津,但那确是我人生的第一篇诗歌文学评论,而非普通鉴赏文。曾在去年考虑理转文,因而在考研复习阶段写下了那篇文章。毕竟丹妮是先爱上诗,再爱上别的文体的,因而将《“蛇”影斑斓——评冯至<蛇>的语言特色》作为了我的第一篇。
今天这一篇是至关重要的,无论你是文学爱好者,或是真爱文学的人。为什么我要这样来区分?先让我来简介下施老,如果通过百度搜索,你能搜到的关键词是“新感觉派”,“现代派作家”,对,施老就是一位有着超前意识的作家,《梅雨之夕》因是我走近他的第一篇文章,然而读后却一头雾水,长期阅读老舍,巴金,张爱玲等写实风格的我对心理分析的文还很陌生,直到我读到西方的《尤利西斯》,《荒原狼》,以及《墙上的斑点》才渐渐接受这类心理小说,也包括施老的《将军底头》,《鸠摩罗什》,《春阳》,有人说他的都市心理小说,与沈从文的乡情小说,是中国文坛对称的两大支柱,共同完成了现代短篇小说的话语构建。
这是时代给施老的标签,一个孤独走在时代之先的文人,也曾因误会,他成了一个在鲁迅先生的杂文里,以“洋场恶少”和“叭儿”的身份,赫然列入长长的鲁氏骂人名单里的可笑反面角色,后经“平反”才咸鱼翻生。
而读到他的《待旦录》,是前几天的事,最近细细品读30位现代散文大家作品,之前读了郁达夫的《闲书》,甚是喜欢,特别是重温了《故都的秋》,也读到许地山的《空山灵雨》,《信仰之衰落》也仍记忆犹新,但只有读到《爱好文学》和《文学之贫困》时,才有鞭策之感,如惊雷打在文学起跑路上的自己身上,指引我走好未来的路。
不管你对于他的爱好文学的热心多么敬佩,但他的作品常常使你没有方法说几句鼓励的话。(现象一)
有不少写文章的人,他们的作品常在各式各样的杂志报纸上发表着,令多数读者觉得满意,然而当你有一个机会和这位作者会面的时候,便会感到很大的诧异,他看上去是多么迟钝和平庸,一点没有关心于文学的神情,除了能喝咖啡,能跳舞,能打牌以外,好像什么都不会的。(现象二)
爱好文学是表示他对于文学有感情,但要成为一个好的创作家,仅仅靠这一点点感情是不够的。(结论一)
若果一个青年要滥用他爱好文学的感情,同时又没有能力或热忱去使他对于文学的修养深入一些,以为自己有了这种肤浅的感情就无异于有了可信的创作能力,于是抛却了他应该学习的专门技能,而从事于写作,结果常是碰到了惨酷的失败。文学界的损失,倒并不是在于他们个人的文学事业之失败,而是在于他们因此而一并牺牲了他们的爱好文学的感情。(结论二)
——摘抄于《爱好文学》
以上施老通过两种现象,简言之,盲目创作的现象和靠旧名气生活的现象,得出的结论是:一,对文学的感情只是成为好的创作家的一小部分因素;二,热爱文学的情感应该成为提高文学修养的动力。
然后又谈到另一个文学陷阱,也就是用对文学的情感脱颖而出的少部分青年人。
这些因为各种偶然的机缘而脱颖而出的青年人,常常是有着相当丰富的摹仿能力。他以为文艺创作不过是一个很单纯的技巧问题。(陷阱)
——摘抄于《爱好文学》
这种利用总结模版,然后填字的人占了文坛的相当多数,比如,总结出“鲁迅文谱”的人的文流行于各大报刊,这样的危害就有二:一,足以使一般爱好文学的青年无法把他们对于文学的感情保持得更长久些;二,足以使文学的趋势永远停滞着,遏止了伟大作品产生的机会。
所以作者说,爱好文学对于有些文学爱好者是一个危机,例如,逃避理工科的学习却又认为文学只是狭隘到读读小说而已(文学的学习科目之广不少于理工科,这点会在下文的《文学之贫困》里提到)。
“技巧在文学创作上是最小的因素”,是施老对“因爱好文学而从事于写作,因写作技巧相当圆熟而得以略有成就的青年”所说的,然而这最小的因素也得有创造精神。在文学创作的途径上,从形式上说,如果不能控制旧语文,即没有能力创造新语文。从内容上说,如果不能熟知人的各种生活,即无法在其作品中表现真实的人生。用别人的形式为自己的形式,用别人的内容为自己的内容,表里都丝毫没有创造性,即使看得过去也还是一个没有灵魂的傀儡。
我想“依葫芦画瓢”并不是文学创作的终点,总结前人的内容或形式,情况好点,不被发现,可以沾到前者的光环(形式模仿者),情况坏点,利用剽窃的噱头大博眼球一番,赚得阅读量(内容模仿者)。所以,真如作者所言,“爱好文学,不一定得从事创作。要从事创作,必须真能爱好文学。”
现代人对于文学这个名称的观念,具体地说起来,仿佛就以为这是诗歌,小说(长 篇及短篇),戏剧,散文的总称而已(有些人还主张加上杂文和报告两类),在这些项目以外,仿佛就没有了文学的疆域。或者还有些人,认为文学的疆域不能限制得这样狭窄,他们要把别的一些文字撰述拉进来算做文学,于是把上述的四种东西称之为纯文学。 这样对于文学的疆域之观念固然开拓了不少,但是诗歌,小说,戏剧,散文这四者仍然被约束在一个“纯”字范围里,作为自成一个流派的东西。
——摘抄于《文学之贫困》
我不知别人是怎样看待“文学的范畴”的,但曾经的我确实是大捧“纯文学”的一类人,甚至对“通俗文学”都有些不屑于顾,包括张爱玲这样的海派作家的小说。当然我犯的另一个观念性错误,就是排斥旧文学的知识摄入,除了在书法学习是会翻看一些古言的含义,或者在小说里撞见一些新典故外,很少去读古籍,这也受到一个北大学“史学”的研究生哥哥的指责,他说我不是一个文化人,更不具备做文化人的态度,起先我只认为这是一个“学史”文人对我的不满,而今才知这是我对“历史”的不尊重,即使我也是个爱看历史纪录片的人,然而“文学的历史”是这样说的:
在古代,无论中国或西洋,却并不如此。希腊人所谓文学, 是连历史,哲学,演说辞都包含在里头的。而且,它们还占了文学中的主要地位。中国也如此。孔门四教,以文为第一。而这个“文”字是统摄六艺而言的。古典的文学观念, 似乎以中国为保持得最长久,一直到晚清,历史和哲学始终没有被赶出文学的大门之外,而小说始终没有被请进会客厅。自从西洋的近代文学观念及教育制度被贩进中国来之后, 于是,小说被选录进中学国文教科书,而哲学及史学在大学院中别自成为一系了。现在,大学中国文学系的科目,只有历代文选,诗选,词曲选和一门文学史了(虽然还有一个语言文字组,但不久比较语言学发达起来,眼见得它也快要别成一系,退出文学范围了)。文学的观念及文学的教育制度,都在倾向着愈纯愈窄的路上走,而说这个时代的文学会比古代更丰富,我很怀疑。
——摘抄于《文学之贫困》
施老又用例证法说明——在古代,现代之所谓纯文学,只是知识阶级的共同必修科而已。 (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又称赞子贡“始可与言诗矣。”)纯文学作品对于社会的作用,也并不像现代一样地只是被当作民众的读物而已。它多半是辅助政教的东西。然而揭露了现代纯文学的社会是这样的:
而现在呢?我们的文学家所能写的只是小说,诗歌,戏剧,散文,上焉者兼有四长,便为全才,下焉者仅得一技,亦复沾沾自喜,俨然自以为凤毛麟角。历史,哲学,政治以及其他一切人文科学全不知道。因此文学家仅仅是个架空的文学家。生活浪漫,意气飞扬,语言乏味,面目可憎,全不像一个有优越修养的样子。就其个人而言,则上不能恢宏学术,下不堪为参军记室;就其与社会之关系而言,亦既不能裨益政教,又不能表率人伦。至多是能制造几本印刷物出来,在三年五载之中,为有闲阶级之书斋清玩,或为无产阶级发泄牢骚之具而已。
——摘抄于《文学之贫困》
再看史学,哲学,法学,外交这些,都很少被优秀的文学爱好者问津,哲学里,更多是尼采,叔本华等,“听说英国的教育制度,凡读政治,法律及外交者,必须先是一个文学士,我想这个办法是很有道理的”。最后,施老说:
我并不主张文学观念之复古。但我不赞成一般文学 (GeneralLiterature)与纯文学(PureLiterature)这两个名称之对立。历史,哲学与政治应该与小说,诗歌,戏剧同样地成为一个有文学修养的学者的表现。文学家不应该仅仅是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的写作者的尊称。甚至,文学家也不应该是一种职业。(据我所知道的,恐怕只有美国有职业的文学家,因为美国的BestSeller可以藉此生活,而欧洲及英国则不然。)而历史,哲学及政治家必须先从文学入手。在教育制度上,我以为大学中国文学系的地位不应该和土木工程系,会计系等专门技术的学系处于同等地位,它至少应该成为文法学院各系的先修系或共同必修科。照现在的情形看来,我们显然可见文学愈“纯”则愈贫困,纵然书店里每月有大量的诗歌,小说,戏曲,散文出版——这是出版业的繁荣,不是文学的繁荣。
——摘抄于《文学的贫困》
这是他的建议,也引起我的反思,当读完《文学之贫困》,让我惭愧于所学的单薄的文学知识。曾在旅途中,认识一爱画画的中年女人,当她知道我说“爱好文学”时,问我懂不懂政治。
我答:“不懂,也不愿懂。”
她说:“你说伊拉克战争对吗?”
我答:“孰是孰非?怎可说。认识一个伊拉克人,他的手臂受到炸弹爆破的伤害,我只看着心疼;认识一个美国士兵,他说他为和平而战,眼看着自己的战友死在自己面前,他也要为和平而战;认识一个利比亚人,他说美国不是最大凶手,是他们自己的人民赶走了萨达姆;认识一个长期做法务工作者,他说伊拉克的石油最后被中国购买,美国战争损失远超石油。”“一个一个说辞,我没有亲眼看见,我不评论,也许我只想做沈从文那样的人,偏安一隅,独善其生,文学不通,便转向服饰研究。”
她坚定地说:“你逃不了的,学文必学政治。”
她的话仍在耳畔,我逃不了的。古文逃不了,政治也逃不了,这是我追逐文学的必由之路。无可置否,曾经文学就是一本小说对我的诱惑,是无聊赖时打发时间的方式,我还一度拿着“我是理科生”的理由来宽慰自己的不进取。真正学文才一年有余,不是回避理工科的逃跑者,是回避庸俗生活的落魄者,成年前立志学医的鲁迅爱好者。
学过会计,金融,法律,最终在文学(现当代文学)上落足,自诩为文学爱好者,写诗,写小说,写散文,书评,游记也可归纳到散文集的范畴,甚是狭隘。
曾记得萧红在《纪念鲁迅先生》一文中提到,“周先生什么书都看”,所以能为萧红鉴赏服饰的穿搭,如果要说学习文学的态度,鲁迅态度仍然是值得借鉴的,广度,深度,精度,我相信这是大多做文字研究工作者的必经之路。也是我当下坚持的事情。
然而当下,“鸡汤文”,“职场文”,“干货文”之风越来越盛,如果说从哲学,历史,政治,和文学等多个方面来定义的文学,转变到由西方传来的小说为主的文学定义,是“文学之贫困”的表现,那么,在现今,当商业文学成为挤压纯文学时,文学之路又将走向何方?
这是我看到的现象,因而仍坚持着写文,也扩大自己的阅读广度。也让自己在母亲的眼里活成了奇葩,当她问我为何不能像普通人那样活着?我说社会必需要两类人:一类是为梦想,为死后的可能性而活的人;一类是为现实,为柴米油盐酱醋茶而活在现世。而我决定做现实以上的人,当我决定那一刻起,就注定我之后的路的贫乏和孤苦,但“空”并不是一种哀苦,而是一种态度,无关好歹。
曾写过一首诗,愿刻在自己死后的碑上,致敬辛波斯卡的《墓志铭》。
曾经施老的同学戴望舒在白色恐怖的20世纪30年代根据“丁香空结雨中愁”写下了哀怨而愁苦的《雨巷》,而今我想赠一首诗给诗人:
《诗人雨》
丹妮/文
一场雨后
一个个鲜活的文字
钻出土壤
奔向诗人
……
雨巷里
风浪不顾尴尬
在一地疙瘩上
荡起涟漪
(谢谢你读完这篇长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