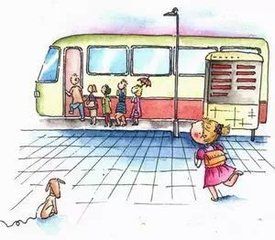第五章
心动
1
夜风送来只属于我自己的恐惧与苍凉。我无助,更孤独,孤独叫我无比忧伤。每当从地下通道卖画回到住处,推开地下室小屋的房门;每当一觉醒来望着灰暗的墙壁,就更加感到难奈的寂寞与孤独了。
晚上,我对着孤灯,独守空房,似乎整个世界只有我一人。四周一片寂静,空气都凝固了。只有那遥远的寒星陪伴我,这就更增加了寂寥和难奈。有时,害怕极了。这是一种独身人的房间里特有的寂静,十分凄凉。就连门外发出的轻微响声,都会使我毛骨悚然。孤独在杀人!
我为青春年华在寂寞、孤独与恐惧中白白流逝而感到无比地惋惜;也为青春年华不能与真诚的爱情相伴,在渐渐凋谢而由衷地伤怀。
我曾不止一次地在最痛苦的时候回忆有家时的幸福。这时,才真切地体味到意大利诗人但丁的那句话:再也没有什么比在苦难的时候回忆幸福而更加痛苦了。
夜晚我又失眠了,失眠的滋味只有失过眠的人才能体会得到,那是魔鬼对人地狱般的折磨。直至天明,我仍然毫无睡意。一束微弱的光穿透天窗照在墙面上,我瞅着脱落了一块墙皮的墙面发呆,瞅得眼睛发涩。看着看着那墙面就变成了一座大山的图形,再看又像是孙天庆的孤魂野鬼;仔细看,还像一个披着长发的女人。
想到女人,我就联想到迟亦菲,她害了我,毁了我的家,她背叛了我,我恨她。可是我还常常思念她。
我的心啊,里面装着一半痛苦,装着一半思念。
人在孤独寂寞的时候最容易伤怀,身在异乡见景生情,常常勾起我对往事的回忆。那天在公交车上,我看见一对情侣相依相偎,情不自禁就回想起我初恋时的情景,往事悠悠……
开往老城钢铁公司的201路公交车,这是我每天上班都要乘坐的专车。在轰轰的马达声中,公交车毫无新意,周而复始,每天都是一副千古不变的老样子,颠簸在老城的黄金古道上。上下班高峰的时间,车箱座无虚席,我常常是手握栏杆站到下车。
汽车开到白塔车站,我的手仍还紧紧地抓住横在头顶上的扶手,随着物理现象中的惯性运动,整个身体随之摇摆。司机很不讲究,常常把客车当作货车驾驶。汽车停下,我也站稳了脚跟。车门开处,下去两人又上来几个人,末尾上来的是一个小姑娘,应该称她为女士。
在女士掏钱买票的当儿,车子猛然开动。小姑娘措手不及没有抓住扶手,她径直向我扑来。同时,在过道站着的几个乘客也像麦浪似地摆起来。在麦浪中,面对突如其来的女人,我迅速腾出一只手去扶她,但她还是闯进了我的怀里。在我怀里,她抬起头,幽幽的眼睛像电光一样刺痛了我。从她的眼神里,我感到,我的脸也一定是红透了。
小姑娘红着脸,说:“对不起!”
当然,我要说一声没关系。说罢,她像触了电一样迅速躲开。
我真切地感到,被撞的身体热乎乎的。我开始关注这个年轻美丽的姑娘。姑娘上身白衬衫,下身红格裙,头上一只紫红色发卡扎着翘起的马尾巴小辫,像一面小旗帜在颠簸中飘扬。辫子上的发卡无比醒目,犹如一个精灵在我眼前不停地晃动。小姑娘躲到了远处,面向车窗外,一只手紧紧抓着扶手。
到了钢城车站,她下了车,我也下车了,同时下车的还有另外一些老面孔。我走在姑娘的后边,与她相距不足十米。小姑娘走路的姿态,轻快活泼,焕发青春的活力。
步入公司大门,我注意到,小姑娘走进公司总部办公大楼。而我还得继续前行百米之遥,我所在的宣传部办公地点在俱乐部。那时,我的职位是宣传部的美术宣传员。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清楚地记得,我曾和小姑娘在201路公交车上有过三次邂逅。在车上,每当彼此的目光相遇之时,我们几乎都是同时迅速地把目光移开。背地里,我时不时地把目光落在那个动人的紫红色发卡上。尽管汽车仍旧颠簸,但是满怀相撞的奇迹再难出现了。
有了上次经验,小姑娘的手总是紧紧地握住扶手。而我对那次温柔甜蜜的相撞,始终保存着依依的记忆。我认为,虽然她和我之间有三五个乘客的阻挡,她也应该在适当的时机转过脸,在空隙间看见我,可是她却偏偏把美丽的面庞转向车窗外,这叫我很失望。
有一次,她在无意间转过身面向了我,我却莫名其妙地紧张起来,一颗心咚咚地跳。
时光慢悠悠,我利用工作空闲和业余时间,创作油画《炼钢工人》系列作品。我的理想,是有朝一日举办个人画展。为了画展,我已经准备了两年多了。
这一年,我24周岁。我还没有真正意义地处过女朋友,对女人的了解还处在懵懂时期。不过对男人,我已经很了解了。我是在梦中懂得了男人,并认识了自己,是在未来的生活中了解了女人,认识了生活。懂得男人的时候,我17岁。
那年的某夜,我梦见了中学同学严淑贤,她是我蒙昧的少年时代暗暗喜欢的一个女同学。在梦里,我和她骑着一匹白马,奔跑在草原上,广袤原野花花草草。在奔跑中,我感到身体发涨,从未有过的一种感觉,就像吸食了海洛因,飘忽、兴奋还有畅快。
我在梦中惊醒!醒来之时,发现下边已是黏糊糊溽热地湿成了一片,不知道那里流出的是什么东西?我以为是出血了,用手往下摸一把,浆糊样的东西粘满手心。担心蹭到被子上,我将一条腿蜷起来,用腿将被子支成凉棚状。一只手攥着琼浆玉液,直到天亮。
东方微茫,天亮了。我张开手掌,做贼似地把眼去看,以为一定会看到一片鲜红。然而,掌心里的琼浆玉液早已干涸,没有颜色。几天过后,才晓得,我已经长大了,终于认清自己已经是一个男人了……
一个男人,在一个雨天被阻隔在车站。下班的高峰已经过了多时,刚才我还孤零零地立于站牌下等车,现在我却跑到一家小店的廊檐下避雨。
西北上方翻卷的乌云,铺天盖地漫过天空。电光闪闪,雷声隆隆,闪着白光的雨丝横斜着扑向大地,地上的角角落落都积满了水,水面仿佛有无数个张着嘴的小青蛙,哗哗啦啦在唱歌,在吐水泡,掀起一圈圈涟漪,好像在和我开玩笑。保住了上身没有淋到雨水,而鞋子和裤脚却湿成了一片。夏雨吓小鬼,夏天的雨是下不长的。
天上的云又白得透亮了,散发着天国的幽光。车站牌下已空无一人,而对面的房檐下却聚集了好多焦急等车的身影。西边的铁路桥下瞬间就积满了雨水,公交车被阻隔在桥的那边。这是每当雨天,它固定的模式,没有人去责怪,也没有人对公交车报有什么幻想,人们早已经习惯了。
只能等待,等待雨停,再想办法回家。远处钢铁公司参差错落的高炉被朦胧的雨雾淡化,神话般像天上的宫阙。那边的铁路桥,桥下的流水,近处的车站,映着天光的小路以及民宅构成一幅淡淡的水墨画,悠远而绵长。
不知何时,远处的桥旁现出几个卖雨具的人,好像从地底下长出来的一样,有水就有鱼,下雨便有商机。
雨小了,一顶红色雨伞在远处奇迹般地冒出来,飘然而至。我被灰蒙雨景多添一笔红色而激动,一步就迈出廊檐,暴露在雨中,以欣赏的目光凝望着红雨伞。雨伞美丽了城市的风景,为水墨画增添了色彩。
玫瑰色长裙赋予车站一派生机,没有车的车站有了青春,我宁愿这样。罩在雨伞下的长裙迎风招展,小旗帜上的紫红色发卡,虽小却十分耀眼,猛地一晃,像闪烁的星,小姑娘在眺望桥那边的公交车。顺着她的目光,我也向烟雨迷茫的铁路桥望去。
不知何时,雨伞来到我的身旁,又笼罩在我头顶上的一方天空。
“为什么叫雨淋着?”
“没……没有。”我语无伦次。
小姑娘送来一阵淡淡的芳香,她擎着红雨伞,望着我。“你叫贺鸿鹏,我知道。”
“你怎么知道?”
“知道就是知道,你是美术学院毕业的大学生,画油画的。”
我在老城钢铁公司还算是小有名气,大学毕业三年,勉强也算个文化人。公司员工都晓得摆在总部宣传栏里的宣传画是我的大作,还有公司门外高耸而立的厂区鸟瞰宣传油画。
“奇怪!你呢?”
“我在办公室当文员,你们的名字我都知道。”她的样子有些得意。
“你们?哦……”
原来如此。我一阵紧张,紧张得感到淋在身上的雨水都是热的。此时的雨明显地小了,但仍然在不依不饶地下,公交车还没有出现。这一切都好像是上帝的安排,机不可失,我不能错过上帝赐给我们的良缘。
“你怎么才下班?”
“有个材料要写。”她问我:“你呢?”
“画画,所以赶上雨了。”我问她:“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
“迟亦菲。”
“哦,迟亦菲,好听。”
天上的小雨变成了蒙蒙细雨,小城也跟着阴暗下来,想必太阳早已在云层后面悄悄落山。街灯像似听到了口令,齐刷刷地同时点亮,地面汪着水,一盏盏街灯成双成对地倒映。我想到了“成双成对”这个词,也联想到,如果每天都能成双成对地上班下班,把今天的故事延长再延长,不会是梦吧?201路公交车,在不该出现的时候驶来了,停在站牌下。
从四面八方涌来几十个人,依次上车,并都找到了座位。迟亦菲收起红雨伞,在我之前上车,找到座位。我俩先后坐下。我再也找不到什么话语和她攀谈,迟亦菲也不可能扭过头与坐在身后我唠嗑。毕竟我们不熟悉,毕竟我还摸不准她的思路。但是,今天这个良好开端,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
毕竟,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请看下集 —— 追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