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故事,只能发生在香港
![]()
高级的黑帮故事,跟权谋异曲同工。
文 | 清晏 编辑 | 沈小山
表面在说江湖,深究则是宿命。
读罢《鸳鸯六七四》,就能明白为什么杜琪峰要找马家辉合作剧本。
马家辉这本新书的故事开端,就是在江湖局上,同时充盈着荒诞和宿命:江湖大佬哨牙炳金盆洗手暨六十大寿宴会,开席前的赌桌上,哨牙炳连续三把拿到牌九局里的四张最大烂牌,也就是书名所说的「鸳鸯六七四」——
「鸳鸯六」,指的是两只花色不一样的六点;「七四」,指的是一只七点和一只四点。
它就是从哨牙炳连摸三把烂牌开始往回追溯的:他怎样被小伙伴孤立,怎样收了钱却没帮老妈看好偷情的门,怎样死掉父亲,又怎样辗转到香港,从一个一心只想睡女人、开妓院的账房伙计,被时事和命运裹挟成香港「新兴社」大佬,最后在金盆洗手大会上突发剧变然后离奇失踪。
这个以江湖、赌桌和烂牌为开端的故事,隐喻着江湖男女的各种赌——与出身赌,与时机赌,更跟时代和命运赌:以哨牙炳为主线的男主,都出身腌臜,尽管他们都生过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苟且之心;但命运大潮起起伏伏,让他们不得不与赌上身家性命,从前清乱世到英国殖民,再到日本鬼子,最后在趋于繁华和规整的六十年代末烟消云散。
这当然不涉及剧透,因为在马家辉笔下,结果并不是最重要的。它无非是一个主角或生或死,或圆满或遗憾的归宿。真正值得留恋的是,萦绕在过程里的细节,它们鲜活、生动地再现着命运对个人的把赏和玩弄,以及它侧过身后留下的一地虚空。
云波诡谲的过程,和变幻多端的细节,构筑起潮起潮落的江湖。
中国人为什么把地下世界称之为江湖?
因为江湖的基本形态就是水的基本形态。
在江湖里,水无形流动,恪守着自己的规律,我行我素,而人充其量只能因势利导,或是借力用力。能够消灭水的,只能是水本身。河入海,江汇川,死的只是大鱼小鱼,永生的总是如水江湖。
这就是为什么,《鸳鸯六七四》沿袭马家辉的上一本小说《龙头凤尾》,从陆南才死做小说开枝散叶节点的缘由:陆南才死之前,香港已然龙蛇混杂,孙兴社之外还有东莞帮、蜀联社等;而陆南才之后,其弟陆北风改建新兴社时,仅弹丸之地的九龙城寨,就有三支势力强悍的黑组织,如雷大爷的蜀联社、郑昊的东北帮,和刘方正的宝安帮等。
这些黑恶势力,就跟英国殖民和日本侵略者等势力一样,有着你方唱罢我登场的顽强生命力。
不变的是为争夺话事权而龙争虎斗的倾轧和厮杀,变的是那些为倾轧和厮杀而不断更换的角色——即便以恶制恶,也没有谁能永远称霸。
越早参透这个道理,就能越早在江湖上立于不败之地。所以小说里有个虽然不是主角却作用甚大的人物,英国警察力克。这个怀揣艺术梦的英国佬,过早地参透中国底层的生存法则,削尖脑袋钻进香港警队后,与势利最强悍的两家黑帮大佬义结金兰,因为他明白:
世界上有抓不完的贼,而懂得用贼,就等于抓完了所有的贼。
这个逻辑,像不像《黑社会2》里,被迫接受龙头棍的古天乐?

《黑社会2:以和为贵》剧照
被形势胁迫才赶鸭子上架的古天乐,自以为坐稳一届就能把龙头棍这个烫手山芋给甩出去,孰料机关算尽别人,自己却被更大的势利盯得死死的。
也就是说,马家辉和杜琪峰一样,戳破了江湖与庙堂交接的灰色地带的联通与相似:这两者虽然一黑一白,但运作规律实则相同,而其最大的不同处,则在于谁的势力更庞大。这就是为什么在《鸳鸯六七四》中,马家辉多次提及力克所属的英政府,面对油麻地、湾仔尤其是九龙城寨的黑恶势力,态度极其暧昧的缘故。
高级的黑帮故事,永远都跟权谋有着异曲同工的妙处。
比如《水浒传》,比如这部《鸳鸯六七四》。
但这不过是马家辉略逞才能的添花之笔。即便深谙这世俗且恒久的社会法则,他那颗悲天悯人的心,也让他抽离在更广博的人世之上,而这正是他与杜琪峰不谋而合的另一处,即都参透了一个道理:
命运的确掌握在你手中,但你的手却是那样软弱无力。
通俗来讲,这就是宿命,以及荒诞。
它们是一体双生的矛盾面:宿命带有必然性,荒诞却充盈着偶然性,二者参合在一起,构筑起人活于世的真相。所以在《非常突然》里,那些警察自以为把悍匪一网打尽,结果却在与他们瞧不上的笨贼遭遇时全线牺牲;而《暗花》里自视甚高的刘青云和梁朝伟,对玩转江湖摆平一切深信不疑,可机关算尽的最后,却双双死在一个眉目慈祥到连面都没露两次的洪先生手里。

《暗花》剧照
宿命让杜琪峰的电影带有悲观色彩,荒诞却用一个个偶然和随机把它消解,以至于命运这种看似硕大无朋的词汇,在近乎戏谑的嘲弄里,失掉了本该有的尊严和庄重。
《鸳鸯六七四》,观感亦如此。
比如书中一个仅存在数页纸的小人物骆仲衡,出现时是因为抽大烟,而死也是因为抽大烟——关键是中间这个阶段,他戒掉了,还有过风生水起的生活。但提及横死街头的终局,马家辉这么写道:
「高明雷没法知道到底是因为骆仲衡再堕毒海所以妻子下堂,抑或是因为妻子下堂令他再碰毒品,反正人死了,这都不重要了。高明雷猜想他的最大遗憾只是死了便无法再尝瘾头……所以出殡那天,给他烧了三包鸦片,再把三包鸦片塞进他的棺材。」
在这个兼顾故事波折和人物状态的小插曲里,马家辉把他对宿命和荒诞的参悟,呈现出管中窥豹的精妙来:比如荒诞何以为荒诞的抽离感,宿命何以是宿命的不可抗,以及这二者相互依附又彼此转化时的微妙和恐怖。
在《鸳鸯六七四》里,马家辉对待世界始终冷眼旁观。因为冷眼,也就没有偏袒,也就更能看到人之所以为人的有点和缺陷,和社会何以为社会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是并行不悖的美与丑、善与恶、懦弱与勇敢、热爱和憎恨、凶狠与怜悯,是这些事物环环相扣里的阴差阳错和沟壑纵横,以及水到渠成时的功亏一篑。
这些看似针锋相对的事,内里总有着千丝万缕的勾连。
这就是为什么作为主角的哨牙炳,为全书传递一种阿Q精神的缘故。就像他连摸三把鸳鸯六七四,都还能乐呵呵地遮掩自己的慌张和焦虑,除了面子和尊严,他不断用逆来顺受提醒自己,告诫自己「发生坏事情,不见得必然有坏结局,换个心态去面对,坏事未尝不能被称为好事……在逆境里发萧是一种连老天也要佩服的本领。」
他笑对一切的乐观背后,当然有精神胜利的犬儒。但透过这层迷障,马家辉更是在表达宿命的荒诞性:宿命是必然的,像是上天布置好的过程与结局,但荒诞是偶然的,它是崩裂在秩序之外的非秩序、理性之外的非理性,它以轻佻的身影嘲弄宿命——所以一辈子都在逃避责任的哨牙炳,反倒成了一家大小的顶梁柱,甚至心不甘情不愿地支撑起新兴社,成了自己都觉得可笑的人。
类似关于宿命与荒诞的体悟,《鸳鸯六七四》中比比皆是,它横亘在每个人路上,无论男女、不分事情。这也让整本书带有一定的禅机,比如它对男女之事浓墨重彩地渲染后,冷不丁来一句:「只要男人不死,女人永远有活路;只要女人有活路,男人便不愿意死。」
除了江湖、宿命和荒诞,《鸳鸯六七四》还有很多可解读探讨的空间。
而重点摹刻的黑帮更迭和政治勾连,不仅带有为底层社会旺盛生命力擂鼓助威的赞颂,更是他渴求读者能在精神上达成默契的诉求,仿佛马家辉指着地上那滩血,对着读者挤眉弄眼、一脸坏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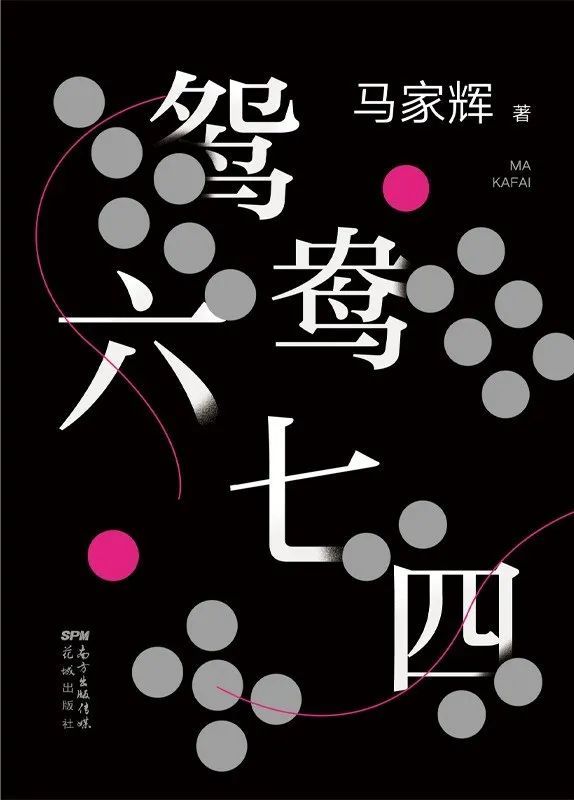 《鸳鸯六七四》
《鸳鸯六七四》
作者:马家辉
出版社:花城出版社
出品方:青马文化
来源|南都周刊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