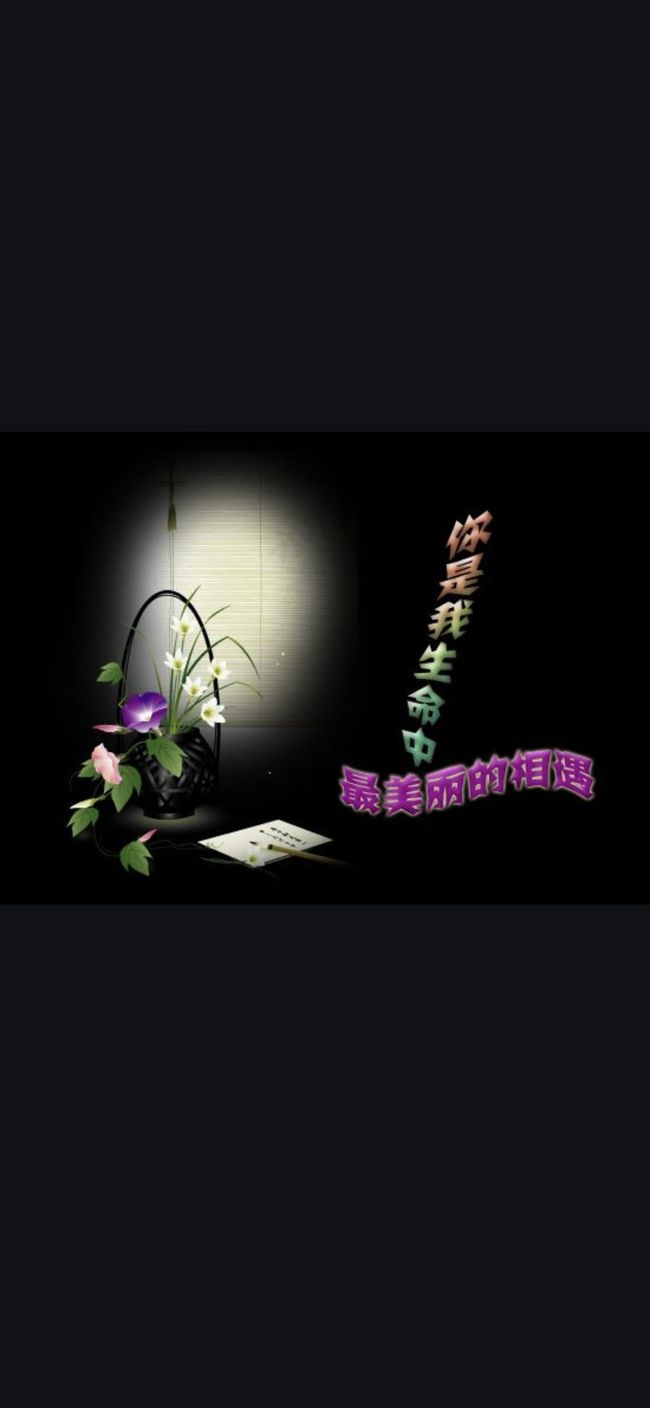- 坚持地努力
旦旦日记
很享受这种在家的感觉。昨天上午出去跑了一圈,下午和晚上都是在家里工作,学习电商。同一件事情,让不同阶段的自己来做,效果是大大的不一样。就像我这次重新拾起淘宝,几乎就等于拾起最后一根稻草的感觉,不管你想不想学好、能不能学好,结果是你都得必须学好。因为一家子就指靠着这个生活呢,我特意在书桌上摆了珺祎的四罐奶粉,一扭头就能看到,就是为了时刻提醒自己挣奶粉钱。虽然说现在浙江业务的收入来源足够保证我们这一大
- 不要为了恋爱而恋爱……
小呆先生
18年秋,9月12日,小呆如愿进入了大学,大学的一切事物无不吸引着他,进入大学意味着自由,脱离了高中老师的步步紧逼,离开的父母的管束,自由的空气让小呆喜出望外……他对许多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他不知所以的加入了学生会,也加入了学生社团,本来他想在学生会学点有用的东西,结果发现并不能学到什么,只是多了许多无休无止的来自学长学姐的任务,他的时间被学生会的事物占满,咋一看好像活的很充实,但其实小呆自己清楚,
- 和珅本来是一个标准的三好文艺青年,他是这样被乾隆慢慢带坏的
数学真美
在人们的心目中,和珅是个大贪官,可谓老幼皆知,遗臭万年。其实很少有人知道,他曾经也是一个三好青年,怪只怪碰上乾隆爷这么一个纵容贪污腐败行为的皇帝,把他慢慢的带坏了。乾隆是历史上最为追求完美的皇帝之一,他从小就立志要做象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那样流芳于世的千古一帝。而且他对儒家文化非常地崇拜,简直到了痴迷沉沦的地步,他酷爱写诗,每天不是写诗就是在写诗的路上。虽然诗写得很烂,但他持之以恒,80多年如一日地
- 2021-07-19
大步走起来
知世故而不世故,是最成熟的天真。少年不惧岁月长,歌声温柔,内心明亮。愿你永远赤诚、简单,为自己保留一份初心和纯粹。愿你既有大人的成熟,也能有孩子的烂漫。愿你生活不拥挤,笑容不刻意。知世故而不世故,历圆滑而留天真。
- ShardingSphere 架构解析
我是廖志伟
Java场景面试宝典DatabaseDistributedSystemsShardingSphere
我是廖志伟,一名Java开发工程师、《Java项目实战——深入理解大型互联网企业通用技术》(基础篇)、(进阶篇)、(架构篇)清华大学出版社签约作家、Java领域优质创作者、CSDN博客专家、阿里云专家博主、51CTO专家博主、产品软文专业写手、技术文章评审老师、技术类问卷调查设计师、幕后大佬社区创始人、开源项目贡献者。拥有多年一线研发和团队管理经验,研究过主流框架的底层源码(Spring、Spri
- 肉肉学习记录-想要改变的动力 F6
肉肉的天下
我是肉肉,坚信个人的力量能带给身边的人无穷的能量。励志坚持写作,将肉肉的成长和正向积极的价值人生分享给身边的朋友,赋能朋友圈。这是我的原创文章第6篇。阅读《不吼不叫》这本书中,收获了非常深刻的一句话:让你决定改变的时候,就已经是送给家人和自己最好的礼物了。图片发自App是的,我们曾经一直认为,我们应该维持自己原本的样子,不应该为了谁去改变我们自己,这样不值得,也不应该。所以,当我们试图改变孩子、家
- 预测导管原位癌浸润性复发的深度学习:利用组织病理学图像和临床特征
浪漫的诗人
论文深度学习人工智能
文章目录研究内容目的方法数据集模型开发模型训练与评估外部验证统计分析研究结果模型性能风险分层外部验证特征重要性原文链接原文献:Deeplearningforpredictinginvasiverecurrenceofductalcarcinomainsitu:leveraginghistopathologyimagesandclinicalfeatures研究背景【DCIS与IBC的关联】乳腺导管
- 面试经验分享 | 成都某安全厂商渗透测试工程师
更多大厂面试题看我的主页或者专栏找我免费领取目录:所面试的公司:某安全厂商所在城市:成都面试职位:渗透测试工程师岗位面试过程:面试官的问题:1.平常在学校打CTF嘛,获奖情况讲下,以及你自己的贡献如何?2.内网渗透主要思路说一下吧?3.web打点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过waf?怎么绕过的4.现在给你一个站你会怎么做信息搜集?5.如何快速检测定位网站目录下的webshell呢?6.简单讲下反弹shell的
- 如何在寻求不被割韭菜的取经路上,不再被割一次?
XiaojunHong
笑来老师其实是一个思想上的孤独者,他教别人独立思考。做一个“孤独者”,随着时间的推移,你的思考越深入,最终的结果就是。。。你身边没有谁能跟你讨论,没有谁值得你参考。这是一种极高的境界。每一个独立思考者都追求的境界。昨天听到的一句话“AlwaysBiggerFish——把英雄从危险中拯救出来的拯救者其实是一个更大的危险”。很受启发。统治本质就是暴力的。是小部分人对大部分人的征收。在进入任何领域的时候
- Python类中魔术方法(Magic Methods)完全指南:从入门到精通
盛夏绽放
python开发语言
文章目录Python类中魔术方法(MagicMethods)完全指南:从入门到精通一、魔术方法基础1.什么是魔术方法?2.魔术方法的特点二、常用魔术方法分类详解1.对象创建与初始化2.对象表示与字符串转换3.比较运算符重载4.算术运算符重载5.容器类型模拟6.上下文管理器7.可调用对象三、高级魔术方法1.属性访问控制2.描述符协议3.数值类型转换四、魔术方法最佳实践五、综合案例:自定义分数类Pyt
- Python面向对象编程(OOP)详解:通俗易懂的全面指南
盛夏绽放
python开发语言有问必答
前些天发现了一个巨牛的人工智能学习网站,通俗易懂,风趣幽默,忍不住分享一下给大家。点击跳转到网站。文章目录Python面向对象编程(OOP)详解:通俗易懂的全面指南一、OOP基本概念1.什么是面向对象编程?2.OOP的四大支柱3.核心概念对比表二、类和对象1.类(Class)vs对象(Object)2.类结构详解三、OOP三大特性详解1.封装(Encapsulation)2.继承(Inherita
- HTML与HTML5知识点复习整理
bottle Shen
html前端
**本篇文章食用的简单说明**本篇文章为复习HTML与HTML5进行了知识点梳理,其中标题六部分涉及CSS知识(有标注),加粗部分为重点!!!加粗加红为重重点!!!如有遗漏欢迎在评论区补充~推荐大家按记忆梳理部分的内容自行回忆知识点,如有遗忘部分在左下方目录处点击相应部分可以进行跳转。又是努力学习前端的一天,希望大家共同进步~~~(QAQ我只是一个表情)❤***记忆梳理***一、HTML是什么二、
- Java零基础-三维数组详解!
喵手
零基础学Javajava开发语言
哈喽,各位小伙伴们,你们好呀,我是喵手。运营社区:C站/掘金/腾讯云/阿里云/华为云/51CTO;欢迎大家常来逛逛 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些自己日常学习到的一些知识点,并以文字的形式跟大家一起交流,互相学习,一个人虽可以走的更快,但一群人可以走的更远。 我是一名后端开发爱好者,工作日常接触到最多的就是Java语言啦,所以我都尽量抽业余时间把自己所学到所会的,通过文章的形式进行输出,希望以这种方式
- 【短篇小说】你家祖坟冒青烟
沐子小六
01今日,叶泠打扮的分外素净,仅着一身淡蓝色绸缎长裙,乌黑浓密的长发披于秀肩上,插一只简单的木簪。少女素颜宛如刚剥壳的鸡蛋,一双杏眼干净澄澈,越发衬的她更加惹人怜爱。祖坟边,少女跪下,虔诚的祈祷:“信女叶泠,唯愿兄长叶宣此次科举考试能金榜题名。”良久,叶泠起身,惊讶地看着面前的祖坟,生起了一缕缕的白烟。“这是……”叶泠想起娘亲恨铁不成钢地骂着叶宣,若叶宣能中举,必定得是祖坟上冒青烟。再一转头,果真
- 《小狗钱钱》学习心得(第三、四、五章)
A01琪公子
《小狗钱钱》学习心得(第三、四、五章)最近在跟战友读一本《小狗钱钱》的书,今天把读到的精华与对这本书的感悟分享给正在看文章的你,希望对你有用。一、成功笔记:1.昨天的梦想相册的三个重要梦想开始在我脑海中浮现,我闭眼想到靠自己努力买房并装修好的新房的温馨舒适、爸妈安享晚年的幸福时刻,以及清晨爱人醒来那甜蜜的微笑。2.给客户重新发了合同,不在急急燥燥,而是准备好,只要有机会,就紧紧抓住。3.用心读完了
- 2019-7-17
yl柠檬草的味道
六项精进姓名:袁丽公司:上海缘缀包装材料有限公司【日精进打卡第353天】【知~学习】《六项精进》1遍共242遍《大学》1遍共242遍公司使命、愿景、价值观1遍共23遍【经典名句分享】【行~实践】一、修身:(对自己个人)1、步行:80002、坚持学习19天3、做早餐二、齐家:(对家庭和家人)1、和家人视频,都都快过来了,让她把要带过来的东西准备好,不错!小家伙能熟背我的手机号码了!三、建功:(对工作
- Java零基础 - 数组的定义和声明
喵手
零基础学Javajava开发语言
哈喽,各位小伙伴们,你们好呀,我是喵手。 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些自己日常学习到的一些知识点,并以文字的形式跟大家一起交流,互相学习,一个人虽可以走的更快,但一群人可以走的更远。 我是一名后端开发爱好者,工作日常接触到最多的就是Java语言啦,所以我都尽量抽业余时间把自己所学到所会的,通过文章的形式进行输出,希望以这种方式帮助到更多的初学者或者想入门的小伙伴们,同时也能对自己的技术进行沉淀,加以
- 记录一次年终奖
陈小星520
昨天带着皓皓去老板娘家做客,三个孩子一起玩的时候,老板娘喊我到房间里算今年的提成,后来因为账目对不上,我们一起去了厂里。果然有一本账落在厂里了,当老板娘说出一个提成点数时,心里着实一惊,太给力了。回想这一年,有一段时间周日去厂里,我都不知道该干啥好,在自己的工位上坐着,耗时间,拿着薪水,却像没创造效益,一度怀疑自己的价值。我就跟老板娘说,如果有事你就叫我过来,没事我就不来厂里了吧,不然没干活还要你
- 京东618红包怎么领取红包口令在哪里领取(京东618大额红包密令怎么领取方法)
全网优惠分享
2023年京东618红包将在5月29日开始发放,本文讲解2023年京东618红包领取方法,教大家怎么领取京东618红包!京东618元现金红包获取方法:京东618元红包领取地址:https://u.jd.com/as2ixNh(复制打开领取)618元红包口令:¥CEDHP3lrm2Geq82U¥复制打开京东APP即可领取或者打开京东APP扫一扫下面的二维码也可获取京东购物省钱秘籍分享(认真看完你就会
- 认知篇(21):如何找到职业的乐趣?
未伊
前言:承接上一篇文章,继续谈“敬业”和“乐业”的问题。工作辛苦,所以极少有人乐意工作。不仅不乐意,也还要发些牢骚,吐槽一下工作。但梁先生反问一句:“做工苦,难道不做工就不苦吗?”而我要说,做工苦,不做工应该是更苦。不工作,光是没收入这一条就已经够苦了。更何况,我们还有“不工作也有收入”这种奢望,理想和现实的冲突,心里是苦上加苦。所以,作为成人,要尊重现实,接受现实。而在工作中,找到乐趣,便是我们回
- 积极主动和坚持不懈
野生提莫
图片发自App对于这个话题,讨论起来我不太有把握,因此我督促你在采取我的建议之前先读一下并完全弄懂。不管怎样,规则很简单:在遇见(或约会)女人时,你必须要坚持不懈。在你出去开始对每个你遇到的女人展开攻势之前,先让我解释一下关于坚持不懈的意思。概括地说来,所谓坚持不懈就是说,如果你对一个女人起了化学反应,你就不应当害怕跟她后续。我不是说你应该对你“真的喜欢”的所有女孩都展开攻势。因此当我对你说要坚持
- 长隆游记
源之泉
自开始写文章以来,第一次卡着时间点,第一次写游记,这次感触良多。春节前几天打算趁春节假期来长隆,当时查阅了酒店和航班的信息之后,异常拥挤,不仅人多、价格还贵,就果断放弃。决定过完春节孩子没有开学之前来一次旅行,时间刚刚好。一个朋友告诉我可以办一张工行长隆信用卡,珠海、广州门票一张信用卡片对应一张门票可以打五折优惠,门票的价格高,可以省几百块,非常实惠,家庭出游建议提前准备,非常实惠哦,而且现在办理
- 〖Python 数据库开发实战 - Redis篇②〗- Linux系统下安装 Redis 数据库
哈哥撩编程
#⑤-数据库开发实战篇Python全栈白宝书python数据库数据库开发实战linux安装redis
订阅Python全栈白宝书-零基础入门篇可报销!白嫖入口-请点击我。推荐他人订阅,可获取扣除平台费用后的35%收益,文末名片加V!说明:该文属于Python全栈白宝书专栏,免费阶段订阅数量4300+,购买任意白宝书体系化专栏可加入TFS-CLUB私域社区。福利:加入社区的小伙伴们,除了可以获取博主所有付费专栏的阅读权限之外,还有机会加入星荐官共赢计划,详情请戳我。作者:不渴望力量的哈士奇(哈哥),
- 灵契之绚烂
泡泡国漫漫研社
文|泡泡圈漫评团九•落叶“端木熙!”杨敬华看着正埋在书里的某人愤愤不平,“怎么了?”端木熙视线从书上移开,打量着杨敬华。“我说端木,你就这样打算整天在家看书?”杨敬华随手拿了一本书翻了几页。“嗯。”简短的一个字让杨敬华险些跌倒。“端木,我很想知道你以前是怎么过日子的!”杨敬华有些无语地看着他。“以前啊!”端木熙放下手中的书,看着杨敬华。“以前不是工作就是上学或者在家看书。”好吧!杨敬华服了。“行了
- html 显示 数据库图片.js,html实时显示数据 怎么让数据库的数据在html显示出来
UnstructuredIO
html显示数据库图片.js
用JS实时调用数据显示在HTML页面上不要站在现在的高度,去判定未来的事情,因为未来的你是会成长的,会有新的选择和判断。html页面上怎么显示动态数据通过AJAX实现,在html页面用ajax请分享后台获取动态数据。获取range的值就行了,然后将其显示出来,你实时改变range的值,显示的就会实时改变0functionchange(){varvalue=document.getElementBy
- 请你停下3秒:写作的捷径,肯定有
叶两步
文/叶老巫(2018年:12/365)本文关键词:捷径、多读、多写、特色【壹】人,是很懒的另类动物。凡事,在思维上,首先想的是,怎样快速到达目的地。在写作上,也是如此。写作水平,要有所提高,是有捷径走的。有一条捷径,你必须走,才能到达你梦想的地方。这条捷径,我说出来,你会失望的。唯一的捷径,就是必须多读,还要多写。【贰】你会睁大眼睛,看着我,心里一个大大的问号:为什么是这个呢?话说,多读多写,人人
- 周末慢生活
春暖花会开燕子
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都很忙,要么要早起升旗,要么要早起听课,有的时候是要早起上第一节课,女儿每天被我催的,可以说没睡过懒觉也没好好吃过早饭。周末了,可以不用早起了,所以我也放纵了自己一次,允许自己陪着女儿多睡一会儿。于是昨天午饭后本来是午饭后犯困想着小憩一会儿的,刚开始女儿没睡,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睡着了,大概两点多的时候我被电话吵醒了,记得迷迷糊糊的听见女儿说她要睡觉,等到接电话的时候发现女儿不知道
- 爱上一个人,你就会有心记住关于他的一切好坏
喜欢孤独的小女人
平时有的人看着傻傻的,记忆力也很差。但是,等他爱上一个人的,他就会变得对所爱的人特别地敏感和细心,记住关于他的所有一切的好坏。他也被自己吓到了,原来自己也有怎么专注和细心的时候,而且记忆力变得超好,或许这就是爱的力量吧!
- Glary Utilities(系统优化工具) v6.20.0.24 专业便携版
周大侠工作室
电脑软件
GlaryUtilities允许你清理系统垃圾文件,无效的注册表,上网记录,删除插件,查找重复文件,优化内存,修理或删除快捷方式,管理windows启动程序,卸载软件,安全删除文件,右键菜单管理等等。激活方法有标注Portable名称的,无需注册码注册用户名:applek激活码(二选一):序列号:S788-6167-958S-5GF9-KXJI序列号:M788-6167-958M-USVN-7VM
- 《雨天》
好物坊娇娇
雨天,似乎是司空见惯的!在一年四季的日子里,春季的毛毛细雨,夏季的暴雨如注、磅礴大雨,秋季连绵不断的连阴雨!冬季的雨夹雪。雨,水的另一种组合方式。在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时节,以不同的姿态陪伴了我们的许多年华!图片发自App晶莹剔透的雨从天际落下,所有的明朗都不见了。但是却有一种清洗过后的清晰,水样的美好。像美女梨花带雨的眼眸,有一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朦胧的美好!你会想到红酒,因为你要将美色穿肠。你也会
- 安装数据库首次应用
Array_06
javaoraclesql
可是为什么再一次失败之后就变成直接跳过那个要求
enter full pathname of java.exe的界面
这个java.exe是你的Oracle 11g安装目录中例如:【F:\app\chen\product\11.2.0\dbhome_1\jdk\jre\bin】下的java.exe 。不是你的电脑安装的java jdk下的java.exe!
注意第一次,使用SQL D
- Weblogic Server Console密码修改和遗忘解决方法
bijian1013
Welogic
在工作中一同事将Weblogic的console的密码忘记了,通过网上查询资料解决,实践整理了一下。
一.修改Console密码
打开weblogic控制台,安全领域 --> myrealm -->&n
- IllegalStateException: Cannot forward a response that is already committed
Cwind
javaServlets
对于初学者来说,一个常见的误解是:当调用 forward() 或者 sendRedirect() 时控制流将会自动跳出原函数。标题所示错误通常是基于此误解而引起的。 示例代码:
protected void doPost() {
if (someCondition) {
sendRedirect();
}
forward(); // Thi
- 基于流的装饰设计模式
木zi_鸣
设计模式
当想要对已有类的对象进行功能增强时,可以定义一个类,将已有对象传入,基于已有的功能,并提供加强功能。
自定义的类成为装饰类
模仿BufferedReader,对Reader进行包装,体现装饰设计模式
装饰类通常会通过构造方法接受被装饰的对象,并基于被装饰的对象功能,提供更强的功能。
装饰模式比继承灵活,避免继承臃肿,降低了类与类之间的关系
装饰类因为增强已有对象,具备的功能该
- Linux中的uniq命令
被触发
linux
Linux命令uniq的作用是过滤重复部分显示文件内容,这个命令读取输入文件,并比较相邻的行。在正常情 况下,第二个及以后更多个重复行将被删去,行比较是根据所用字符集的排序序列进行的。该命令加工后的结果写到输出文件中。输入文件和输出文件必须不同。如 果输入文件用“- ”表示,则从标准输入读取。
AD:
uniq [选项] 文件
说明:这个命令读取输入文件,并比较相邻的行。在正常情况下,第二个
- 正则表达式Pattern
肆无忌惮_
Pattern
正则表达式是符合一定规则的表达式,用来专门操作字符串,对字符创进行匹配,切割,替换,获取。
例如,我们需要对QQ号码格式进行检验
规则是长度6~12位 不能0开头 只能是数字,我们可以一位一位进行比较,利用parseLong进行判断,或者是用正则表达式来匹配[1-9][0-9]{4,14} 或者 [1-9]\d{4,14}
&nbs
- Oracle高级查询之OVER (PARTITION BY ..)
知了ing
oraclesql
一、rank()/dense_rank() over(partition by ...order by ...)
现在客户有这样一个需求,查询每个部门工资最高的雇员的信息,相信有一定oracle应用知识的同学都能写出下面的SQL语句:
select e.ename, e.job, e.sal, e.deptno
from scott.emp e,
(se
- Python调试
矮蛋蛋
pythonpdb
原文地址:
http://blog.csdn.net/xuyuefei1988/article/details/19399137
1、下面网上收罗的资料初学者应该够用了,但对比IBM的Python 代码调试技巧:
IBM:包括 pdb 模块、利用 PyDev 和 Eclipse 集成进行调试、PyCharm 以及 Debug 日志进行调试:
http://www.ibm.com/d
- webservice传递自定义对象时函数为空,以及boolean不对应的问题
alleni123
webservice
今天在客户端调用方法
NodeStatus status=iservice.getNodeStatus().
结果NodeStatus的属性都是null。
进行debug之后,发现服务器端返回的确实是有值的对象。
后来发现原来是因为在客户端,NodeStatus的setter全部被我删除了。
本来是因为逻辑上不需要在客户端使用setter, 结果改了之后竟然不能获取带属性值的
- java如何干掉指针,又如何巧妙的通过引用来操作指针————>说的就是java指针
百合不是茶
C语言的强大在于可以直接操作指针的地址,通过改变指针的地址指向来达到更改地址的目的,又是由于c语言的指针过于强大,初学者很难掌握, java的出现解决了c,c++中指针的问题 java将指针封装在底层,开发人员是不能够去操作指针的地址,但是可以通过引用来间接的操作:
定义一个指针p来指向a的地址(&是地址符号):
- Eclipse打不开,提示“An error has occurred.See the log file ***/.log”
bijian1013
eclipse
打开eclipse工作目录的\.metadata\.log文件,发现如下错误:
!ENTRY org.eclipse.osgi 4 0 2012-09-10 09:28:57.139
!MESSAGE Application error
!STACK 1
java.lang.NoClassDefFoundError: org/eclipse/core/resources/IContai
- spring aop实例annotation方法实现
bijian1013
javaspringAOPannotation
在spring aop实例中我们通过配置xml文件来实现AOP,这里学习使用annotation来实现,使用annotation其实就是指明具体的aspect,pointcut和advice。1.申明一个切面(用一个类来实现)在这个切面里,包括了advice和pointcut
AdviceMethods.jav
- [Velocity一]Velocity语法基础入门
bit1129
velocity
用户和开发人员参考文档
http://velocity.apache.org/engine/releases/velocity-1.7/developer-guide.html
注释
1.行级注释##
2.多行注释#* *#
变量定义
使用$开头的字符串是变量定义,例如$var1, $var2,
赋值
使用#set为变量赋值,例
- 【Kafka十一】关于Kafka的副本管理
bit1129
kafka
1. 关于request.required.acks
request.required.acks控制者Producer写请求的什么时候可以确认写成功,默认是0,
0表示即不进行确认即返回。
1表示Leader写成功即返回,此时还没有进行写数据同步到其它Follower Partition中
-1表示根据指定的最少Partition确认后才返回,这个在
Th
- lua统计nginx内部变量数据
ronin47
lua nginx 统计
server {
listen 80;
server_name photo.domain.com;
location /{set $str $uri;
content_by_lua '
local url = ngx.var.uri
local res = ngx.location.capture(
- java-11.二叉树中节点的最大距离
bylijinnan
java
import java.util.ArrayList;
import java.util.List;
public class MaxLenInBinTree {
/*
a. 1
/ \
2 3
/ \ / \
4 5 6 7
max=4 pass "root"
- Netty源码学习-ReadTimeoutHandler
bylijinnan
javanetty
ReadTimeoutHandler的实现思路:
开启一个定时任务,如果在指定时间内没有接收到消息,则抛出ReadTimeoutException
这个异常的捕获,在开发中,交给跟在ReadTimeoutHandler后面的ChannelHandler,例如
private final ChannelHandler timeoutHandler =
new ReadTim
- jquery验证上传文件样式及大小(好用)
cngolon
文件上传jquery验证
<!DOCTYPE html>
<html>
<head>
<meta http-equiv="Content-Type" content="text/html; charset=utf-8" />
<script src="jquery1.8/jquery-1.8.0.
- 浏览器兼容【转】
cuishikuan
css浏览器IE
浏览器兼容问题一:不同浏览器的标签默认的外补丁和内补丁不同
问题症状:随便写几个标签,不加样式控制的情况下,各自的margin 和padding差异较大。
碰到频率:100%
解决方案:CSS里 *{margin:0;padding:0;}
备注:这个是最常见的也是最易解决的一个浏览器兼容性问题,几乎所有的CSS文件开头都会用通配符*来设
- Shell特殊变量:Shell $0, $#, $*, $@, $?, $$和命令行参数
daizj
shell$#$?特殊变量
前面已经讲到,变量名只能包含数字、字母和下划线,因为某些包含其他字符的变量有特殊含义,这样的变量被称为特殊变量。例如,$ 表示当前Shell进程的ID,即pid,看下面的代码:
$echo $$
运行结果
29949
特殊变量列表 变量 含义 $0 当前脚本的文件名 $n 传递给脚本或函数的参数。n 是一个数字,表示第几个参数。例如,第一个
- 程序设计KISS 原则-------KEEP IT SIMPLE, STUPID!
dcj3sjt126com
unix
翻到一本书,讲到编程一般原则是kiss:Keep It Simple, Stupid.对这个原则深有体会,其实不仅编程如此,而且系统架构也是如此。
KEEP IT SIMPLE, STUPID! 编写只做一件事情,并且要做好的程序;编写可以在一起工作的程序,编写处理文本流的程序,因为这是通用的接口。这就是UNIX哲学.所有的哲学真 正的浓缩为一个铁一样的定律,高明的工程师的神圣的“KISS 原
- android Activity间List传值
dcj3sjt126com
Activity
第一个Activity:
import java.util.ArrayList;import java.util.HashMap;import java.util.List;import java.util.Map;import android.app.Activity;import android.content.Intent;import android.os.Bundle;import a
- tomcat 设置java虚拟机内存
eksliang
tomcat 内存设置
转载请出自出处:http://eksliang.iteye.com/blog/2117772
http://eksliang.iteye.com/
常见的内存溢出有以下两种:
java.lang.OutOfMemoryError: PermGen space
java.lang.OutOfMemoryError: Java heap space
------------
- Android 数据库事务处理
gqdy365
android
使用SQLiteDatabase的beginTransaction()方法可以开启一个事务,程序执行到endTransaction() 方法时会检查事务的标志是否为成功,如果程序执行到endTransaction()之前调用了setTransactionSuccessful() 方法设置事务的标志为成功则提交事务,如果没有调用setTransactionSuccessful() 方法则回滚事务。事
- Java 打开浏览器
hw1287789687
打开网址open浏览器open browser打开url打开浏览器
使用java 语言如何打开浏览器呢?
我们先研究下在cmd窗口中,如何打开网址
使用IE 打开
D:\software\bin>cmd /c start iexplore http://hw1287789687.iteye.com/blog/2153709
使用火狐打开
D:\software\bin>cmd /c start firefox http://hw1287789
- ReplaceGoogleCDN:将 Google CDN 替换为国内的 Chrome 插件
justjavac
chromeGooglegoogle apichrome插件
Chrome Web Store 安装地址: https://chrome.google.com/webstore/detail/replace-google-cdn/kpampjmfiopfpkkepbllemkibefkiice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只需替换一个域名就可以继续使用Google提供的前端公共库了。 同样,通过script标记引用这些资源,让网站访问速度瞬间提速吧
- 进程VS.线程
m635674608
线程
资料来源:
http://www.liaoxuefeng.com/wiki/001374738125095c955c1e6d8bb493182103fac9270762a000/001397567993007df355a3394da48f0bf14960f0c78753f000 1、Apache最早就是采用多进程模式 2、IIS服务器默认采用多线程模式 3、多进程优缺点 优点:
多进程模式最大
- Linux下安装MemCached
字符串
memcached
前提准备:1. MemCached目前最新版本为:1.4.22,可以从官网下载到。2. MemCached依赖libevent,因此在安装MemCached之前需要先安装libevent。2.1 运行下面命令,查看系统是否已安装libevent。[root@SecurityCheck ~]# rpm -qa|grep libevent libevent-headers-1.4.13-4.el6.n
- java设计模式之--jdk动态代理(实现aop编程)
Supanccy2013
javaDAO设计模式AOP
与静态代理类对照的是动态代理类,动态代理类的字节码在程序运行时由Java反射机制动态生成,无需程序员手工编写它的源代码。动态代理类不仅简化了编程工作,而且提高了软件系统的可扩展性,因为Java 反射机制可以生成任意类型的动态代理类。java.lang.reflect 包中的Proxy类和InvocationHandler 接口提供了生成动态代理类的能力。
&
- Spring 4.2新特性-对java8默认方法(default method)定义Bean的支持
wiselyman
spring 4
2.1 默认方法(default method)
java8引入了一个default medthod;
用来扩展已有的接口,在对已有接口的使用不产生任何影响的情况下,添加扩展
使用default关键字
Spring 4.2支持加载在默认方法里声明的bean
2.2
将要被声明成bean的类
public class DemoServ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