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我可不喜欢“光速不变”了
 这世界有光,本是天经地义,可以用“上帝之旨意”来解释的一件事。但这世界有光速C(299,792,458米/秒),却颇有些蹊跷,说来说去,是一名叫爱因斯坦的蓬头老头子出面,自说自话为地球人拍板认下的一个所谓事实。话说当年,躲在专利局里埋头摆弄公式时,此公突然来了兴致,整出一个震古烁今的狭义相对论,自此名扬天下。这条被n多后生小辈奉行不渝并拿来混饭碗的理论写着:真空中的光速对于所有观察者均不变。
这世界有光,本是天经地义,可以用“上帝之旨意”来解释的一件事。但这世界有光速C(299,792,458米/秒),却颇有些蹊跷,说来说去,是一名叫爱因斯坦的蓬头老头子出面,自说自话为地球人拍板认下的一个所谓事实。话说当年,躲在专利局里埋头摆弄公式时,此公突然来了兴致,整出一个震古烁今的狭义相对论,自此名扬天下。这条被n多后生小辈奉行不渝并拿来混饭碗的理论写着:真空中的光速对于所有观察者均不变。
相信绝大多数人在接受“光速不变”时,都痛苦了好一阵子,因为这确实是日常中无法体验并违反直觉的现象。倘若你到今天还为此痛苦的话,千万不要懊恼,可以告诉你,没办法或者不愿意接受这一点的其实大有人在,包括不少绝顶聪明的脑袋。剑桥出身的宇宙物理学家、葡萄牙人乔奥•马古悠(Joao Magueijo)在《比光速还快——爱因斯坦错了?》(有中文版)一书里提出了VSL(光速可变)理论,认为宇宙早期光速是大于C的,用来取代目前被广为接受的暴胀理论。马古悠还称自己经历了无数不眠之夜后,痛苦得抓耳挠腮简直要把头皮都揭掉,突然有日被幸运女神眷顾,想到了早期光速是怎样大于C的:设想我们今天看到的光其实并非真正沿着直线传播的,而是螺旋式前进——就像一条麻花那样绕啊绕啊地往前去,那么,把这条麻花扯平以后,不就是更大的速度了嘛!
第二个假设从何而来?
洛克菲勒大学的米切尔•费根鲍姆(Mitchell Feigenbaum,混沌理论的创始人之一)是最著名的一个坚持其实狭义相对论只是描述时空、和光速没有多大关系的人——且不管那些教科书怎么说,用他的原话来讲:“不仅仅是不需要这样,而且在该理论中几乎没有它(光速)的容身之地。”
费根鲍姆2008年6月在物理网站arXiv.org发表了一篇《相对论:伽利略的孩子》(The Theory of Relativity - Galileo's Child)引起不小轰动,他相信如果17世纪的伽利略只要知道一点点的现代数学知识,就有可能走得和爱因斯坦一样远,“伽利略的思想已经有400年历史了,但仍然非常有效,它可以自己得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而不需要借助额外知识。”
文章讨论的焦点集中在1905爱因斯坦在阐述他的狭义相对论时作的两个假设。第一个假设是无可辩驳的:物理定律对于静止的人或者恒速运动的人来说都是一样的。这个原理来自伽利略,他在写成于1632年的论文《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里面借一个虚构人物“萨尔维蒂”之口表明:在一条匀速行驶的船上,旅客无法意识到自己是在动还是保持静止,只要船身不乱晃。在当时这条原理对哥白尼“日心说”是一个重要而有力的支持,因为反对者们驳斥哥白尼的理由就是你说地球在动,为啥我感觉不到?伽利略让他们哑口无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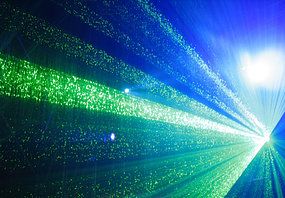 相对论原理好好地工作了250年,直到19世纪苏格兰物理学家麦克斯韦(James Clerk Maxwell)提出了电磁场理论之时,遇到了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在麦克斯韦方程中,明确指明光是一种以恒速运行的波,然而奇怪是,它并没有指明到底谁是这个速度的测量者。想要适用于伽利略的原理,那么麦克斯韦就将面临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如果无法知道谁测量了光速,那么如何修正它以应用到其它坐标系?爱因斯坦告诉我们,没关系,他有办法——在第一条假设上加一句话不就行了嘛:相对于任何一个观察者,光速始终不变。
相对论原理好好地工作了250年,直到19世纪苏格兰物理学家麦克斯韦(James Clerk Maxwell)提出了电磁场理论之时,遇到了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在麦克斯韦方程中,明确指明光是一种以恒速运行的波,然而奇怪是,它并没有指明到底谁是这个速度的测量者。想要适用于伽利略的原理,那么麦克斯韦就将面临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如果无法知道谁测量了光速,那么如何修正它以应用到其它坐标系?爱因斯坦告诉我们,没关系,他有办法——在第一条假设上加一句话不就行了嘛:相对于任何一个观察者,光速始终不变。
这句加上去的话,最终成为那许多让普通人不得要领、被科幻作家视若珍宝的奇怪事件的源头:什么扭曲的时空啦、走得乱糟糟的钟啦。在此基础上,爱因斯坦继续动了动他那不可思议的大脑,整出了伟大的广义相对论。
其实,尽管狭义相对论的结论确实得到过实验验证,但只要它的两个逻辑前提——相对性原理和光速不变原理——未有确凿的实验证据,它们就仍然带有假设成分和“先验”性质。爱因斯坦本人也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一点,1922年他就光速不变写了以下一段话:“相对论常遭到指责,说它未加论证就把光的传播放在中心理论的地位,以光的传播定律作为时间概念的基础。然而(导致作出这条假设的)情形大致如下:如欲赋予时间概念以物理意义,就需某种能建立不同地点之间关系的过程。为这样的时间定义,究竟选择哪一种过程是无关重要的。可为了理论只选用那种已有某些确定解的过程是有好处的。拜麦克斯韦与洛伦兹的研究所赐,和任何其他可考虑选用的过程相比,我们对于光在真空中的传播了解得更清楚。”
《相对论:伽利略的孩子》一文通过数学逻辑计算,还真从伽利略相对论原理导出了一个不变的光速,结论部分费根鲍姆写道:很重要的一点是,必须明白我们目前的运动学不是依赖光的性质建立起来的。他认为光获得如此特殊地位,完全属于一个历史事件,但说实话这是个很讨厌的东西。它被确立以后,物理学家们就不得不忙活很多事情:要证明不同频率的光的速度是否都为C;要证明同一个惯性系不同方向上的光速是否一样;要证明不同惯性系之间的光速是否一样……另外,光子有没有质量呢?理论预言它是没有静止质量的,可没有静止质量的粒子上哪里找?诸如此类。由此可见,“光速不变”不讨人喜欢的可说是理由一大把。
还不如直接找出跑得比光快的东西把它推翻算了!没错,很多人都在这么做。
一负到底的粒子
快子(tachyon)也叫做超光速子,是一种质量平方为负的粒子,该思想最早由德国理论物理学家、量子力学的奠基人之一阿诺•索莫菲(Arnold Johannes Wilhelm Sommerfeld)提出。此人据说前无古人地获得过81次诺贝尔奖提名,不过最终没有得到过评委青睐。关于这个81且不去追究真伪,但需知道他是哪两个大名鼎鼎的人物的博士导师,任谁都要肃然起敬了,他们是“测不准原理”的海森堡和“不相容原理”的泡利!
1962年,O.M.比拉纽克(Olexa-Myron Bilaniuk)和乔治•苏达杉(George Sudarshan)在《美国物理杂志》上首次发表关于这种粒子的论文《逾越光速的粒子》(Particles beyond the light barrier),5年后,哥伦比亚大学的杰拉尔德•范伯格(Gerald Feinberg)正式对它进行了命名,从而确定了它在学科领域中的地位。具体而言,这种粒子和其他已知物质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具有负引力特征,所以,“万有引力”定律在它身上要改成“万有斥力”才行。此外其他性质倒无甚稀奇,比如也可以有自旋,有自己的反粒子。量子场论和后来的弦论,都对其进行了很独特的描述。
理论提出,按照静止质量的平方来区分粒子,大于零的是慢子,等于零的是光子,小于零的就是快子了。快子的提出带来了一系列激动人心的想法:慢子构成的是我们现在熟知的这个宇宙,称作“慢宇宙”,而由快子构成的宇宙,则是“快宇宙”。“快宇宙”里的种种动力学行为和“慢宇宙”的行为是恰恰相反的:在“慢宇宙”中静止的物体能量为零,一旦它获得能量,便会运动得越来越快,能量无限大时就能以光速运动。但在“快宇宙”中,如果物体的能量为零,它是以无限大速度运动的,一旦被赋予能量就会慢下来,能量无限大的时候将降低到光速。这实在是相当匪夷所思:光速竟然成了它的速度下限!跟随快子运动的话,有可能出现一种因果悖论(事实上这是所有超光速系统都将面临的麻烦:时间倒流),就像一首诗里面写的那样:
名叫布赖特的年轻女子
她能走得比光还快
那日出了个远门
回来却是在前天夜里
快子理论的另一个问题是它的存在会使得真空不稳定。由于负能量出现,将意味着任何一个物理系统,可以通过无限地释放快子而处于不稳定状态,能量越来越多,聚集其中……能想象得出接下去会发生什么吗?在我看来,那一定一定很可怕。
尽管如此,科学家们还是在想法设法觅其踪影,欲一睹方颜。翘首以盼的这群人无非寄望于两大途径:对撞机和宇宙射线。1973年,据说有几个人从高能宇宙射线中发现过某种小么子具有超过C的运行速度,不过就昙花一现,此后再也没有幸运者看到过。它是不是快子更无从考究了。
量子世界你靠边站
熟悉量子力学发展史的人都知道,1927年布鲁塞尔的索尔维会议上,相对论掌门爱因斯坦和量子论老大玻尔之间旷日持久的论战即已拉开序幕,两人你来我往、拉锯多年。事态愈演愈升级,1935年更达到白热化,老爱联合波里斯•波多尔斯基(Boris Podolsky)和内森•罗森(Nathan Rosen)两人在《物理评论》上发表了《可以认为量子力学对物理实在的描述是完备的吗?》(Can quantum-mechanical description of physical reality be considered complete?),提出一个著名的思想实验——以三人姓氏头字母命名为EPR佯谬,目的是为了证明量子力学无法自圆其说。这个影响深远的命题可以描述如下:假设有一对粒子,总自旋为零,想办法让它们在空间上尽可能远远分开,比如一个在地球上,一个在月球上(甚至更远)。按照量子力学原理推测,若单独测量地球上粒子的自旋,向上或向下的概率各为1/2,一旦真实状态在某个时刻被确定,那么月球上粒子就不用测了,必然该是另一个状态。这听上去有些荒谬,想想看,隔着遥不可及的距离,未经测定的那个粒子怎么可能即刻知晓已测定粒子的自旋、并且采取与它相反的方式呢?
所以老爱开始得意洋洋,老玻啊,知道自己错了吧。
老玻一如既往地固执,毫不迟疑发文章回敬,说不管相隔多么远,对其中一个粒子实行局域操作,一定会瞬间引致另一个粒子状态骤变,简言之,两个粒子处在一种“量子纠缠态”(quantum entanglement)上。这说法被老爱嗤之以鼻,讽刺为真不愧“幽灵般的远距作用”。结果还是谁也说服不了谁,反正他们吵啊吵的那些年里,没人能用实验证明到底有没有这样的粒子对。
恐怖的是,近年来,量子纠缠却被真实地观察到了。1997年,瑞士日内瓦大学的物理学家尼古拉斯•吉森(Nicolas Gisin)等人将一对纠缠态光子分开、通过两根光纤发送到相距18公里的两个村庄,沿途它们会经过特殊的探测器分别测定其“颜色”。实验证实:两个光子正如量子理论预测的那样,一个变红,另一个也将一起变红,而且,改变的时刻测不出时间差。考虑到实验精确程度,这当中需要有一种至少比光速快1万倍的“传递”在发生作用才行!次年,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和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大学的两个研究小组也传出了支持量子力学观点的消息。
不仅如此,这里出现的还未见得是量子世界对光速极限的唯一突破,有一种“量子隧穿效应”(Quantum tunneling,指粒子逃出高于其自身能量的势垒,这在经典物理体系内绝对无从立足)中的诡异超光速现象也被许多人所津津乐道。1962年,就有一群物理学家声称做到了以 4.7c的速度穿过11.4厘米宽势垒传输莫扎特第40交响曲。尽管关于其中很多细节都有颇多争议,但这个实验方向却被一些科学家坚持下来并不断改进。2007年,来自德国科布伦茨大学的君特•尼姆兹(Günter Nimtz)和阿冯斯•斯达霍芬(Alfons Stahlhofen)又完成了一次量子隧穿实验,得出结论认为亚原子粒子在一定条件下可达到某个目前甚至无法作出测量的速度。他们将两块相同的长40厘米的玻璃棱镜拼放在一起,让一束波长为33厘米的微波光量子依次通过,在行进的过程当中,骤然分开棱镜,第一块棱镜不出意料将反射掉部分光量子,但仍然有一部分光量子会设法隧穿过两者之间的缝隙进入第二块棱镜。然而,无论是反射的光量子还是隧穿的光量子,到达探测器竟然都是同时的!由于隧穿的光量子显然经过了更长一段距离,这意味着它们的速度超过了反射的那部分光量子。
曲相推进任我游
派拉蒙公司推出的大型科幻系列电影《星际旅行》(Star Trek)的剧情中构建了一个以“曲相推进”(Warp Drive)为基础的空间运输系统,它的第一代飞船由NASA于21世纪中期设计完成,在接下来几个世纪里经过多重改进,日臻完善,成就了人类舰队的一番霸业。
据说,该剧编剧还煞有其事地设定了一套Warp Drive标准,“其中Warp 1等于光速,之后每提高一个级别,速度都以指数的形式增加:Warp 2等于10.079c……Warp 5是213.75c……Warp 9是1516.4c;而Warp 9.9999则是199516c,也就是59,813,392,050.3公里/秒。以Warp 9的速度穿越太阳系只要26秒,到比邻星需要1.2天;倘若达到Warp 9.9999,那么用0.2秒就可以穿越太阳系,12.8分钟到达比邻星,6个月可以穿越整个银河系,到仙女座星系只要10年。”这个大胆妄为的设想,完全得益于爱因斯坦当年一举突破牛顿体系对空间进行的全新解读,他认为空间的形状会受到物质的影响而改变,事实上,重力就源于空间的曲率。
1994年,墨西哥数学家米古尔•阿库别瑞(Miguel Alcubierre)对空间弯曲的可能性进行了数学建模,创造出了一个如同波浪般起伏的时空几何结构。这项工作独到在于规避了相对论原先所描述的“以接近光速运动的物体会遭遇质量增加及时间延长效应”的问题,因为在这种状态下移动的船,其相对于局域平坦空间来说甚至相当于静止。当中真正起作用造成推进的是飞船邻近处的空间变形——后方的空间扩张,前方的空间压缩,飞船沿着这个“曲速泡”前进。在外面的观察者看来,船质量不变,却能以超光速运动,并且始终保持在一条类时世界线上。
阿库别瑞的奇思妙想看似高招,却带来了一个大麻烦:按照他的模型计算,要产生时空扭曲,所需能量超过了整个宇宙能够提供的能量总和。1999年,罗马尼亚天主大学的布卢克(Chris Van Den Broeck)对这一理论的可行性做了些补充改进,他把曲速泡表面积缩小了,同时扩大其内部3维体积,由此算起来,只需要原先能量的1/10⁶²就行了。这样运输几颗小原子好像还可以试试,只需要3个太阳那么多的质量就差不多啦。显然,变革者自己对这结果还比较满意:“距离第一架曲速引擎的日子还远得很,但比起不可能来说,我们算是走近了点。”
可以看到,问题的关键落在了用什么办法获得那看似不可能得到的巨大能量,来自德州贝勒大学的两名物理学家理查德•奥伯塞(Richard Obousy)和杰拉德•克里夫(Gerald Cleaver),在2008年2月发表于arXiv.org上的一篇文章《曲相推进:一种新手段》(Warp Drive: A New Approach)中指出,绝对不可以忘了那被认为是促使宇宙加速膨胀的暗能量!至于怎么利用嘛,可以考虑的方法之一,是去操纵弦论(目前最有希望统一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理论之一,它认为我们的世界有11个维度)所预言的除了长、宽、高和时间之外的6个隐藏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