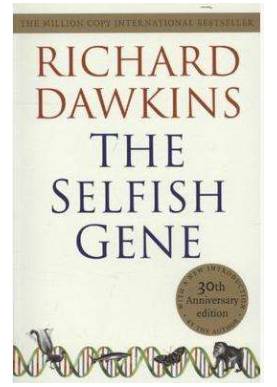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写过一首《责子诗》,其云:
“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
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
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
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
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
通子垂九龄,但觅梨子粟。
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
清人王世祯《古诗笺》的本诗按语中说,渊明有舒俨、宣俟、雍份、端佚、通佟五子。诗中提到的舒、宣、雍、端、佟,皆为其小名。据诗中描述,老大阿舒年十六,四体不勤,一身懒骨;老二阿宣已近“志学之年”——十五岁,不继父志,不读书,不习文;老三阿雍、老四阿端为孪生兄弟,同为十三岁,不识数算,智商堪忧;最后一位阿通九岁了,只知道夺食抢物,仨梨两枣而已,无远大志向……唉,眼看着几个儿子一天天长大,又看不到成材的任何希望,可怜天下父母心,为父的陶渊明心中的焦灼、无奈可想而知。比较一下辛弃疾《清平乐·茅檐低小》中所描述的“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辛氏诸儿起码还知道劳动创造财富,大儿锄草,中儿织笼,一为大田劳作,一为手工编织,将来都可自食其力。而陶渊明种豆,却无帮手,有《种豆》诗为证:“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如阿舒能像辛氏大儿一样,锄豆南山,也可帮父亲一把。有专家从现代医学角度分析,渊明诸儿多痴愚恰与他所说的“且进杯中物”有关,男人醉酒后同房,所生子女迟钝愚笨的概率极高。陶令天天酒不离口,所谓“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移居》),其自传云:“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五柳先生传》)如陶令有知,似应在《责子》诗之外,还要多写一首《自责》诗。
艺术手法上,《责子》已达到“无技巧”、“欲辩忘言”的高超境界,寥寥数十言,通体白描,不仅把五个儿子的各自特点刻画得活灵活现,而且写出作者对儿子的训责、恨爱、忧虑、无奈,及人到晚年对孩子的殷切期待及恨铁不成钢的怅然心情。宋人梅尧臣有云:“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读邵不疑诗卷》)陶诗正是这种典型。
欣赏一首诗,可有不同角度。除了一般所及的视角之外,《责子》诗实际还触及到文化资本的转换与传承的问题。表面上,陶令是在为孩子的前途担忧,若深一层看,它实际还透露出对家人后代无法继承自己知识、文化的隐忧,所谓“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是也,而这同他爱读书、“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五柳先生传》)不可同日而语。
文化资本是法国学者皮埃尔·布迪厄提出的概念。2002年1月23日,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和哲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因癌症去世,享年71岁。他在思想界的地位可用格拉斯·约翰逊的一句话来概括:作为思想家,皮埃尔·布迪厄对20世纪后半期的影响,恰如萨特曾经对20世纪前半期的影响那样重要。在其名著《资本的形式》中,布迪厄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文化资本的理论。他认为,资本可以表现为三种基本类型:(1)经济资本,它可以直接转换成金钱,这一转换过程是以私人产权的形式制度化的;(2)文化资本,其特点为不可直接进行人际转换,但在某些条件下,它可以转换成经济资本,这一转换过程是以教育资质的形式制度化的;(3)社会资本,它由社会义务所构成,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转换成经济资本,而这一转换过程是以某种高贵身份的形式被制度化的。文化资本,实际上是一种信息资本(Information Capital)。而单就文化资本而言,又主要表现为三种形式:(1)身体化的存在,即文化人;(2)客观化的存在,即文化产品;(3)制度化的存在,即文化制度。
文化人,是文化资本存在的第一种形式。其特点表现为实体化、身体化的状态,它体现在行动者精神和身体持久的性情倾向之中,是与资本的投资者和拥有者的身体、肉体相联系的,存在于文化、教育、修养等具体形式之中的,行动者必须通过自己身体化的、具体化的实践活动来获取它。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类型的文化资本具有特殊的累积性和传递性。就积累而言,它与个人及其生物特性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不能超越个体行动者及其表现能力,并随着拥有者的肉体身心能力一起衰落和消亡;就传递、转换而言,“这种具体的资本是转换成个人有机组成的外来财富,是转换成个人习性的外来财富,和金钱、产权以及贵族头衔不一样的是,它无法通过馈赠、买卖和交换进行当下的传承”。(《资本的形式》)若换成比较中国式的表述,就是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所说的:“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秦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移其子弟。”文化知识作为一种资本、一种遗产的最大特性,就是不能像经济资本那样随意地直接地转让给他人,包括自己的后代,所谓“虽在父兄,不能移其子弟”是也,这也正是陶令望着五个“总不好纸笔”的孩子伤心而又无奈的又一重要原因。
布尔迪厄认为:“文化资本的原始累积,文化资本最有力的象征性功效原则,存在于它的传递逻辑之中。一方面,呈现于客观化状态中的文化资本,以及令这一客观化发生所需要的时间,这样取决于整个家庭所拥有的文化资本,另一方面,文化资本的原始积累,以及每一类有用的文化资本的易于积累的先决条件之下,只有拥有强大资本的家庭的教育开始于最初阶段,没有延迟,也没有耽误时间。在此情况下,累积的时间涵盖在整个社会化时期当中。紧跟着的是文化资本的转换状况。文化资本的传承转换无疑也是以最隐秘的形式出现。”按照这种观点,其实陶渊明是最具有“文化资本”原始积累的家庭,但是唯独缺乏文化资本传递的重要一环 —— 可以继承其“资本”的传人,即几个儿子,据诗中描述,老大阿舒年十六,四体不勤,一身懒骨;老二阿宣已近“志学之年”——十五岁,不继父志,不读书,不习文;老三阿雍、老四阿端为孪生兄弟,同为十三岁,不识数算,智商堪忧;最后一位阿通九岁了,只知道夺食抢物,仨梨两枣而已,无远大志向……唉,眼看着几个儿子一天天长大,又看不到成材的任何希望,可怜天下父母心,为父的陶渊明心中的焦灼、无奈可想而知。
身体化的文化资本德最大特征是不可重复的个性。文化人的肉体消亡了,与之相依相随的活生生的才气、智慧、能力也就同时随风飘逝,“物是人非事事休”;当然这不排除其精神仍然以作品的形式“活”下来,代代传承,但作为他本人所独有的个性、气质、才华却永不存在了,原创能力也无法延续了,引起后人的无限遐思,所谓“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杜甫《咏怀古迹》),李白《夜泊牛渚怀古》有云:“牛渚西江夜,青天无片云。登舟望秋月,空忆谢将军。余亦能高咏,斯人不可闻。明朝挂帆席,枫叶落纷纷。”“空忆”、“不可闻”的惋惜语气中,寄寓着后人的多少怅惘!
再把思维延伸一下,陶渊明《责子》所蕴含的意思实际上还有基因的传承问题。
20世纪70年代,英国学者里查德•道金斯撰写了一部很有名气的书,题为《自私的基因》,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道金斯指出,包括我们人在内的动物、植物和微生物这些世界上所有的千姿百态的生命体,只不过是基因借以生存的机器,所谓“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人生者,百代之过客”是也。从肉眼看不见的病毒,到巨型生物红杉、蓝鲸和大象,从最低级的细菌,到具有复杂结构和高级智慧的人类,它们都拥有同一类型的复制基因。这种基因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DNA分子。生物个体总在不停地消失。人类,作为基因生存一种机器,其寿命算是较长的。但一个人在世上能活到七八十岁也是古稀之事。古代的皇帝要他的臣民们呼他万岁,但他们的寿命也不比普通人长。但世界上的基因可望生存的时间比万岁还要万岁,竟要以千百万虽来计算。
基因的天职就是复制,它不断地将自己拷贝到不同的生存机器中去。基因不会因改变了栖身的个体而被破坏,它调换了伙伴又继续前进。生存器只是它们的运载体。每个运载体的行程都是有限的,因为一切个体都有寿终正寝之日。但基因的寿命不会随着个体的死亡而终结,个体完成职责之后便被弃之一旁,基因将继续走它的路,永不停息。基因不仅是亘古长存的,而且还是自私的。基因为了生存,必须与它的等位基因竞争。等位基因就是争夺它们在后代染色体位置的对手。在基因库能牺牲等位基因而增加自己生存机会的任何基因都会生存下去。反之,如果它们不自私,就会在竞争中被消灭掉。所以,生存下来的基因必定是自私的基因,不可能是利他的基因。
每个个体生命消失之后,遗留下两样东西:基因和米姆。我们来到这世上,实际上是当一辈子基因的生存机器,为基因传宗接代。但是,在三代之后,这个可悲的人生使命将会被渐渐淡忘。你的儿女,甚至你的孙儿女也许五官与你长得很像,也许同你一样酷爱音乐,也许头发的颜色也和你一样。但是,你的基因每隔一代就要减少一半。这样,随着一代一代的繁衍,用不了很久,你的基因比例就会变得微乎其微。基因也许是不朽的,但是构成我们个人的基因结合体最终将会消亡。伊丽莎白二世是征服者威廉的嫡系后代,但是,也许她身上的基因没有一个是先王的。于是,生命短暂的我们应该寻找另一种基因 —— 文化基因。道金斯将其称为“米姆”。道金斯认为,我们需要用一个名称来称呼这种新的复制者,它要能表达文化遗传单位,或是模拟单位这样的概念“mimeme”这个词源出自希腊语,但我想要一个单音节词,读上去有点像gene(基因)。如果我把“mimeme”缩略成“meme”,我希望研究古希腊语言的朋友们会原谅我。不管你会怎么说,这个新词在词形上多少还有些可取之处,它可以和“memory”(记忆)联系起来,与法语“meme”也有点联系。这个词应和“cream”(奶油)押韵,读作“米姆”。米姆的例子多不胜数,例如,曲调、思想、妙语、时装以及制陶和建筑工艺等。基因通过精子和卵子代代遗传,在基因库里不断繁殖。同样,通过广义上说的模拟,米姆从一个大脑传到另一个大脑,在米姆库内不断繁殖。如果一名科学家听说或谈到一个巧妙的构思,会马上将它传给同事和学生。他会在文章里和课堂上提到这个构思。一旦它被人们理解了,我们将可以说它得到了繁殖,在大脑之间广为传播。
简言之,肉体生命短暂,精神基因不朽。如果一个人对世界文化有所贡献,提出过一个伟大的思想,谱过一首好曲子,发明过一个电火花插头,或者作过一首好诗,它们就会永远流传下去,即使在他的基因已融入公库之后,它们仍旧永垂不朽。G.C.威廉曾经说过,苏格拉底恐怕早已没有什么基因遗留在当今世上了吧,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像苏格拉底、达•芬奇、哥白尼和马可尼这些伟人的米姆复合体仍然生机勃勃。天下一致百虑,殊途同归。这也与中国古代贤哲的理解不谋而合,如魏文帝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就有过类似的思考: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
曹丕贵为君王,享尽人间荣华富贵,但惟其如此,根据马斯洛揭示的人生需求层次的逻辑,已经实现的人生目标不再成为人生的动力,一欲既偿,他欲随之,故其内心时常萦绕着对人生短促、生命无常的忧虑之情,其焦虑往往倍于常人。
天下智慧生命的心灵都是相通的。此外,国学大师王国维的理解也与此暗合,其云:
“天下有最神圣、最尊贵而无与于当世之用者,哲学与美术是已。天下之人嚣然谓之曰“无用”,无损于哲学、美术之价值也。至为此学者自忘其神圣之位置,而求以合当世之用,于是二者之价值失。夫哲学与美术之所志者,真理也。真理者,天下万世之真理,而非一时之真理也。其有发明此真理(哲学家),或以记号表之(美术)者,天下万世之功绩,而非一时之功绩也。…… 夫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岂不以其有纯粹之知识与微妙之感情哉?至于生活之欲,人与禽兽无以或异。后者政治家及实业家之所供给,前者之慰藉满足非求诸哲学及美术不可。且政治上之势力,有形的也,及身的也;而哲学美术上之势力,无形的也,身后的也。故非旷世之豪杰,鲜有不为一时之势力所诱惑者矣。虽然,无亦其对哲学美术之趣味有未深,而于其价值有未自觉者乎?今夫人积年月之研究,而一旦豁然悟宇宙人生—之真理,或以胸中倘恍不可捉摸之意境一旦表诸文字、绘画、雕刻之上,此固彼天赋之能力之发展,而此时之快乐,决非南面王之所能易者也。”(王国维《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
陶渊明《责子》诗,布迪厄的文化资本,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曹丕的《典论•论文》,王国维的《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其间隐然有一条内在逻辑红线,这就是肉体生命有限,精神生命永存,人世间,真正有价值的是精神文化基因的传承,其势如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注释:
1、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包亚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