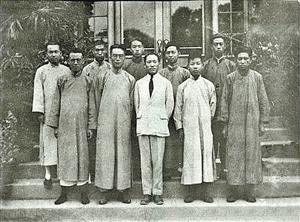“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所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
他本人从来没有被称为“大师”,但在他的任内,却为清华请来了众多的大师,并为后世培养出了众多的大师。他被称为清华“永远的校长”。
在遍布世界的清华校友心目中,提到梅贻琦就意味着清华,提到清华也就意味着梅贻琦。他以不同凡响的教育智慧和由贤入圣的人格魅力,奠定了清华大学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的灵魂。
欧美曾有著名大学校长在1941年清华建校30周年时称赞清华:“西土一千年,中邦三十载。”
1889年梅贻琦出生于天津,父亲中过秀才,后沦为盐店职员,梅贻琦懂事之初,家境已每况愈下。但梅贻琦的父亲始终没有放弃对子女的教育。
梅贻琦自幼熟读经史,且善背诵。他的同仁回忆说,有一次梅贻琦表示,“假如我们之中有谁背诵任何中国古经传有错漏,我可以接背任何章节。”
1908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南开私立学校第一届师范班。1908年,他以南开学堂全校第一成绩毕业,进入保定高等学堂就读,次年便顺利考取首批庚款留美生。600多名学生中,他考到了第六名。
到美国后,梅贻琦攻读电机系,在同学的眼中,他是个成绩优良、性格温厚,永远轻声细语的人。然因家境实在平困,获得学士学位后,梅贻琦就放弃了攻读研究生的机会,回到中国任清华物理系主任。那时他才26岁。
当时的清华大学,当校长不容易,常有校长教授被师生赶下台,所以任期都不长。
罗建伦当着全体师生面提出辞职。结果学生们纷纷表示:“无论国父同意与否,我们皆无挽留之意。”
因为清华园用的是庚款办校,就是教育部也奈何不了任何人。随后,政府派乔万选接任校长,当踌躇满志的乔万选带着武装卫兵进校时,学生们单独将他请进了礼堂,等乔万选出来,校方已经拿到承诺,上面由乔万选亲笔写道:“将永不任清华校长。”
容不得一点专制和独裁,清华师生宁可11个月无人管理学校,将教育部提名的校长统统拒之门外。当时觊觎校长之位人数众多,在期盼而又戒备的心情中,清华师生向教育部提出了5个条件:
1、 没有党派色彩。
2、 知识渊博。
3、 要有很高的威望。
4、 人格要高尚。
5、 能实实在在发展清华。
发生校长风波时,梅贻琦正在美国,担任清华留美学生监督处监督,管理全美各地的清华留学生。
1928年,39岁的梅贻琦接到调令。当他重回清华时,学生们都抱以观望心态。而就在就职演说上,梅贻琦发表了那段著名的讲话:
“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一个大学之所以成为大学,并不在于它有多少幢大楼,而在于它有多少个大师。梅贻琦将一个大学的师资力量,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梅贻琦看来,大学的目的只有两个。第一是研究学术,第二是造就人才。这两者的实现,全依赖于教授。
盛传当时的清华有三难:进校门难、读学分难、出校门难。任何一门课,59.99分的成绩也要重读,没有补考,然而绝对公正。
梅贻琦是严肃的,若不与其相当熟悉,一般看不到他的言笑,然而他偶尔也有幽默的一面。
梅先生担任了十八年清华校长,有人问他秘诀,梅先生说:“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没有人愿意倒霉(梅)!”
“校长的任务就是给教授搬搬椅子,端端茶水的”
梅贻琦曾将自己比喻成京戏里“王帽”的角色:“他每出场总是王冠齐整,仪仗森严,文武将官,前呼后拥,像煞有介事。其实会看戏的绝不注意这正中端坐的‘王帽’,他因为运气好,搭在一个好班子里,那么人家对这台戏叫好时,他亦觉得‘与有荣焉’而已。’”
这当然是梅贻琦的自谦之词。实际上,梅贻琦对清华的贡献,恰恰是“搭成了一个好班子”,而非是他自己说的“运气好”,凑巧在一个好班子。
“对知识分子心态了解之深,当时少有如他的人。”梅贻琦在礼聘教师方面,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他任教务长时,就力排众议,使布衣之身的陈寅恪成为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之一。
他亲自到火车站,把留美归来的语言学博士赵元任接到学校。
华罗庚只有初中文化程度,被破格召进清华,破格从系资料员转升助教,破格送到剑桥大学“访问研究”,最后又破格未经讲师、副教授阶段而被聘为教授。
这种不唯学历,不唯资历,只凭真才实学,照样可以当教授的用人理念,在梅先生看来是正常不过的事。
许渊冲先生说,破格提拔资历浅、学历不高的钱钟书、华罗庚、吴晗等名教授,梅校长曾经谦虚地说,他的工作只是帮人搬搬凳子而已。清华或者西南联大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与梅校长不惜代价诚聘国内外一流的师资是分不开的。
为使教师免去后顾之忧,安心教学,梅贻琦大幅度提高清华教师的待遇。当时,清华教授每月最高可拿500元,工作一定年限后,可以休假一年,赴欧美研究,学校开一半薪水,还给予往返路费。
这个传统在西南联大时结出硕果:西南联大的教师名士如云,共开出课程1600门。
校中既有闻一多、吴晗等进步人士,也有国民党直属区党部,有三青团直属西南联大分部,此外还有地下党组织,有中国民主同盟的组织。
学术自由与独立思考在这样的环境里蔚然成风,且大大滋养了学生。
梅贻琦始终旗帜鲜明地主张:“大学教育之重,在于人格。如果一个学生没有完善的人格,那么走上社会也不会对社会有利。”
“学生没有坏的,坏学生都是被教坏的”
其实初到清华时,学生们都怀疑他的能力。清华一直崇尚实干,没想到梅贻琦就职后,竟像空气一样。
学校开会,他坐在一旁听讲,从不干涉教授们的发言,只是偶尔站起来给大家倒倒茶水。和那些试图在清华大展身手的校长不同,梅贻琦从不独断、专横,人家说什么他就听什么人们经常从他口中听见的三个字,就是“我从众”。除了这三个字,他很少发表观点。
叶公超用“慢、稳、刚”三个字形容他。
梅贻琦宽厚温良,个性沉静,被弟子们称为“寡言君子”,但实际上,他“嘴里不说,骨子里自有分寸”。清华学生曾戏作打油诗描述梅校长的谦逊含蓄:“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认为,恐怕仿佛不见得。”
他在《大学一解》中提到:教师不但要专长明晰知识的讲授,还要为学生的“修养、意志、情绪”树立楷模,因而阐述了著名的“从游论”:
“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
正因为他的坚持,清华学术自由之风,教授自治之风,和学生人格培养之风盛行。正是梅贻琦的不断努力,清华从一个名气大但无学术之实的高校,跃升为中国首屈一指的大学。日后从这里走出的学生,不少都是誉享全球的大师。
1935年底,日寇压境,华北危急,清华进步学生蒋南翔发出著名声音:“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一二·九”运动后,清华曾经发生过数千军警闯入学校逮捕学生的事件。事前得知了这个消息,学校的几位领导人在梅贻琦家里商量如何应对。
大家说了很多意见,惟有梅校长默然不发一言,最后大家都等他说话,足足有两三分钟,他还是抽着烟一句话不说。
冯友兰教授问:“校长——你看怎么样?”梅贻琦还是不说话。
叶公超教授忍不住了,问道:“校长,您是没有意见而不说话,还是在想着而不说话?”他隔了几秒钟回答:“我在想,现在我们要阻止他们来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只可以想想如何减少他们来了之后的骚动。”
对于学生,梅贻琦一律采取爱护的态度。
学生们怀疑军警特工手里的名单是校方提供的,学生们看到教务长潘光旦拄着拐杖来到校园,立即进行围攻,将他的拐杖夺过扔到地上,不依不饶高声喊着讨伐口号。
此时,他们的校长身着一件深灰色长袍,从科学馆方向慢步走来,梅停留片刻,大体弄明白事情经过,快步来到潘光旦身边的台阶上站定,面带愠色,表情严肃,眼睛瞪着二三百学生,有半分钟未发一言,尽量抑制胸中的愤怒,挺起胸膛,厉声说道:“你们要打人,就打我好了!你们如果认为学校把名单交给外面的人,那是由我负责。
随后,梅校长以极沉痛的心情而低沉幽默的口气告诫同学:“青年人做事要有正确的判断和考虑,……徒凭血气之勇,是不能担当大任的。尤其做事要有责任心,昨天早上你们英雄式的演出,将人家派来的官长吊了起来,你不讲理,人家更可不讲理,晚上来势太大,你们领头的人不听学校的劝告,出了事情可以规避,我做校长的不能退避的。人家逼着要住宿学生的名单,我能不给吗?”
停了一下校长说:“我只好很抱歉地给他一份去年的名单,我告诉他们可能名字和住处不大准确的。……你们还逞强称英雄的话,我很难了。不过今后如果你们能信任学校的措施与领导,我当然负责保释所有被捕的同学,维护学术上的独立。”
现场的学生顿时被梅贻琦的威严姿态和坚定如铁的话镇住,瞪着眼睛互相望望,缩着脖子悄无声息的散去,事后梅贻琦将所有被捕的学生保释出来。
坚定果断,毫不含糊。他以他的担当,他的言行来告诉学生该怎样做人。
“生斯长斯,吾爱吾庐”
梅贻琦嗜酒,在这一点上也堪称“君子”。
考古学大师李济回忆:“我看见他喝醉过,但我没看见他闹过酒。这一点在我所见过的当代人中,只有梅月涵先生与蔡孑民先生才有这种‘不及乱’的记录。”
曾有一篇纪念他的文章,标题就叫《清华和酒》:“在清华全校师生员工中,梅先生的酒量可称第一……大家都知道梅先生最使人敬爱的时候,是吃酒的时候,他从来没有拒绝过任何敬酒人的好意,他干杯时那种似苦又似喜的面上表情,看到过的人,终身不会忘记。”
西南联大附中教学质量高,云南省主席龙云的女儿极想考进联大附中,结果名落孙山。龙云心里不痛快,叫秘书长去和梅贻琦疏通。秘书长说,“我打听过了,梅校长的女儿梅祖芬也未被录取。”龙云一听怒气全消,他以身作则,维护教育的公平,绝不因权势因私情有丝毫退让,并以此赢得所有人的尊重。
不管是著述、才华,还是恋爱、婚姻,相比于其他同时期的知识分子,梅贻琦生前经历的故事性都显得颇为平淡。除了在西南联大期间发表的《大学一解》,他没有惊世的著作和才华,也没有轰轰烈烈的恋爱,同妻子简单相遇相识而直接走入平静的婚姻。
梅贻琦行为克己,虽身居高位,却清贫如洗。
出任清华校长,按规定可以享受免交电话费、免费雇家庭帮工、免费拉两吨煤等“特权”,但梅贻琦都主动放弃了。
梅夫人韩咏华回忆,在昆明“经常吃的是白饭拌辣椒,没有青菜,有时吃菠菜豆腐汤,大家就很高兴了。”生活拮据,梅夫人不得不自谋生计,摆地摊变卖孩子旧衣服挣10元招待客人有之,提着篮子寄卖“定胜糕”有之,到医院、首饰店、衣帽工厂、盲童学校打短工亦有之。
在西南联大,梅贻琦与教授一样租住民房,他将校长专车交给学校共用,自己家庭符合条件却不拿补助金。
1941年7月他去成都公差,已订好回昆明的飞机票,恰好可乘邮政汽车,为给学校节约200多元,梅贻琦毫不犹豫退掉机票,改乘邮政车回昆明。
西南联大之魂
1937年,北平沦陷。清华被占,南开几乎夷为平地。为保存中国教育的希望,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南迁,造就了中国教育史上的梦幻奇迹,西南联大。
当时联大有三个常委,张伯苓和蒋梦麟都在重庆做事,真正管理联大的人只有梅贻琦一位。
清华严谨、北大自由、南开活泼,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学风,三个学校的教授更是课业重叠,各有各的思想和观点。明明讲的是同一堂课的内容,不同的教授却有不同的讲法。但梅贻琦将清华的学术自由之风,带到了西南联大,仍旧尊重每位教授。虽然教授之间有互相瞧不上的,但对于温文尔雅、寡言少语的梅贻琦,无人不是尊重信服。
闻一多是民主斗士,性情率真,动不动就在清华课堂发表鼓动演说,满嘴都是“过激”的言论。
尽管如此,梅贻琦从不干涉。
1944年,国民政府施压,要求西南联大解聘闻一多等教授,梅贻琦听了,根本不予理会。
等到蒋介石约他来面谈,他反倒说:“少数言论确有行为不当,很多同仁也都深不以为然,此数人之举乃一时之冲动,或因其家属众多,时有病人,生活太困难,愁闷郁于胸中,所以才找机会发些火气。”
蒋介石听了连连点头:“生活问题甚是重要。”
一番话不但巧妙保住了教授,还叫蒋介石提高了教授待遇。
中国学者的完美典型
梅贻琦身材颀长,风度翩翩,常着一身青布长衫,脸如雕塑般棱角分明,堪称那个时代的美男子,曾被来中国访问的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誉为“中国学者的完美典型”。
他那“从容不迫的态度”早在1909年考取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时,就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据他的同届同学徐君陶回忆,发榜那天,考生们都很活跃,考上的喜形于色,没考上的则面色沮丧。只有瘦高的梅贻琦,始终神色自若,“不慌不忙、不喜不忧地在那里看榜”,让人觉察不出他是否考取——而实际上,在全国630名考生当中,他名列第六。
西南联大学生何兆武也回忆说:我多次看见梅先生和我们一起跑警报,梅先生那时快60岁,他从来不跑,总是安步当车,手持拐杖,神态稳重,毫不慌张,而且嘱咐大家不要拥挤。梅先生的从容,给我们做了一个典范。
抗战胜利后,大陆局势逐渐明晰起来。所有人都面对走与不走的选择。身在解放区的吴晗竭力让他留下,全校学生也含泪挽留。梅贻琦却选择踏上了离开的飞机,因当时庚款还有大笔基金,而要动用这笔校款,需要两人签字,一是教育部部长,二是清华校长。梅贻琦知道,一旦自己不做校长,国民政府极容易推选一人,动用这笔款项。
危急时刻观人之言行更可见其性情。1948年,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北京城内人心惶惶,梅先生去意已决。
12月14日,有飞机来接胡适之,有人打电话给梅先生,凡是那时在围城中的人,都焦急地渴望离开,预料梅先生问询后一定大喜若狂,立刻行动。
哪知道梅先生听到此事,并弄清这架飞机并不是接他之后,他竟无动于衷,一如平日缓和低沉的声调,说不是接他的,他并不预备去。
虽然被一再告以时局的危机,错过这架飞机,可能不会有机会;但他始终若无其事地谢绝了这建议,后来政府接梅先生和各位教授的飞机来了,他才把一切事情安排妥帖后,从容不迫地提着一架打字机,拿着两本书走了。
许多人在平日装腔作势,好似高不可及,一旦遇到危急关头,便丑态百出,以求苟免,因为他内心本没有真正高贵自尊的地方。而梅先生则是已把高贵自尊建基于本身,因此才能夷险一节,不为外境左右。甚至在生死存亡的关头,都一直保持着尊贵不群的风格,使人顽廉懦立,肃然起敬。——这才真是中国读书人传统的最高修养;这才不愧是一个‘人物’”。
沉默而坚持的梅贻琦为何选择远离新政呢?或许可以从他的日记中能够有所推断,“我对政治没有研究,与共产主义也没有多大认识,但颇具怀疑”,这个“怀疑”之词代表了当时许多知识分子对于当时政局以及对中共的看法。没有人能够真正了解梅贻琦的想法,但是对于思想文化的观点不同,这确实是一些工作者选择离开的重要原因。
离开大陆后,60岁梅贻琦先去了美国,在非常简陋的办公室管理庚款基金,自己给自己定薪300元,和庚款资助生一样。国民政府曾要求他将薪水上调至1500元,被他坚决拒绝。那时,夫人韩咏华在衣帽车间做过工,在首饰店里卖过货,在医院里当过代班,为了生计,任劳任怨。听说这些事后,对梅贻琦保护庚款颇为不满的官员,甚至叫他“守财奴”。
手握清华基金的梅贻琦,晚年生活一直非常清贫。
1955年,他回到台湾办校,于新竹复立国立清华大学,不顾政府办大办强的要求,先设立了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精耕细作,实事求是,在这个基础上才一步步壮大新竹清华。
1960年梅贻琦被确诊罹患癌症。他终身从事教育,毫无积蓄。台湾新竹清华大学为其垫付一部分治疗费,医院又酌情减少了一部分,还是不够。清华校友们商议募捐,半年间募集台币65万元。躺在病床上的梅贻琦看到凝聚着爱心的募捐记录,“阅后半晌无语,后曾流泪颔首”。
1962年5月19日,梅贻琦先生在台湾溘然长逝,享年72岁。蒋公中正亲题“勋昭作育”, 万人空巷送灵迎灵,千人执绋、灵柩上覆盖着他的清华不朽的旗帜,百姓们自发立祭案、燃放鞭炮、敬献花圈…
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叶公超在回忆文章中说道:“梅先生是个外圆内方的人,不得罪人,避免和人摩擦;但是他不愿意作的事,骂他打他他还是不作的。”短短几语,已触到了梅贻琦的典型性格和心灵深处。
由蒋梦麟等人组成的治丧委员会随即撰祭文写下:“呜呼——天之将丧斯文欤?胡夺我先生之速!”评价之高亦可见一斑。
他逝世后,秘书把他在病中一直带在身边的手提包封存了。两个星期后,在有各方人士参加的场合下启封后大家都怔住了:箱子里保存的是清华庚款账目,从17年前到现在,一笔又一笔,清清爽爽,分毫不差。
清华校史研究专家黄延复曾这样评价梅贻琦:“他长母校几十年,然清华基金雄厚,竟不苟取分文。在贪污成风的社会,竟能高洁、清廉到这样地步,真是圣人的行为。只这一点,已足可为万世师表。”这样看来,如果说梅贻琦是清华基金的“守护神”一点也不为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