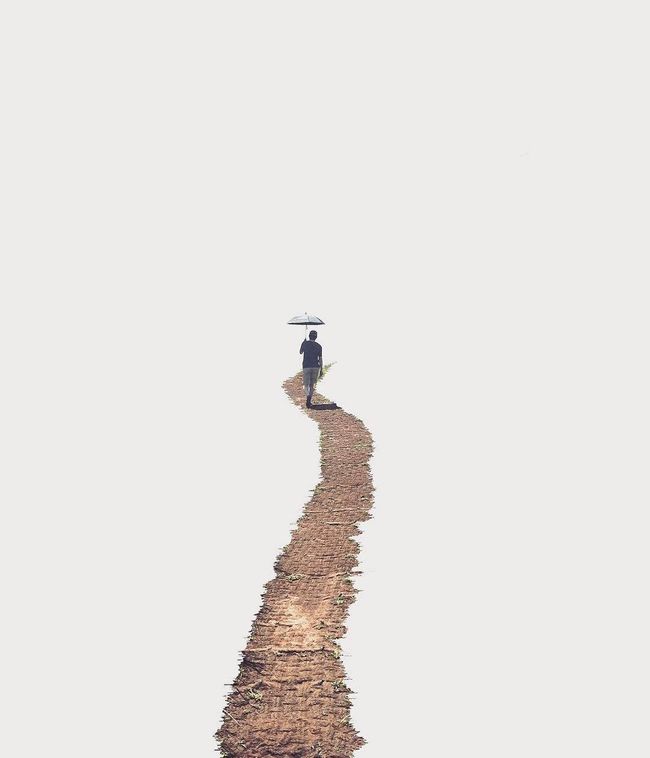别人家遛狗,狗子在前头飞奔,主人拽着绳在后面喘:“祖宗!你慢点!”
葡萄家遛狗,主人走走走,回头一瞅,怒吼一声:“豆豆!你快点!”
“讲真,这确定不是猪么?”林森诚恳地问。
那只斗牛犬,肥得像个插上四根筷子的猪肘。走两步喘一下,再两步,停下来大口喘。
“等它跑过来,我都能跟你干一盘坏事了。”林森一把揽住葡萄的腰,手往曲线最高处滑:“来亲亲。”
葡萄嗔笑着躲开,两步走出斑驳的树影:“专心遛狗,豆豆……”
女友不配合,林森耸肩:“你家这狗怎么这么宝贝啊?全家出去玩,还专门留你在家里伺候它?”
胖狗悠悠挪过来,伸着舌头一步一停。葡萄蹲下去挠它脖子:“它啊,地位比我都高,这是我奶奶的心头肉啊。”
十年前,豆豆来到葡萄家的时候,爷爷刚去世。
爷爷奶奶的爱情故事挺传奇。简单点说,就是霸道县长爱上大家闺秀。
葡萄的爷爷参军早,战功赫赫,没到30就到某地去上任县长。县长大人新官三把火,千头万绪都要抓。抓来抓去,就抓到了葡萄她奶奶。
那是一个月黑风高之夜,县长在办公室里写材料。写着写着突然心神不宁,决定去巡夜。
“等会儿等会儿……你爷爷是第一任县长??哪儿的?”林森打断葡萄,他没想到女友有这种背景。
葡萄白他一眼:“反正不是这儿!”
回头看一眼,豆豆还在费劲地颠儿,林森点点头:“你说你接着说。”
那会儿的政府大院儿都是借用的老宅子,一到晚上就没人了。县长惦记着白天收进来的一批资产,就举了个风灯去巡视。
夜深人静,一盏昏黄风灯在大院里飘忽。这种几重几进格局的宅子,夜里小风穿堂过,呜呜声细如鬼嘶。但县长是不怕的,县长是上过战场见过死人的。人死了连话都不会说,更不用提发出声音了。
然而,当他站在侧院门口的时候,他的世界观就开始动摇了。
因为那两扇挂了锁的木门下方,老门槛底下,有个小洞正吭哧着,慢慢向外喷射泥土。
县长想了想,熄了灯蹲在一边等。他要看看这个洞里有哪路神仙。没多大会,泥土不喷了,一个圆圆脑袋冒了出来。
先是盘在头上的辫子,然后两只机敏的大眼睛,然后是一张小巧的嘴,嘴里还咬着根树枝。
葡萄她奶奶闪亮登场。
“大半夜的,你奶奶在那干嘛??”林森挨着葡萄坐下,豆豆还在努力爬。
“因为白天被查抄的就是我奶奶家。”葡萄说。
早前县里有几个大家族,奶奶家就是最大的一个。她又是这家唯一的独苗,N亩良田N多铺子的产业,就她一个姑娘家继承。
按说有这样身家,奶奶只用装装白莲花,玩玩柔弱就能过好这一辈子。偏偏她爹脑子一热,非要去投身革命。
投就投吧,还投得不是我军。稀里糊涂死在了内战。
这就悲了个催的。成王败寇,一家子都跟着遭了殃。县里整肃,奶奶家里所有产业都被查封,土地铺子收归国有,金银细软全部充公。
奶奶是县里有名的美人,可惜现在一点也看不出来, 灰头土脸一身泥,刚露个头就被县长提溜起来了。
“你谁啊?!你在这干嘛?!”县长呆了,他还没开口啊喂,这小贼先指责上了。
而且,这还是个女的??赶快撒手。
“问你呢!”小女贼叉着腰中气十足
县长想了想,那句我是县长又咽了回去:“这里面晚上不能来,你快回去吧。”
县长走了很远,边走边摇头。这小丫头大晚上到这里来肯定不干好事。可是刚才他看过了,门槛下那个洞太小,她不可能夹带东西出来。
算了。今天月亮不错,放她一马。县长在乌云遮天的黑夜里大步流星,一点不脸红。
“喂,你等等我!”夭寿,那个小女贼又追来了。
大小姐跑得直喘,站住了伸手一抹,明亮的小脸晃得人眼珠一颤:“打……打更的,我找不到路了,你带我出去吧。”
妈了个巴子什么情况这是??我还成了打更的了??
县长想了想,那句我是县长又咽了回去:“好,我带你出去。”
“谢谢啊……喂你走慢点!我跟不上!”
“后来呢?”林森买了酸奶递过来。葡萄拆开盖子给豆豆舔:“后来就在一起了呗。”
豆豆吧唧吧唧舔酸奶,活像当年的媒人吧唧吧唧抽烟袋。
旱烟袋里烧的是烟丝,这玩意呛。不能使劲吸,只能一口一口慢慢嘬。
老媒人这会儿都快把烟嘴儿给嘬烂了——他郁闷。
这媒怎么做啊?县长和没落财主家的大小姐?而且大小姐她家刚刚被抄?
原想着肯定不能成,没想到大小姐一口就答应了。媒人欢天喜地走了,大小姐风轻云淡回屋——磨刀。
她打算结婚那天捅死县长。
大小姐没见过县长,但是她家产的是县里扣走抄没的,所以她认为县长得负责。
那时候百废待兴,县长结婚也就是俩枕头并一起,喝两杯薄酒就算数。新娘子很乖,顶了盖头默默等。
一等就是大半天,闷得要命。
县长乐颠颠回来揭盖头,大小姐等得不耐烦正好撩开透气。两厢一对眼,都呆了。
“打更的,你在这干嘛??”
新郎官憋成内伤,想半天,老子是县长这句话又咽了回去:“我是新郎。”
新娘瞪着眼上上下下看他半天,泄了气,把手里东西往桌子上一放:“我饿了,厨房在哪?”
县长装作没看见她放下的剪刀:“哦,在外面,我带你去。”
于是俩人出门左转,烧火做饭。
从那天起,奶奶开启了数落爷爷模式。
“从来不等我,连结婚当天都不等我!就那么两步路都走得飞快!每次都得直着脖子在后面喊!”
奶奶恨恨地说。
县长确实走得快,工作下乡赶集,从来步履盎然。大小姐每次都得吼:“打更的,你慢点!”
就连县长落魄那些年也一样。
“落魄?什么意思?”林森抱着豆豆挠耳朵,肥狗惬意地爬在他怀里哼哼。
葡萄抱着膝盖依在他身边,看着小区里的路灯一盏盏亮起来:“哪有人能一帆风顺呢。我爸刚出生那几年,爷爷受到奶奶家里的牵连,被停了公职。全家都搬到县城外一个窝棚里,守着几分薄田。”
突然从一县长官变成农夫,爷爷的腰杆依旧笔直。只是步子迈得更快,每天一大早就去下地。
那时候,夜空才刚开始清醒,逐渐透明的深蓝色穹顶上,几颗寥落的星星。寒意鬼影般缠上来,爷爷也不管,风地里走得浑身是汗。
奶奶看着他在田埂上来来回回的走,没有叫他。
爷爷不会种田,两年下来,打的粮食连自家吃都成问题不够。奶奶也着急:儿子已经慢慢大了,这么过下去哪是办法。
于是这天早上,爷爷一睁眼,身边只有儿子,媳妇不见了。
大风大浪都不动声色的男人,这下慌了神。他几乎是滚下床的,敞着怀就跑出了门。房前屋后全找遍了,地里也没有。爷爷越找心越空,腿脚都开始哆嗦。
最后,他在黑漆漆的田埂边蹲下去,抱住脑袋。
“媳妇肯定是过不下去跑了啊。都怪我笨……连个种地都不会啊……当初说一定让她过好日子,结果让她受这个罪……是我对不起她啊……丫头啊丫头……”
眼泪鼻涕一起流,胡须都糊成了绺。爷爷闷头哽了半晌,终于嚎出声。他哭得太投入,没听到身侧有衣裤的窸窣脆响。
“打更的,你神经啥!”一声压低了的娇叱。
爷爷惊得抬起头,只见他的丫头叉腰站在眼前,犹如二人第一次见面一样,一头一身的土。
“走快回家......”奶奶没说完,就觉得眼前一花。世界一个大颠倒,头顶上是地,屁股后面是天——她男人扛着她正飞奔。
儿子还没醒,俩人躲进了灶间。爷爷紧抱着媳妇不撒手,鼻涕眼泪又要流。奶奶不耐烦地往外挣:“快松开,我有正事跟你说。”
爷爷头埋在奶奶腋下,俩胳膊箍得结实:“不说好不好?我以后努力种地,我去做生意,我什么都干,好不好?你别说了好不好?”
奶奶也着急:“快松开!一会儿娃醒了就不好办了!”
爷爷更不松手了,开始带哭腔:“丫头,媳妇,我什么都不问,你不说好不好?”
“死打更的!你看这是啥!!”
“咣当”一物落地。
爷爷一愣神,奶奶挣脱出来伸手捡起,献宝一样捧到她面前:“呐,这东西我埋了好久了。今早偷偷刨出来的。你赶快把它截下来一段,够咱开个小买卖了。”
一根金条,在奶奶手里泛着幽光。
“金条??哪来的金条??”林森懵了。
“你以为那年我奶奶夜探县政府大院,半夜钻地洞干嘛去了?”
“所以……你当时……“爷爷也是懵一脸。
奶奶白他一眼:“我用嘴叼出来的!裹了块破布,你以为是树枝!”说着坐下来捶肩膀:“埋得太隐蔽,害我刨了半天才找到。哎对了,你哭啥?你以为我要说啥??”
爷爷想了想,那句我以为你要跟人跑了又咽了回去:“没事没事,我去做饭啊……”
“靠了这根金条,日子渐渐有了起色。再后来,爷爷被起用,爸爸读书也争气,全家搬到这里,生活也就安稳了。”
葡萄摸着豆豆的后背,宽厚的脊背上全是肉褶。
就这么一天一天的,除了爷爷走路依旧太快,其他一切都好。直到十年前,爷爷和奶奶逛早市。
清晨的十字路口没几个人,绿灯一亮,奶奶赶快过马路。今天的玉米菜够新鲜,回家一烫就能吃了。可到了路对过,一回头,爷爷还站在原地没动。
那个一辈子都腰杆笔直的老头子,佝偻着身子愣在原地。手里两把菜叶,脸上一片茫然。
医生说,这叫帕金森,也就是老年痴呆。没有解药,没有办法。
奶奶终于不再埋怨爷爷走的快了。
“你等等我”变成了“你快点”。
“爷爷去世以后,奶奶就养了这只狗。”葡萄挽着林森往回走:“豆豆小时候就胖,越长越肥,路都走不动了。我爸几次想给它减肥,奶奶都拦住了。”
“它走得和老头子一样慢。我这么吼着它,心里就舒坦。哼!老货,让你一辈子走那么快,总的有等你的时候。”
奶奶这么说着,眼睛里有波光闪烁。
林森沉默。
世界一片模糊,墨色天空往下坠落,在城市灯火上方停住。天色彻底黑透,该回去了。他揽住葡萄肩膀,对远处那只肥狗吼道:
“豆豆!你快点……算了,你慢慢走。”
(本文已在版权印备案,如需转载请访问版权印808647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