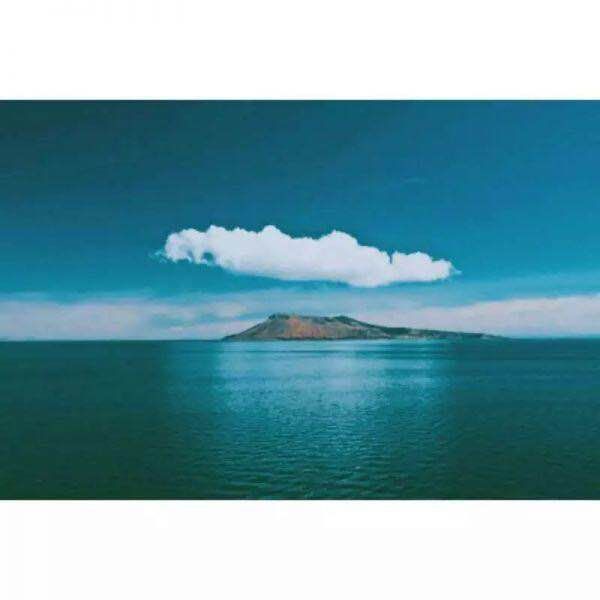“平局。”
我站起身,拍了拍身上的灰尘,也没搭话,准备迎接下一轮的挑战。他想杀我,他却救了我。
这个赌局仿佛已经失去了它原本的意义,或许,是我一开始就没懂这个局。我以为我的对手是诗人,或者那个雇佣兵,可我从迷雾中穿过,才发现战场上空无一人,只有我,还有浮尘。
“接下来赌什么?”
诗人没有回答我。弯下腰身,从他的长筒靴里掏出来一个黑色的东西。两根不同粗细的管子伸到我面前,和他眼中的黑洞一样,深不见底。
这是一把左轮手枪。
“俄罗斯轮盘。”
诗人从T恤衫的领口掏出一个黑色的项链,类似于草结的绳子,中间挂着一颗子弹。诗人轻轻一扯,子弹就乖乖躺在了他的掌心。
“这颗子弹是我的战利品,我用一只眼睛换回来的。0.45英寸钢芯子弹,从太阳穴里钻进去,只会留下一个不到1厘米的小口,然后掀开一半的头盖骨,从另一边穿出来,血和脑浆会喷满这整间屋子,会装满你刚才喝的茶杯。”诗人用没有起伏的音调说着,仿佛给我们讲一个入睡前的童话故事。他将子弹装进去,然后拨动弹巢,手轻轻一抖,咔的一声就轻轻合上了。
“这一局不是我跟你的赌局。是你跟你的宿命的赌局。你只要对自己的太阳穴开一枪,你就赢了。”诗人把枪轻轻放在桌子上,盯着我说:“这会有两种情况,你没死,你赢了;你死了,你也赢了。”
诗人把枪把转过来,推到我面前的桌子上。
“这把枪有6个弹巢,里面有1颗子弹。17%的机率你会死在这里,如果我是你,我就放弃。”
枪就在面前。审判就这样开场了。神会宽恕我吗?袖袖车里的鼓声从地底下传来,一下一下,冲到我心里,融成了心跳的节奏,从灵魂深处泛起了对死亡的坚信,一种超脱的快感迷惑了心神,我漫无目的的伸出手去,握住了那把左轮手枪。
袖袖的手紧紧地压着我的手腕,她眼里的焦急流了下来。
“别傻了,你死了也救不了你。”
她仿似看出了我眼里的决绝。疯了一样的趴在我手上,不让我抬起那把枪。我手上一阵温热,她就那样放声大哭起来:
“你别傻了,别傻了,别傻了...”
我鼻子一阵发酸。强忍着自己红了的眼眶,不漏出一些多余的东西。袖袖的哭声逐渐小了下去。我摸了摸她的头,我们是同病相怜的人,只是我才开始投入的痛,而她早已痛到麻木。
我轻轻扶起她。清秀的脸上像下过一场小雨,露出雾蒙蒙的眼和挂着雨滴的鼻尖,比夜空中的繁星还美丽,比夏天的荷塘还美丽。
我挪开她的手。把枪举起来,顶在了自己的太阳穴上。
袖袖转过身去,两肩瑟瑟发抖。这也是我为数不多的贝壳了,被苦难包裹着,却结出了珍珠般的惊喜。
“袖袖,你出去。”我压低嗓音,命令她道。
“不,我不能走。你要是死了,我好给你的魂带路。带你回家。”
家?!
她总是能很轻易地找到我的软肋。即使我在城里安生立命,在我梦里辗转的,一直都是那个农村老房子里的烟火灶台。
我慢慢放下手枪,低下了头,我把身上的包取下来,扔在了诗人的脚边。
“我输了。”
我转过身,朝门外走去。
“等等,”诗人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就这么走了吗?”
我缓缓转过身来,抬起头注视着他的眼睛:“你还想怎么样?”
“你就这样放弃了吗?孬种。”
我立在当场,没有任何言语。我把自己变成了一场零和游戏,不管往天平的哪一端增加砝码,败的永远都是我。
“你想要我怎么样?”
“你知道吗?看来你是不知道了。鱼儿有心脏病,她是不能怀孕的。随时都会要了她的命。”
诗人用这颗子弹狠狠地在我脑袋上开了一枪。不断起伏的情绪过于强烈,已经超过了承受的阈值了。
“你是幸运的,鱼儿爱你,可以不顾及自己的性命,而你呢,就甘愿做一个临阵脱逃的逃兵。你要么就别上战场,不管你是否愿意。命运不就是这样吗?什么时候会给你准备时间。”诗人缓缓走到我面前。抬起一只手,举到我面前晃了晃,问我: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就是命运。”
话音未落,他的那只手就抽到了我的脸上,打得我魂飞魄散。右边脸颊失去了知觉,我已感觉不到疼痛,血顺着嘴角流了下来。我突然感觉好受了一些。
“同样不会给你准备的时间。这一巴掌你早就该挨的。可能你生命中的人都太过宽待你了。你居然能不知道鱼儿有心脏病,你能蠢到什么地步,你才会不知道啊?”他顿了顿,接着说道,“你逃避不了的。你往前走一步看看,看你今天是不是要死在这里。”
我往前踏出一步,又拾起了那把手枪,举到太阳穴上。
所有人都在注视着我。诗人,袖袖,还有鱼儿,所有与我关联的,所有的贝壳此刻都静静地围在我的四周,丢掉的和没丢掉的,他们都来了。
这是我与自己的一场决斗。不管输赢,我都可以与自己和解了。
我把食指勾在扳机上,大大地睁着眼睛,看着在场的所有人。我看到了我远在天国的爸爸,看到了养我长大因病去世的大伯,看到了我差点错失的老张,看到了不知道在哪的鱼儿。
我抬起头,对着屋顶一声嚎叫,“我错了!!!”
眼泪像从远古洪荒中奔流而来,瞬间就将我彻底淹没了。
我扣动了扳机,对着自己的太阳穴连开了六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