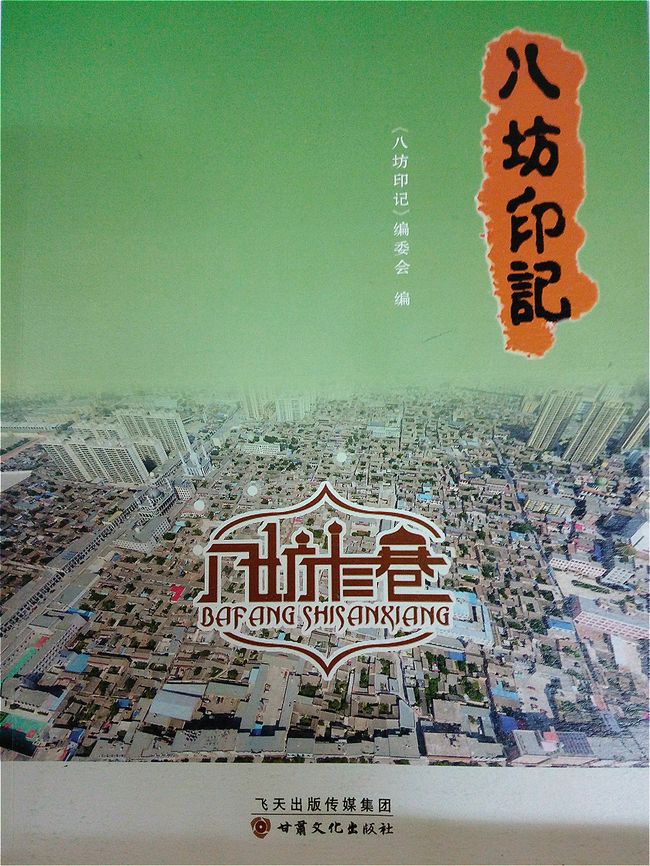- 深度学习篇---矩阵
Atticus-Orion
嵌入式知识篇上位机知识篇嵌入式硬件篇深度学习矩阵人工智能
在机械臂解算、深度学习网络等硬件和软件领域中,矩阵运算作为核心数学工具,承担着数据表示、变换、映射和优化的关键作用。以下从具体领域出发,详细总结涉及的矩阵运算及对应的核心知识:一、机械臂解算领域机械臂解算(运动学、动力学分析)的核心是描述“关节空间”与“操作空间”的映射关系,矩阵运算用于精准刻画坐标系转换、运动传递和力/力矩分析。1.运动学解算(正/逆运动学)核心目标:通过矩阵描述关节角度与末端执
- 微信视频号红心可以买嘛,一百个多少钱
神州网络公司
微信视频号红心可以买嘛,一百个多少钱视频号点赞大拇指通常是30元100个,价格会有所波动,如果大量通常在200-300之间。对于视频号来说大拇指是收藏,而爱心是点赞。是不是和抖音略有不同。一、微信视频号小爱心意义在微信视频号里面,小红心就是点赞,而那个大拇指则表示收藏。大多数考核都是基于爱心考核的,重要程度高些。用户点击小红心就表示对这个作品的赞同,因此,如果作品的小红心数量很多,就代表这个作品很
- 飞算JavaAI:力臻开发之本真,破 AI 代码之繁琐,传统项目一键生成
微学AI
人工智能javajavaAI
飞算JavaAI:力臻开发之本真,破AI代码之繁琐,传统项目一键生成文章目录飞算JavaAI:力臻开发之本真,破AI代码之繁琐,传统项目一键生成一、前言二、飞算JavaAI是什么?2.1背景与实力2.2飞算JavaAI的“独门绝技”三、飞算JavaAI实战体验3.1IDEA插件安装配置3.2Main中写一个简单的梯度下降算法3.3main函数搭建一个卷积神经网络网络3.4飞算JavaAI:需求分析
- PyCharm 高效入门指南:从安装到进阶,解锁 Python 开发全流程
作为Python开发者的利器,PyCharm的安装与配置是开启高效编程之旅的第一步。面对Community和Professional两个版本,该如何选择呢?Community版是免费开源的,适合初学者和简单项目开发,包含基础的Python开发功能;而Professional版虽收费,但功能更强大,支持Web开发、数据库连接等高级功能,适合专业开发者和复杂项目。1.安装与配置下载与安装下载PyCha
- 嵌入式硬件篇---继电器
Atticus-Orion
嵌入式硬件篇嵌入式硬件继电器
继电器是一种通过小电流控制大电流的电磁开关,广泛应用于自动化控制、电力系统和电子设备中。以下从工作原理、应用场景和电路特点三个方面详细介绍:一、工作原理继电器本质是电磁控制的机械式开关,核心部件包括:线圈(Coil):通电时产生磁场。铁芯(IronCore):增强磁场强度。衔铁(Armature):受磁场吸引动作的金属部件。触点(Contacts):由衔铁控制通断的开关。工作过程:线圈不通电:衔铁
- 嵌入式知识篇---机械臂的运动学结算(简单2自由度)
Atticus-Orion
嵌入式知识篇上位机知识篇嵌入式硬件篇人工智能机械臂解算
机械臂的“解算”本质是运动学解算,核心是解决“关节角度”和“末端位置”的互转问题。下面用最通俗的方式解释,并结合2自由度平面机械臂(结构最简单,适合入门)给出Python和ESP32代码,以及参数细节。一、机械臂运动学解算的通俗原理想象你有一条“简化的手臂”:只有大臂和小臂两个关节(类似人类的上臂和前臂),只能在桌面(X-Y平面)内运动。正解:知道“大臂转30°,小臂转60°”,算出“手掌”的位置
- 可信数据空间:概念、架构与应用实践
小赖同学啊
testTechnologyPrecious架构
可信数据空间:概念、架构与应用实践一、可信数据空间的核心定义可信数据空间(TrustedDataSpace)是一种基于技术架构与制度设计的安全数据共享生态,通过构建“数据可用不可见、可控可追溯”的流通环境,解决数据要素市场化过程中的隐私保护、主权确认、流通合规等核心问题。其本质是通过密码学、区块链、智能合约等技术组合,实现数据在不同主体间的可信交互,同时保障数据所有者的权益与安全。二、核心技术要素
- 好省邀请码怎么写?好省app升级运营商容易吗?
日常购物小技巧
好省的邀请口令是什么?怎么获取好省APP邀请口令?好省邀请码千万不要随便填写,不然会后悔1、好省app是什么?好省【这个是花桃邀请码:999999【佣金更高,模式更好】】是一个领取天猫淘宝内部优惠券的APP,免费下载注册即可成为合伙人,不仅可以帮你平时网购省钱40%以上,推广分享还能赚佣金,我们平时在手机上经常看到的那些优惠券群主、主播都是靠这个赚钱的,最主要的是完全免费、0门槛!2.好省APP里
- 那些年追过的1988
etme
今天在追《runningman》的时候,里面想起了1988的歌曲,瞬间脑袋里呈现了电视剧里面的镜头,第二刷1988,也是在前不久。1988,主要是讲的友谊,里面顺带也延伸出了很多其他方面的东西,亲情,爱情。住在韩国首尔双门洞巷子里的几家人,代表着现在社会上的不同层次,也把我们那时候,小伙伴的身份完美的体现了出来。德善~一个大大咧咧的孩子,一个倒霉孩子。家里的地位,让人觉得可怜,姐姐的欺负,父母对她
- Axios泛型参数解析与使用指南
编程随想▿
TypeScriptTSaxios前端web开发语言
目录一、Axios泛型参数的核心价值二、基本用法解析1.响应数据泛型参数2.POST请求中的泛型应用三、高级泛型参数配置1.自定义响应结构2.完整AxiosResponse泛型3.错误处理泛型四、实战应用示例1.封装带泛型的API客户端2.带分页的泛型响应处理五、最佳实践与注意事项六、总结一、Axios泛型参数的核心价值Axios的泛型参数允许我们为HTTP响应数据指定类型,使TypeScript
- Spring Cloud学习:如何实现Gateway 服务网关限流
杨荧
springcloud学习gateway
目录一、SpringCloud介绍二、什么是服务网关三、Gateway的优势和应用场景四、如何实现Gateway服务网关限流一、SpringCloud介绍SpringCloud是一个基于SpringBoot的微服务架构开发工具集,它整合了多种微服务解决方案,为开发者提供了一站式的微服务开发体验。SpringCloud的核心组件包括服务发现、配置管理、消息传递、负载均衡、断路器等,这些组件可以帮助开
- 早晨冥想15分钟,288天
飞扬_7
今天早上5:30醒来。冥想15分钟。今天早上准备了充足的时间吃饭。吃过饭以后上班。金句288:一个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就可以忍受任何一种生活。——尼采
- 【乳腺超声、乳腺钼靶、宫颈癌、CT骨折】等项目数据调研,及相关参考内容整理汇总
钱多多先森
人工智能(AI)医学影像深度学习乳腺钼靶乳腺超声宫颈癌
文章目录一、乳腺超声内容整理1.1、数据集1.2、可以参考的论文1.3、可以参考的GitHub代码1.4、可以参考的博客1.5、简单任务需求二、宫颈癌风险智能诊断2.1、数据集2.2、KFB读取文件显示三、乳腺钼靶3.1、数据集3.2、拍摄方式:3.3、拍摄和观察视图3.4、DDSM标注文件解析四、CT骨折4.1、数据集五、总结本博客是一个笔记类的记录文档,主要是记录了在调研各个项目的过程中,遇到
- 麦吉丽加盟条件及费用
广州时尚王子
麦吉丽加盟条件主要包括以下几点:1.创业热情与决心:对化妆品行业充满热情,并具备强烈的创业意愿,愿意与麦吉丽共同开拓市场,创造美丽事业。2.资金实力与财务规划:需要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包括加盟费、店面租金、装修费、进货费等,建议加盟前做好充分的财务规划和资金准备。3.合法经营与商业信誉:具备合法经营资格,并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共同打造诚信、规范的商业环境。4.店面选址与面积要求:选择在人流量大、消费
- OCR 赋能发票管理系统:守护医疗票据合规,让管理更智能
EkihzniY
ocr人工智能大数据
医疗收费电子票据种类多、数据杂,票据编号、金额、诊疗项目等信息的合规核验是医院财务管理的重点。传统人工核对易出错,还难以及时发现票据篡改、重复报销等问题。OCR技术为发票管理系统装上“智慧眼”。它能快速识别电子票据上的关键信息,自动与医院HIS系统的收费数据比对,核验金额是否匹配、票据是否真实有效。一旦发现异常,系统立即预警,从源头阻断不合规票据流入财务流程。同时,OCR将票据信息自动录入管理系统
- OCR 身份识别:让身份信息录入场景更高效安全
EkihzniY
ocr安全
在银行柜台开户、线上平台实名认证等场景中,身份信息录入是基础环节,OCR身份识别产品正成为提升效率与安全性的关键。传统人工录入身份证信息,不仅耗时久,还易因手误导致姓名、号码出错,影响业务办理进度。而OCR身份识别产品能快速扫描身份证,1秒内精准提取姓名、身份证号、地址等信息,自动填入业务系统,大幅缩短办理时间。在线上实名认证时,OCR结合人脸识别技术,先识别身份证信息,再比对人脸与证件照片,确保
- 5商学习笔记
爱英思谭523
【Jocelyn1月25日习得小结:】1.知识划重点(R):快速学习:如何用20小时,快速学习?2.我的理解(I):润总这个快速学习,跟李笑来老师的最小必要知识很类似,都是通过快速掌握入门的知识,完成从0到1的跨越。时间越快,掌握大概知识越多进门就越快。3.我的相关经验或经历(A1):复述其实是帮助自己去理解概念的绝佳方式。自己带课这几年,对于教材中的概念从浅入深的学习和理解,跟我面对无数个不一样
- OCR 识别:综合信息采集仪的 “核心引擎”
EkihzniY
ocr
综合信息采集仪作为多场景信息收集的重要设备,需处理身份证、营业执照、票据等多种载体的信息。传统采集依赖人工录入,面对海量且格式多样的资料,不仅效率低下,还易因人为失误导致信息偏差。OCR识别技术让综合信息采集仪实现质的飞跃。它能快速精准提取各类证件、票据上的文字信息,自动转化为结构化数据存入系统,几秒内完成单份资料的信息采集,效率较人工提升数十倍。无论是模糊的扫描件、复杂的多语种文本,还是不规则的
- 国庆假期结束,你的微梦想清单实现了没?
Hi菜篮
2019.10.1-2019.10.7国庆假期复盘1.我为年度目标做了那些事情?✅到公司集体观看祖国70周年阅兵仪式✅带女儿、公婆看电影《我和我的祖国》✅跟老公一起看了《中国机长》✅回看综艺《偶像来了》✅读完《我决定活得有趣,并输出行动清单》✅输出文章《你,是焦虑养育者吗?》✅理财课3节✅公众号文章排版✅9月复盘,2019年目标回顾和调整✅一家人到九里峰山游玩,小家三口到飞龙岛玩;吃了一顿火锅✅晚
- ab命令压力测试---网站性能压力测试
凯凯恺恺恺恺凯凯
ab命令性能测试
网站性能压力测试是服务器网站性能调优过程中必不可缺少的一环。只有让服务器处在高压情况下,才能真正体现出软件、硬件等各种设置不当所暴露出的问题。性能测试工具目前最常见的有以下几种:ab、http_load、webbench、siege。今天我们专门来介绍ab。ab是apache自带的压力测试工具。ab非常实用,它不仅可以对apache服务器进行网站访问压力测试,也可以对或其它类型的服务器进行压力测试
- 和孩子交上朋友
苹子的天空
对于逆反心理较强的孩子,作为班主任的我们不应对他们恶语相加,更不能把他们冷落在偏僻的角落,而应该走进孩子的内心,与他做心灵的沟通。陶行知先生认为,“师爱最高境界不是母爱也不是父爱,而是朋友之爱、同志之爱。”一个有智慧的班主任,当孩子出现逆反的心理问题时,可以从他们的兴趣爱好入手,亲近他们,和他们一起玩耍、嬉戏,和孩子交上朋友,使师生能够真正在心灵与心灵之间架起信任的桥梁。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年级的增高
- 保护黄河流域,合理种植作物
7c769bedc29d
7月11日,青岛农业大学化学与药学院推进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社会实践团在东营开展社会实践活动,活动开展至今已5天,今日主题为关于黄河流域作物品种的调研。团队成员收集相关信息了解到,黄河滩地抗盐碱的作物有:油葵、苜蓿。普通作物:白薯、西瓜、棉花等。山东省是传统的农业大省,是我国粮食和北方水果的主要产地。山东省季风气候显著,旱雨季分明,且雨热同期,因此适合种植小麦,花生,玉米,棉花等。随着工业经济和现
- 0224第6天打卡:五好家庭,从我做起!
谭琳_freeisok
“存好心读好书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念先生好】:老公,我今天下午开车的时候,感受着自己不断提醒自己慢一点再慢一点,我又再一次感受到你一个隐藏得很深的优点:遇事总是不慌不忙,不轻易被周围的环境所干扰。以前我可真的是对这一点恨得不行,总感觉效率太低,让我这急性子总是恨得牙痒痒的,也总是因为这个吵架。这些年,我才慢慢看明白,每一次有什么事,我总是匆匆忙忙地想要个结果,我的心是不安的,是躁动的,而你却是实
- 2022-04-18团练笔记(第三次)
花火喜珠
昨天上午团练摸打滚爬三小时,不觉得累,难道是我体能有增?今天左右臀部,后腰,大臂酸疼,看样子老师还是加了些量,不过还不够过瘾!因为,课后我又步行四十分钟回家了。挑战了一个一直以来很惧怕的动作,有一点点心得,还是比较怕。慢慢来吧。左右侧后翻需要做出分解慢动作。横线组合地面旋转一圈半,一直是摸鱼混过去的,需要多练练。改掉耸肩毛病,动作再舒展一些。呼吸带动动作,听着容易,看老师做的也容易,为啥自己做起来
- 2019-11-10
珊珊正常奋斗中
深圳市雅诺讯科技有限公司日精进打卡第145天(知学)今日读六项精进1遍共累计78遍,大学通编1遍共累计78遍,志工精神十二条1遍共累计78遍分享《缺乏价值观支撑的勤奋不能持久》真正的勤奋,都是需要价值观支撑的。这种价值观就在于,你是真正认可勤奋工作的意义,还是觉得勤奋是给别人看的。很多人都在演勤奋。这不是说那种没有战略、没有效率的勤奋,而是说很多人在表演,要么是展现给领导同事看,要么单纯是为了发个
- 谁说准备不重要
新之焕
一次,听了个这样的八卦:一个大嫂,过年的时候,打电话给在丈母娘家的儿子,叫他回来吃团圆饭。儿子回来一看,米在锅里,据说是是忘记摁按钮,还是生的;除了桌上的两个剩菜,其余的在冰箱里还没有解冻;蔬菜还在地里要去摘。儿子顿时怒火中烧:“哈,一遍遍打电话催我们回来吃饭,我放下丈母娘家一桌子丰盛的饭菜,哦,回来就这样。”大嫂的意思:“我不是在打电话叫你们回来吗,你们不回来我煮给谁吃。”不知谁对谁错。是观念的
- 《宫斗:嫡女虎又娇,权臣折了腰》姜瑶、谢昀免费阅读,宫斗:嫡女虎又娇,权臣折了腰小说免费阅读全章节无弹窗_笔趣阁
霸道推书3
小说简介:春天的大宴上,皇后突然给中书令谢昀和太傅家的宝贝闺女来了个“惊喜”赐婚。大家都知道,权臣和太傅在朝廷里头那是冤家对头,见面就掐,斗了多少年了。皇后娘娘这一手,简直比戏文还精彩,京城里的人们都议论纷纷,说皇后娘娘这招儿真是高!可她却没想到,这两人偏偏擦出了火花……书名:《宫斗:嫡女虎又娇,权臣折了腰》主角配角:姜瑶、谢昀推荐指数:✩✩✩✩✩———小说内容试读———“你尝尝这个牛乳糕,超级好
- 移动网络http请求不到数据,wifi下可以
添码星空
Android开发HTTP网络连接
今天客户反馈手机登录不上去,用wifi可以,但是切换到移动网络就不行。查找相关文档发现由于AndroidP(版本27以上)限制了明文流量的网络请求,非加密的流量请求都会被系统禁止掉。所以如果当前应用的请求是htttp请求,而非https,这样就会导系统禁止当前应用进行该请求。请看下面的官方说法:Android致力于保护用户们的设备和数据安全。我们保证数据安全的方法之一是保护所有进入或离开Andro
- 《开创新品类》第七章第9节:差异化战略方案构成与优势
a57051ee1ea8
战略方案的制定其实有四个方面构成:1、战略,方向及布局;步骤:规划→制定→实施;方式:多元化战略→企业战略→品牌战略→差异化战略→技术战略→人才战略→竞争战略→职能战略→融资战略→资源战略;2、策略,组织成员进行战斗;方式:不战而胜→先发制人→集中攻击→力量而行→避实就虚→借鸡生蛋→狡兔三窟→暗渡陈仓→围魏救赵→背水一战→釜底抽薪;3、战术,指对指导进行战斗的方法;步骤:部署→协同→指挥→行动→保
- 【Kafka】深入理解 Kafka MirrorMaker2 - 理论篇
文章目录MirrorMaker2架构:不止是一个工具,更是一个框架工作原理揭秘1.远程主题(RemoteTopics)2.消费位移同步(OffsetSync)3.工作流图核心配置参数详解总结实战注意事项与最佳实践最近,我们团队启动了一个新项目,需要从零开始搭建一套高可用的Kafka集群。谈到高可用,异地容灾是绕不开的话题。我们选择了Kafka官方推荐的MirrorMaker2(MM2)作为我们的跨
- html
周华华
html
js
1,数组的排列
var arr=[1,4,234,43,52,];
for(var x=0;x<arr.length;x++){
for(var y=x-1;y<arr.length;y++){
if(arr[x]<arr[y]){
&
- 【Struts2 四】Struts2拦截器
bit1129
struts2拦截器
Struts2框架是基于拦截器实现的,可以对某个Action进行拦截,然后某些逻辑处理,拦截器相当于AOP里面的环绕通知,即在Action方法的执行之前和之后根据需要添加相应的逻辑。事实上,即使struts.xml没有任何关于拦截器的配置,Struts2也会为我们添加一组默认的拦截器,最常见的是,请求参数自动绑定到Action对应的字段上。
Struts2中自定义拦截器的步骤是:
- make:cc 命令未找到解决方法
daizj
linux命令未知make cc
安装rz sz程序时,报下面错误:
[root@slave2 src]# make posix
cc -O -DPOSIX -DMD=2 rz.c -o rz
make: cc:命令未找到
make: *** [posix] 错误 127
系统:centos 6.6
环境:虚拟机
错误原因:系统未安装gcc,这个是由于在安
- Oracle之Job应用
周凡杨
oracle job
最近写服务,服务上线后,需要写一个定时执行的SQL脚本,清理并更新数据库表里的数据,应用到了Oracle 的 Job的相关知识。在此总结一下。
一:查看相关job信息
1、相关视图
dba_jobs
all_jobs
user_jobs
dba_jobs_running 包含正在运行
- 多线程机制
朱辉辉33
多线程
转至http://blog.csdn.net/lj70024/archive/2010/04/06/5455790.aspx
程序、进程和线程:
程序是一段静态的代码,它是应用程序执行的蓝本。进程是程序的一次动态执行过程,它对应了从代码加载、执行至执行完毕的一个完整过程,这个过程也是进程本身从产生、发展至消亡的过程。线程是比进程更小的单位,一个进程执行过程中可以产生多个线程,每个线程有自身的
- web报表工具FineReport使用中遇到的常见报错及解决办法(一)
老A不折腾
web报表finereportjava报表报表工具
FineReport使用中遇到的常见报错及解决办法(一)
这里写点抛砖引玉,希望大家能把自己整理的问题及解决方法晾出来,Mark一下,利人利己。
出现问题先搜一下文档上有没有,再看看度娘有没有,再看看论坛有没有。有报错要看日志。下面简单罗列下常见的问题,大多文档上都有提到的。
1、address pool is full:
含义:地址池满,连接数超过并发数上
- mysql rpm安装后没有my.cnf
林鹤霄
没有my.cnf
Linux下用rpm包安装的MySQL是不会安装/etc/my.cnf文件的,
至于为什么没有这个文件而MySQL却也能正常启动和作用,在这儿有两个说法,
第一种说法,my.cnf只是MySQL启动时的一个参数文件,可以没有它,这时MySQL会用内置的默认参数启动,
第二种说法,MySQL在启动时自动使用/usr/share/mysql目录下的my-medium.cnf文件,这种说法仅限于r
- Kindle Fire HDX root并安装谷歌服务框架之后仍无法登陆谷歌账号的问题
aigo
root
原文:http://kindlefireforkid.com/how-to-setup-a-google-account-on-amazon-fire-tablet/
Step 4: Run ADB command from your PC
On the PC, you need install Amazon Fire ADB driver and instal
- javascript 中var提升的典型实例
alxw4616
JavaScript
// 刚刚在书上看到的一个小问题,很有意思.大家一起思考下吧
myname = 'global';
var fn = function () {
console.log(myname); // undefined
var myname = 'local';
console.log(myname); // local
};
fn()
// 上述代码实际上等同于以下代码
m
- 定时器和获取时间的使用
百合不是茶
时间的转换定时器
定时器:定时创建任务在游戏设计的时候用的比较多
Timer();定时器
TImerTask();Timer的子类 由 Timer 安排为一次执行或重复执行的任务。
定时器类Timer在java.util包中。使用时,先实例化,然后使用实例的schedule(TimerTask task, long delay)方法,设定
- JDK1.5 Queue
bijian1013
javathreadjava多线程Queue
JDK1.5 Queue
LinkedList:
LinkedList不是同步的。如果多个线程同时访问列表,而其中至少一个线程从结构上修改了该列表,则它必须 保持外部同步。(结构修改指添加或删除一个或多个元素的任何操作;仅设置元素的值不是结构修改。)这一般通过对自然封装该列表的对象进行同步操作来完成。如果不存在这样的对象,则应该使用 Collections.synchronizedList 方
- http认证原理和https
bijian1013
httphttps
一.基础介绍
在URL前加https://前缀表明是用SSL加密的。 你的电脑与服务器之间收发的信息传输将更加安全。
Web服务器启用SSL需要获得一个服务器证书并将该证书与要使用SSL的服务器绑定。
http和https使用的是完全不同的连接方式,用的端口也不一样,前者是80,后
- 【Java范型五】范型继承
bit1129
java
定义如下一个抽象的范型类,其中定义了两个范型参数,T1,T2
package com.tom.lang.generics;
public abstract class SuperGenerics<T1, T2> {
private T1 t1;
private T2 t2;
public abstract void doIt(T
- 【Nginx六】nginx.conf常用指令(Directive)
bit1129
Directive
1. worker_processes 8;
表示Nginx将启动8个工作者进程,通过ps -ef|grep nginx,会发现有8个Nginx Worker Process在运行
nobody 53879 118449 0 Apr22 ? 00:26:15 nginx: worker process
- lua 遍历Header头部
ronin47
lua header 遍历
local headers = ngx.req.get_headers()
ngx.say("headers begin", "<br/>")
ngx.say("Host : ", he
- java-32.通过交换a,b中的元素,使[序列a元素的和]与[序列b元素的和]之间的差最小(两数组的差最小)。
bylijinnan
java
import java.util.Arrays;
public class MinSumASumB {
/**
* Q32.有两个序列a,b,大小都为n,序列元素的值任意整数,无序.
*
* 要求:通过交换a,b中的元素,使[序列a元素的和]与[序列b元素的和]之间的差最小。
* 例如:
* int[] a = {100,99,98,1,2,3
- redis
开窍的石头
redis
在redis的redis.conf配置文件中找到# requirepass foobared
把它替换成requirepass 12356789 后边的12356789就是你的密码
打开redis客户端输入config get requirepass
返回
redis 127.0.0.1:6379> config get requirepass
1) "require
- [JAVA图像与图形]现有的GPU架构支持JAVA语言吗?
comsci
java语言
无论是opengl还是cuda,都是建立在C语言体系架构基础上的,在未来,图像图形处理业务快速发展,相关领域市场不断扩大的情况下,我们JAVA语言系统怎么从这么庞大,且还在不断扩大的市场上分到一块蛋糕,是值得每个JAVAER认真思考和行动的事情
- 安装ubuntu14.04登录后花屏了怎么办
cuiyadll
ubuntu
这个情况,一般属于显卡驱动问题。
可以先尝试安装显卡的官方闭源驱动。
按键盘三个键:CTRL + ALT + F1
进入终端,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登录终端:
安装amd的显卡驱动
sudo
apt-get
install
fglrx
安装nvidia显卡驱动
sudo
ap
- SSL 与 数字证书 的基本概念和工作原理
darrenzhu
加密ssl证书密钥签名
SSL 与 数字证书 的基本概念和工作原理
http://www.linuxde.net/2012/03/8301.html
SSL握手协议的目的是或最终结果是让客户端和服务器拥有一个共同的密钥,握手协议本身是基于非对称加密机制的,之后就使用共同的密钥基于对称加密机制进行信息交换。
http://www.ibm.com/developerworks/cn/webspher
- Ubuntu设置ip的步骤
dcj3sjt126com
ubuntu
在单位的一台机器完全装了Ubuntu Server,但回家只能在XP上VM一个,装的时候网卡是DHCP的,用ifconfig查了一下ip是192.168.92.128,可以ping通。
转载不是错:
Ubuntu命令行修改网络配置方法
/etc/network/interfaces打开后里面可设置DHCP或手动设置静态ip。前面auto eth0,让网卡开机自动挂载.
1. 以D
- php包管理工具推荐
dcj3sjt126com
PHPComposer
http://www.phpcomposer.com/
Composer是 PHP 用来管理依赖(dependency)关系的工具。你可以在自己的项目中声明所依赖的外部工具库(libraries),Composer 会帮你安装这些依赖的库文件。
中文文档
入门指南
下载
安装包列表
Composer 中国镜像
- Gson使用四(TypeAdapter)
eksliang
jsongsonGson自定义转换器gsonTypeAdapter
转载请出自出处:http://eksliang.iteye.com/blog/2175595 一.概述
Gson的TypeAapter可以理解成自定义序列化和返序列化 二、应用场景举例
例如我们通常去注册时(那些外国网站),会让我们输入firstName,lastName,但是转到我们都
- JQM控件之Navbar和Tabs
gundumw100
htmlxmlcss
在JQM中使用导航栏Navbar是简单的。
只需要将data-role="navbar"赋给div即可:
<div data-role="navbar">
<ul>
<li><a href="#" class="ui-btn-active&qu
- 利用归并排序算法对大文件进行排序
iwindyforest
java归并排序大文件分治法Merge sort
归并排序算法介绍,请参照Wikipeida
zh.wikipedia.org/wiki/%E5%BD%92%E5%B9%B6%E6%8E%92%E5%BA%8F
基本思想:
大文件分割成行数相等的两个子文件,递归(归并排序)两个子文件,直到递归到分割成的子文件低于限制行数
低于限制行数的子文件直接排序
两个排序好的子文件归并到父文件
直到最后所有排序好的父文件归并到输入
- iOS UIWebView URL拦截
啸笑天
UIWebView
本文译者:candeladiao,原文:URL filtering for UIWebView on the iPhone说明:译者在做app开发时,因为页面的javascript文件比较大导致加载速度很慢,所以想把javascript文件打包在app里,当UIWebView需要加载该脚本时就从app本地读取,但UIWebView并不支持加载本地资源。最后从下文中找到了解决方法,第一次翻译,难免有
- 索引的碎片整理SQL语句
macroli
sql
SET NOCOUNT ON
DECLARE @tablename VARCHAR (128)
DECLARE @execstr VARCHAR (255)
DECLARE @objectid INT
DECLARE @indexid INT
DECLARE @frag DECIMAL
DECLARE @maxfrag DECIMAL
--设置最大允许的碎片数量,超过则对索引进行碎片
- Angularjs同步操作http请求with $promise
qiaolevip
每天进步一点点学习永无止境AngularJS纵观千象
// Define a factory
app.factory('profilePromise', ['$q', 'AccountService', function($q, AccountService) {
var deferred = $q.defer();
AccountService.getProfile().then(function(res) {
- hibernate联合查询问题
sxj19881213
sqlHibernateHQL联合查询
最近在用hibernate做项目,遇到了联合查询的问题,以及联合查询中的N+1问题。
针对无外键关联的联合查询,我做了HQL和SQL的实验,希望能帮助到大家。(我使用的版本是hibernate3.3.2)
1 几个常识:
(1)hql中的几种join查询,只有在外键关联、并且作了相应配置时才能使用。
(2)hql的默认查询策略,在进行联合查询时,会产
- struts2.xml
wuai
struts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
<!DOCTYPE struts PUBLIC
"-//Apache Software Foundation//DTD Struts Configuration 2.3//EN"
"http://struts.apach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