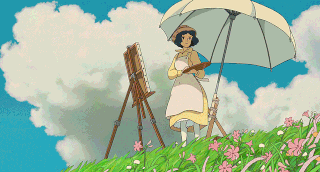九月,整个烟台的燃气费都交给海鲜了
![]()
在外游荡的人,最念烟台的一股鲜味儿。
这鲜味很难言说。不是单哪一样海鲜的味道,而是在城市的空气上方飘着的,风的味道,海水的味道,和家家户户灶前屋头的饭香,门前杂摊儿的烟火气。
先是海的味道。一下火车,烟台站背后就靠着轮渡码头,海味儿和温度刚好的风鼓荡着把这味儿送到鼻子旁。烟台的风路子野,烟台人从小都是被大耳刮子一样的风扇乎惯了的。冬天,这风割脸,能吹掉嘴巴子,能钻进厚厚的毛围脖,能推着人走。下雨天,这风能把雨伞骨拆了,人人举着一个反锅盖,雨伞就成了笑话。
唯独9月,风还没冷到无情,反倒温和可人。火车站顶上通透的大厅里一站,风从海上来,凉凉的。人从空调火车里出来,本来做好了嗡得一热的打算,结果硬着的头皮忽然舒开了,车里车外差不多温度,都托了风的福。
吹着熟悉的海风,胜过人在海边了。浪一层层刷沙滩的声音,打石头的声音,落到石头中间空当,咕咚一下灌下去的声音,闭上眼都想象得到。
但无论是沙滩上还是礁石旁,最热闹的定是人声。小孩子追着跑闹的笑声,情侣喁喁的私语,精壮的烟台老爷爷击水搏浪的声音,疲惫的人就在这片背景声里沉默着看海,一言不发。我小时候曾在海边晒曝了皮。晚上在铺上,背后灼灼地痛,躺不行,趴也趴不住。这是白天贪玩的缘故,泡在海水里不肯出来,一晒就是一整天。
海是咸的,齁咸。但海里的生物却神奇地鲜甜。游水累了之后,找个浅滩站定不动,双脚往下钻,下面的沙细细软软,很容易就踩到贝壳。两个一起对着撞,好运气时能撞得开,柔软的蛤蜊肉儿就在眼前了。吸一口汁水,粗粗嚼了,再扭来扭去地去踩下一个。
海边最容易扒到的是花蛤,黑色的壳,有白花纹。运气好也有飞蛤,黄色壳,肉肥厚,只是不容易捕,有时候踩着时明明是在,低头去摸却没了,它一呲水自己能飞老远,所以叫飞蛤。
这法子是爸爸小时候教的,我亲眼看他吃了好几个,才肯尝一尝。那时候我当然不知道海鲜可以生吃,更不懂以后在饭店里吃到的青口和生贝,可比门前市场三块钱一斤的海虹和飞蛤贵得多了,虽然讲究起来,它们也算是一家祖宗。
我妈说,我小时候,我家是不怎么买螃蟹的。想吃了,我爹背个麻袋出去,回来时能搂半兜子,煮一大盆,一顿吃不完,总能送邻居些。我早忘了这些,但记得家里确实有一个带呼吸管的游泳镜,跟人家浮潜的家伙事儿差不多。想想我爸30年前就这么潮了,不由得感慨生活确实是不如从前。
忘了说,潮在烟台是脑子不好的意思。所以我们不说人“潮”。但是到了退潮的傍晚,那确实是人潮人海中有你有我。大叔大爷,大妈大姨,下了班的主妇,撒了欢的孩子,拎着塑料袋,拎着网兜,拎着小铲子小桶,奔向他们的战场。
战利品不局限于螃蟹和蛤,海草和海蜇,礁石上的海蛎子和波漏儿(一种海螺),都一个小桶兜着,晚上回家就是一盘。
文艺青年对着海寻情的时候,我们海边儿青年,对着海觅食。
![]()
这趟回家,舅舅请客,切了好大一盆海蜇。海蜇就是水母,不蜇人的时候圆润可爱。鲜食的海蜇汤只在海边有,因为海蜇身体里百分之九十多都是水,所以稍纵即化,不喝很快会变成海水一盆。所以它只能在海边喝到,并且餐馆里不好备货,多也是不卖的。
这和大家在馆子里吃到的老醋蛰头是一个东西,但不是一个品种。那些通常是加工过的海蜇头和海蜇皮,腌制又泡发,鲜味当然仍有,只是不如喝新鲜。
海蜇汤是我姐姐最馋的东西。因为北京啥也能买到,唯独喝不上这一口。趁着海蜇还囫囵,多洗几遍,细细切了,撒上香菜末子和小米辣,一点香油和白醋,出溜出溜喝,冰冰的,溜滑,一咬还咯吱咯吱的,酸辣适口,鲜得溜溜儿的。
我一口气能喝四碗海蜇汤。当然这还不包括正餐里的三四只螃蟹和小半盆皮皮虾。皮皮虾我们叫虾爬了,因为它是在水底爬呀爬呀的,名字和飞蛤一样,都来自运动天赋。
其他各地的温州大排档里,也都能吃得到新鲜的皮皮虾。只不过我总觉得椒盐不如蒸煮,啥也不用蘸,可以剥一盆。
皮皮虾,海螺,螃蟹这些,肉满膏肥,可都属寒凉。蘸着姜汁醋,仍然两滴香油,祛寒解腻。蟹配黄酒,温一壶,加点姜丝,撒上枸杞红枣,一口蟹,一口酒,神仙不换。
去年夏天我做了一大盆醉蟹钳,下酒也极好。活蟹白酒泡了,吞吐间排净洗好。加绍兴陈年黄酒,放大姜,小米辣,干辣椒,八角花椒香叶尽扔进去,味极鲜和盐调味。一罐一罐冰箱冷藏格封好,馋了解开一只,酒香冲鼻,鲜美非常。蟹膏扑在白米饭上,腾腾的热气一冲,如坐海中央。
配白米饭的还有一样最好,是我的童年美食。那时海胆价格不太贵,班长(我总叫我妈刘班长)骑着摩托车载着我讲价。她总是等人都走尽了才张口,一口气买一大堆回来。避开层层的刺,敲开,黄色的一颗颗,软嫩地露出来。一锅鸡蛋汤,将开锅了海胆肉滚进去,汤稠稠的,海胆肉嫩滑若无,我能多吃一碗米。
![]()
鲜味都是海的馈赠。有时候逢着好风,海边会忽然像藏宝库一样,一夜之间冒出许多海鲜,都是刮上来的。有时候是海蛎子,有时候是水母,有时候是其他什么,一刮就是一整个沙滩,晨练的阿姨大爷匆忙回家拿家巴什儿,过年一样捡到中午头。
去蓬莱长岛之前,我对渔业没有理解。长岛最出名的金钩海米,是铺在街上晒的,跟内陆的农村晒苞米一样壮观。到了晒海米的时候,一整个村子的街道都一片金黄。晒海带的季节,又是一片深褐。
摄影:赵金阳(齐鲁晚报)
走在街边,随便拣了就吃,海米小小一粒,鲜滋味能爆开整个口腔。
长岛的海就是富矿。鲍鱼大个儿,海参也长得肥。八代(鱿鱼的一种)和鱼就更不用说,吃到嘴里从没有柴这一说,都是肥且嫩。
那时候,吃海鲜论麻袋的年代已经过去了。我经常跟着渔业口的记者李娜去拍休渔和开海,扇贝肥美的时候,我们觅了海边刚刚停下的船,挑刚从网子上摘下来的扇贝,哼哧哼哧背回家。
娜姐是临沂人,曾爱吃三文鱼。不过在烟台跑了三年渔业之后,她吃够了。这一度成为了我们夸耀烟台的段子,大烟台,真没辙。
![]()
那天坐在桌前扒螃蟹到脱力之后,我忽然想,鲜是不抢眼的。它从来不是主角儿,大多陪着酸甜辣咸。但里面好像多点跟其他调料不一样的东西,好像有了鲜味儿,这道菜才有生命力。
鲁菜的鲜是有说头的。最早的说法就是海肠。故事里的大厨临死才告诉徒弟自己做菜的秘诀,海肠晒干,磨粉,藏在袄袖子里,将出锅的时候背着人那么一撒,菜自然与众不同。
这个意思,跟今天的味精鸡精是一样。人类学会保存鲜味不易,可却没法把所有的鲜味统统分门别类,对应成化学原料。大骨头汤吊出来的鲜,烤松茸在铁板上配着黄油滋滋作响的鲜,海蛎子壳里积下的出溜一口汤水的鲜,各有各的勾人。
我最爱烤海肠里面的那一点汤。海肠在炭火上收缩,腔子里留下一点鲜汤,真是无上的鲜味。3块钱那么一小根,一定平着端慢慢移,嘴靠过去,吸一边儿。这下吮了汤,再一根海肠慢慢嚼着,落肚为安。
多年之后,我曾经要求我爹做香辣虾,被回绝了。我爹的理由是,香辣都是从前海货运到内陆,失了鲜味,多放辣子去盖它。刚捞上来的,只有蒸了原汁原味,本色本香。
当时不服,现在信然。
互动
你吃过最酣畅淋漓的一顿海鲜是在哪里?
“开渔”这件事,曾经怎样影响过你的饭桌?
欢迎留言分享
(本文转载自公号“逸响”,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逸晌 w-armdre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