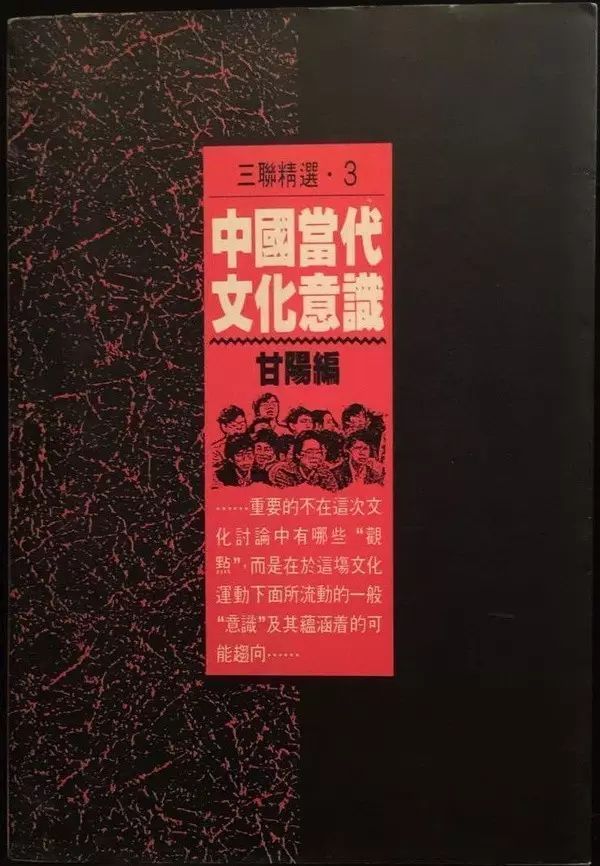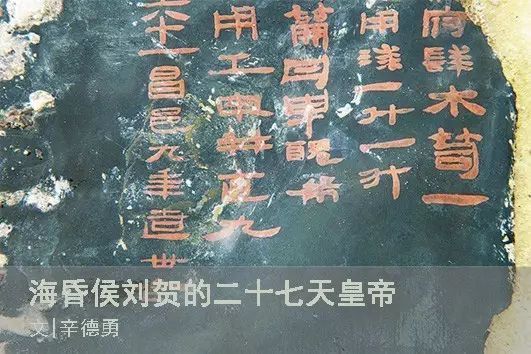甘阳:八十年代,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犹疑彷徨 |"文化:中国与世界"三十年系列二
微信ID:sanlianshutong
『生活需要读书和新知』
“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孕育于八十年代的文化讨论热潮之中。在八十年代末,作为“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主编,甘阳即着手选编了一部《中国当代文化意识》,此书1989年在香港、台湾印行了繁体字初版;2006年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印行简体字版,并改名为《八十年代文化意识》。甘阳说,此书——
并不打算也不可能包揽无遗地反映这场文化反思的全貌。同时,与通常的做法不同,它也不打算面面俱到地把所谓各家各派的观点罗列在一起。……在这种过渡性的年代中,在中国知识分子普遍学术准备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所有的一切思考都必然只能是极度“过渡性”,极度不成熟的。因此,重要的不在于这次文化讨论中有哪些“观点”,而是在于这场文化运动下面所流动着的一般“意识”及其所蕴涵着的可能趋向。我的目的,就是想通过这本《中国当代文化意识》来多少反映出这种“意识”及趋向。根据这种考虑,我把全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名为“反叛”,下编则标为“彷徨”。
以下发布的是甘阳为此书写的“再版前言”(2005年)、“初版前言”(1988年);最后则是甘阳的一则短文“八十年代中国文化讨论五题”,此文更多表露了一种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犹疑彷徨的态度,颇不同于他曾突出强调的“继承发扬传统的最强劲手段恰恰就是反传统”这一激进态度。小标题系编者所拟。
文 | 甘阳
1 八十年代似乎已经是一个非常遥远的时代
— 再版前言(2005年) —
八十年代似乎已经是一个非常遥远的时代。八十年代的“文化热”在今天的人看来或许不可思议:“文化”是什么?这虚无缥缈的东西有什么可讨论的?不以经济为中心,却以文化为中心,足见八十年代的人是多么地迂腐、可笑、不现代!但不管怎样,持续近四年(1985-1988)的“八十年代文化热”已经成为中国历史意识的一部分,而对许多参与者而言,八十年代不但是一个充满青春激情的年代,而且也是一个纯真素朴、较少算计之心的年代。
这本《八十年代文化意识》,是我于1988年10月编定,并于1989年先后由香港三联书店和台湾风云时代出版公司在香港和台北出版(原名《中国当代文化意识》)。但本书的国内版却由于我当时赴美求学而一直耽搁了下来。今承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美意,得以在国内再版而与读者见面,总算还了一件心愿。由于本书内容已具有历史文献性质,此次再版未作一字一句增减,篇目次第亦一仍其旧,以保持历史原样。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当时是属于北京民间学术团体“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的出版物之一。这个编委会成立于1985年,在短短三四年间曾主持出版了“现代西方学术文库”、“新知文库”、“人文研究丛书”,以及《文化:中国与世界研究集刊》等上百种出版物。当年编委会的成员为:于晓、王庆节、王炜、王焱、方鸣、甘阳、纪宏、刘小枫、刘东、孙依依、杜小真、苏国勋、李银河、何光沪、余量、陈平原、陈来、陈维钢、陈嘉映、林岗、周国平、赵一凡、赵越胜、胡平、徐友渔、钱理群、黄子平、郭宏安、曹天宇、阎步克、梁治平。令人痛惜的是,其中王炜兄已于今年离我们而去,我谨将这本八十年代的文集献给这位亡友,以纪念当年朝夕相处的难忘岁月。
▲《八十年代文化意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与九十年代的“经济人时代”相比,八十年代堪称是最后的“文化人时代”,其中的主体是知青一代中的文化人。白湖散人陶博吾大师的一副对联,或可借来描述一代知青文化人所走的路:
尝遍苦辣酸甜,几番东扑西颠,浊骨敢追超脱者。
历尽风霜雨雪,纵使千磨万折,黄泉不作可怜魂。
2005年12月31日
— 初版前言(1988年) —
“ 西方自身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陷入深刻的精神危机和思想危机之中。……现代化的进程并不只是一套正面价值的胜利实现,而且同时还伴随着巨大的负面价值。……然而,就中国目前的状况言,问题的全部复杂性就在于:一方面,现代社会的正面价值(自由、民主、法制)还远远没有真正落实,而另一方面,现代社会的负面价值(拜金主义、大众文化)却已日益强烈地被人感受到了。
中国大陆1985年兴起并在随后的两年中达到高潮的“文化热”,如今已被海内外普遍看作是继“五四”以来中国规模最大的一次文化反思运动。这场反思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和影响,它最终又会把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引向哪些维度,目前都还远远不到盖棺论定的时候。不过,从那以来毕竟已经三年过去了,从一定的意义上讲,这场文化反思的最初阶段确实也已经结束。在这样的时候,给已经走过的路留下一个小小的路标,以便使人们能进而思索下一步将走的路,或许是适时且必要的。
这里选编的这本《中国当代文化意识》并不打算也不可能包揽无遗地反映这场文化反思的全貌。同时,与通常的做法不同,它也不打算面面俱到地把所谓各家各派的观点罗列在一起。因为事实上,我们必须承认,严格说来这场文化讨论在理论上迄今尚未产生出多少足可一观的东西(这或许要到九十年代甚至下世纪初才有可能)——在这种过渡性的年代中,在中国知识分子普遍学术准备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所有的一切思考都必然只能是极度“过渡性”,极度不成熟的。因此,重要的不在于这次文化讨论中有哪些“观点”,而是在于这场文化运动下面所流动着的一般“意识”及其所蕴涵着的可能趋向。我的目的,就是想通过这本《中国当代文化意识》来多少反映出这种“意识”及趋向。根据这种考虑,我把全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名为“反叛”,下编则标为“彷徨”。
▲《中国当代文化意识》,香港三联书店,1989
“上编“的目的主要是想通过美术、电影、小说、诗歌、建筑这些最能见出文化情绪和前卫意识的感性文化领域来反映中国大陆的现实文化状况。这些文章大多清晰地勾勒出了“文革”以后特别是近些年来中国思想文化氛围的变化过程及发展路向,从而为我们展现了近年文化讨论的大背景。人们在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近年来的“文化讨论”实际上仍是七十年代末以来对“文革”进行反省的继续和深入,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的“文化讨论”实际上从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社会政治性,更确切地说,它实际上是对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意识形态的“反叛”。但是,应该注意的是,这种文化反思尽管带有强烈的社会政治性,但同时却又恰恰意味着要求超越社会政治性,其原因就在于,人们在思考的过程中日益认识到,几千年来的中国传统文化机制和几十年来的“左”的僵化社会体制实际有一共同的根本弊病,这就是它的强烈的“泛政治化大一统”倾向,亦即要求一切都绝对服从政治,一切都首先从政治的尺度来衡量。因此,在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特别是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看来,对“文革”及其历史根源的批判反省如果仍然仅仅只停留在社会政治批判的层次上,那么这种批判本身就仍然是一种非批判的意识,因为它实际上仍落入旧的藩篱之中而不得其出。根本的问题乃是要彻底打破“泛政治化大一统”本身,使各文化领域逐渐摆脱政治的过分羁绊,真正取得自身的相对独立性。近些年来各文艺领域普遍出现的“非政治化”倾向,“纯文学”、“纯艺术”的倾向,以至于常常被批评为“缺乏社会现实感”等等,实际都是这种意识使然。但这里提出的问题实际并不仅仅限于文学艺术领域,而是牵涉到更为一般的所谓“文化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极其复杂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在今后的文化反思中必将日渐凸显出来,正如它早已是近些年来西方思想界的热门课题(例如福柯的“知识/权力”理论等等)。
我把我自己1985年所写的“八十年代文化讨论的几个问题”一文也收入上编,尽管我自己对该文一直都不满意,但是该文“说传统”部分(曾载《读书》1986年2月号)提出的所谓“继承发扬传统的最强劲手段恰恰就是反传统”这种激进态度,确实可以说几乎是当时青年知识分子们的普遍情绪,大概也是因为如此,海内外一些论者都把该文看成是“一派”的代表之一(一种流行的分法认为李泽厚的“西体中用”说为一派,杜维明等海外“新儒学”为一派,我和其他一些人则为“反传统”的一派,这种分法其实意义不大,而且易使问题简单化)。但是应该指出,尽管“反传统”确实是当时青年一代的基本态度,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主张把传统文化统统扔光,更不意味着我们这代人对中国传统文化就没有任何感情瓜葛。相反,正如从我几乎同时所写的“八十年代中国文化五题”(载《瞭望·海外版》1986年1月号)这篇短文中即可看出的,我们实际上在当时就相当清醒地意识到,“伦理本位的文化(传统文化)必然是更富人情味的,知识本位的文化(现代文化)则必须削弱人情味……也因此,现代人几乎必然怀有一种若有所失的失落感”。换言之,我们对于传统文化,不但有否定的、批判的一面,同时也有肯定的、留恋的一面,同样,对于“现代社会”,我们不仅有向往、渴求的一面,同时也有一种深深的疑虑和不安之感。我以为,这种复杂难言的、常常是自相矛盾的感受将会长期地困扰着我们,并将迫使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至少是其中部分人)在今后不得不采取一种“两面作战”的态度:不但对传统文化持批判的态度,而且对现代社会也始终保持一种审视的、批判的眼光。如何处理好这两方面的关系在我看来正是今后文化反思的中心任务,今后相当时期内中国文化的发展多半就处于这种犬牙交错的复杂格局之中。
上编 反叛
八十年代文化讨论的几个问题(甘阳)
当代中国美术运动(高名潞)
1985年以来中国建筑文化思潮纪实(王明贤)
论新时期小说的基本主题(季红真)
中国新电影:从意识形态的观点看(姚晓濛)
中国现代主义诗歌与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对话)(杨炼 [美]弗·杰姆逊)
在学术与政治间徘徊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许纪霖)
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一个文化的检讨(梁治平)
我对“下编”材料的取舍也正是从上述考虑出发的。“下编”力图着重反映出近年来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对现当代西方文化的研究和思考。这里应该首先指出,在通常情况下,人们往往习惯于把“中国的文化讨论”首先看成是对“中国文化”的讨论;由此,在选编有关文化讨论的文集时,自然就十分顺理成章地仅仅只收集那些直接讨论中国文化的基本性质、主要特点、价值内涵等等问题的有关言论。这种角度并非不能成立,但我以为太窄。因为,近代以来历次“中国的文化讨论”都并不仅仅只是对“中国文化”的反省和讨论,而且总是同时甚至首先就是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和思考。说到底,没有西方文化的东渐,也就根本没有必要一次又一次地掀起“中国的文化讨论”。因此,在我看来,要想切实地理解和评价“中国的文化讨论”之进展和成果,也就不能仅仅只看它对“中国文化”的反省和讨论有什么进展,同时还应看它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和思考有什么进展。如果说,以往历次“中国的文化讨论”之主要结果是把马克思主义这一西方文化结晶引入了中国,那么八十年代及以后“中国的文化讨论”之根本任务则是双重性的:一方面,深刻地反省并纠正以往在理解西方文化上的种种不足、偏差和错误,把近几十年来被粗暴地拒绝排斥的近代西方文化的基本价值特别是自由、民主、法制重新下大力气引入中国,并使之立地生根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内在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则要深入地思考20世纪以来特别是近几十年来西方文化和学术的发展,以期更深刻地把握现当代西方文化的内在机制和根本矛盾,从而富有远见地思索今后中国文化可能面临的问题。
诚如哈佛著名中国思想史专家史华慈(B.I.Schwartz)教授早在七十年代初就已预言的:一旦中国知识分子从“文革”的噩梦中醒来,重新恢复他们对西方的兴趣时,他们就会发现,今日的西方已不是“五四”人眼中的西方了,因为西方自身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陷入深刻的精神危机和思想危机之中。不消说,这种状况必然会对正在思索中国现代化之路的中国知识分子造成极大的“困惑”,因为它意味着:现代化的进程并不只是一套正面价值的胜利实现,而且同时还伴随着巨大的负面价值。而最大的困惑更在于:至少在西方,这些正面价值与负面价值并不是可以一刀切开的两个东西,而恰恰是有着极为深刻的内在关联的。简单点说,自由、民主、法制这些基本的正面价值实际上都只是在商品化社会中才顺利地建立起来的,但是商品化社会由于瓦解了传统社会而必然造成“神圣感的消失”,从而几乎必然导致人(尤其是敏感的知识分子)的无根感、无意义感,尤其商品化社会几乎无可避免的“商品拜物教”和“物化”现象及其意识以及“大众文化”的泛滥,更使知识分子强烈地感到在现代社会中精神生活的沉沦、价值基础的崩溃。人类在现代社会中所面临的最根本二难困境正在于此。在我看来,近现代以来尤其是本世纪以来西方大思想家的中心关注实际上都是围绕着这个根本困惑而进行的,因此我们对于现当代西方文化的把握必须紧紧抓住这个人类共同面临的中心性大问题即所谓“现代性”(Modernity)的问题,而不在于应用一些“新三论”或“老三论”之类的所谓新方法。本书下编基本上即是想反映出近年来青年知识分子们对“现代性”的困惑之感。所收几篇文章分别论述了马克斯·韦伯、丹尼尔·贝尔、马尔库塞、弗洛姆、本雅明、阿多尔诺、海德格尔、福柯的思想以及欧陆人文学哲学的基本走向,其中心关注都是在于:力图通过研究这些西方当代大思想家对西方近现代文化的反省和检讨,来更全面地把握现当代西方文化的内在机制和根本矛盾,从而也就是间接地在反思中国文化今后的走向。
下编 彷徨
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的思路(苏国勋)
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贝尔的文化运思(赵一凡)
从绝望哲学到圣经哲学——列夫·舍斯托夫的存在哲学(刘小枫)
现代“文人”:波希米亚流浪汉——本雅明的体验与寓言(张旭东)
否定辩证法的冒险和拯救——阿多尔诺论历史与自然(廖世奇)
超越·否定·理性——论马尔库塞批判的社会哲学(赵越胜)
超越“社会内在的伦理”——论弗洛姆的“人道主义伦理学”(孙依依)
走向澄明之境——海德格尔之路(王庆节)
人文科学的批判哲学——福柯和他的话语理论(徐贲)
从“理性的批判”到“文化的批判”(甘阳)
然而,就中国目前的状况言,问题的全部复杂性就在于:一方面,现代社会的正面价值(自由、民主、法制)还远远没有真正落实,而另一方面,现代社会的负面价值(拜金主义、大众文化)却已日益强烈地被人感受到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生存在这夹缝之中,真有无逃于天地之感!我在前面之所以说,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在今后将不得不采取一种“两面作战”的态度,原因也就在此。这里自然就引出了“现代性”问题的另一面:知识分子作为文化和价值的主要创造者、承担者,其自身的终极价值依托究竟应置于何处?换言之,知识分子自身的人格理想和价值认同究竟应该是什么?儒家的路子行不行?道家的路子行不行?儒道互补的路子又怎样?同样,从尼采到今日德里达等后结构主义者的“虚无主义”道路行不行?从狄尔泰到今日伽达默尔等的“诠释学”路子行不行?从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到今日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立场又怎样?从当年阿诺尔德(M.Arnold)到今日贝尔的“文化保守主义”路子又怎样?所有这些问题说到底也就是整个社会的价值重建问题。也就是说,在旧的价值信念、旧的理想追求已被证明是虚幻的以后(这是当年的“红卫兵”、“知识青年”们普遍的痛苦感受),还要不要、能不能建立起新的、真正的价值信念和理想追求。这不但在“文革”后的中国一直是个根本性的大问题,而且在西方也同样是近现代以来特别是近几十年来一直困扰人的大问题。对这一问题的思索,无疑将是一条漫长的、极其艰难的道路。
本书最后以陈来博士的“思想出路的三动向”收尾。因为正如前面所说,这本文集并不是一部“客观的”资料汇编,而是多多少少贯穿着我的某种“主观”思路的。陈来的文章相当客观、平实地介绍并分析了近年来文化反思的几个主要侧面,聊可补充本文集的片面性。
1988年10月于北京
— 八十年代中国文化讨论五题(1986年) —
(一)今日文化讨论有必要首先区分这样几个不同范畴:前现代文化的文化系统(或形态);现代化的文化系统;后现代化的文化系统。
不存在抽象的“中国文化”,只有具体的、历史的中国文化。尽管时下对“五四”颇多议论,但仍必须明确:“五四”以前的中国文化是前现代形态的中国文化;“五四”则开创了中国文化由前现代形态向现代形态转折的历史起点。八十年代中国文化讨论的根本任务,是要决定性地完成这个历史转折,真正建立中国现代文化系统,也就是说,彻底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
今日发达国家许多有识之士较为关心“后现代文化”的问题,这是因为他们早已完成了现代化。但是,八十年代中国文化讨论的主题,却不应是“后现代文化”而必须紧扣“现代文化”。原因十分简单:中国还没有实现现代化。这并不是要主张急功近利、毫不考虑“后现代文化”,而是要强调:我们必须大踏步进入现代文化形态,才能真正敞开后现代文化的种种可能,否则,主观上想登高望远,客观上却多半仍只是滑落于“前现代文化”的井底之中。
(二)“前现代文化”与“现代文化”是不同质的范畴,二者是有矛盾、有冲突的,我把这称为“文化的冲突”。任何国家要进入现代化,都不可避免地会遭遇这种冲突。因此,问题不在于否认或回避这种冲突,而在于正确认识这种冲突。
文化讨论的一大障碍是人们习惯于把“前现代化”看成纯粹的贬义辞,而又把“现代化”当作十足的褒义辞,这就难免引起巨大的情感纠纷而阻碍理智分析。其实,这二者的区别并不是优劣高低的价值判断,而是价值中立的社会学分析。现代化并非什么都好,相反,它必然具有自身内在的难题和弊病,前现代化也并非一切都坏,而是往往具有现代化反而有所失落的某些价值。“文化冲突”的深刻性和复杂性就在于此,它并不是“文明与愚昧的冲突”,而恰恰是“文明与文明的冲突”,因而更多地是黑格尔所说那种悲剧性的不可解决的历史二律背反冲突。建立现代文化系统的全部困难正在于此。
(三)前现代文化与现代文化之所以矛盾冲突,是因为从前现代社会到现代社会的社会变迁中,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导致社会的价值取向发生根本变化,从而必然造成文化系统的重大变迁(文化的核心在于一套价值标准)。社会学分析表明,这种社会结构变化(社会学所谓“结构分析”)的最基本表现是,在现代化过程中,家庭与人的各种社会活动(经济的、政治的等等)日益分离了开来;由此直接导致人际关系的重大变化:前现代社会的人际关系是以所谓“第一级关系”(自然血缘关系、亲属关系,即儒家所谓“亲亲尊尊”)为基础;现代化社会人际关系则以所谓“第二级关系”(工作关系、法律关系)为基础(韦伯把“职业”概念作为核心概念,实际正是突出了这点)。这种变化极为深刻的导致了社会价值标准的重大变化。从上面已可看出,前现代社会的基本结构是以伦理关系(在中国即是“五伦”)为根基的,因此其价值标准也就必然首先是一种伦理标准(在中国是以“孝”为核心的一套“礼”),这样,只要时其文化系统也就主要是一种伦理系统(以修身为本即可治国平天下)。但是,现代化社会的基本结构则是以职业分工关系为根基的,因此其价值标准也首先是一种职业能力标准(能否胜任某项工作),其文化系统则主要是一种知识系统(所谓“知识就是力量”),这种知识系统并非只是自然知识,而且是社会知识系统尤其是法律知识系统。
可以说,前现代文化是伦理本位的,现代文化则是知识本位的,所谓从前现代文化转向现代文化,实际即是要从伦理本位的文化系统转到知识本位的文化系统。这在实践上表现为从人治(圣人治国)转向法治(专家治国),在理论上则表现为从人生哲学转向知识分析。近代西方哲学以“知识论转向”为标志,正是这种“文化转向”的最深刻的反映。康德完成这种转向后又力主“扬弃知识为信仰留地盘”,则是这种“文化冲突”(二律背反)的最高哲学表述。
伦理本位的文化必然是更富人情味的,知识本位的文化则必须削弱人情味,著名的帕森斯模式变量(社会学一般以此作为划分现代与前现代的标准)即说明了这种矛盾。也因此,现代人几乎必然怀有一种若有所失的失落感。文化冲突的悲剧意味即在于此。换言之,现代化必然要求付出代价,而且是很高的代价。
(四)中国是前现代文化最发达的国家,尤其是儒家那种“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伟大伦理政治,“必也使无讼乎”的美好人治理想。“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的浓厚人情味,堪称为世界上最完善、最成功的伦理系统,也确足以使中外学子一唱三叹,难以忘怀。然而,所有这些,恰恰又必然使中国成为建立现代文化系统最艰难的国家,因为中国前现代文化系统中这些最优秀、最有价值的东西恰恰是与一个现代文化系统两相牴牾、直接冲突的。这对于中国学人来说是极其痛苦的现实,但是,在这痛苦中正孕育着中国文化新的伟大、新的光荣!
(五)“后现代文化”或许是审美本位的?
▲《哲学研究》1986年第5期
本文最初刊于《瞭望》周刊(海外版)1986年2月24日,第8期第36-37页〔已收入《古今中西之争》(甘阳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后又刊于《哲学研究》1986年 第5期第75-76页。现发布的文字悉依《哲学研究》。
![]()
【“文化:中国与世界”三十年 系列专题】
— END —
欢迎关注三联学术通讯
微信公众号:sdx_bulletin
▼ 点击图片,阅读近期专题
----
ID:sanlianshutong
▲长按二维码即可订阅
----
▲和友人交流,点击右上角分享到朋友圈
▲回复好文,阅读更多专题文章
▲回复听课,了解书店里的大学公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