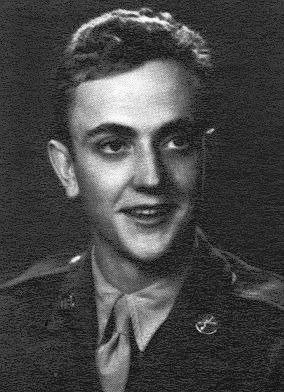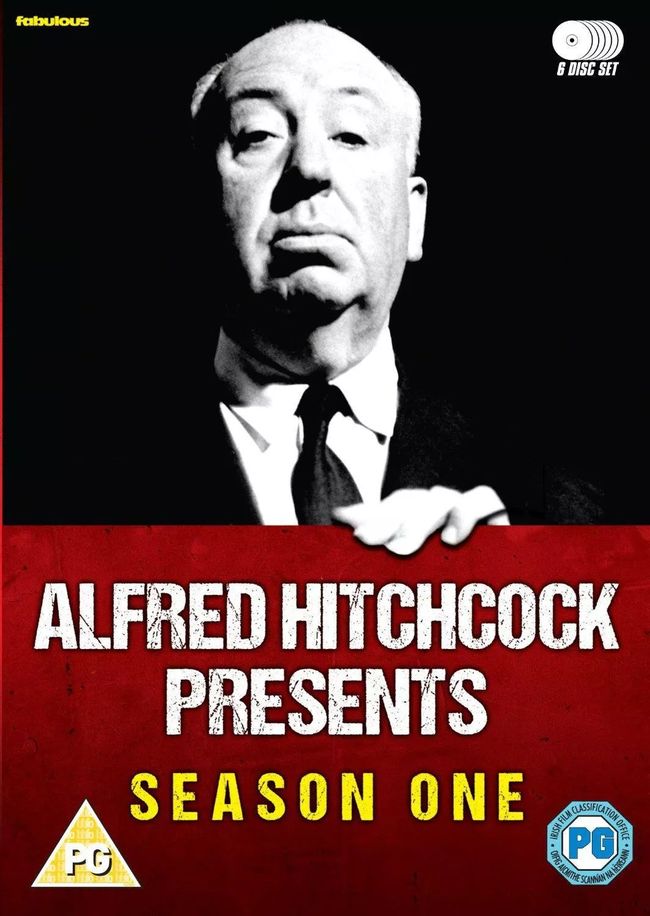“在夹板一样的年代里,写作者很容易成为文学孤儿”
先是在北影学剧本写作,之后学的是德语,然后是比较文学,再到艺术史和艺术商业,杨好的求学路径在外人看来有些不明所以,但对她来说,“在创造力层面上,这些分明属于一个领域。”“有的学习经历更多是祛魅,祛除那种‘aura光晕’,有时候这样的光晕会晃得写作者无从下笔,最终是要靠自己来克服。”
2019年,这些同一领域的给养已经汇聚成了一本《黑色小说》,供我们窥探这场大迁徙中那个隐身的杨好:
“叫黑色小说多少是对‘黑色电影’的致敬,我在电影学院的毕业论文和毕业大剧本都是黑色电影。”
“我面临的一个真实困境就是,在国内的时候就开始通过西方文学、电影和思潮去窥视西方,但等真到了西方后,那种窥视会让你在日常生活里反观自己的中国身份。这时候,异域和原乡可能不再是一对反义词了。”
“当时我并不是抱着想要从事艺术的目的去学的这两个专业。我就像一个偷窥者一样观察着这个领域。艺术领域里的动力和人们太迷人了,透过这个领域能看到世界上所有的欲望和幻灭。”
在《黑色小说》这本处女作中,M是一个有志于文学却才华不足的作家,W是一个有点精神洁癖的学艺术的姑娘,两者互为镜像,又可以明显看到作者本人的经验。在杨好看来,W其实是M另一个极端的自我,W也完全可以用作者的故事来讲自己的处境,“小说就是真真假假的艺术,生活和虚构的边界就是显现自我和隐藏自我的边界”。而文学对她来说,“依然充满了极私人的救赎意味”。
“黑色小说” 是对“黑色电影”的致敬,
充满怀疑和心理危机
文学奖:怎么理解反复出现的詹姆斯·汉密尔顿公爵 ,这样一个贯穿性的“幽灵”是如何找到的?
杨好:这个回答得特别俗,但想了想,确实如此也没有更准确的表达了——是他找到了我而不是我找到了他。可以说,先有了汉密尔顿公爵才有了《黑色小说》,他是我真实生活中一个毕业论文的主人公,那段研究经历确实涉及到十七世纪的书信和公爵的家族,整个过程恍惚又动人,当时就想,把他只放在论文里太可惜了,他是一个很好的小说主人公。
文学奖:书中充满大量的心理活动,两个人物的心理轨迹是如何建构起来的?这些心理描写从一开始的主题色就是“黑色”吗?为什么这本书要叫“黑色小说”?
杨好:叫 “黑色小说” 多少是对“黑色电影”的致敬。我在电影学院的毕业论文和毕业大剧本都是黑色电影,现在这个阶段还没有过去,这个类型依然让我动心,要下手去写。其实“黑色”更多不是颜色上的黑,而是一种类型,这类故事充满怀疑和心理危机。在《黑色小说》里,我实验着去掉所有剧情化的悬念,让这些因素全部蒸馏提纯,看看得到什么化学残余。这也是一个不典型黑色的“黑色小说”。
文学奖:本书开篇的“读者须知”,“这是一本没有真正顺序的小说”,读者可以从头到尾阅读,也可以随意翻开某个章节进行阅读,这个设定是创作初就设定好的吗?你认为这种结构和叙事策略是必要的吗?你在结构和叙事上的追求是什么?
杨好:是必要的,文学总是不能一成不变吧,得有大胆实验。《黑色小说》想打碎的是一个线性时间,这本书的结构其实是被切割的瞬间,以书本的形式呈现一个这样蒙太奇镜像的故事,提示M和W是对比来阅读的,但是很有遗憾的是排版和目录篇章的整体编辑没有和“读者须知”匹配起来,显得目前的“读者须知”有点儿跳。不得不说,文学出版在创造力的野心上确实不似电影和话剧,但有点儿遗憾总是好的吧,全是经验。
文学奖:你在后记里写道“一部文学作品是有他们自己的生命的,它们会随着不同人的阅读而滋生蔓延的欲望。”那么,你作为它的创造者,同时现在也可以说是旁观者了,反复审视这部《黑色小说》,它在你心中,又“滋生”出什么样崭新的“欲望”?
杨好:一个故事写完了,你们之间的直接纠葛就结束了,余下的就是故事自身能够荡起的回声大小了,就像抛石头打水花一样,石头的形状和重量决定了水花的大小。在你开始动笔的时候,故事里的人物他们自己也有了命运走向,就像是木头姑娘一样自己活了过来。《黑色小说》是一个口口都开放的故事,不同的读者会用自己的方式去解读人物的生命线,这其中就是永无止境的想象的欲望。
异域和原乡不再是反义词,
写作者很容易成为文学孤儿
文学奖:西川说“这部小说可以说是相当国际范儿的”,因为你个人的海外经历和多元化视角,促使对“文学的理解可能更偏向一个国际公约数”,但同时,“这个‘国际’是西方的‘国际’”,你怎么理解这句话?作为你的文学处女作,在写作空间上,对异域写作的主动寻求,而未搁浅于原乡,是主动选择还是本能上的自觉?你是如何考量的?
杨好:我想没有人在写作的时候会不断提醒自己“国际化”这个说法吧,那样的话出来的东西肯定特别慷慨激昂。西川老师说的这个“西方”可能更多是文化意义上的。我面临的一个真实困境就是在国内的时候就开始通过西方文学、电影和思潮去窥视西方,这时候你也没什么感觉,觉得这就是文学和电影,但等真到了西方后,那种窥视会让你在日常生活里反观自己的中国身份,一方面你会在民族自尊心上时刻紧绷,恨不得展示一个血缘上的中国身份;另一方面会迷失,迷失在文化的折射中,各种陌生和熟悉混杂。
这时候,异域和原乡可能不再是一对反义词了。北京、苏格兰和伦敦可能都有粘连我生活状态的地方,但它们都有深不见底的故事会时不时斩断这种连接。《黑色小说》需要一个悬浮的空间,从根本上来说,还是隐藏的汉密尔顿的所在决定了故事的发生地。虽然我曾经也像M和W一样在伦敦过过一段时间很混账的闲逛生活,当时的真空对我来说完全是一个祛魅的过程。我有了机会重新审视那些结结实实魅惑过我的东西比如文学艺术哲学,比如历史高尚光荣等等等等。所以伦敦在《黑色小说》里象征着一个祛魅之地。但不可否认的是,写作者就会很容易在其中成为一个文学孤儿了。
文学奖:读的时候,会想起库切的《青春》,也会想起加缪的《局外人》,但人物的异乡感是不同的,库切是从殖民地来到宗主国时的流离感,加缪是存在主义式的荒诞疏离。在异乡人的整个文学脉络里,你觉得哪些作为年轻写作者的现代性经验是哪些?
杨好:或者换一个角度来说,“异乡”的文学脉络不是自觉形成的,而是不知不觉中被阅读者靠拢起来的,异乡可以是地理上的、心理上的和国境线上的,我们很容易就能辨别出这个词语。库切和加缪都是我非常喜爱的作家,他们是在城市欲望里孤僻着的人。我们处在一个夹板一样的年代,比上或比下,既不能无所顾忌又不能开天辟地,我们这代写作者好像越来越返古和保守了,这也是新的状态。我们生活的时代很膨胀也很日常,虽然这些都将是年轻写作者的财富。
在文学上我们都有很多祖先,
没有一种写作没有来历
文学奖:不少报道里都提及了你的“文二代”身份,而且如此之多的当代文坛先驱,都来为本书加持,这会对你造成压力或者困扰吗?
杨好:这个说法总要来的,我坦然面对。一直不觉得这是个“身份”,所以既不需要贴上也不需要摘下,文学的困扰和兴奋只来自于文学本身,要是这么在乎标签,就不要写作了。如果这是一个来自文学定义上对我的批判,我乐于正视这种批判,时间会让这个说法成为继续写下去的某种激励。说到先驱的推荐(“加持”这个词也太金光闪闪了,这本书没那么法力无边),他们也为很多新人作序和推荐,在文学上面,他们是很无私的,一代代的新人都是在推荐、扶持和批评中成长起来的。
文学奖:你在后记里写“在之前10年的时间里,除了爸爸之外,我几乎不和人谈论文学”,“别相信活着的人写的文字”,这是父亲告诫W的话,那么你和父亲的文学谈话,对你最具启示意义的有哪些?书中的M“从骨子里反感子承父业,包括承袭父亲的稳定阶级。”这是你的某种内心写照吗?如何看待父辈的书写对你的影响?
你是如何向前辈们,比如自己的父亲、李敬泽、西川等介绍自己的小说处女作的?
杨好:我不能回避和选择的事情是,父亲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我的文学老师,虽然有些时候会觉得和爸爸在一起大多数时间都是聊文学有点儿奇怪,但关于文学的聊天总是特别真诚。但这也使得我对书斋的环境既顺从又排斥。谁没有一点儿对父辈兼而有之的顺应和反抗呢?
书中的M和W既是我也不是我,他们的反抗一个微弱一个极端,其实都没有真正去处理和上一辈的关系,他们都是搁置着过生活。其实在文学上我们都是拥有很多祖先的,没有一种写作是没有来历的。父辈,祖父辈,祖宗辈,他们都会对一代代的写作者产生影响,逼得我们想要学习或是叛逆。文字的虚构有时会具有幽灵一样的魔力,书房里面装满了祖先们的声音,这恰恰是新的写作者需要面对的问题。
小说不是用来介绍的吧,是用来阅读的,面对谁也都是这样的。很感谢这些前辈们能抽出时间读完我的小说,我知道敬泽老师每年都会面对大量新的作品给出意见,能读完一个新人新作,而且准确给出批评还是很宝贵的。
文学奖:你会如何向读者介绍《黑色小说》?你自己会怎么评价《黑色小说》?
杨好:介绍特别一言难尽,尤其是作者本人的介绍。这不是必读书,有兴趣的看看。
文学奖:创作这样一部看起来很难与中国本土性相关联的小说,是否有对某种文学传统的反抗?是否与你所说的“对文学与写作都有一种故意压制的强迫”一脉相承?
杨好:本土性?如何定义才叫本土性?不能说因为写了在本国境内发生的事情其实内核是马尔克斯就叫本土性,也不能说因为发生地不在本国境内就不叫本土性。面对在异乡的本土生活这也是一个类型,我不觉得这个小说不本土。
文学传统就在那儿,你不可能视而不见,但反抗和“本土”无关,那是文学本身的新陈代谢。有时候在动笔之前想了太多或是读了太多都会形成一定的障碍,你会想——唉呀,冯内古特把这个都说尽了;《唐传奇》里就已经讲了这件事儿了……创作难免有感山穷水尽的时候,这时候的绝处逢生就是强迫后的张力。
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1922—2007),美国黑色幽默作家,美国黑色幽默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
小说是真真假假的艺术,
生活和虚构的边界是显现和隐藏自我的边界
文学奖:“文学对我来说,依然充满了极私人的救赎意味”,为什么是“依然”?这种“救赎”具体是指什么?文学对你有功能性吗?你怎么理解写作和文学的价值?
杨好:不光是文学,所有的创作,电影也好,小说也好,艺术也好音乐也好,都是既私人又公共的。写作的过程是很私人的,只能由一个人来写,但是当写作以书的形式所呈现,这就不得不成了一个产品,一个团队工作的总和结果。写作比较吃亏的是所有的群体工作是隐在后面的,不像电影,一开始观众的预设就是teamwork,但是观众在看一本书的时候会把书最后呈现的形式(包括腰封、定价、排版、宣发、别字校对等等)都指向作者一人,很多事情写作者也是无法掌控的,因为任何群体工作都有合拍不合拍一说,不可能百分百精准,何况写作者往往不会是一个好导演。但是当一个作品出来的时候,其实写作者已经默许了所有的公共形式,不管怎样你得认。
“救赎”永远是私人的,甚至很微弱,所以这句话我只能偷偷写在《黑色小说》的后记部分,我承认这有点儿像是给自己凿一个任性的树洞,在公共状态里留一个相对私人的空间。
文学奖:你的文学趣味和审美是怎样的?想请你谈谈那些影响了你的创作的人或作品,不一定局限在文学、艺术。
杨好:我是一个挺博爱的人,对。文学、艺术、电影、音乐还有游戏,这些项目(不太喜欢领域这个词,在创造力层面上,这些分明属于一个领域)中我都会标记一些自己的路标,时不时折返回来看看,比如比利·怀尔德,丢勒,卡夫卡,梅西安和暴雪公司1996年版的《暗黑破坏神》。
文学艺术电影都说挺多了,对我个人而言,当年的pc游戏和ps时代的RPG游戏确实都给我留下了挺震撼的审美烙印的。
文学奖:在M的部分你写道,“如果一个人开始放弃写作的底线,那他就永远无法开始写作了。写作的底线就是不做记录,既不记录自己,也不记录别人。”这也许是你为M设定的文学观,那么,你作为写作者的文学观是什么?
杨好:我不设定文学观。要是刚刚开始写作就给自己设立文学观我觉得挺主题先行的。文学观不能唰地立起来,是个经验积累的过程。
文学奖:女主W在苏格兰一所古老的大学学习艺术史,也会讲德语,也是一样的论文议题,这和你自身的经历很相似,而且在W的部分,能明显感觉比男主M部分,有着更多且更明确的心理走位和观念,你觉得你作为女性写作者,在写作中有成功隐藏自我和自我经验吗?这个边界是什么?
杨好:对于“女性写作者”这个说法我既不能辩驳也不能接受,承认或否认都有问题。对了,想到之前有个问题是说“文学观”,我不愿意主题先行,但放在这里我想说,“写作者”对我来说是一个中性的词。“自我”首先是作为人的自我,我不太倾向先把自己置于一个女性的地位去说自我,就像男性写作者不会强调自己是一个男性的写作者一样。小说就是真真假假的艺术,W可以用我的故事来讲W的处境,我们也可以窥探《青春》里有多少真实的库切或者十四行诗里哪句暴露了莎士比亚的真正恋人。别女性写作者了,作为写作者没有必要刻意隐藏或是暴露自己,交给故事去决定。生活和虚构的边界就是显现自我和隐藏自我的边界,我认为掌握这个边界最好的老师就是希区柯克。
直面“虚荣”的写作有时候挺危险的
文学奖:你反复写到M没有写作的天分,要么是M清晰的自我认知,要么是你以创作者视角的侧写,为什么要这样处理一个对文学执著以求却又有先天文学缺陷的人物?
杨好:M这个人物是一个非英雄的主人公,他既不是时代的英雄也不是自我的英雄。他是一个典型的希望过着作家式的生活或者说希望通过作家式的生活而博得一个作家称号的人,我恰恰认为他是一个很典型和具有吸引力的人物。
文学奖:M和W是互为嵌套式的镜像投射,都“对贵族生活充满向往,异国上流对他们同样都充满吸引力,这种“虚荣”的设置动机是什么?同时写到了“贵族,显然是所有异乡人和英国中产阶级一厢情愿的设想,他们渴望一种理所应当的社会秩序和生活标准,他们以为贵族的生活满足了他们对所有‘优雅’‘品位’‘高贵’的想象。”好像作者偶尔也会跳出来讽刺这种“虚荣”,这是有意为之的吗?你自己是怎么理解这种“虚荣”,以及对“贵族”的想象的?你会怎么理解阶级和身份?
杨好:直面“虚荣”的写作有时候挺危险的,好多读者在看到一堆品牌名字或者生活方式的时候会只记住了它们,而忽视了它们旁边的情节。这种“虚荣”的描述之前本雅明在“拱廊计划”的写作里有过示例,在当代生活中,购物的展开和对贵族生活方式的谈论其实反而一出国特别明显。伦敦所有昂贵下午茶的订位基本都被亚洲和美国游客预定了,这是非常有趣的现象,在北京不是,在苏格兰不是,只有在伦敦。
我当然也没那么高尚,我也曾挤破头去订下午茶,刻意带上在北京不会穿的裙子去吃一个裘德·洛光顾的餐厅,后来才发现可能有爵位的英国贵族好多在玩儿别的,所谓“高贵”是旁观者的定义,是现代素质教育的有趣产物。M和W身处其中,他们按照人物逻辑去走,而作者按照作者逻辑去走,同时要和两面镜子都纠缠一下。
窥探艺术是为了祛除看到的欲望和幻灭
文学奖:你在书中最后,让W发出一句“去他妈的艺术”,从而“释放了她近乎20年生命的重量”,这种对艺术最终幻灭的“秘密”,和你自身研习艺术史和艺术收藏的经验有什么关系?
杨好:W的设定是一个有点精神洁癖的姑娘,她其实是M另一个极端的自我,这样的姑娘完全也过着“艺术化”的生活,但并不为成为艺术家而为了艺术本身,我在书里说的“艺术”其实更多是“美”的想像,不光是艺术这个行当。前面其实也有提过,所有的学习经历在我看来更多是祛魅,祛除那种“aura光晕”,有时候这样的光晕会晃得写作者无从下笔,最终是要靠自己来克服。
必须坦诚的是,当时我并不是抱着想要从事艺术的目的去学的这两个专业。现在想来,我就像一个偷窥者一样观察着这个领域。艺术领域里的动力和人们太迷人了,透过这个领域能看到世界上所有的欲望和幻灭。你想,世界上只有这一个行当的收入和微软相当,从业人数却只有微软的几十分之一;只有这一个行当的交易有着硬通货的价格却又不是黄金钻石,这其中不是艺术行当了,这都是人性的有趣之处呀!
文学奖:“世俗这件事情让W觉得恶心,这似乎是在她身边终生与她同生共长的蛆虫。她受不了俗气的脸和俗气的活法。”“永恒是属于死亡的,正因为如此,永恒才能体面地躲避世俗的谬语。”你曾经几度更改专业,后来学的艺术品收藏,可以视作“永恒”与“世俗”的结合,你怎么理解这两个概念?在你看来,艺术、文学与“世俗”的关系是怎样的?
杨好:它们是一种永动关系,你追我赶同生共长,谁也离不开谁,却彼此厌恶。文学和艺术在我看来就是既不神圣,也不世俗。
文学奖:你的下一部写作计划是怎样的?你对文学最大的追求或者说你心中的理想小说是什么样的?
杨好:能用写作完成写作就很好了。理想小说和所有的修正只能通过写作来接近。
【相关文章】
2019年宝珀理想国文学奖
文学,期待意外 | 2019年第二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初名单公布
2019第二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决选名单
路内:作家就是从一个荒凉星球来到人世间, 把那个地方的故事带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