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美国电影大师,知道他名字的人太少了
作者:Dave Kehr
译者:陈思航
校对:Issac
来源:Moving Image Source

在大多数的标准电影史中,拉乌尔·沃尔什只能获得一句旁注,但他理应获得更多的位置。

拉乌尔·沃尔什
沃尔什一生一共制作了超过一百部电影,他的从影生涯开始于青年时代与大卫·格里菲斯的合作(他在《一个国家的诞生》里扮演了约翰·威尔克斯·布斯),结束于六十年代早期在华纳兄弟的工作。他制作了好莱坞的一些最具活力、最为个性化、技术最精湛的作品。

《一个国家的诞生》
然而,除了五十年代在巴黎结成的一个又小又奇怪的异端团体之外,沃尔什从未受到过评论家的拥护。他的名字总是在霍克斯和福特的旁边被提及,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的地位似乎从来没有得到过保证。人们认为他的作品是重要的,这种看法是如此广泛,又如此正确,但却很少有人运用聪明才智来剖析他的影片——我实在很难想到一个处境与他相似的导演。
或许沃尔什的部分问题在于,他的风格与价值是如此紧密地与他的类型——动作冒险——结合在一起,以至于我们很难辨明,类型特征与导演贡献之间存在的界限在哪里。

拉乌尔·沃尔什
不过,安德鲁·萨里斯在《美国电影》中为沃尔什撰写了一节简短的论述,他指出,沃尔什的主角有一些独有的特征:
他们一般有着情感上的脆弱性,无法展露自己的痛苦、依赖与不安——而这只是冰山一角罢了。沃尔什的主角,要比福特和霍克斯的主角更频繁地处于私人危机之中。福特的主角可以通过他们的朋友和专业技能来定义自己,但沃尔什的主角则没有什么可依靠的。他是一张白纸,没有过去,也没有什么要逃避的东西。
《歼匪喋血战》
他的任务——可以采取多种形式,譬如一次探索或一件任务,一次生意上的成功,或是树立某种声誉——是要发明他自己。他可能很脆弱,但这是因为他身上有某种粗粝、稚嫩、无礼的东西。他的性格仍然处于动荡之中,仍然可以被改变、被影响。
沃尔什以他的速度而闻名:《歼匪喋血战》最初的那段蒙太奇,或许是电影史上速度最快、最为有力的开场,它将詹姆斯·卡格尼作为病态劫匪的生涯,缩减到了一个凌厉而狂乱的火车抢劫段落中。

《歼匪喋血战》
沃尔什的许多影片都会像这样直接切入主题,他会熟练地使用纷乱的动作,达成这种曝露的效果。他的许多主角也拥有这种魔鬼般的速度,他们似乎常常受到未知邪恶力量的驱使——有些人会像《歼匪喋血战》中的科迪·贾瑞特那样,去超越某种边界;另一些人会像《绅士吉姆》中的詹姆斯·J·科贝特那样,去获取个人的成功或声誉。

《绅士吉姆》
在沃尔什的影片中,那种美式的、关乎成功与流动的神话,可以找到一种心理层面、乃至存在层面的共鸣:沃尔什的主角在成功的同时,也达成了自我的实现。
如果说沃尔什的影片从核心人物的内在动力出发,找到了自身的节奏与活力,那么它们也可以让主角决定影片的形态与结构。
总体上来说,沃尔什被两种组织形式所吸引:「……的兴衰」式的传记性情节(譬如《私枭血》、《马革裹尸》、《绅士吉姆》、《狮子上街》),以及一种更松散、更为轶事化的结构,我们可能可以将它们称为「地图电影」——这类影片以地图上的一个大「X」开始,沿着逐渐前行的虚线,追踪着角色从A点行进到B点的轨迹。
《狮子上街》
沃尔什的地图电影——其中最好的包括《反攻缅甸》、《落基山分水岭》、《军鼓》和《萨斯喀彻温》——既不是流浪汉式的冒险,也不是英雄般的征服。
通常情况下——正像《反攻缅甸》和《军鼓》的后半部分那样——影片的角色处于一种撤退的状态,他们躲避着一些敌人,穿越充满敌意的、原始的领域。
《反攻缅甸》
从本质上来说,他们面对的困难,与那些传记片主角在社会语境下面临的挑战是一样的:他们都要向世界施加一种意志,都要征服特定的城市或自然环境。
传记片的主角穿越的是时间,而地图电影的主角穿越的则是空间,但这两者的运作规律是相似的——不是关乎惩罚或净化,而是关乎学习与试探。角色们会从这种对抗中汲取一些东西,它们的力量与身份感会不断增强。
对于福特来说,终极的关注点是社会,而对霍克斯来说则是集体。但沃尔什唯一的关注点是个体——他的经历、他的成长与他的进化。(此处的阳性代词并不总是适用,沃尔什最引人注目的主角之一就是一位女性:《玛米·斯托弗的反抗》中简·拉塞尔饰演的角色。)
《玛米·斯托弗的反抗》
沃尔什那些散漫的、离题性的情节,在主角身边营造了一种自由的氛围,仿佛主角的行动本身就能决定电影的方向。
沃尔什的那些最薄弱的影片——例如《中东谍影》——基本都有着严谨的、精心构建的情节,他似乎并不擅长处理复杂的叙事线索,也难以描摹那种有着局限性的、无法掌控自己命运的主角。
《中东谍影》
而沃尔什在三十年代为派拉蒙制作的一系列快节奏音乐剧,可以算作是他最具娱乐性的(尽管远非他最好的)一些影片,它们包括《前往好莱坞》、《夜逢八点》、《艺术家和模特》和《大学秋千》,这些作品基本都被设计成当红娱乐明星的展示柜。如果它们中存在情节的话,那么这些情节只会被忽略。
《前往好莱坞》
这些作品呈现为一系列令人振奋的、自由而轻松的歌曲唱段,以及一些喜剧段落和角色们华丽出场的场景。他在统御这一切的时候,使用了非常愉快的、极富开放性的方式。沃尔什可以自如地用个性与精神性来操控自己的节奏,而不是使用情节或结构。
只有像他这样的导演,才能以一种统一的方式来呈现这些影片:它们是自由而非脆弱的,是开放而非笨拙的。
但是,沃尔什对自由的赞颂也就到此为止了:在他的影片里也存在着阴暗面,以及一种无序的质感,许多他最好的影片都着力于寻找界限——当主角的内在动力转向毁灭与疯狂的时候,自由会变成一种混乱的状态。
在这类影片中,最为突出的是《卡车斗士》。在刚开始的时候,这部影片是一部社会剧,讲述了一位独立卡车司机逐渐成为公司头目的故事。但在中途的时候,它突然转化成一部关于一位女人的法庭情节剧,她谋杀了自己的丈夫,以便为自己的情人扫清道路。
《卡车斗士》
在这部影片中存在着一次转化,我们先是看到了服务于积极目的的个人能量,而后目睹了服务于破坏性目的的性能量。虽然沃尔什没有清晰地为观众呈现转化的过程,但这确实是他的一部最大胆的电影。
沃尔什的大多数早期电影都已经散佚或是无法看到了。我们只能看到少数来自二十年代的作品——《巴格达大盗》、《幸运女士》和《光荣何价》——这些影片基本上都遵循着当时通行的标准风格,依赖于剪辑以及根据画面节奏使用的、大幅度的镜头运动。在三十年代初期,可以看到沃尔什开始探索深焦影像和摇摄镜头(《波威》和《艺人丽影》)。
《波威》
不过,直到临近1939年、他在华纳兄弟开始任职的时候,他的视觉风格才完全成熟起来。他的深度构图得到了拓展,摄影机运动和人物运动之间也开始产生了共鸣。
安德烈·巴赞在探讨现实主义和深焦影像之间的关系时,选择了威廉·惠勒和奥逊·威尔斯作为例子,但沃尔什本来可以成为一个更为合适的案例。惠勒倾向于用深焦影像呈现空旷的、绘画式的构图(线与角的延伸),而威尔斯关注的则是戏剧空间的创造性重构。而沃尔什则致力于将他的人物放置在一个确定的物理世界之中。
这种深焦画面表明,影像世界的延伸已经超出了摄影机的范围,甚至溢到了摄影机背部的空间:整个空间都已经被捕获,不受焦平面或构图的限制。在沃尔什的镜头里,很少会出现那种「背景」感:他几乎总是允许透视线——无论是显性还是隐性——一直延伸到地平线。空间是连贯而坚实的,它们暗示着角色与所处的世界之间存在着某种张力。沃尔什最喜欢的镜头是中远景镜头,画框会卡在角色的腰部和膝盖之间。
《艺人丽影》
尽管从构图上来说,角色们是连贯性空间的一部分,但他们自己与空间的关系似乎有些薄弱。他们很少会稳固地、完整地呈现在画面中,与之相反,他们会摇摆不定地悬挂在不稳定的前景处,而世界就在他们身后。
当沃尔什摇摄的时候,他在指示画框外世界的存在——它存在于单一的、简单的构图之外——但他同样也在延展演员与背景之间的张力,使之处于一种动态之中。
他会跟着主角摇动自己的镜头,赋予演员一种显而易见的力量,让他可以决定构图与视点——我们再一次意识到了那种自由感——但是,他使用的是摇摄镜头而不是跟拍镜头,通过这种方式,他让后景处于一种静止的、稳固的状态之中,使之与演员区分开来。
《私枭血》
在跟拍镜头中,周遭的装饰性元素是与演员一同「移动」的,空间也是流动的,它会随演员的运动而发生变化。
在摇移镜头中,空间会保持其完整性。我们在观照它的时候,总是处于同样的轴心。沃尔什的角色自由地在世界中穿梭,但世界并没有向他们屈服:这成为了一场持续性的挑战,既连绵不绝,又携带着某种间离感。
沃尔什的主角们向世界宣战,并在战斗的过程中定义着自己。在影片的高潮段落、斗争的关键点处,沃尔什常常会将影像推到一个更高的层面:譬如卡格尼和鲍嘉在《私枭血》中的公寓枪战,又如鲍嘉在《夜困摩天岭》中的最后一次违法之举。

《夜困摩天岭》
还有那场最著名的戏,那是卡格尼疯狂的顿悟时刻,他站在那个燃烧的油箱上,它随时会爆炸、将他毁灭,这场戏与所有沃尔什的影片产生了呼应。他喊叫着:「世界之巅,啊!世界之巅!」那是沃尔什式的主角,在最艰难、最危险的关头,仍然维持着短暂的、象征式的统治性姿态。
合作邮箱:[email protected]
微信:hongmomgs
![]()
《小丑》,年度最大泡沫
这种电影已经穷途末路,连李安也救不了,难道他行? 这十三部摄影最完美的电影,足以代表美国电影摄影的历史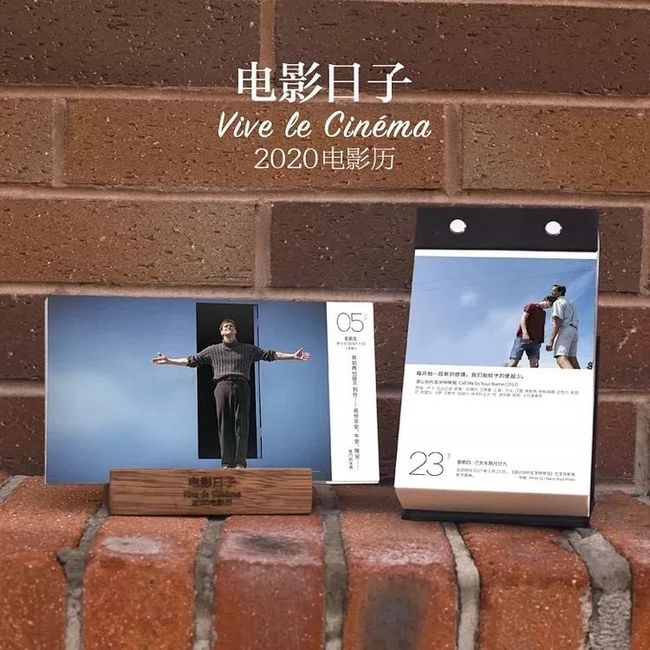
电影日子·2020电影历
双版本预售中
365天 365个电影日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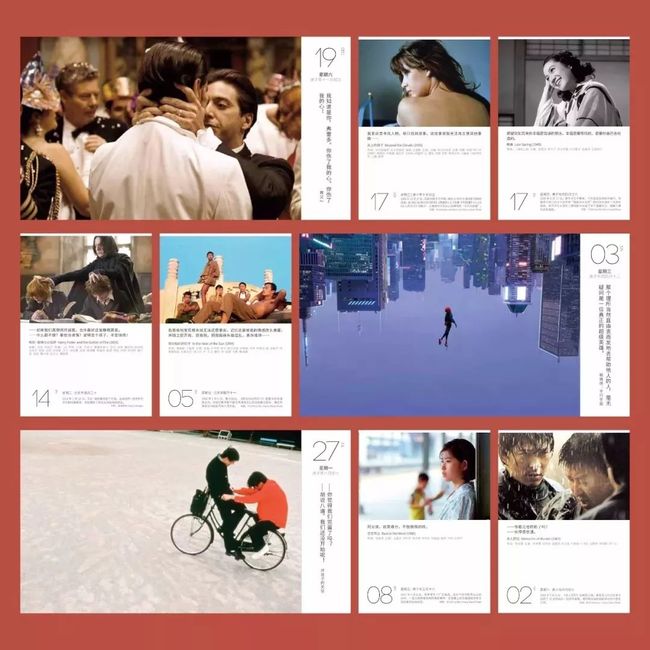
进入虹膜微店购买

长按扫描二维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