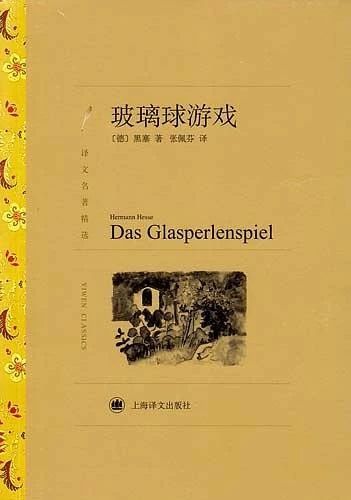文/常书远
自从读过《荒原狼》,赫尔曼·黑塞这个名字就在我的阅读体系中占据了重要位置,被我视为穿越时空的心灵密友与精神导师。很少有哪部小说能让我读出一种“归属感”。我之所以称为归属而不是归宿,是因为黑塞并不给你真正的归宿,恰如研究者指出,黑塞是一个“永远在路上”的人。
赫尔曼·黑塞,德国作家,诗人,194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的作品大多担忧人类的精神危机,其本人摇摆在现实生活和美学世界两个“相对极”之间,一直尝试超越自身背景的文化,于是成为了一个“东方旅行者”。他在晚年最后一部长篇小说《玻璃球游戏》中,这种不断接受内心“召唤”,永远在路上的感觉愈发突出。
精神史诗:与世俗历史相对应
作为黑塞最后一部小说《玻璃球游戏》,因为蕴含黑塞一生对人类思想文化的重大思考,所以并不是一部容易读的书。在我看来,《玻璃球游戏》的阅读难度,在于它是一部精神史诗。虽然小说的要素在这里五脏俱全,但跌宕起伏的情节却是内在于人的精神思想世界,在阅读过程中确实需要耐着性子。然而及至读到尾声,却发现自己已经不知不觉被这本书迷住,尤其读到当伟大的主人公、超凡的玻璃球游戏大师竟死于溺水时,整部小说在我的心里激起了剧烈的震荡,完成了其结构上的“诗性”飞跃。这一结局展现出黑塞在小说艺术处理与精神思想探索上“双重”的不同寻常。这种“双重”性,在我看来正是一个作家攀向思想与艺术高峰的重要标志。
《玻璃球游戏》叙述了在一个未来世界里,一个独立于世俗世界的名叫卡斯塔里的学术王国,综合人类所有的文化思想与艺术,发展出一套符号系统——玻璃球游戏,这是人类所有知识与精神财富的结晶。主人公克乃西特从一介孤儿到被宗教团体收养、选中、培养,凭借出众的才华在这个精英王国中一步步升华,直至顶端,成为玻璃球游戏大师。他天资禀赋,勤于钻研,勇于开拓,不断接受新的召唤,一生可说顺风顺水,每一个节点的选择都是那么的“正确”,简直如上帝的宠儿。克乃西特的一生是智慧与开悟的一生。
然而,当大师响应自己人生最后一次具有反叛与颠覆性的召唤,离开游戏王国,决定奉献世俗世界时,却因为不甘落后自己的学生,在下湖游泳中不幸溺亡。
这种安排的不同寻常在于黑塞制造了一个开放性的死亡事件。主人公一生恢弘的精神思想与死亡的偶然琐屑性形成了强烈反差,整个故事就此戛然而止。就小说艺术而言,出现了一种内在张力,完成了“诗性”飞跃。如果贯穿克乃西特一生的都是抉择“正确”,处处是福,那么大师固然保持了大师的体面,故事构造则不免平凡。但是从另一个层面说,克乃西特的死又使之更像大师,因为有“错误”而更真实,即使是死亡的威胁,也勇于接受召唤,无畏向前,这正是大师的品格。
而这个结局更重要的是其思想上的深邃意蕴。它好像是在试图验证、思考、回应小说中一个经常被提及的主题:历史。
卡斯塔里作为一个独立于世俗世界之外的精神思想王国,信奉精神思想与世俗世界的二元分立,而精神思想是人类真正的价值所在,因而卡斯塔里人不屑于研究世俗世界的历史,甚至认为不是真正的历史。
游戏大师的朋友,一位特立独行、敏感激愤的学员德格拉里乌斯就曾偏激地表达了他对历史的看法:
“人们当然可以用机智的、消遣的、必要时也可以用慷慨激昂的语气阐释历史,谈论历史哲学……自有许多乐趣……但是这一事物本身,人们娱乐的对象——就是所谓历史,却是又丑恶又可怖,同时也是无聊乏味的东西……历史的唯一内容便是人类的自私自利和无限的权力斗争,他们总是过高地评价这类斗争,把它们吹得天花乱坠,实际上追求的只是残酷的、兽性的物质权力……世俗世界的历史不过是无穷无尽一长串无聊乏味的弱肉强食的记录而已。如果把人类真正的历史,也即把没有时间性的精神历史,与老朽愚蠢的权力斗争以及明目张胆地往上爬等相提并论或者试图进行由此及彼的阐释,这种做法本身就是对精神思想的反叛。”(《玻璃球游戏:两个极点》)
应当说,黑塞不一定是要否定以上观念。因为玻璃球游戏王国显然寄托着黑塞的精神理想,但这个理想王国仍然是黑塞预留质疑并想要超越的。这是黑塞与乌托邦思想者的不同,这位漂泊、隐逸的作家就像主人公克乃西特一样“永远在路上”。
游戏大师克乃西特最终“背叛”了培育自己的卡斯塔里王国,放弃其一生来之不易的荣誉与待遇,孤身前往世俗世界,仅为了做一名教授孩童的教师。小说表达了人类的精神历史参与世俗历史建设的重要,通过发生在主人公克乃西特身上的冲突,思考建立精神王国与世俗世界之间桥梁的可能,力求实现二者的超越,进入或许如黑格尔所说的“世界历史”之中。而游戏大师甫一来到世俗世界就死于游泳,至少引发了两种开放性的解读。
一种是消极的解读——说明精神思想世界与世俗世界终不相容。游戏大师不顾最高行政当局的苦苦劝阻,结果他的死亡证明了自己理想的错误。说明没有时间性的精神历史一旦进入有时间的世俗历史中,就只能在时间中宣告终结。
一种是积极的解读——证明要打通精神思想世界与世俗世界是艰难的,是要无惧牺牲的。虽然艰难,却仍然应该去努力实现,这必然会有牺牲。
黑塞钟情于积极的解读,也为消极解读提供了一席之地。这大概是因为黑塞的“双极性”思想,即使对自己钟情的观点也预留质疑的态度。精神思想与世俗世界究竟可否融合,这是一个大问题。
西方视域下的东方魅力实乃西方自身的理想镜像
我们中国人对黑塞的这种双极性思想不会陌生,因为中国哲学或者说东方思想从来都是讲究相对的,认为所有的真理只是某种条件下的正确,可以向其反面转化。黑塞本人也深受中国文化影响,这在《玻璃球游戏》中处处可见。可是中国思想经过西式过滤,化为黑塞的双极性理念却会让我们中国人觉得魅力倍增。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讲相对的时候,无法描述得如黑塞笔下那么激动人心、深邃迷人?经过柏杨所说的几千年酱缸式发酵,我们中国人只要一开口讲相对,为什么总是闪烁着东方式的狡智、圆滑,世故?充满着平庸的折中主义与令人腻味的语言俗套?
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我无法给出确切答案,但我想这与“距离产生美”有关。在以追求绝对真理为主流传统的西方,一个相反的文化精神的嵌入,会因为其异域性导致的神秘性,而产生一种建立在自身反省基础上的超越性解读。前提是这个文明意识到了自身危机,发展进入了瓶颈,故需要一种异质文明的因子作为参照,以实现超越。
因此,当东方文化被部分西方人解读得激动人心,玄妙动人时,其实是注入了西方文化思想自身的需要和想象的,他们无法将这种想象直接作用于自己的文化,故需要一个中介、一个外物来实现。我们中国人若因此而沾沾自喜,那就是文化智慧的问题了。西方人只是利用东方文化这个道具,在自身文化上进行了反省、超越性的想象。这也是为什么《玻璃球游戏》中关于中国式隐居、易经、静坐这些中国元素在黑塞的西方笔触下,会产生别样魅力的原因。事实上主人公克乃西特身上是闪烁着儒者的形象的,比如他的自省、克己、修身,而他那服从内心召唤的快速的行动力,简直俨如心学的门徒!但这样一个有儒者气象的西方人显然与我们熟悉的中国儒者的气质又有很多不同,充满别样的魅力。这是因为这些中国元素经过西式转化,移植到西方人的宗教文化背景中进行演绎时,对我们来说便产生了“距离美”。文明需要交流和对照,需要在一个异域世界中让自己重新容光焕发。一种文化若只沉醉于自身而不可自拔,就会像远古时代内部通婚的部族,迟早衰亡。
所以,正因为西方历经悠久的绝对主义精神道路,才能将相对主义文化阐述得魅力四射、生气勃勃。中国则相反,几千年从来都是相对主义思想鼎盛的国度,故中国人今天若再继续一个劲地谈相对,谈那种庸俗化了的辩证法,散发出的只能是越来越浓重的“酱缸气”。
也因为西方有着“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的思想传统,探索精神思想与世俗生活的融合才会成为一个问题。而在中国文化中,这些从来都是不存在的。中国文化中没有产生过这样的二元性,只有一个世界,就是世俗世界。精神世界也只是接受世俗世界解读的世界。但在西方的视域中,中国文化的这种特征会成为他们的一种理想。只有经历过刻骨铭心的身体与精神的二元对立产生的文化苦痛,才会进一步追求这种理想的超越。而中国人对自己这种文化特征的骄傲自满,是不具备超越性的,与西方人的理解已经大相径庭。
从这一点来说,人类文化交流的价值或许正在于“误读”。唯有“误读”,文化才能新生。在一种文化的内部历史长河中,因阐释、注解产生的有意无意的误读,我们已经可以随处可见,其实质推进了文化的发展。而不同文化之间的“误读”或许对人类更加重要。用那面由自身土壤磨砺出的文化之镜观照大洋彼岸,往往看到的是不一样的对方,本质却是自身的一个理想镜像,引领自身的超越!
更多干货文章,请关注公众号:常书远的文学修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