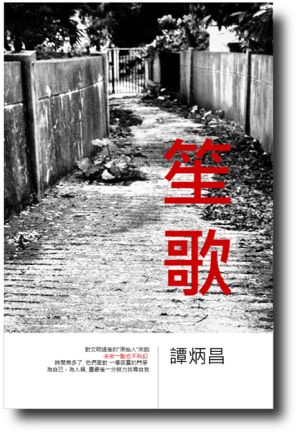出走
宋笙陪老马往浅水湾探老婆回来,看见爸爸心爱的玉麒麟独坐在饭桌中央,下面压着字条。他一口气看了几遍,仍然不大相信内容:“就这样?”
他把字条放回原处,然后开始收拾背包:五条胡萝卜,两个生番茄,两条老爹用鸡油保存的法式炸鸡腿,三个红番薯,几个面饼,一个露营用的小锅,一大瓶水,还有一罐古董豆豉鲮鱼。加件衬衫,短裤,打火机,大毛巾,笔,记事簿,还有本关于狼的书。野狗就是狼,也是人类在蛮荒都市中最有威胁的竞争对手。对它们多一点了解不会错。
他的单车孤零零地停在门口。爸爸的不见了。他背上包,开步便跑。他没有目的地,只想跑,不停地跑,让强健的双腿把自己带走。他不打算去找老爸。经宋焕策划的出走,肯定天衣无缝,要找也不知道从何开始。
不理,先跑!
__________________
他跑得比平常快,体内有股火在推动,双腿像识途老马。今早刚由浅水湾踩车回来,现在又沿路跑步回去。
满脑子都是爸爸的声音。
不要多想,只管活着。不要忘记:适者生存
我自己一个人终老是好事,不是伤心事哦!
这个情势,理智重于一切 。 。 。
老人家的屁股要擦多少年,谁也说不准 。。。特别臭。
万里晴空,连一朵云也没有,蓝得有点儿不真实。宋笙越跑越起劲,除了补充水壶稍停,没有休息片刻。
我们要理性,看清现实。
理性 理性 理性。。。
现实 现实 现实 。 。。
你会希望我快点死去。。。你的心会伤透。。。
痛一辈子。。。
何必呢?
不知不觉,已经跑到浅水湾。
海边有几位老人家在开音乐会。一个满脸长须的老头,精神矍铄,拉着二胡。幽怨的大漠弦声,在他一把年纪的手里竟然活泼起来。歌星是位七十来岁的婆婆。她手扣胸前,一本正经,像个在模仿女高音表演的小女孩,嘹亮的歌声并未在海风和浪涛声前认老。她温馨地望着乐师,沉醉当年。
在那遥远的地方,
有位好姑娘,
每人走过了她的面前都要回头留连的张望 。。。
观众席上的两个老头和一位婆婆,唯一老太太没有打瞌睡。她默默地跟着唱,手打着拍子,但节奏未有跟上。人类在更恶劣的环境中,也懂得找空隙自娱;这方面跟猴子很相似。
老太太边唱边向宋笙招手。遇着平时,他肯定会跟几位老人家聊上半天,唱唱歌,把外面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新闻带给他们。他现在没有这分心情,于是大动作地热情挥手,脚下却毫不热情地继续南奔。想不到平日鬼影不多一只的浅水湾,今天会如此热闹。
到了石澳,他首先参观超市,意外地发现了两罐午餐肉和一罐香肠。这区的富贵人家果然有风范,宁死不吃午餐肉。市区的超市,一倒闭便即时被清仓。连他住的半高档半山区内,平时说话有气无力,中英夹杂的中产街坊,也一夜间露出八国联军的嘴脸,争先闯店,无意识地抢掠。能搬动的,不理合用与否,拿回家再算。但大部分人眼宽肚窄,手快命短,辛辛苦苦夺来的东西,大多成为陪葬品。宋笙无聊的时候,会四处逛空宅,搜刮剩余物资,打发时间,就像以前的人逛商店一样。不过逛空宅是有附带风险的。偶尔碰上了腐烂的屋主在家中发臭,好几天都会失去胃口。
由于没有运输工具,偏远的大型货仓并未遭到大规模洗劫,仍然堆积了不少难降解的现代杂粮。平时养老鼠,必要时还可以应人类之急。
__________________
到了石澳滩,吃过晚餐,宋笙忍不住大哭了一场。
他累得要死,还未哭完没倒下大睡。天未亮便醒了。他平常最怕在黑暗中游泳,今天却想也不想便跳了进了漆黑的大海,拼命往外扒。
别多想,只顾勇往直前。
在黑滑的海水中没有远景,一切就在眼前。宋笙不但不害怕,还觉得被暗无边际的海水包围着很有安全感。手脚一起一落,激起点点磷光。耳边的水声轻漾,把他引入凌波仙境,暂时忘却伤心。他越游越远,直到右脚抽筋才仰卧休息,随波漂荡,把整个人交托给破晓的天空,和几颗留连不去的晨星。
回程时,太阳才在背后缓缓升起。
白昼的沙滩被照得通透死硬,一粒沙也难以遁形,反而没有黑夜中的海水真实。疲乏的脑袋又再迷糊。一生的回忆同时涌现,千丝万缕,混为一片。凌乱的过去互相交织干扰,抵消内容,变成空白。
妈最喜欢沙滩 。 。 。
很久没有想起过妈妈了。她死时宋笙只有十八岁。年少丧亲,比较容易忘记。瘟疫反正要杀人。不是你死便是我亡,亦可能同归于尽。电视不停地报导最新死亡人数,有少许世界杯足球决赛周的气氛。死不去的人为了生存,必须适应,与现实保持距离,尽快忘记。
还是不要想妈妈 。 。 。
但要做到不想,谈何容易?宋笙于是尝试静坐,看书,游泳,希望打灭念头。无奈念头还是东一个西一个地浮现,像沼泽的气泡。
到了黄昏,他终于撑不住了。
他把心门大开,不再设防,一切要来便来,去便去,来了不走也可以。他面对大海,好像舞台上的伤心人,高声问“为何”?为何妈妈要死?为何爸爸要出走?为何命运要他一生寂寞?他越问越伤心,终于忍不住放声嚎啕。他全情投入地哭了不知多久,才有如从大病甦醒,觉得自己很荒诞滑稽,禁不住大笑一番。笑罢望着大海,又再痛哭一轮。
眼泪原来真的可以流干的。宋笙流干眼泪后,意犹未尽,便断断续续地呜咽着。他从未如此哭过,也未见过别人这样哭过。现在无保留地哭了一大场,才知道痛哭的疗效。他的内心本来像淤塞了的下水道,随时有被迫爆的危险。现在经高压通渠,抑屈大减,还有种暴风雨过后的清晰。满目疮痍的背后透露着新希望。
劫后重生的思维比较冷静成熟,充满信心,没有应付不来的事。被压抑了的过去,遗忘了的往事,一幕幕重现眼前。
小时候与父母在芬兰的渡假屋过暑假最温罄。很久没有胆量回忆了。一家人在湖边的桑拿房:妈妈抱着他,爸爸用白桦树枝沾水泼洒火炉上的石头,阵阵热气送着树香扑鼻。幸福就是这么简单 。。。这么脆弱。
他大概五岁吧,坐在爸爸的肩膀上看大坑区的传统中秋火龙。龙身插满香火,烟得他眼睛刺痛,不住流泪。他低头避开烟火,看见爸爸妈妈手拖手相视微笑。他感到莫明其妙的很开心,也笑了。
他一口气跑上山顶。爸爸的晨运之友都在鼓掌。
瘟疫把妈妈杀了。爸爸也失了踪。
他在家里等,十分耐心。他觉得可以等很长的时间,甚至越长越好。只要还在等,一切坏消息尚有待确定。只要还在等,便暂时不须面对相继而来的考验。等,原来也可以是一种逃避。
爸爸现在究竟在哪呢?孤零零一个人,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能够去哪呢?
大滴大滴的眼泪从面额滚下,暖暖的,比刚才的温和,没有哭声,也没有怨忿, 只有默默的伤悲,挂念,祝愿。就这样,宋笙在海边坐了一晚上,看着思潮进进出出。
来吧!你不来,我不能把你释放。
三岁多,父母才让他尝第一口冰淇淋。他打了个巨冷震,差点儿从凳上掉下来,吓得妈妈要死。爸爸一边拍摄录像,一边笑得喘不过气。
他小时候从不游公园。记忆中一次意图闯公园,遇到大批“粉丝”要跟他拍照。 。 。他从未见过妈妈如此凶猛对待陌生人。
零碎的片段,点点滴滴,像一斑几十年不见的老友,陆续出现在爸爸的丧礼。眼泪又流了,但比较温和,不再汹涌。
屁股却痒得要命!
原来过去两天,沙蚤把他咬满了一屁股,他也没有知觉,现在才觉得痕痒难当!
太阳刚升起。真漂亮!真伟大!真了不起!
他吸口气,跳起来为太阳高歌:O Sole Mio . . .
爸爸,你是对的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