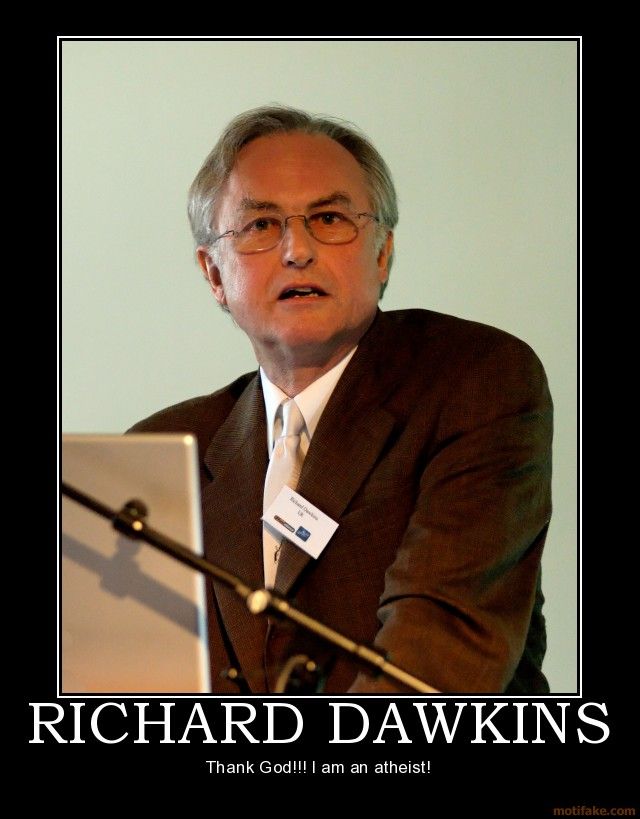- 四、idea环境配置,项目jar包上传nexus
鹏哥哥啊Aaaa
我的轮子intellij-ideajarjava
目录一、基础环境配置1.设置maven的setting.xml2.设置字符编码3.注解生效激活4.编译版本5.FileType过滤6.安装插件lombok二、common的项目结构和pom.xml三、common项目的代码四、上传jar包到nexus一、基础环境配置1.设置maven的setting.xmlE:\mavenSou
- WHAT - React Native 中 Light and Dark mode 深色模式(黑暗模式)机制
文章目录一、Light/DarkMode的原理1.操作系统层2.ReactNative如何获取?3.样式怎么跟着变?二、关键代码示例讲解代码讲解:三、自定义主题四、运行时自动更新五、核心原理一张图组件应用例子最小示例:动态样式按钮的动态样式如何封装一套自定义主题四、如何和ThemeProvider配合?小技巧总结总结一句话这其实是现代移动应用开发中非常常用的功能:自动适配浅色/深色模式(Light
- SaaS 的订阅计费模型设计实战指南:按量、按用户、按功能的架构与实现全解析
SaaS的订阅计费模型设计实战指南:按量、按用户、按功能的架构与实现全解析关键词SaaS计费模型、按量计费、用户数计费、功能模块计费、订阅管理、计费系统架构、账单系统、分级定价、后付费、使用量追踪摘要在企业级SaaS系统架构中,计费模型不仅关系到产品商业化路径的可行性,还直接决定了系统架构、数据采集与账务合规的设计逻辑。本文将深入解析三种主流SaaS订阅计费模式:按量计费(Usage-based)
- 【1.5 漫画TiDB分布式数据库】
漫画TiDB分布式数据库小明:“老王,TiDB作为NewSQL数据库,它是如何既保证ACID又实现水平扩展的?”♂️架构师老王:“TiDB是PingCAP开发的分布式关系数据库,它将传统数据库的ACID特性与NoSQL的扩展性完美结合!让我们深入了解这个’钛’级数据库!”目录TiDB核心架构分布式事务原理SQL兼容性集群部署管理性能优化Java集成实战最佳实践️TiDB核心架构三层架构设计┌─
- Midjourney:AI人工智能图像生成的新方向
AI智能探索者
人工智能midjourney计算机视觉ai
Midjourney:AI人工智能图像生成的新方向关键词:Midjourney、AI图像生成、扩散模型、提示词工程、多模态学习、生成式AI、创意工具摘要:本文将带您走进AI图像生成的前沿领域,以Midjourney为核心,从技术原理到实际应用,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析其背后的“魔法”。我们将通过生活案例、技术拆解和实战演示,揭示Midjourney如何通过扩散模型、提示词工程和多模态学习,重新定义“用
- 初试牛刀 - 使用 Chaos Mesh 进行第一次混沌实验
weixin_42587823
混沌混沌工程
初试牛刀-使用ChaosMesh进行第一次混沌实验第一步:准备实验环境我们的“混沌实验室”需要三个核心组件:一个Kubernetes集群、ChaosMesh平台、以及一个用来做实验的应用。A.安装ChaosMesh我们将使用Helm来安装ChaosMesh,这是官方推荐的最简单的方式。添加ChaosMesh的Helm仓库:helmrepoaddchaos-meshhttps://charts.ch
- 【V15.0 - 交互篇】从“卡顿”到“丝滑”:我用Streamlit三个高级技巧,把AI应用的体验拉满了
在上一篇《告别黑框框:我用Streamlit,3小时给AI穿上了“钢铁侠战衣”》中,我们体验了Streamlit的黑魔法,成功地将我们强大的AI内核,从冰冷的命令行,封装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的Web应用。它能看,能用,看起来已经很酷了。但当我把这个应用的早期版本发给朋友试用时,我收到了三个尖锐的反馈:‘我只是想拖动一下滑块,为什么整个页面都要重新加载一遍,烦死了!’‘你的报告太长了,我只想看结论,能不
- js中批量修改对象属性
首先,有这个对象leta={id:1,name:'张三',age:18,sex:0}需求:同时修改name,id,并添加一个新属性c常规写法:a.id=2;a.name='李四';a.c=1;但这种写法遇到批量就会很麻烦解决方法:方法1:使用Object.assign()Object.assign()常用来拷贝合并对象,相同属性替换,不同属性新增写法:a=Object.assign(a,{id:2
- linux/ubuntu日志管理--/dev/log 的本质与作用
奇妙之二进制
#嵌入式/Linuxlinuxubuntu运维
文章目录**一、基本概念****二、技术细节:UNIX域套接字****三、在不同日志系统中的角色****四、应用程序如何使用`dev/log`****五、查看和验证`/dev/log`****六、总结`/dev/log`的核心作用**一、基本概念/dev/log是一个UNIX域套接字(UnixDomainSocket),是Linux系统中实现进程间通信(IPC)的一种特殊文件。它为应用程序提供了向
- Kotlin 与移动开发的无缝对接秘籍
移动开发前沿
kotlin开发语言androidai
Kotlin与移动开发的无缝对接秘籍关键词:Kotlin、移动开发、Android、iOS、跨平台开发、协程、JetpackCompose摘要:本文深入解析Kotlin在移动开发领域的核心优势与实践方法,通过剖析Kotlin语言特性、跨平台架构、与原生生态的深度集成(如AndroidJetpack和iOSSwift互操作)、异步编程模型(协程)等关键技术,结合完整的项目实战案例,展示如何利用Kot
- 鸿蒙应用多租户为操作系统领域的创新提供动力
操作系统内核探秘
harmonyos华为ai
鸿蒙应用多租户为操作系统领域的创新提供动力关键词:鸿蒙操作系统、多租户架构、操作系统创新、资源隔离、安全沙箱、分布式能力、应用生态摘要:本文深入探讨鸿蒙操作系统(HarmonyOS)中多租户架构的创新设计与实现原理。我们将从操作系统基础概念出发,逐步解析多租户如何为鸿蒙带来独特的竞争优势,包括资源隔离机制、安全沙箱技术、分布式能力支持等核心特性。通过实际代码示例和架构图解,展示鸿蒙如何通过多租户设
- 如何快速删除某几页的页眉页脚
纳兰青华
SkillsWord常用技巧Word常用技巧
如何快速删除某几页的页面页脚问题当我们在插入页眉页脚的时候发现,所有页都插入了,但是我们只想删除固定的几页该如何解决如:我们想删除第一页和第二页的页眉页脚,保留第三第四页方法光标落在你想要删除页的最后页的页面,点击:布局—>分隔符—>连续双击你不想删除页的页眉,点击:链接到前一节任意点击你想删除的页眉页脚其中一页,删除即可
- 《Spring》第五篇 Bean的生命周期 - 创建
搬砖界的小白
#Spring源码框架springjavaspringboot
目录一.Bean的生命周期第一阶段:扫描1.解析配置类上@ComponentScan注解定义的扫描路径,获取资源路径,并生成BeanDefinition2.赋初始值,解析注解,并注册3.合并BeanDefition第二阶段:实例化1.加载类2.实例化前3.实例化4.实例化后第三阶段:属性注入第四阶段:初始化1.初始化前-执行Aware回调2.初始化前-Spring扩展点BeanPostProces
- Docker三分钟部署ElasticSearch平替MeiliSearch轻量级搜索引擎
个人主页:阿木木AEcru(更多精彩内容可进入主页观看)系列专栏:《Docker容器化部署系列》《Java每日面筋》每一次技术突破,都是对自我能力的挑战和超越。目录一、什么是MeiliSearch?二、对比ElasticSearch有什么好处?三、使用场景有哪些?四、docker部署MeiliSearch4.1创建数据持久化文件夹4.2拉取镜像4.3运行容器五、访问测试5.1访问5.2下载测试文
- VLAN间的三层通信
afei00123
数据通信技术
多臂路由(已经淘汰)基于物理接口的VLAN间路由。优点:既能隔离广播域又能实现通信。多臂路由的缺点:每一个VLAN都需要占用路由器上的一个物理接口(也就是说,每一个VLAN都需要路由器从一个物理接口伸出一只手臂来),如果VLAN数目众多,就需要占用大量的路由器接口。事实上,路由器的物理接口资源是非常宝贵而稀缺的,一台路由器上的物理接口数量通常都是非常有限的,无法支持数量较多的VLAN。实际的网络部
- 【网络安全】网络基础第一阶段——第三节:网络协议基础---- VLAN、Trunk与三层交换技术
目录一、交换机1.1交换机定义1.1.1交换机1.2工作原理1.2.1数据帧的转发1.2.2交换机处理数据帧的三种行为1.2.3交换机通信二、虚拟局域网(VLAN)2.1虚拟局域网简介2.1.1为什么需要VLAN2.1.2广播域的分割与VLAN的必要性2.1.3VLAN使用场景2.2VLAN机制详解2.2.1实现VLAN的机制2.2.2直观描述VLAN2.2.3需要VLAN间通信时应该怎么办2.3
- 大数据 ETL 工具 Sqoop 深度解析与实战指南
一、Sqoop核心理论与应用场景1.1设计思想与技术定位Sqoop是Apache旗下的开源数据传输工具,核心设计基于MapReduce分布式计算框架,通过并行化的Map任务实现高效的数据批量迁移。其特点包括:批处理特性:基于MapReduce作业实现导入/导出,适合大规模离线数据迁移,不支持实时数据同步。异构数据源连接:支持关系型数据库(如MySQL、Oracle)与Hadoop生态(HDFS、H
- Python pip与Conda环境的兼容性问题
Pythonpip与Conda环境的兼容性问题关键词:Python环境管理、pip与conda冲突、依赖解析、虚拟环境、包管理、兼容性解决方案、依赖冲突摘要:本文深入探讨Python生态中pip和conda两种主流包管理工具的兼容性问题。我们将从底层机制分析冲突根源,通过具体案例展示常见问题场景,并提供多种解决方案和最佳实践。文章包含详细的依赖解析算法分析、环境隔离技术比较,以及通过实际代码演示如
- 【网络通信安全】OSPF 邻居建立全过程解析:从状态机到实战排错(附 eNSP 动态验证)
不羁。。
网络通信安全开发语言网络运维安全
目录一、引言:OSPF如何构建“网络对话”?二、OSPF邻居状态机:8阶段状态转换图三、逐状态深度解析:每个阶段在“干什么”?1.Down状态:对话的起点2.Attempt状态:NBMA网络的“主动连接”3.Init状态:“我知道你存在”4.2-Way状态:双向通信达成5.Exstart状态:主从关系确立6.Exchange状态:LSDB摘要交换7.Loading状态:补全缺失的LSA8.Full
- 【网络通信安全】深入解析 OSPF 协议:从概念到 eNSP 实战配置(附完整代码与排错指南)
不羁。。
网络通信安全智能路由器网络
目录一、OSPF协议核心概念:为什么它是企业网络的“神经网络”?1.协议本质与设计目标2.核心组件与工作原理(1)链路状态数据库(LSDB)(2)区域划分原则(3)路由器角色二、实验环境搭建:3台路由器构建跨区域OSPF网络1.网络拓扑图2.设备与IP规划表三、逐设备配置详解:从接口到OSPF进程的全流程操作1.基础配置:接口IP与设备命名(以R1为例)2.OSPF进程配置:区域划分与网络宣告(1
- 【网络通信安全】基于华为 eNSP 的链路聚合、手工负载分担模式与 LACP 扩展配置 全解析
不羁。。
网络通信安全服务器开发语言网络华为运维
目录一、引言二、链路聚合技术基础2.1链路聚合的定义与作用2.2链路聚合的工作原理2.3链路聚合的模式分类三、华为eNSP简介3.1eNSP的概述3.2eNSP的安装与配置3.2.1安装环境要求3.2.2安装步骤3.2.3配置虚拟网卡四、手工负载分担模式配置4.1手工负载分担模式的特点4.2手工负载分担模式的配置步骤4.2.1实验拓扑搭建4.2.2配置交换机S14.2.3配置交换机S24.3手工负
- 实现零信任架构(ZTA)的三大技术,从零基础到精通,收藏这篇就够了!
一、零信任架构(ZTA)的三大王牌技术:“SIM”组合拳图1零信任三大技术SIM,安全界的“三剑客”话说2019年,美国国家标准委员会NIST发布了一份“武林秘籍”——《零信任架构ZTA》白皮书,瞬间在安全界掀起了一股“零信任”风暴!这份秘籍里,着重强调了零信任的安全理念,还介绍了实现零信任架构的三大技术,江湖人称“SIM”组合(SDP,IAM,MSG):南北向流量:就像高速公路上的车辆,从用户开
- 工业控制系统五层架构以及PLC、SCADA、DCS系统,从零基础到精通,收藏这篇就够了!
工业控制系统,这玩意儿可不是简单的“自动化”,而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关键基础设施!别再把它想象成几个孤立的PLC盒子了,它是一个活生生的、需要严密保护的生态系统。01***“经典五层架构”?别逗了,安全视角下它漏洞百出!IEC62264-1定义的那个“经典五层架构”,听起来很美,从物理设备到企业决策,层层递进。但说实话,在网络安全专家眼里,它简直就是一张漏洞百出的地图!L0物理设备层:传感器、执行器?
- 通过dockerfile设置镜像的时区和中文编码
%%'' OR 1=1
项目总结dockerdocker
背景我们的项目中有一块日志收集的功能,主要来收集容器化之后的一些实例的日志,项目在运行之后发现收集到的日志时间过滤有问题,并且中文显示乱码。中文乱码问题分析因为乱码问题涉及的点一般会比较多,遇到这种问题要从根源去分析是哪个环节导致的,有的是系统不支持中文,有的是因为数据库编码问题,有的是代码中编码问题。我们的场景是从pod中获取日志,然后经过代码解析,然后写入到数据库,以上提到的三个方面都涉及了。
- 冒泡和快速排序的区别
郭尘帅666
算法数据结构
冒泡算法快速排序时间复杂度O(n^2)最坏/平均O(nlogn)平均,O(n^2)最坏空间复杂度O(1)O(logn)最好/O(n)最坏稳定性很稳定(元素顺序不变)不稳定(元素顺序可能改变)适用场景小规模数据或接近有序的数据大规模数据核心思想重复遍历,每轮都会把最大的元素移至末尾选择基准值,比基准值小的元素放左边,大的放右边代码实现对比1.冒泡排序publicstaticvoidbubbleSor
- 解锁阿里云ACK:开启Kubernetes容器化应用新时代
云资源服务商
阿里云云计算云原生
引言:云原生时代下的ACK在当今数字化飞速发展的时代,云原生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着软件开发和部署的格局。随着企业对应用敏捷性、弹性扩展以及成本优化的需求日益增长,云原生已成为众多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的关键路径。在云原生的技术体系中,容器编排技术无疑是核心之一,而阿里云Kubernetes版(ACK)则是这一领域的佼佼者,为企业提供了强大、高效且易于管理的容器编排解决方案。Kubernetes作
- 基于KANO模型的调研问卷设计避坑
Alex艾力的IT数字空间
产品经理原型模式产品运营交互设计规范腾讯会议蓝湖
KANO模型调研中,设计无引导性偏差的问卷需遵循中立表述、选项平衡、逻辑验证原则。一、避免引导性偏差的核心策略1.问题中性化设计禁用倾向性词汇:避免“优化”“提升”等暗示性词语,改用中性描述。❌引导性:“增加扫码支付功能会让体验更好吗?”✅中性化:“扫码支付功能的存在对您来说如何?”对称性表述:正向/反向问题结构完全对仗,仅改变核心条件。正向:“提供XX功能时,您的满意度如何?”反向:“不提供XX
- 安装Hadoop集群&入门&源码编译
只年
大数据Hadoophadoop大数据分布式
安装Hadoop集群完全分布式先决条件准备三台机器NameStaticIPDESCbigdata102192.168.1.102DataNode、NodeManager、NameNodebigdata103192.168.1.103DataNode、NodeManager、ResourceManagerbigdata104192.168.1.104DataNode、NodeManager、Seco
- Java中List集合的遍历
Karson Tiger
Javajavalist
一、序言List集合在Java日常开发中是必不可少的,只要懂得运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就可以大大提高我们开发的效率,适当活用各种方法才会使我们开发事半功倍。本文总结了三种List集合的遍历方式,下面将依次进行介绍。二、遍历方式进行遍历前,需要有一个实体类以供遍历使用,参见“三、实体类”;2.1for循环指定下标长度,使用List集合的size()方法,进行for循环遍历,这种遍历方式最基础;import
- Unity-MMORPG内容笔记-其三
KhalilRuan
笔记
继续之前的内容:战斗系统无需多言,整个项目中最复杂的部分,也是代码量最大的部分。属性系统首先我们要定义一系列属性,毕竟所谓的战斗就是不断地扣血对吧。属性系统是战斗系统的核心模块,负责管理角色的所有属性数据,包括初始属性、成长属性、装备加成和Buff效果,并通过多阶段计算得出最终属性值。系统支持属性实时更新,当角色等级提升、装备变化或Buff增减时,会自动重新计算并同步属性数据。属性含义说明-Max
- knob UI插件使用
换个号韩国红果果
JavaScriptjsonpknob
图形是用canvas绘制的
js代码
var paras = {
max:800,
min:100,
skin:'tron',//button type
thickness:.3,//button width
width:'200',//define canvas width.,canvas height
displayInput:'tr
- Android+Jquery Mobile学习系列(5)-SQLite数据库
白糖_
JQuery Mobile
目录导航
SQLite是轻量级的、嵌入式的、关系型数据库,目前已经在iPhone、Android等手机系统中使用,SQLite可移植性好,很容易使用,很小,高效而且可靠。
因为Android已经集成了SQLite,所以开发人员无需引入任何JAR包,而且Android也针对SQLite封装了专属的API,调用起来非常快捷方便。
我也是第一次接触S
- impala-2.1.2-CDH5.3.2
dayutianfei
impala
最近在整理impala编译的东西,简单记录几个要点:
根据官网的信息(https://github.com/cloudera/Impala/wiki/How-to-build-Impala):
1. 首次编译impala,推荐使用命令:
${IMPALA_HOME}/buildall.sh -skiptests -build_shared_libs -format
2.仅编译BE
${I
- 求二进制数中1的个数
周凡杨
java算法二进制
解法一:
对于一个正整数如果是偶数,该数的二进制数的最后一位是 0 ,反之若是奇数,则该数的二进制数的最后一位是 1 。因此,可以考虑利用位移、判断奇偶来实现。
public int bitCount(int x){
int count = 0;
while(x!=0){
if(x%2!=0){ /
- spring中hibernate及事务配置
g21121
Hibernate
hibernate的sessionFactory配置:
<!-- hibernate sessionFactory配置 -->
<bean id="sessionFactory"
class="org.springframework.orm.hibernate3.LocalSessionFactoryBean">
<
- log4j.properties 使用
510888780
log4j
log4j.properties 使用
一.参数意义说明
输出级别的种类
ERROR、WARN、INFO、DEBUG
ERROR 为严重错误 主要是程序的错误
WARN 为一般警告,比如session丢失
INFO 为一般要显示的信息,比如登录登出
DEBUG 为程序的调试信息
配置日志信息输出目的地
log4j.appender.appenderName = fully.qua
- Spring mvc-jfreeChart柱图(2)
布衣凌宇
jfreechart
上一篇中生成的图是静态的,这篇将按条件进行搜索,并统计成图表,左面为统计图,右面显示搜索出的结果。
第一步:导包
第二步;配置web.xml(上一篇有代码)
建BarRenderer类用于柱子颜色
import java.awt.Color;
import java.awt.Paint;
import org.jfree.chart.renderer.category.BarR
- 我的spring学习笔记14-容器扩展点之PropertyPlaceholderConfigurer
aijuans
Spring3
PropertyPlaceholderConfigurer是个bean工厂后置处理器的实现,也就是BeanFactoryPostProcessor接口的一个实现。关于BeanFactoryPostProcessor和BeanPostProcessor类似。我会在其他地方介绍。
PropertyPlaceholderConfigurer可以将上下文(配置文件)中的属性值放在另一个单独的标准java
- maven 之 cobertura 简单使用
antlove
maventestunitcoberturareport
1. 创建一个maven项目
2. 创建com.CoberturaStart.java
package com;
public class CoberturaStart {
public void helloEveryone(){
System.out.println("=================================================
- 程序的执行顺序
百合不是茶
JAVA执行顺序
刚在看java核心技术时发现对java的执行顺序不是很明白了,百度一下也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资料,所以就简单的回顾一下吧
代码如下;
经典的程序执行面试题
//关于程序执行的顺序
//例如:
//定义一个基类
public class A(){
public A(
- 设置session失效的几种方法
bijian1013
web.xmlsession失效监听器
在系统登录后,都会设置一个当前session失效的时间,以确保在用户长时间不与服务器交互,自动退出登录,销毁session。具体设置很简单,方法有三种:(1)在主页面或者公共页面中加入:session.setMaxInactiveInterval(900);参数900单位是秒,即在没有活动15分钟后,session将失效。这里要注意这个session设置的时间是根据服务器来计算的,而不是客户端。所
- java jvm常用命令工具
bijian1013
javajvm
一.概述
程序运行中经常会遇到各种问题,定位问题时通常需要综合各种信息,如系统日志、堆dump文件、线程dump文件、GC日志等。通过虚拟机监控和诊断工具可以帮忙我们快速获取、分析需要的数据,进而提高问题解决速度。 本文将介绍虚拟机常用监控和问题诊断命令工具的使用方法,主要包含以下工具:
&nbs
- 【Spring框架一】Spring常用注解之Autowired和Resource注解
bit1129
Spring常用注解
Spring自从2.0引入注解的方式取代XML配置的方式来做IOC之后,对Spring一些常用注解的含义行为一直处于比较模糊的状态,写几篇总结下Spring常用的注解。本篇包含的注解有如下几个:
Autowired
Resource
Component
Service
Controller
Transactional
根据它们的功能、目的,可以分为三组,Autow
- mysql 操作遇到safe update mode问题
bitray
update
我并不知道出现这个问题的实际原理,只是通过其他朋友的博客,文章得知的一个解决方案,目前先记录一个解决方法,未来要是真了解以后,还会继续补全.
在mysql5中有一个safe update mode,这个模式让sql操作更加安全,据说要求有where条件,防止全表更新操作.如果必须要进行全表操作,我们可以执行
SET
- nginx_perl试用
ronin47
nginx_perl试用
因为空闲时间比较多,所以在CPAN上乱翻,看到了nginx_perl这个项目(原名Nginx::Engine),现在托管在github.com上。地址见:https://github.com/zzzcpan/nginx-perl
这个模块的目的,是在nginx内置官方perl模块的基础上,实现一系列异步非阻塞的api。用connector/writer/reader完成类似proxy的功能(这里
- java-63-在字符串中删除特定的字符
bylijinnan
java
public class DeleteSpecificChars {
/**
* Q 63 在字符串中删除特定的字符
* 输入两个字符串,从第一字符串中删除第二个字符串中所有的字符。
* 例如,输入”They are students.”和”aeiou”,则删除之后的第一个字符串变成”Thy r stdnts.”
*/
public static voi
- EffectiveJava--创建和销毁对象
ccii
创建和销毁对象
本章内容:
1. 考虑用静态工厂方法代替构造器
2. 遇到多个构造器参数时要考虑用构建器(Builder模式)
3. 用私有构造器或者枚举类型强化Singleton属性
4. 通过私有构造器强化不可实例化的能力
5. 避免创建不必要的对象
6. 消除过期的对象引用
7. 避免使用终结方法
1. 考虑用静态工厂方法代替构造器
类可以通过
- [宇宙时代]四边形理论与光速飞行
comsci
从四边形理论来推论 为什么光子飞船必须获得星光信号才能够进行光速飞行?
一组星体组成星座 向空间辐射一组由复杂星光信号组成的辐射频带,按照四边形-频率假说 一组频率就代表一个时空的入口
那么这种由星光信号组成的辐射频带就代表由这些星体所控制的时空通道,该时空通道在三维空间的投影是一
- ubuntu server下python脚本迁移数据
cywhoyi
pythonKettlepymysqlcx_Oracleubuntu server
因为是在Ubuntu下,所以安装python、pip、pymysql等都极其方便,sudo apt-get install pymysql,
但是在安装cx_Oracle(连接oracle的模块)出现许多问题,查阅相关资料,发现这边文章能够帮我解决,希望大家少走点弯路。http://www.tbdazhe.com/archives/602
1.安装python
2.安装pip、pymysql
- Ajax正确但是请求不到值解决方案
dashuaifu
Ajaxasync
Ajax正确但是请求不到值解决方案
解决方案:1 . async: false , 2. 设置延时执行js里的ajax或者延时后台java方法!!!!!!!
例如:
$.ajax({ &
- windows安装配置php+memcached
dcj3sjt126com
PHPInstallmemcache
Windows下Memcached的安装配置方法
1、将第一个包解压放某个盘下面,比如在c:\memcached。
2、在终端(也即cmd命令界面)下输入 'c:\memcached\memcached.exe -d install' 安装。
3、再输入: 'c:\memcached\memcached.exe -d start' 启动。(需要注意的: 以后memcached将作为windo
- iOS开发学习路径的一些建议
dcj3sjt126com
ios
iOS论坛里有朋友要求回答帖子,帖子的标题是: 想学IOS开发高阶一点的东西,从何开始,然后我吧啦吧啦回答写了很多。既然敲了那么多字,我就把我写的回复也贴到博客里来分享,希望能对大家有帮助。欢迎大家也到帖子里讨论和分享,地址:http://bbs.csdn.net/topics/390920759
下面是我回复的内容:
结合自己情况聊下iOS学习建议,
- Javascript闭包概念
fanfanlovey
JavaScript闭包
1.参考资料
http://www.jb51.net/article/24101.htm
http://blog.csdn.net/yn49782026/article/details/8549462
2.内容概述
要理解闭包,首先需要理解变量作用域问题
内部函数可以饮用外面全局变量
var n=999;
functio
- yum安装mysql5.6
haisheng
mysql
1、安装http://dev.mysql.com/get/mysql-community-release-el7-5.noarch.rpm
2、yum install mysql
3、yum install mysql-server
4、vi /etc/my.cnf 添加character_set_server=utf8
- po/bo/vo/dao/pojo的详介
IT_zhlp80
javaBOVODAOPOJOpo
JAVA几种对象的解释
PO:persistant object持久对象,可以看成是与数据库中的表相映射的java对象。最简单的PO就是对应数据库中某个表中的一条记录,多个记录可以用PO的集合。PO中应该不包含任何对数据库的操作.
VO:value object值对象。通常用于业务层之间的数据传递,和PO一样也是仅仅包含数据而已。但应是抽象出的业务对象,可
- java设计模式
kerryg
java设计模式
设计模式的分类:
一、 设计模式总体分为三大类:
1、创建型模式(5种):工厂方法模式,抽象工厂模式,单例模式,建造者模式,原型模式。
2、结构型模式(7种):适配器模式,装饰器模式,代理模式,外观模式,桥接模式,组合模式,享元模式。
3、行为型模式(11种):策略模式,模版方法模式,观察者模式,迭代子模式,责任链模式,命令模式,备忘录模式,状态模式,访问者
- [1]CXF3.1整合Spring开发webservice——helloworld篇
木头.java
springwebserviceCXF
Spring 版本3.2.10
CXF 版本3.1.1
项目采用MAVEN组织依赖jar
我这里是有parent的pom,为了简洁明了,我直接把所有的依赖都列一起了,所以都没version,反正上面已经写了版本
<project xmlns="http://maven.apache.org/POM/4.0.0" xmlns:xsi="ht
- Google 工程师亲授:菜鸟开发者一定要投资的十大目标
qindongliang1922
工作感悟人生
身为软件开发者,有什么是一定得投资的? Google 软件工程师 Emanuel Saringan 整理了十项他认为必要的投资,第一项就是身体健康,英文与数学也都是必备能力吗?来看看他怎么说。(以下文字以作者第一人称撰写)) 你的健康 无疑地,软件开发者是世界上最久坐不动的职业之一。 每天连坐八到十六小时,休息时间只有一点点,绝对会让你的鲔鱼肚肆无忌惮的生长。肥胖容易扩大罹患其他疾病的风险,
- linux打开最大文件数量1,048,576
tianzhihehe
clinux
File descriptors are represented by the C int type. Not using a special type is often considered odd, but is, historically, the Unix way. Each Linux process has a maximum number of files th
- java语言中PO、VO、DAO、BO、POJO几种对象的解释
衞酆夼
javaVOBOPOJOpo
PO:persistant object持久对象
最形象的理解就是一个PO就是数据库中的一条记录。好处是可以把一条记录作为一个对象处理,可以方便的转为其它对象。可以看成是与数据库中的表相映射的java对象。最简单的PO就是对应数据库中某个表中的一条记录,多个记录可以用PO的集合。PO中应该不包含任何对数据库的操作。
BO:business object业务对象
封装业务逻辑的java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