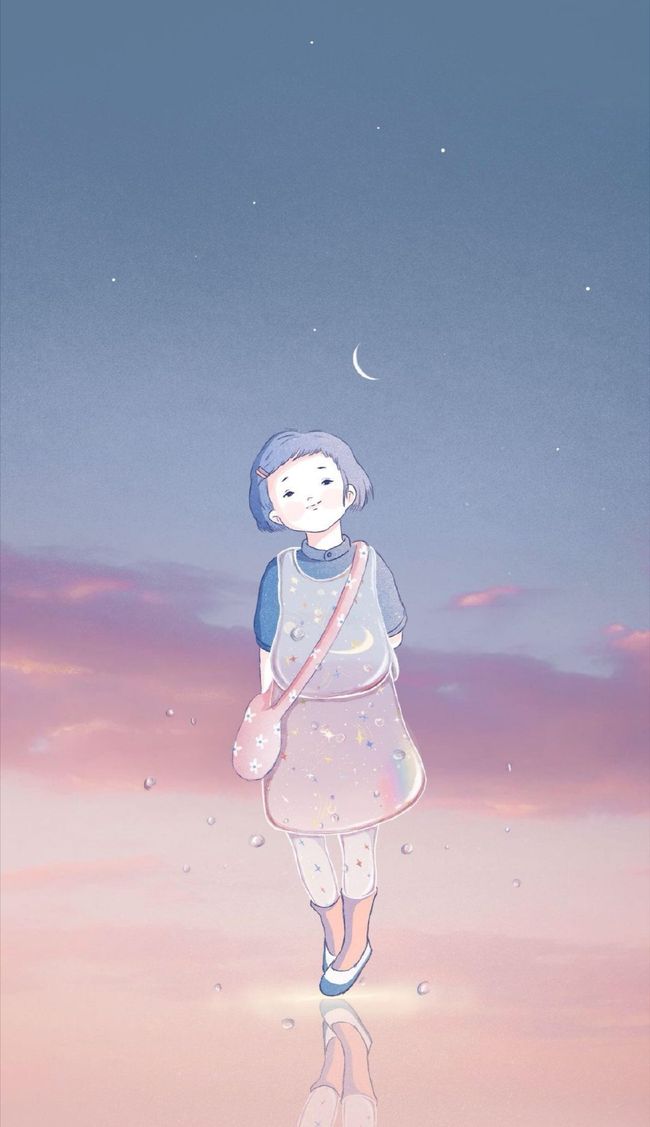- 情绪觉察日记第37天
露露_e800
今天是家庭关系规划师的第二阶最后一天,慧萍老师帮我做了个案,帮我处理了埋在心底好多年的一份恐惧,并给了我深深的力量!这几天出来学习,爸妈过来婆家帮我带小孩,妈妈出于爱帮我收拾东西,并跟我先生和婆婆产生矛盾,妈妈觉得他们没有照顾好我…。今晚回家见到妈妈,我很欣赏她并赞扬她,妈妈说今晚要跟我睡我说好,当我们俩躺在床上准备睡觉的时候,我握着妈妈的手对她说:妈妈这几天辛苦你了,你看你多利害把我们的家收拾得
- 10月|愿你的青春不负梦想-读书笔记-01
Tracy的小书斋
本书的作者是俞敏洪,大家都很熟悉他了吧。俞敏洪老师是我行业的领头羊吧,也是我事业上的偶像。本日摘录他书中第一章中的金句:『一个人如果什么目标都没有,就会浑浑噩噩,感觉生命中缺少能量。能给我们能量的,是对未来的期待。第一件事,我始终为了进步而努力。与其追寻全世界的骏马,不如种植丰美的草原,到时骏马自然会来。第二件事,我始终有阶段性的目标。什么东西能给我能量?答案是对未来的期待。』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便
- 谢谢你们,爱你们!
鹿游儿
昨天家人去泡温泉,二个孩子也带着去,出发前一晚,匆匆下班,赶回家和孩子一起收拾。饭后,我拿出笔和本子(上次去澳门时做手帐的本子)写下了1\2\3\4\5\6\7\8\9,让后让小壹去思考,带什么出发去旅游呢?她在对应的数字旁边画上了,泳衣、泳圈、肖恩、内衣内裤、tapuy、拖鞋……画完后,就让她自己对着这个本子,将要带的,一一带上,没想到这次带的书还是这本《便便工厂》(晚上姑婆发照片过来,妹妹累得
- 2021年12月19日,春蕾教育集团团建活动感受——黄晓丹
黄错错加油
感受:1.从陌生到熟悉的过程。游戏环节让我们在轻松的氛围中得到了锻炼,也增长了不少知识。2.游戏过程中,我们贡献的是个人力量,展现的是团队的力量。它磨合的往往不止是工作的熟悉,更是观念上契合度的贴近。3.这和工作是一样的道理。在各自的岗位上,每个人摆正自己的位置、各司其职充分发挥才能,并团结一致劲往一处使,才能实现最大的成功。新知:1.团队精神需要不断地创新。过去,人们把创新看作是冒风险,现在人们
- 《策划经理回忆录之二》
路基雅虎
话说三年变六年,飘了,飘了……眨眼,2013年5月,老吴回到了他的家乡——油城从新开启他的工作幻想症生涯。很庆幸,这是一家很有追求,同时敢于尝试的,且实力不容低调的新星房企——金源置业(前身泰源置业)更值得庆幸的是第一个盘就是油城十路的标杆之一:金源盛世。2013年5月,到2015年11月,两年的陪伴,迎来了一场大爆发。2000个筹,5万/筹,直接回笼1个亿!!!这……让我开始认真审视这座看似五线
- 我校举行新老教师师徒结对仪式暨名师专业工作室工作交流活动
李蕾1229
为促进我校教师专业发展,发挥骨干教师的引领带头作用,11月6日下午,我校举行新老教师师徒结对仪式暨名师专业工作室工作交流活动。图片发自App会议由教师发展处李蕾主任主持,首先,由范校长宣读新老教师结对名单及双方承担职责。随后,两位新调入教师陈玉萍、莫正杰分别和他们的师傅鲍元美、刘召彬老师签订了师徒结对协议书。图片发自App图片发自App师徒拥抱、握手。有了师傅就有了目标有了方向,相信两位新教师在师
- 向内而求
陈陈_19b4
10月27日,阴。阅读书目:《次第花开》。作者:希阿荣博堪布,是当今藏传佛家宁玛派最伟大的上师法王,如意宝晋美彭措仁波切颇具影响力的弟子之一。多年以来,赴海内外各地弘扬佛法,以正式授课、现场开示、发表文章等多种方法指导佛学弟子修行佛法。代表作《寂静之道》、《生命这出戏》、《透过佛法看世界》自出版以来一直是佛教类书籍中的畅销书。图片发自App金句:1.佛陀说,一切痛苦的根源在于我们长期以来对自身及外
- 高级编程--XML+socket练习题
masa010
java开发语言
1.北京华北2114.8万人上海华东2,500万人广州华南1292.68万人成都华西1417万人(1)使用dom4j将信息存入xml中(2)读取信息,并打印控制台(3)添加一个city节点与子节点(4)使用socketTCP协议编写服务端与客户端,客户端输入城市ID,服务器响应相应城市信息(5)使用socketTCP协议编写服务端与客户端,客户端要求用户输入city对象,服务端接收并使用dom4j
- 抖音乐买买怎么加入赚钱?赚钱方法是什么
测评君高省
你会在抖音买东西吗?如果会,那么一定要免费注册一个乐买买,抖音直播间,橱窗,小视频里的小黄车买东西都可以返佣金!省下来都是自己的,分享还可以赚钱乐买买是好省旗下的抖音返佣平台,乐买买分析社交电商的价值,乐买买属于今年难得的副业项目风口机会,2019年错过做好省的搞钱的黄金时期,那么2022年千万别再错过乐买买至于我为何转到高省呢?当然是高省APP佣金更高,模式更好,终端用户不流失。【高省】是一个自
- 2018-07-23-催眠日作业-#不一样的31天#-66小鹿
小鹿_33
预言日:人总是在逃避命运的路上,与之不期而遇。心理学上有个著名的名词,叫做自证预言;经济学上也有一个很著名的定律叫做,墨菲定律;在灵修派上,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法则,叫做吸引力法则。这3个领域的词,虽然看起来不太一样,但是他们都在告诉人们一个现象:你越担心什么,就越有可能会发生什么。同样的道理,你越想得到什么,就应该要积极地去创造什么。无论是自证预言,墨菲定律还是吸引力法则,对人都有正反2个维度的影响
- 今日联对0306
诗图佳得
自对联:烟销皓月临江浒,水漫金山荡塔裙。一一肖士平2020.3.6.1、试对肖老师联:烟销皓月临江浒,夜笼寒沙梦晚舟。耀哥求正2、试对萧老师联:烟销浩月临江浒,雾散乾坤解汉城。秀霞习作请各位老师校正3、自对联:烟销皓月临江浒,水漫金山荡塔裙。一一肖士平2020.3.6.4、试对肖老师垫场联:烟销皓月临江浒,雾锁寒林缈葉丛。小智求正[抱拳]5、试对肖老师联:烟销皓月临江浒;风卷乱云入峰巅。一一五品6
- 2022-07-08
保利学府里李楚怡1307022
——保利碧桂园学府里——童梦奇趣【科学实验室】「7.9-7.10」✏玩出大智慧约99-144㎡二期全新升级力作
- 2022-04-18
Apbenz
语重心长的和我说,不要老是说不行,人至而立之年危机四伏,内在的,外在的,感觉就是心力憔悴,让人无所适从。面对职场的无情,突然好羡慕干体力劳动的外卖小哥。难道命运是想让我去送外卖了吗?干体力活才能让我活下去?fastadmin打卡成功,淘宝金币任务完成。ㅏㅓㅗㅜㅡㅣㅐㅔㅑㅕㅛㅠㅢㅒㅖY行。야자여자요리우유의사얘기예
- 《小满细雨轻湿尘》
快乐的人ZZM
图片发自App《小满细雨轻湿尘》文/快乐的人zzm小满细雨轻湿尘石榴花开落纷纷落红不是无情物坠入泥土育养根2018-5-23
- 怎么起诉借钱不还的人?怎样起诉欠款不还的人?
影子爱学习
怎么起诉借钱不还的人?怎样起诉欠款不还的人?如果遇到难以解决的法律问题,我们可以匹配专业律师。例如:婚姻家庭(离婚纠纷)、刑事辩护、合同纠纷、债权债务、房产(继承)纠纷、交通事故、劳动争议、人身损害、公司相关法律事务(法律顾问)等咨询推荐手机/微信:15633770876【全国案件皆可】借钱不还起诉对方需要哪些资料起诉欠钱不还的,一般需要的材料包括以下这些:借据、收据、欠条、付款凭证等证据,以及向
- 2019-12-22-22:30
涓涓1016
今天是冬至,写下我的日更,是因为这两天的学习真的是能量的满满,让我看到了自己,未来另外一种可能性,也让我看到了这两年这几年的过程中我所接受那些痛苦的来源。一切的根源和痛苦都来自于人生,家庭,而你的原生家庭,你的爸爸和妈妈,是因为你这个灵魂在那一刻选择他们作为你的爸爸和妈妈来的,所以你得接受他,你得接纳他,他就是因为他的存在而给你的学习和成长带来这些痛苦,那其实是你必然要经历的这个过程,当你去接纳的
- Goolge earth studio 进阶4——路径修改与平滑
陟彼高冈yu
Googleearthstudio进阶教程旅游
如果我们希望在大约中途时获得更多的城市鸟瞰视角。可以将相机拖动到这里并创建一个新的关键帧。camera_target_clip_7EarthStudio会自动平滑我们的路径,所以当我们通过这个关键帧时,不是一个生硬的角度,而是一个平滑的曲线。camera_target_clip_8路径上有贝塞尔控制手柄,允许我们调整路径的形状。右键单击,我们可以选择“平滑路径”,这是默认的自动平滑算法,或者我们可
- 509. 斐波那契数(每日一题)
lzyprime
lzyprime博客(github)创建时间:2021.01.04qq及邮箱:2383518170leetcode笔记题目描述斐波那契数,通常用F(n)表示,形成的序列称为斐波那契数列。该数列由0和1开始,后面的每一项数字都是前面两项数字的和。也就是:F(0)=0,F(1)=1F(n)=F(n-1)+F(n-2),其中n>1给你n,请计算F(n)。示例1:输入:2输出:1解释:F(2)=F(1)+
- 今又重阳
芮峻
今又重阳图片发自App白露成霜菊花黄,岁岁重阳,今又重阳。登高远望,君不见,那来时路上少年,青丝已染雪霜。落日一点一点西坠,谁有力量,托住使其回往。转眼缺了大半,又能怎样?江天两茫茫。给我一壶烈酒,我要敬那斜阳,看谁先醉?笑指西天红了一片,借点酒力,老夫聊发一次少年狂。老严.2019年重阳节.杭州
- 2020.11.19
隆非凡
日精进,今日体验:在维修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把源头找到,在进行下一步开始。不要停留在一个点上,合理调整心态,把当下事做好。
- 18-115 一切思考不能有效转化为行动,都TM是扯淡!
成长时间线
7月25号写了一篇关于为什么会断更如此严重的反思,然而,之后日更仅仅维持了一周,又出现了这次更严重的现象。从8月2号到昨天8月6号,5天!又是5天没有更文!虽然这次断更时间和上次一样,那为什么说这次更严重?因为上次之后就分析了问题的原因,以及应该如何解决,按理说应该会好转,然而,没过几天严重断更的现象再次出现,想想,经过反思,问题依然没有解决与改变,这让我有些担忧。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难道我就真的
- 2018/02/12
Tracy_zhang
人生并不在于获取,更在于放得下。放下一粒种子,收获一棵大树;放下一处烦恼,收获一个惊喜;放下一种偏见,收获一种幸福;放下一种执著,收获一种自在。放下既是一种理性抉择,也是一种豁达美。只要看得开放得下,何愁没有快乐的春莺在啼鸣,何愁没有快乐的泉溪在歌唱,何愁没有快乐的鲜花绽放!
- 郎朗大婚娶公主:所有光环的背后,都是十年如一日的自律
简小尘
近日,关于郎朗大婚的新闻上了热搜,看了新娘的照片,既有天使般的面容,更有魔鬼般的身材,关键是人家还身世好,又有才华,这真的是让所有男人羡慕嫉妒恨哪。有些人不禁会想,“凭什么郎朗的人生就象开挂了一样,可我却每天都活得这么狼狈!”其实,每个开挂的人生背后,都是苦行僧般的自律。01欲戴王冠,必承其重。练琴不能只靠兴趣,更需要自律!我们先来看一下朗朗在小时候的作息时间表:早晨5:45起床,练琴1小时。中午
- 【华为OD机试真题2023B卷 JAVA&JS】We Are A Team
若博豆
java算法华为javascript
华为OD2023(B卷)机试题库全覆盖,刷题指南点这里WeAreATeam时间限制:1秒|内存限制:32768K|语言限制:不限题目描述:总共有n个人在机房,每个人有一个标号(1<=标号<=n),他们分成了多个团队,需要你根据收到的m条消息判定指定的两个人是否在一个团队中,具体的:1、消息构成为:abc,整数a、b分别代
- 2023-04-17|篮球女孩
长一木
1小学抑或初中阶段,在课外书了解到她的故事。“篮球女孩”。当时佩服她的顽强,也对生命多了一丝敬畏。今天刚好在公众号看到,长大后的“篮球女孩”。佩服之余又满是心疼。网络侵删祝那素未蒙面的女孩,未来一切顺遂。
- 少了生活气息
我爱大草莓
最近啊,总觉得自己日更的内容缺了点什么。我仔细地想,大概是少了些生活气息。这两三个月减少了许多与别人相处的时间,独自生活,偶尔只是出去买菜,总觉得生活好像变空了许多。买菜的时候会跟档口的阿姨聊一两句话,让自己感觉在真实地生活着。幸好我也不是一宅到底,偶尔周末也会约着跟好朋友见面,面对面交流跟隔着屏幕交流,效果还是不一样的,至少有更为真实的生活感。写作不仅需要有阅读量,有文笔,生活阅历也是非常重要的
- 398顺境,逆境
戴骁勇
2018.11.27周二雾霾最近儿子进入了一段顺境期,今天表现尤其不错。今天的数学测试成绩喜人,没有出现以往的计算错误,整个卷面书写工整,附加题也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且做对。为迎接体育测试的锻炼有了质的飞跃。坐位体前屈成绩突飞猛进,估测成绩能达到12cm,这和上次测试的零分来比,简直是逆袭。儿子还在不断锻炼和提升,唯恐到时候掉链子。跑步姿势在我的调教下,逐渐正规起来,速度随之也有了提升。今晚测试的50
- 从0到500+,我是如何利用自媒体赚钱?
一列脚印
运营公众号半个多月,从零基础的小白到现在慢慢懂了一些运营的知识。做好公众号是很不容易的,要做很多事情;排版、码字、引流…通通需要自己解决,业余时间全都花费在这上面涨这么多粉丝是真的不容易,对比知乎大佬来说,我们这种没资源,没人脉,还没钱的小透明来说,想要一个月涨粉上万,怕是今天没睡醒(不过你有的方法,算我piapia打脸)至少我是清醒的,自己慢慢努力,实现我的万粉目标!大家快来围观、支持我吧!孩子
- python是什么意思中文-在python中%是什么意思
编程大乐趣
Python中%有两种:1、数值运算:%代表取模,返回除法的余数。如:>>>7%212、%操作符(字符串格式化,stringformatting),说明如下:%[(name)][flags][width].[precision]typecode(name)为命名flags可以有+,-,''或0。+表示右对齐。-表示左对齐。''为一个空格,表示在正数的左侧填充一个空格,从而与负数对齐。0表示使用0填
- 2019-08-08
65454
东莞家庭聚会出行旅游去哪里玩住?想起来有很久没有和家里人聚会啦,这次组织家人来到威廉古堡别墅轰趴,一大家子27个人,在别墅订了一天办,玩的非常的开心,小孩子玩游戏机,也很放心不会丢,我们就在唱歌、打麻将、打桌球一系列的活动,还准备小次等小孩生日在别墅举办,还可以给孩子做一个生日的策划
- SAX解析xml文件
小猪猪08
xml
1.创建SAXParserFactory实例
2.通过SAXParserFactory对象获取SAXParser实例
3.创建一个类SAXParserHander继续DefaultHandler,并且实例化这个类
4.SAXParser实例的parse来获取文件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
- 为什么mysql里的ibdata1文件不断的增长?
brotherlamp
linuxlinux运维linux资料linux视频linux运维自学
我们在 Percona 支持栏目经常收到关于 MySQL 的 ibdata1 文件的这个问题。
当监控服务器发送一个关于 MySQL 服务器存储的报警时,恐慌就开始了 —— 就是说磁盘快要满了。
一番调查后你意识到大多数地盘空间被 InnoDB 的共享表空间 ibdata1 使用。而你已经启用了 innodbfileper_table,所以问题是:
ibdata1存了什么?
当你启用了 i
- Quartz-quartz.properties配置
eksliang
quartz
其实Quartz JAR文件的org.quartz包下就包含了一个quartz.properties属性配置文件并提供了默认设置。如果需要调整默认配置,可以在类路径下建立一个新的quartz.properties,它将自动被Quartz加载并覆盖默认的设置。
下面是这些默认值的解释
#-----集群的配置
org.quartz.scheduler.instanceName =
- informatica session的使用
18289753290
workflowsessionlogInformatica
如果希望workflow存储最近20次的log,在session里的Config Object设置,log options做配置,save session log :sessions run ;savesessio log for these runs:20
session下面的source 里面有个tracing
- Scrapy抓取网页时出现CRC check failed 0x471e6e9a != 0x7c07b839L的错误
酷的飞上天空
scrapy
Scrapy版本0.14.4
出现问题现象:
ERROR: Error downloading <GET http://xxxxx CRC check failed
解决方法
1.设置网络请求时的header中的属性'Accept-Encoding': '*;q=0'
明确表示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压缩格式,避免程序的解压
- java Swing小集锦
永夜-极光
java swing
1.关闭窗体弹出确认对话框
1.1 this.setDefaultCloseOperation (JFrame.DO_NOTHING_ON_CLOSE);
1.2
this.addWindowListener (
new WindowAdapter () {
public void windo
- 强制删除.svn文件夹
随便小屋
java
在windows上,从别处复制的项目中可能带有.svn文件夹,手动删除太麻烦,并且每个文件夹下都有。所以写了个程序进行删除。因为.svn文件夹在windows上是只读的,所以用File中的delete()和deleteOnExist()方法都不能将其删除,所以只能采用windows命令方式进行删除
- GET和POST有什么区别?及为什么网上的多数答案都是错的。
aijuans
get post
如果有人问你,GET和POST,有什么区别?你会如何回答? 我的经历
前几天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我说GET是用于获取数据的,POST,一般用于将数据发给服务器之用。
这个答案好像并不是他想要的。于是他继续追问有没有别的区别?我说这就是个名字而已,如果服务器支持,他完全可以把G
- 谈谈新浪微博背后的那些算法
aoyouzi
谈谈新浪微博背后的那些算法
本文对微博中常见的问题的对应算法进行了简单的介绍,在实际应用中的算法比介绍的要复杂的多。当然,本文覆盖的主题并不全,比如好友推荐、热点跟踪等就没有涉及到。但古人云“窥一斑而见全豹”,希望本文的介绍能帮助大家更好的理解微博这样的社交网络应用。
微博是一个很多人都在用的社交应用。天天刷微博的人每天都会进行着这样几个操作:原创、转发、回复、阅读、关注、@等。其中,前四个是针对短博文,最后的关注和@则针
- Connection reset 连接被重置的解决方法
百合不是茶
java字符流连接被重置
流是java的核心部分,,昨天在做android服务器连接服务器的时候出了问题,就将代码放到java中执行,结果还是一样连接被重置
被重置的代码如下;
客户端代码;
package 通信软件服务器;
import java.io.BufferedWriter;
import java.io.OutputStream;
import java.io.O
- web.xml配置详解之filter
bijian1013
javaweb.xmlfilter
一.定义
<filter>
<filter-name>encodingfilter</filter-name>
<filter-class>com.my.app.EncodingFilter</filter-class>
<init-param>
<param-name>encoding<
- Heritrix
Bill_chen
多线程xml算法制造配置管理
作为纯Java语言开发的、功能强大的网络爬虫Heritrix,其功能极其强大,且扩展性良好,深受热爱搜索技术的盆友们的喜爱,但它配置较为复杂,且源码不好理解,最近又使劲看了下,结合自己的学习和理解,跟大家分享Heritrix的点点滴滴。
Heritrix的下载(http://sourceforge.net/projects/archive-crawler/)安装、配置,就不罗嗦了,可以自己找找资
- 【Zookeeper】FAQ
bit1129
zookeeper
1.脱离IDE,运行简单的Java客户端程序
#ZkClient是简单的Zookeeper~$ java -cp "./:zookeeper-3.4.6.jar:./lib/*" ZKClient
1. Zookeeper是的Watcher回调是同步操作,需要添加异步处理的代码
2. 如果Zookeeper集群跨越多个机房,那么Leader/
- The user specified as a definer ('aaa'@'localhost') does not exist
白糖_
localhost
今天遇到一个客户BUG,当前的jdbc连接用户是root,然后部分删除操作都会报下面这个错误:The user specified as a definer ('aaa'@'localhost') does not exist
最后找原因发现删除操作做了触发器,而触发器里面有这样一句
/*!50017 DEFINER = ''aaa@'localhost' */
原来最初
- javascript中showModelDialog刷新父页面
bozch
JavaScript刷新父页面showModalDialog
在页面中使用showModalDialog打开模式子页面窗口的时候,如果想在子页面中操作父页面中的某个节点,可以通过如下的进行:
window.showModalDialog('url',self,‘status...’); // 首先中间参数使用self
在子页面使用w
- 编程之美-买书折扣
bylijinnan
编程之美
import java.util.Arrays;
public class BookDiscount {
/**编程之美 买书折扣
书上的贪心算法的分析很有意思,我看了半天看不懂,结果作者说,贪心算法在这个问题上是不适用的。。
下面用动态规划实现。
哈利波特这本书一共有五卷,每卷都是8欧元,如果读者一次购买不同的两卷可扣除5%的折扣,三卷10%,四卷20%,五卷
- 关于struts2.3.4项目跨站执行脚本以及远程执行漏洞修复概要
chenbowen00
strutsWEB安全
因为近期负责的几个银行系统软件,需要交付客户,因此客户专门请了安全公司对系统进行了安全评测,结果发现了诸如跨站执行脚本,远程执行漏洞以及弱口令等问题。
下面记录下本次解决的过程以便后续
1、首先从最简单的开始处理,服务器的弱口令问题,首先根据安全工具提供的测试描述中发现应用服务器中存在一个匿名用户,默认是不需要密码的,经过分析发现服务器使用了FTP协议,
而使用ftp协议默认会产生一个匿名用
- [电力与暖气]煤炭燃烧与电力加温
comsci
在宇宙中,用贝塔射线观测地球某个部分,看上去,好像一个个马蜂窝,又像珊瑚礁一样,原来是某个国家的采煤区.....
不过,这个采煤区的煤炭看来是要用完了.....那么依赖将起燃烧并取暖的城市,在极度严寒的季节中...该怎么办呢?
&nbs
- oracle O7_DICTIONARY_ACCESSIBILITY参数
daizj
oracle
O7_DICTIONARY_ACCESSIBILITY参数控制对数据字典的访问.设置为true,如果用户被授予了如select any table等any table权限,用户即使不是dba或sysdba用户也可以访问数据字典.在9i及以上版本默认为false,8i及以前版本默认为true.如果设置为true就可能会带来安全上的一些问题.这也就为什么O7_DICTIONARY_ACCESSIBIL
- 比较全面的MySQL优化参考
dengkane
mysql
本文整理了一些MySQL的通用优化方法,做个简单的总结分享,旨在帮助那些没有专职MySQL DBA的企业做好基本的优化工作,至于具体的SQL优化,大部分通过加适当的索引即可达到效果,更复杂的就需要具体分析了,可以参考本站的一些优化案例或者联系我,下方有我的联系方式。这是上篇。
1、硬件层相关优化
1.1、CPU相关
在服务器的BIOS设置中,可
- C语言homework2,有一个逆序打印数字的小算法
dcj3sjt126com
c
#h1#
0、完成课堂例子
1、将一个四位数逆序打印
1234 ==> 4321
实现方法一:
# include <stdio.h>
int main(void)
{
int i = 1234;
int one = i%10;
int two = i / 10 % 10;
int three = i / 100 % 10;
- apacheBench对网站进行压力测试
dcj3sjt126com
apachebench
ab 的全称是 ApacheBench , 是 Apache 附带的一个小工具 , 专门用于 HTTP Server 的 benchmark testing , 可以同时模拟多个并发请求。前段时间看到公司的开发人员也在用它作一些测试,看起来也不错,很简单,也很容易使用,所以今天花一点时间看了一下。
通过下面的一个简单的例子和注释,相信大家可以更容易理解这个工具的使用。
- 2种办法让HashMap线程安全
flyfoxs
javajdkjni
多线程之--2种办法让HashMap线程安全
多线程之--synchronized 和reentrantlock的优缺点
多线程之--2种JAVA乐观锁的比较( NonfairSync VS. FairSync)
HashMap不是线程安全的,往往在写程序时需要通过一些方法来回避.其实JDK原生的提供了2种方法让HashMap支持线程安全.
- Spring Security(04)——认证简介
234390216
Spring Security认证过程
认证简介
目录
1.1 认证过程
1.2 Web应用的认证过程
1.2.1 ExceptionTranslationFilter
1.2.2 在request之间共享SecurityContext
1
- Java 位运算
Javahuhui
java位运算
// 左移( << ) 低位补0
//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110 然后左移2位后,低位补0:
//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1 1000
System.out.println(6 << 2);// 运行结果是24
// 右移( >> ) 高位补"
- mysql免安装版配置
ldzyz007
mysql
1、my-small.ini是为了小型数据库而设计的。不应该把这个模型用于含有一些常用项目的数据库。
2、my-medium.ini是为中等规模的数据库而设计的。如果你正在企业中使用RHEL,可能会比这个操作系统的最小RAM需求(256MB)明显多得多的物理内存。由此可见,如果有那么多RAM内存可以使用,自然可以在同一台机器上运行其它服务。
3、my-large.ini是为专用于一个SQL数据
- MFC和ado数据库使用时遇到的问题
你不认识的休道人
sqlC++mfc
===================================================================
第一个
===================================================================
try{
CString sql;
sql.Format("select * from p
- 表单重复提交Double Submits
rensanning
double
可能发生的场景:
*多次点击提交按钮
*刷新页面
*点击浏览器回退按钮
*直接访问收藏夹中的地址
*重复发送HTTP请求(Ajax)
(1)点击按钮后disable该按钮一会儿,这样能避免急躁的用户频繁点击按钮。
这种方法确实有些粗暴,友好一点的可以把按钮的文字变一下做个提示,比如Bootstrap的做法:
http://getbootstrap.co
- Java String 十大常见问题
tomcat_oracle
java正则表达式
1.字符串比较,使用“==”还是equals()? "=="判断两个引用的是不是同一个内存地址(同一个物理对象)。 equals()判断两个字符串的值是否相等。 除非你想判断两个string引用是否同一个对象,否则应该总是使用equals()方法。 如果你了解字符串的驻留(String Interning)则会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
- SpringMVC 登陆拦截器实现登陆控制
xp9802
springMVC
思路,先登陆后,将登陆信息存储在session中,然后通过拦截器,对系统中的页面和资源进行访问拦截,同时对于登陆本身相关的页面和资源不拦截。
实现方法: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