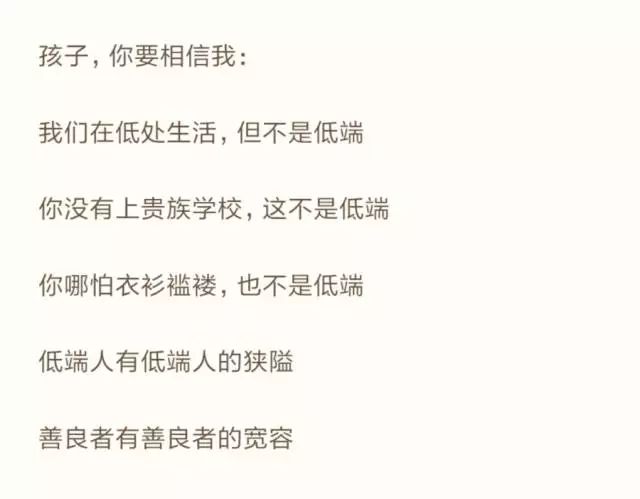先来做一个如果的设想。
如果达尔文没有提出物种进化论,如果法国人孟德斯鸠没有提出三权分立的主张,如果人们不知道法国人马克斯·韦伯的社会阶层理论,如果我八岁那年没有打死那只咬我的蚂蚁,那很多事情就会不一样,虽然好或坏不得而知。
什么物种进化,什么优胜劣汰,什么权利,什么阶层,什么以大欺小,什么以强欺弱,是不是就没有那么多广为流传的故事,现在也就没有那么多引人触目惊心事故。
说说一个还在童年时代记得位数不多的故事。
小时候生活无聊,没有找到玩伴就自己独自观察昆虫的活动,每个男孩小时候都是一个对未知世界的探险家,蚂蚁的群体活动是我观察的项目之一,虽然那时没有对蚂蚁活动行为的知识储备,但并不妨碍我对他们的行为感兴趣。
我用那双幼小的眼睛观看蚂蚁生活的世界,有些蚂蚁一直辛劳地在搬运食物,搬运泥巴草料筑巢,个头比一般的蚂蚁还要大,可以用皮黑精悍来形容,搬运比自己个头大两三倍的物体不在话下,两三个队友在一起就能拉动一条大昆虫,蚂蚁家族的晚餐就这样解决了,为此要看到蚂蚁搬运比自己体型大数倍的物体,我时常把一个粮食丢到蚂蚁窝的旁边,等待观察蚂蚁来搬运回家,这是不可多得的乐趣。
后来长大,上学学习一些生物学知识,才了解到蚂蚁世界的分工,知道我经常『调戏』那些搬东西的蚂蚁就是『工蚁』和『兵蚁』,它们干最辛苦的活,搬运泥巴建筑巢穴,相当于我们人类社会的农民工为城市建筑房子;寻找食物为蚁后提供食物来源,相当于我们人类社会的餐厅服务员;抚育后代的活也由这些工蚁和兵蚁来完成,可以看成人类社会出现的家政服务人员,比如奶妈;而大个头的兵蚁除了干以上这些活之外,防御家园打架也是它们的活,当遭到别的蚁群进行袭击时,兵蚁的责任就是保卫自己的家园,甚至付出自己的生命,所以这就是经常看到蚁窝周边残死兵蚁的尸体,这都是双方激战的结果。
在自然界中,这些看似弱小的蚂蚁就构成了一个蚁类世界,习惯人类世界运作的规则,更多看到的只是利己主义和排他主义,表面上打着集体主义的旗子过街招摇呐喊。
我们虽自认为自己是高等物种,但却学不到『蚂蚁的生存哲学』,蚂蚁在生死存亡面前不计患得患失,只要是集体利益需要,蚂蚁可以没日没夜辛苦劳作,甚至付出自己生命,秉持着一种利他主义精神在蚁群中生存,承担蚁群世界的分工,哪有那么多我们现在网络中热论的阶层、等级、高端、低端……
关于蚂蚁的故事,大家最为熟悉的真是故事,在非洲大丛林里,一场大火把一群蚂蚁团团围住,眼看自己生存逃生的领地越来越小,面对大伙,无数小蚂蚁的性命危在旦夕。此时,蚁群迅速围成一团蚁球滚出火海,外面的蚂蚁被活活烧死,大部分蚂蚁逃过此难。
也许我们生活的矩序过于复杂,燃烧一场大火就会揪出很多本该存留的矛盾,有人努力去掩饰矛盾的存在,有人想去清除引起矛盾的本源,这些矛盾的背后一切都是归于人为,驱赶并不会解决问题最优的办法。
往大的方向说,每个物种的世界每个个体都承担相应的分工;往小的方向说,既然热衷分层级,本就不该有高低端之分,不该有隔断,因为你们所认为的低端是别人暂时在底处的生活,有的人生很快就走出去,有人可能会生活长一点而已。
在我生活的地方,只要是工作日,我每天都会从小区通过一条小路到达上班的园区,路上的左侧是一个废品场,右侧是正在施工建筑的写字楼商业区,楼下是马上要建成的地铁口,过不了多久这里就会变成一个新的商圈,进进出出的不再是提着超大饮水杯,穿着破旧染满混泥土灰尘的农民工,推着三轮小车捡破烂的大叔大妈,而是穿着靓丽,鞋包明亮的白领上班族,还有身穿黄色、蓝色骑着摩托车的送餐员。
那些人将会去到你看不见的地方,又有可能出现在那片围起来即将开发的地方,只是你不曾认出其中任何一个人的面孔。
今年夏天的某个周末下午,在公司加班,像往常一样走路回到住处,路过那个废品场时看到几个小孩在破烂堆里玩耍,穿衣有些脏兮兮,笑声明亮。
我走进去一看,一个手里拿着破旧大嘴猴的布娃娃,一个手持一把已经断掉一半的玩具枪,一个骑着需要自己坐在上面用力使劲摇才能晃动的摇摇车,一个穿着比他脚大好几倍的轮滑鞋,地上还有一个漏气干瘪的排球,他们拿来当足球踢……
这些物品没有一件是完好的,没有一件的他们自己新买的,那几个小孩是生活在垃圾场几户人家的小孩,他们的父母在废品场生活。
有的去周边商场、办公区、小区收集废弃的纸箱,饮料瓶,废弃的电缆,废弃建筑里拉出来的钢筋,废弃的自行车……只要别人不用能卖钱的废品,通过那台自己组装的三轮小车拉回废弃场;有的在废弃场开装卸车,把废弃品装载到卡车上,每天早上都会几辆卡车来运输这些废弃物品到其他地方加工。
然后,再回我们的生活中,包着价值昂贵物品的快递箱子,深夜便利边冰柜里形色各异的饮料,摆放在路边的各种颜色的共享单车……
我不知道这个废品场里的废品是否有一件循环到我手中,但肯定会循环到在城市生活的另一个人手中,是谁提供给我们在城市生活便利的一切?
当你道知道这些孩子为什么没有昂贵的玩具的时,他们会说爸妈不给他们买,慢慢他们会明白爸妈不给他们买是因为他们家庭生活需要钱,读书需要钱,他们的父母坚信读书是从现在所处低处的生活中走出去的理由,这是他们能想到唯一解决的办法,只要快乐的生活着就没有高低端之分。
看着他们在废品场简陋的住处,做饭的厨房就房子外面,风吹日晒的厨房做出一家人吃的饭菜,这种情况即使有一百万个不愿意和无能无力,你曾试问过他们是不是比原来好一点,收入多一点?
很多他们这样的群体,没有正式劳务合同,没有这座城市的社保,甚至没有这座城市的居住证,意味着这些孩子不可能在这座城市读书,这里他们付不起费用给孩子接受学前教育,这些孩子即将回到他们的家乡。
他们也许会给家乡的其他孩子讲诉他们看到城市的高楼,灯火阑珊,挤满人的地铁车厢,只能看外边看看的游乐场……
就像拿着把断掉一半的玩具枪男孩说的一样,他们有梦想,他指着对面正在装修的高楼,他想成为那个拿着图纸的建筑师,画一座比这栋还要漂亮还要高的大楼;拿着大嘴猴的男孩说想盖一座很大很大的游乐场,起着摇摇的车男孩说想成为一个赛车手……
这些梦想对你来说可能天真得有点可笑,我们不能够确定这些他们心中单纯的梦想,正在引领他们走出这个低处的生活,让我想到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中写到:『如果你想知道周围有多么黑暗,你就得留意远处的微弱光线。』
如果有更好的选择,谁会愿意在泥沼中苟且。
现在这个废品场已经被围起来,右侧的写字楼商业区即将完成,隐约地看到挖土机的挖臂已经有一半伸到废品场,那几间简陋的房子屋顶插着一面五星红旗,经过右侧灰泥土洗礼,风吹日晒,日常看起来显得有些陈旧,在快要落山的太阳照耀下,看起个格外明亮。
当挖掘机翻过那条路来到这个废品场,他们又将往何处?哪几个笑声明亮的小孩去了哪里?
如果再遇到,我想把余秀华的这首诗送给他们:
『在梦中的城市里,他正值青春,而到达依西多拉城时,他已年老,广场上有一堵墙,老人们倚坐在那里看着过往的年轻人,他和这些老人并坐在一起。当初的欲望已是记忆。』
音乐|知道世界的尽头
题图|废品场的路灯 阿礼尔拍摄
到你来说
说说你如何从低处的生活中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