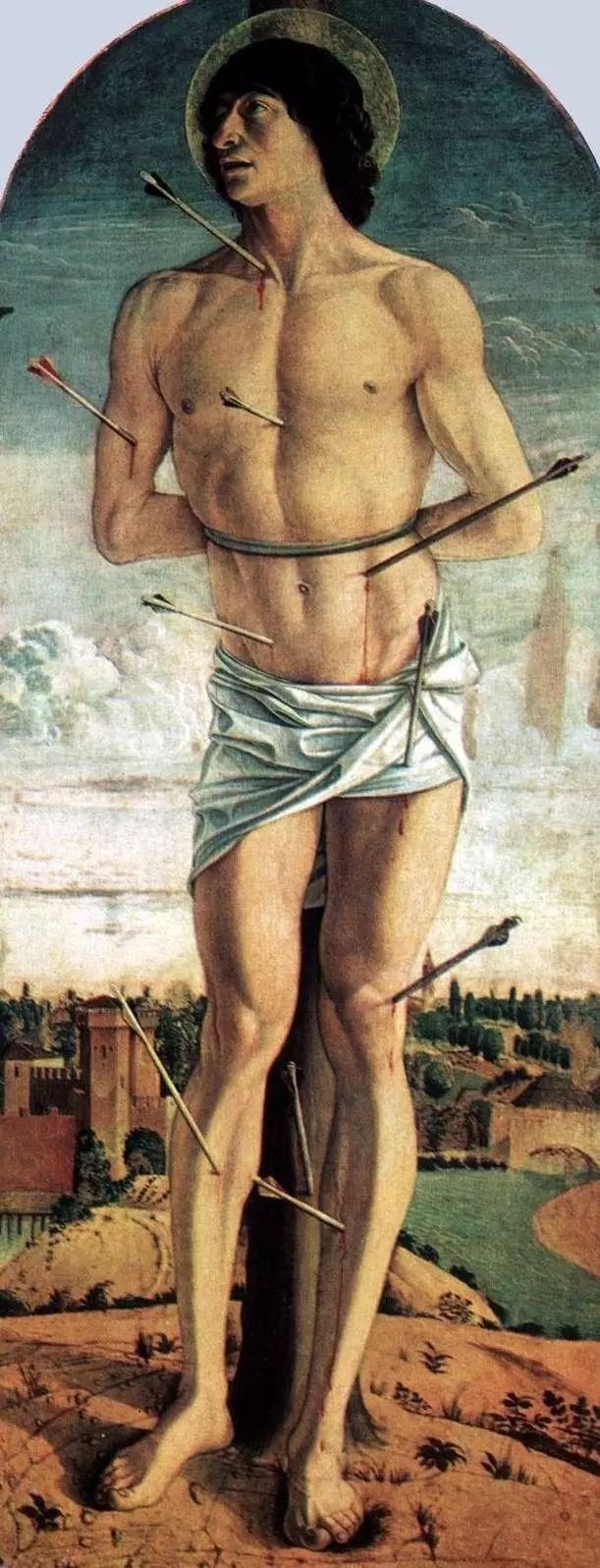- C++ 11 Lambda表达式和min_element()与max_element()的使用_c++ lamda函数 min_element((1)
2401_84976182
程序员c语言c++学习
既有适合小白学习的零基础资料,也有适合3年以上经验的小伙伴深入学习提升的进阶课程,涵盖了95%以上CC++开发知识点,真正体系化!由于文件比较多,这里只是将部分目录截图出来,全套包含大厂面经、学习笔记、源码讲义、实战项目、大纲路线、讲解视频,并且后续会持续更新如果你需要这些资料,可以戳这里获取#include#include#includeusingnamespacestd;boolcmp(int
- Leetcode 148. 排序链表
文章目录前引题目代码(首刷看题解)代码(8.9二刷部分看解析)代码(9.15三刷部分看解析)前引综合性比较强的一道题,要求时间复杂度必须O(logn)才能通过,最适合链表的排序算法就是归并。这里采用自顶向下的方法步骤:找到链表中点(双指针)对两个子链表排序(递归,直到只有一个结点,记得将子链表最后指向nullptr)归并(引入dummy结点)题目Leetcode148.排序链表代码(首刷看题解)c
- 精通Canvas:15款时钟特效代码实现指南
烟幕缭绕
本文还有配套的精品资源,点击获取简介:HTML5的Canvas是一个用于绘制矢量图形的API,通过JavaScript实现动态效果。本项目集合了15种不同的时钟特效代码,帮助开发者通过学习绘制圆形、线条、时间更新、旋转、颜色样式设置及动画效果等概念,深化对Canvas的理解和应用。项目中的CSS文件负责时钟的样式设定,而JS文件则包含实现各种特效的逻辑,通过不同的函数或类处理时间更新和动画绘制,提
- 嵌入式系统LCD显示模块编程实践
本文还有配套的精品资源,点击获取简介:本文档提供了一个具有800x480分辨率的3.5英寸液晶显示模块LW350AC9001的驱动程序代码,以及嵌入式系统中使用C/C++语言进行硬件编程的实践指南。该模块的2mm厚度使其适用于空间受限的便携式设备。内容包括驱动程序源代码、硬件控制接口使用方法,以及如何在嵌入式系统中进行图形处理、电源管理与性能优化。1.嵌入式系统原理1.1嵌入式系统概念嵌入式系统是
- 深入剖析OpenJDK 18 GA源码:Java平台最新发展
想法臃肿
本文还有配套的精品资源,点击获取简介:OpenJDK18GA作为Java开发的关键里程碑,提供了诸多新特性和改进。本文章深入探讨了OpenJDK18GA源码,揭示其内部机制,帮助开发者更好地理解和利用这个版本。文章还涵盖了PatternMatching、SealedClasses、Records、JEP395、JEP406和JEP407等特性,以及HotSpot虚拟机、编译器、垃圾收集器、内存模型
- Python爱心光波
系列文章序号直达链接Tkinter1Python李峋同款可写字版跳动的爱心2Python跳动的双爱心3Python蓝色跳动的爱心4Python动漫烟花5Python粒子烟花Turtle1Python满屏飘字2Python蓝色流星雨3Python金色流星雨4Python漂浮爱心5Python爱心光波①6Python爱心光波②7Python满天繁星8Python五彩气球9Python白色飘雪10Pyt
- Python流星雨
Want595
python开发语言
文章目录系列文章写在前面技术需求完整代码代码分析1.模块导入2.画布设置3.画笔设置4.颜色列表5.流星类(Star)6.流星对象创建7.主循环8.流星运动逻辑9.视觉效果10.总结写在后面系列文章序号直达链接表白系列1Python制作一个无法拒绝的表白界面2Python满屏飘字表白代码3Python无限弹窗满屏表白代码4Python李峋同款可写字版跳动的爱心5Python流星雨代码6Python
- 基于链家网的二手房数据采集清洗与可视化分析
Mint_Datazzh
项目selenium网络爬虫
个人学习内容笔记,仅供参考。项目链接:https://gitee.com/rongwu651/lianjia原文链接:基于链家网的二手房数据采集清洗与可视化分析–笔墨云烟研究内容该课题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将二手房网站上的存量与已销售房源,构建一个二手房市场行情情况与房源特点的可视化平台。该平台通过HTML架构和Echarts完成可视化的搭建。因此,该课题的主要研究内容就是如何利用相关技术设计并实现这样
- 【超硬核】JVM源码解读:Java方法main在虚拟机上解释执行
HeapDump性能社区
java开发语言后端jvm
本文由HeapDump性能社区首席讲师鸠摩(马智)授权整理发布第1篇-关于Java虚拟机HotSpot,开篇说的简单点开讲Java运行时,这一篇讲一些简单的内容。我们写的主类中的main()方法是如何被Java虚拟机调用到的?在Java类中的一些方法会被由C/C++编写的HotSpot虚拟机的C/C++函数调用,不过由于Java方法与C/C++函数的调用约定不同,所以并不能直接调用,需要JavaC
- 算法学习笔记:15.二分查找 ——从原理到实战,涵盖 LeetCode 与考研 408 例题
呆呆企鹅仔
算法学习算法学习笔记考研二分查找
在计算机科学的查找算法中,二分查找以其高效性占据着重要地位。它利用数据的有序性,通过不断缩小查找范围,将原本需要线性时间的查找过程优化为对数时间,成为处理大规模有序数据查找问题的首选算法。二分查找的基本概念二分查找(BinarySearch),又称折半查找,是一种在有序数据集合中查找特定元素的高效算法。其核心原理是:通过不断将查找范围减半,快速定位目标元素。与线性查找逐个遍历元素不同,二分查找依赖
- 2025代码块种类以及作用
2501_92758067
intellij-ideaphpstormideajupyter
https://www.bilibili.com/opus/1088624478422827030https://www.bilibili.com/opus/1088624529930977287https://t.bilibili.com/1088633635294150662https://www.bilibili.com/opus/1088633635294150662https://t.b
- Python 脚本最佳实践2025版
前文可以直接把这篇文章喂给AI,可以放到AI角色设定里,也可以直接作为提示词.这样,你只管提需求,写脚本就让AI来.概述追求简洁和清晰:脚本应简单明了。使用函数(functions)、常量(constants)和适当的导入(import)实践来有逻辑地组织你的Python脚本。使用枚举(enumerations)和数据类(dataclasses)等数据结构高效管理脚本状态。通过命令行参数增强交互性
- LeetCode算法题:电话号码的字母组合
吱屋猪_
算法leetcodejava
题目描述:给定一个仅包含数字2-9的字符串,返回所有它能表示的字母组合。答案可以按任意顺序返回。给出数字到字母的映射如下(与电话按键相同)。注意1不对应任何字母。2->"abc"3->"def"4->"ghi"5->"jkl"6->"mno"7->"pqrs"8->"tuv"9->"wxyz"例如,给定digits="23",返回["ad","ae","af","bd","be","bf","cd
- Python七彩花朵
Want595
python开发语言
系列文章序号直达链接Tkinter1Python李峋同款可写字版跳动的爱心2Python跳动的双爱心3Python蓝色跳动的爱心4Python动漫烟花5Python粒子烟花Turtle1Python满屏飘字2Python蓝色流星雨3Python金色流星雨4Python漂浮爱心5Python爱心光波①6Python爱心光波②7Python满天繁星8Python五彩气球9Python白色飘雪10Pyt
- 深入解析 TCP 连接状态与进程挂起、恢复与关闭
誰能久伴不乏
tcp/ip网络服务器
文章目录深入解析TCP连接状态与进程挂起、恢复与关闭一、TCP连接的各种状态1.**`LISTEN`**(监听)2.**`SYN_SENT`**(SYN已发送)3.**`SYN_RECEIVED`**(SYN已接收)4.**`ESTABLISHED`**(已建立)5.**`FIN_WAIT_1`**(关闭等待1)6.**`FIN_WAIT_2`**(关闭等待2)7.**`CLOSE_WAIT`**
- 【前端】jQuery数组合并去重方法总结
在jQuery中合并多个数组并去重,推荐使用原生JavaScript的Set对象(高效简单)或$.unique()(仅适用于DOM元素,不适用于普通数组)。以下是完整解决方案:方法1:使用ES6Set(推荐)//定义多个数组constarr1=[1,2,3];constarr2=[2,3,4];constarr3=[3,4,5];//合并数组并用Set去重constmergedArray=[...
- CentOS7环境卸载MySQL5.7
Hadoop_Liang
mysql数据库mysql
备份重要数据切记,卸载之前先备份mysql重要的数据。备份一个数据库例如:备份名为mydatabase的数据库到backup.sql的文件中mysqldump-uroot-ppassword123mydatabase>backup.sql备份所有数据库mysqldump-uroot-ppassword123--all-databases>all_databases_backup.sql注意:-p后
- centos7安装 mysql5.7(安装包)
heiPony
linuxmysqlmariadbcentosmysql
一.卸载centos7自带数据库查看系统自带的Mariadbrpm-qa|grepmariadbmariadb-libs-5.5.44-2.el7.centos.x86_64卸载rpm-e--nodepsmariadb-libs-5.5.44-2.el7.centos.x86_64删除etc目录下的my.cnfrm/etc/my.cnf二.检查mysql是否存在(有就卸载,删除相关文件)rpm-q
- EMQX 社区版单机和集群部署
pcj_888
MQTTMQTTEMQ
EMQ支持Docker,宿主机,k8s部署;支持单机或集群部署。以下给出EMQX社区版单机和集群部署方法1.Docker单机部署官方推荐最小配置:2核4G下载容器镜像dockerpullemqx/emqx:5.3.2启动容器dockerrun-d--nameemqx\-p1883:1883\-p8083:8083\-p8883:8883\-p8084:8084\-p18083:18083\emqx
- npm proxy setting
kjndppl
[Node.jsJavaScriptnpmhttpsproxypassword
清理npmconfigdeletehttp-proxynpmconfigdeletehttps-proxy具体设置步骤如下:1.执行npmconfig后,将看到下一行提示信息npmconfigls-ltoshowalldefaults.2.执行npmconfigls-l后,在一大长串的settign中找出userconfig项(大概位于倒数第4项)[b]userconfig[/b]="C:\\Us
- Shader面试题100道之(81-100)
还是大剑师兰特
#Shader综合教程100+大剑师shader面试题shader教程
Shader面试题(第81-100题)以下是第81到第100道Shader相关的面试题及答案:81.Unity中如何实现屏幕空间的热扭曲效果(HeatDistortion)?热扭曲效果可以通过GrabPass抓取当前屏幕图像,然后在片段着色器中使用噪声或动态UV偏移模拟空气扰动,再结合一个透明通道控制扭曲强度来实现。82.Shader中如何实现物体轮廓高亮(OutlineHighlight)?轮廓
- Linux/Centos7离线安装并配置MySQL 5.7
有事开摆无事百杜同学
LInux/CentOS7linuxmysql运维
Linux/Centos7离线安装并配置MySQL5.7超详细教程一、环境准备1.下载MySQL5.7离线包2.使用rpm工具卸载MariaDB(避免冲突)3.创建系统级别的MySQL专用用户二、安装与配置1.解压并重命名MySQL目录2.创建数据目录和配置文件3.设置目录权限4.初始化MySQL5.配置启动脚本6.配置环境变量三、启动与验证1.启动MySQL服务2.获取初始密码3.登录并修改密码
- 前端 NPM 包的依赖可视化分析工具推荐
前端视界
前端艺匠馆前端npmarcgisai
前端NPM包的依赖可视化分析工具推荐关键词:NPM、依赖管理、可视化分析、前端工程、包管理、依赖冲突、性能优化摘要:本文将深入探讨前端开发中NPM包依赖可视化分析的重要性,介绍5款主流工具的使用方法和特点,并通过实际案例展示如何利用这些工具优化项目依赖结构、解决版本冲突问题以及提升构建性能。文章将帮助开发者更好地理解和掌控项目依赖关系,提高开发效率和项目可维护性。背景介绍目的和范围本文旨在为前端开
- Linux操作系统磁盘管理
CZZDg
linux运维服务器
目录一.硬盘介绍1.硬盘的物理结构2.CHS编号3.磁盘存储划分4.开机流程5.要点6.磁盘存储数据的形式二.Linux文件系统1.根文件系统2.虚拟文件系统3.真文件系统4.伪文件系统三.磁盘分区与挂载1.磁盘分区方式2.分区命令3.查看与识别命令4.格式化命令5.挂载命令四.LVM逻辑卷1.概述2.管理命令五.磁盘配额1.概述usrquota:支持对用户的磁盘配额grpquota:支持对组的磁
- 计算机网络技术
CZZDg
计算机网络
目录一.网络概述1.网络的概念2.网络发展是3.网络的四要素4.网络功能5.网络类型6.网络协议与标准7.网络中常见的概念8.网络拓补结构二.网络模型1.分层思想2.OSI七层模型3.TCP/IP五层模型4.数据的封装与解封装过程三.IP地址1.进制转换2.IP地址定义3.IP地址组成成分4.IP地址分类5.地址划分6、相关概念一.网络概述1.网络的概念两个主机通过传输介质和通信协议实现通信和资源
- npm 切换 node 版本 和npm的源
爱敲代码的小冰
npm前端node.js
在开发过程中,不同项目可能需要不同版本的Node.js,同时于由XX原因,我们需要切换npm的源。这时如果需要切换node版本或者npm的源,我们可以使用以下方法。使用nvm切换Node版本1、安装npminstallnvm-g2、使用#列出所有可用版本nvmlist-remote#安装指定版本nvminstall16.15.1#使用指定版本nvmuse16.15.1#查看当前使用的版本nvmcu
- ThinkSound V2版 - 一键给无声视频配音,为AI视频生成匹配音效 支持50系显卡 一键整合包下载
昨日之日2006
ai语音音视频人工智能
ThinkSound是阿里通义实验室开源的首个音频生成模型,它能够让AI像专业“音效师”一样,根据视频内容生成高度逼真、与视觉内容完美契合的音频。ThinkSound可直接应用于影视后期制作,为AI生成的视频自动匹配精准的环境噪音与爆炸声效;服务于游戏开发领域,实时生成雨势变化等动态场景的自适应音效;同时可以无障碍视频生产,为视障用户同步生成画面描述与环境音效。今天分享的ThinkSoundV2版
- 无线鼠标产品整体技术分析总结
悟空胆好小
计算机外设
无线鼠标产品对比分析,以小米为例文章目录无线鼠标产品对比分析,以小米为例一.小米无线鼠标产品对比1.1小米无线鼠标XMSMSB05YM2.4G单模款1.2小米无线鼠标XMSMSB01YM2.4G+BT双模款二.**单模鼠标与双模的区别****1.连接方式****2.通信性能与可靠性****3.功耗管理****4.适用场景****5.技术扩展性**6.**小结**三.无线鼠标产品技术重点分析3.1.
- 微软 Bluetooth LE Explorer 实用工具的详细使用分析
悟空胆好小
microsoft
微软BluetoothLEExplorer实用工具的详细使用分析文章目录微软**BluetoothLEExplorer**实用工具的详细使用分析1.**工具定位与核心功能**2.**关键特性与更新**3.**使用场景示例**4.**系统要求与依赖**5.**与专业工具对比**6.**局限性**7.**实践建议**结论以下是微软BluetoothLEExplorer实用工具的详细使用分析:1.工具定
- 消息中间件巡检
搬砖小常
消息中间件运维笔记RocketMQkafka中间件巡检运维
除资源使用情况外,消息中间件RocketMQ、kafka还可以巡检哪些?一、RocketMQ巡检1、检查broker写入耗时是否有压力2、检查brokerbusy的数量与频率3、主题发送TPS、发送错误率巡检4、从节点消费情况检查5、集群各broker消息流转情况巡检二、Kafka巡检1、检查是否有分区发生ISR频繁扩张收缩2、检查分区leader选举值是否处于正常水平3、检查controller
- 数据采集高并发的架构应用
3golden
.net
问题的出发点:
最近公司为了发展需要,要扩大对用户的信息采集,每个用户的采集量估计约2W。如果用户量增加的话,将会大量照成采集量成3W倍的增长,但是又要满足日常业务需要,特别是指令要及时得到响应的频率次数远大于预期。
&n
- 不停止 MySQL 服务增加从库的两种方式
brotherlamp
linuxlinux视频linux资料linux教程linux自学
现在生产环境MySQL数据库是一主一从,由于业务量访问不断增大,故再增加一台从库。前提是不能影响线上业务使用,也就是说不能重启MySQL服务,为了避免出现其他情况,选择在网站访问量低峰期时间段操作。
一般在线增加从库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mysqldump备份主库,恢复到从库,mysqldump是逻辑备份,数据量大时,备份速度会很慢,锁表的时间也会很长。另一种是通过xtrabacku
- Quartz——SimpleTrigger触发器
eksliang
SimpleTriggerTriggerUtilsquartz
转载请出自出处:http://eksliang.iteye.com/blog/2208166 一.概述
SimpleTrigger触发器,当且仅需触发一次或者以固定时间间隔周期触发执行;
二.SimpleTrigger的构造函数
SimpleTrigger(String name, String group):通过该构造函数指定Trigger所属组和名称;
Simpl
- Informatica应用(1)
18289753290
sqlworkflowlookup组件Informatica
1.如果要在workflow中调用shell脚本有一个command组件,在里面设置shell的路径;调度wf可以右键出现schedule,现在用的是HP的tidal调度wf的执行。
2.designer里面的router类似于SSIS中的broadcast(多播组件);Reset_Workflow_Var:参数重置 (比如说我这个参数初始是1在workflow跑得过程中变成了3我要在结束时还要
- python 获取图片验证码中文字
酷的飞上天空
python
根据现成的开源项目 http://code.google.com/p/pytesser/改写
在window上用easy_install安装不上 看了下源码发现代码很少 于是就想自己改写一下
添加支持网络图片的直接解析
#coding:utf-8
#import sys
#reload(sys)
#sys.s
- AJAX
永夜-极光
Ajax
1.AJAX功能:动态更新页面,减少流量消耗,减轻服务器负担
2.代码结构:
<html>
<head>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function loadXMLDoc()
{
.... AJAX script goes here ...
- 创业OR读研
随便小屋
创业
现在研一,有种想创业的想法,不知道该不该去实施。因为对于的我情况这两者是矛盾的,可能就是鱼与熊掌不能兼得。
研一的生活刚刚过去两个月,我们学校主要的是
- 需求做得好与坏直接关系着程序员生活质量
aijuans
IT 生活
这个故事还得从去年换工作的事情说起,由于自己不太喜欢第一家公司的环境我选择了换一份工作。去年九月份我入职现在的这家公司,专门从事金融业内软件的开发。十一月份我们整个项目组前往北京做现场开发,从此苦逼的日子开始了。
系统背景:五月份就有同事前往甲方了解需求一直到6月份,后续几个月也完
- 如何定义和区分高级软件开发工程师
aoyouzi
在软件开发领域,高级开发工程师通常是指那些编写代码超过 3 年的人。这些人可能会被放到领导的位置,但经常会产生非常糟糕的结果。Matt Briggs 是一名高级开发工程师兼 Scrum 管理员。他认为,单纯使用年限来划分开发人员存在问题,两个同样具有 10 年开发经验的开发人员可能大不相同。近日,他发表了一篇博文,根据开发者所能发挥的作用划分软件开发工程师的成长阶段。
初
- Servlet的请求与响应
百合不是茶
servletget提交java处理post提交
Servlet是tomcat中的一个重要组成,也是负责客户端和服务端的中介
1,Http的请求方式(get ,post);
客户端的请求一般都会都是Servlet来接受的,在接收之前怎么来确定是那种方式提交的,以及如何反馈,Servlet中有相应的方法, http的get方式 servlet就是都doGet(
- web.xml配置详解之listener
bijian1013
javaweb.xmllistener
一.定义
<listener>
<listen-class>com.myapp.MyListener</listen-class>
</listener>
二.作用 该元素用来注册一个监听器类。可以收到事件什么时候发生以及用什么作为响
- Web页面性能优化(yahoo技术)
Bill_chen
JavaScriptAjaxWebcssYahoo
1.尽可能的减少HTTP请求数 content
2.使用CDN server
3.添加Expires头(或者 Cache-control) server
4.Gzip 组件 server
5.把CSS样式放在页面的上方。 css
6.将脚本放在底部(包括内联的) javascript
7.避免在CSS中使用Expressions css
8.将javascript和css独立成外部文
- 【MongoDB学习笔记八】MongoDB游标、分页查询、查询结果排序
bit1129
mongodb
游标
游标,简单的说就是一个查询结果的指针。游标作为数据库的一个对象,使用它是包括
声明
打开
循环抓去一定数目的文档直到结果集中的所有文档已经抓取完
关闭游标
游标的基本用法,类似于JDBC的ResultSet(hasNext判断是否抓去完,next移动游标到下一条文档),在获取一个文档集时,可以提供一个类似JDBC的FetchSize
- ORA-12514 TNS 监听程序当前无法识别连接描述符中请求服务 的解决方法
白糖_
ORA-12514
今天通过Oracle SQL*Plus连接远端服务器的时候提示“监听程序当前无法识别连接描述符中请求服务”,遂在网上找到了解决方案:
①打开Oracle服务器安装目录\NETWORK\ADMIN\listener.ora文件,你会看到如下信息:
# listener.ora Network Configuration File: D:\database\Oracle\net
- Eclipse 问题 A resource exists with a different case
bozch
eclipse
在使用Eclipse进行开发的时候,出现了如下的问题:
Description Resource Path Location TypeThe project was not built due to "A resource exists with a different case: '/SeenTaoImp_zhV2/bin/seentao'.&
- 编程之美-小飞的电梯调度算法
bylijinnan
编程之美
public class AptElevator {
/**
* 编程之美 小飞 电梯调度算法
* 在繁忙的时间,每次电梯从一层往上走时,我们只允许电梯停在其中的某一层。
* 所有乘客都从一楼上电梯,到达某层楼后,电梯听下来,所有乘客再从这里爬楼梯到自己的目的层。
* 在一楼时,每个乘客选择自己的目的层,电梯则自动计算出应停的楼层。
* 问:电梯停在哪
- SQL注入相关概念
chenbowen00
sqlWeb安全
SQL Injection:就是通过把SQL命令插入到Web表单递交或输入域名或页面请求的查询字符串,最终达到欺骗服务器执行恶意的SQL命令。
具体来说,它是利用现有应用程序,将(恶意)的SQL命令注入到后台数据库引擎执行的能力,它可以通过在Web表单中输入(恶意)SQL语句得到一个存在安全漏洞的网站上的数据库,而不是按照设计者意图去执行SQL语句。
首先让我们了解什么时候可能发生SQ
- [光与电]光子信号战防御原理
comsci
原理
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后方,敌人都有可能用光子信号对人体进行控制和攻击,那么采取什么样的防御方法,最简单,最有效呢?
我们这里有几个山寨的办法,可能有些作用,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实验一下
根据光
- oracle 11g新特性:Pending Statistics
daizj
oracledbms_stats
oracle 11g新特性:Pending Statistics 转
从11g开始,表与索引的统计信息收集完毕后,可以选择收集的统信息立即发布,也可以选择使新收集的统计信息处于pending状态,待确定处于pending状态的统计信息是安全的,再使处于pending状态的统计信息发布,这样就会避免一些因为收集统计信息立即发布而导致SQL执行计划走错的灾难。
在 11g 之前的版本中,D
- 快速理解RequireJs
dengkane
jqueryrequirejs
RequireJs已经流行很久了,我们在项目中也打算使用它。它提供了以下功能:
声明不同js文件之间的依赖
可以按需、并行、延时载入js库
可以让我们的代码以模块化的方式组织
初看起来并不复杂。 在html中引入requirejs
在HTML中,添加这样的 <script> 标签:
<script src="/path/to
- C语言学习四流程控制if条件选择、for循环和强制类型转换
dcj3sjt126com
c
# include <stdio.h>
int main(void)
{
int i, j;
scanf("%d %d", &i, &j);
if (i > j)
printf("i大于j\n");
else
printf("i小于j\n");
retu
- dictionary的使用要注意
dcj3sjt126com
IO
NSDictionary *dict = [NSDictionary dictionaryWithObjectsAndKeys:
user.user_id , @"id",
user.username , @"username",
- Android 中的资源访问(Resource)
finally_m
xmlandroidStringdrawablecolor
简单的说,Android中的资源是指非代码部分。例如,在我们的Android程序中要使用一些图片来设置界面,要使用一些音频文件来设置铃声,要使用一些动画来显示特效,要使用一些字符串来显示提示信息。那么,这些图片、音频、动画和字符串等叫做Android中的资源文件。
在Eclipse创建的工程中,我们可以看到res和assets两个文件夹,是用来保存资源文件的,在assets中保存的一般是原生
- Spring使用Cache、整合Ehcache
234390216
springcacheehcache@Cacheable
Spring使用Cache
从3.1开始,Spring引入了对Cache的支持。其使用方法和原理都类似于Spring对事务管理的支持。Spring Cache是作用在方法上的,其核心思想是这样的:当我们在调用一个缓存方法时会把该方法参数和返回结果作为一个键值对存放在缓存中,等到下次利用同样的
- 当druid遇上oracle blob(clob)
jackyrong
oracle
http://blog.csdn.net/renfufei/article/details/44887371
众所周知,Oracle有很多坑, 所以才有了去IOE。
在使用Druid做数据库连接池后,其实偶尔也会碰到小坑,这就是使用开源项目所必须去填平的。【如果使用不开源的产品,那就不是坑,而是陷阱了,你都不知道怎么去填坑】
用Druid连接池,通过JDBC往Oracle数据库的
- easyui datagrid pagination获得分页页码、总页数等信息
ldzyz007
var grid = $('#datagrid');
var options = grid.datagrid('getPager').data("pagination").options;
var curr = options.pageNumber;
var total = options.total;
var max =
- 浅析awk里的数组
nigelzeng
二维数组array数组awk
awk绝对是文本处理中的神器,它本身也是一门编程语言,还有许多功能本人没有使用到。这篇文章就单单针对awk里的数组来进行讨论,如何利用数组来帮助完成文本分析。
有这么一组数据:
abcd,91#31#2012-12-31 11:24:00
case_a,136#19#2012-12-31 11:24:00
case_a,136#23#2012-12-31 1
- 搭建 CentOS 6 服务器(6) - TigerVNC
rensanning
centos
安装GNOME桌面环境
# yum groupinstall "X Window System" "Desktop"
安装TigerVNC
# yum -y install tigervnc-server tigervnc
启动VNC服务
# /etc/init.d/vncserver restart
# vncser
- Spring 数据库连接整理
tomcat_oracle
springbeanjdbc
1、数据库连接jdbc.properties配置详解 jdbc.url=jdbc:hsqldb:hsql://localhost/xdb jdbc.username=sa jdbc.password= jdbc.driver=不同的数据库厂商驱动,此处不一一列举 接下来,详细配置代码如下:
Spring连接池
- Dom4J解析使用xpath java.lang.NoClassDefFoundError: org/jaxen/JaxenException异常
xp9802
用Dom4J解析xml,以前没注意,今天使用dom4j包解析xml时在xpath使用处报错
异常栈:java.lang.NoClassDefFoundError: org/jaxen/JaxenException异常
导入包 jaxen-1.1-beta-6.jar 解决;
&n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