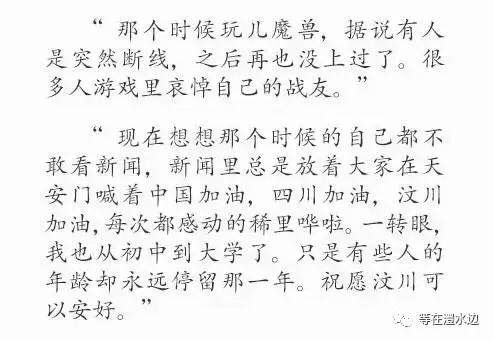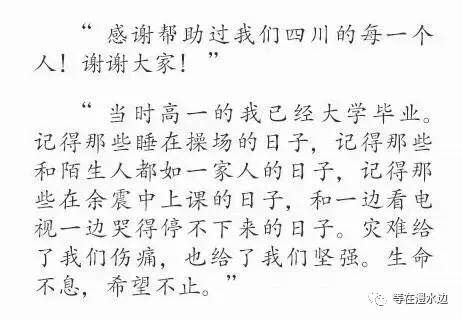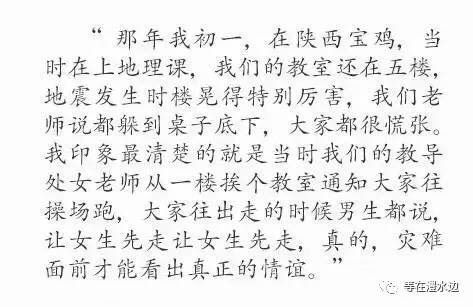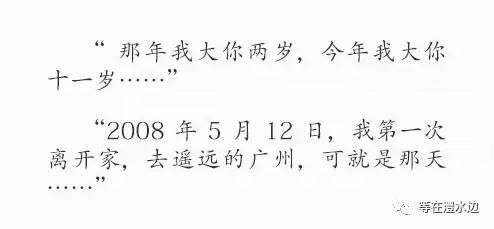在有限的时空里,过无限广大的日子
——三毛
每到5.12,网上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汶川地震时你在做什么?
回答这个问题我不用思考,那时我正在三楼上课,下午的第一节。
突然教室一阵骚动,学生都低头看地面,当时他们给我的感觉是:他们发现了一只老鼠,他们的目光从前面一直随它追到后面。
还有学生说:老师,他在后面推我座位。
而站立的我摇晃了一下,反射弧比较长的我居然都没意识到是地震,我扶着一个学生的课桌稳了稳心神,心想这向太劳累了,然后听到紧邻教室的后街传来人群的嘈杂声,后来又发现校园里也聚满了从教室跑出来的师生,我这才意识到地震了,要学生紧急下楼。
下到二楼时,我跑到当时我担任班主任的56班,要他们也赶快下楼。
后来我常常想,如果我是处于汶川地震重灾区,我一定是连那年5.12的黄昏都已看不到的人,这还不是最坏的,还有那么多娃,一想到这点都好后怕,感觉罪不可赦。
也算天佑钝人。
记得当时儿子在对面的北楼教学楼,他的班主任早已把他们疏散出来了,我看见他立在早已标为危墙的图书馆边,我跑过去要他和他的几位同学立即走开。
有个同事给她成都的姐姐打电话,无法拨通,给她姐夫打,也没打通,同事们安慰她,这可能只是信号中断,安慰着安慰着,就都抱着哭了起来。
我太理解她的心情了。记得是2000年吧,北京闹非典很严重,我天天守着电视机看北京疫情,那段时间不但没好转,还有人因此丧生。我害怕得不行,我老弟在北京,当时座机电话都还没普及,我跑到隔壁霞老师家给我老弟打电话,打了三遍都没人接听,我坐在电话机旁嚎啕大哭起来。
霞老师就安慰我,说北京那么大,感染的人概率还是蛮小的。
我不甘心,再打,终于有人接了,是一个陌生人,他是我老弟所在的外企员工,他们正在开会,开会前都必须要交出手机的。
我简单地问了他们那里的基本情况,连说抱歉了打扰了,心里十分释然地放了电话。
同事后来也了解到,成都虽然也地震了,伤亡较小,姐姐一家幸好没事。
虽然湖南石门离震源比较远,但还是到处弥漫着一种紧张危险的气氛,晚上大家都不敢深睡,事实上,很多人没敢进屋睡。
当时我想让儿子能好好休息,但又怕地震真的会发生,我就和他爸爸站在他的床头守着。
大概深夜一点,小区院子里的人越来越多,人声鼎沸,我儿子醒了,问是怎么回事,我们怎么站在那里。
我说,怕地震,万一地震,我就扑上床拉你。
后来我们一家还是去呆到院子里的空旷处。
第二天早自习,我没上,拉上教室窗帘,师生集体补觉。
后来我们学校组织给地震灾区捐款,我在班上倡议的时候,几度哽咽。
虽然我没有亲临地震的恐怖现场,但却真真切切感受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存在。
那年的记忆就这样深深地刻在脑海里,在以后平淡而忙碌的庸常日子里,它时不时地飘出来提醒我,平安地活着,就是一种美好。
去年七月底八月初,我和我的朋友们从长沙、西宁、西藏到成都等地旅游了一圈,看到了不一样的风景,也可以说,从一个侧面,浅层次地体会了不一样的人生,只所以说浅层次,是因为人生的各种痛,任何人都无法做到真正的感同身受,哪怕是同一事件的经历者。
从西藏飞成都的第二天,我们就去了当时受灾严重的映秀镇漩口中学。
她是我们这一行的导游,地震发生时,她正读高二,班上37人,4人遇难。
图为“四川汶川特大地震漩口中学遗址”。
学校周边开设有各项“地震体验”项目,人来人往,已看不出当年地震时的一丝恐惧和伤痕。
我对导游说,政府重视,现在这里建设得挺好的,人们的生活恢复了正常。
她说,过得再好,心里都有伤痛。
我们一时陷入沉默。有些痛,不是不在了,而是蛰伏在心底,变成了人的一部分。
导游说,到目前为止,这栋坍塌的废墟里还埋有师生。 我对地震的观察和感受,都是肤浅的,然而,我还是忍不住背对着行人,望着这个永远定格在2:28的时钟流下了眼泪。
有些楼,直接从顶楼变成了负一楼。
母亲保护孩子。
所有照片里,只有这张来自网络,其余的都是我用手机拍的。
参观完这所学校,导游提出带我们去看看附近的公墓,我第一个提出反对。
不敢面对那份惨烈,虽然已既成事实。
后来几天我们还去过都江堰等地,现在很多地方已经是全程高速,很难再发现地震造成的破坏,一切都是欣欣向荣的景象,但是只有当地那些真正受过地震伤害的人,才知道内心的重建,是灾后重建中最难的。
下面是网友的留言。
记得看《唐山大地震》,我哭得稀里哗啦,里面有句台词特哲理:没了,才知道,什么是真的没了。
地震把世界倏地一分为二,活着的和逝去的。活着的,真的该认真审视自己所拥有的。
然后像三毛所说,在有限的时空里,过无限广大的日子。
尽管她自己没有践行。
我的个人微信公众号:等在澧水边或luckyhup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