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诗作若不能经得起种种翻译,也就离僵死不远了
《鹿柴》
空山不见人,
但闻人语响。
返景入深林,
复照青苔上。
诗的作者是王维(约公元700-761年),生时以富裕的佛家画师和书法家闻名,被后世公认是唐朝这个大师辈出时代的大诗人。这首四行诗是诗人为辋川种种风景所作二十首诗作之一。这些诗是一幅巨幅山水画创作的一部分,此类山水画正是诗人开创的。数百年来,画作一直被临摹(翻译)。真迹已消失,现存最早摹本来自17世纪:历经九百年变形的王维风景。
在古汉语里,每一个字(意符)代表一个单音节的词。像寻常认为的那样,很少有字完全是具象式的。但有些基本词汇的确是象形的,而用这数百个字,你就可以佯装能够阅读汉文。
自左向右、自上而下读,第一行第二个字明显可见是座“山”;同一行最后一字是“人”——两者都由更加明显的文字表征风格发展而来。第一行第四个字是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的最爱:他阐释为两条腿上的眼睛,也即运动之眼,“去看”的意思。第三行第五个字是两棵树,“森林”的意思。第三行第三个字,“入”,以及第四行第五个字,“上”,形象地描绘了空间关系。
更典型的汉字是第四行第二个字,“照”,左上方一个太阳的图像,下面一把火,外加右上方一个纯粹的语音元素——这个字读音的关键。其余大多数字都没有值得解读的象形内容。
以下为王维《鹿柴》8篇译作
▼
1944年
《唐诗续》
《鹿苑》 一座空山,不见一人 但我听到人语的回响。 傍晚的斜阳穿透幽深的林子 闪耀并反映在青蓝的地衣上。 ——索姆·杰宁斯
《The Deer Park》
An empty hill, and no one in sight But I hear the echo of voices. The slanting sun at evening penetrates the deep woods And shines reflected on the blue lichens.
——Soame Jenyns
干巴,却颇为直白,杰宁斯唯一添加的是无可避免的“我”,并解释了太阳是“傍晚的斜阳”。他是译者里唯一一个偏好地衣胜于苔藓的,尽管这个词的复数形式不是一般的丑。
第四行里的zhao(照)变成了既shines(闪耀)又reflected(反映),而不是其中之一。但他还是掉进了“返照”的圈套:太阳从哪里返照的?
汉语诗歌是建立在对物理世界的精确观察之上的。而在杰宁斯及其他译者所出身的那个传统里,明确诗意画面的想法是一个不明智的举动,在他们那里,“诗意”这个词本身就与“梦幻”同义。
如果他译为And shines reflected by the blue lichens(被青蓝的地衣所闪耀并反映),也许还可以幸免于难——虽不精确于王维,却也忠于自然。然而杰宁斯——当时是大英博物馆东方古物部助理,在“二战”的伦敦空袭中仓皇逃生——与这首诗的体验有着太过遥远的隔膜。乃至他认为有必要给第二行添加一个注:“林子茂密到樵夫与牧人皆被隐藏不见。”
1948年
《中国文学选集》
《森林》
在山上,一切皆是孤独, 能听到远远的人语声, 穿破森林深处的太阳, 把自己的光线倒映在青苔上。
——马古礼
《La Forêt》
Dans la montagne tout est solitaire, On entend de bien loin l’écho des voix humaines, Le soleil qui pénètre au fond de la forêt Reflète son éclat sur la mousse vert.
——G. Margouliès
马古礼喜欢泛化王维的具指:“鹿柴”简化成“森林”;“不见人”变成了“一切皆是孤独”,呆板而抑郁。第二行,译者将人语声诗化了,说它是“远远”而来。法语的不定代词恰到好处地去除了叙述者。
1958年
《诗选》
《鹿林兰若》 穿过深林,斜阳 投射着斑驳的图案在绿玉青苔上。 这寂寞的山中,瞥不见一人, 然而隐约的人语声在空中飘荡。
——常茵楠&刘易斯·C.沃姆斯利
《Deer Forest Hermitage》
Through the deep wood, the slanting sunlight Casts motley patterns on the jade-green mosses. No glimpse of man in this lonely mountain, Yet faint voices drift on the air.
——Chang Yin-nan & Lewis C. Walmsley
常茵楠与沃姆斯利的这个译本是王维作品在英语世界里的第一本书,但不幸的是,这部作品与王维原作没什么相似之处。
在这首诗里,联句毫无因由地被颠倒。人语声是“隐约”的,“在空中飘荡”。山是“寂寞的”(空=寂寞,一种西方式的比喻,有损王维的佛家气息),青苔绿如玉,阳光“投射着斑驳的图案”,不过是一种装饰主义者的愉悦。
这是译者企图“改进”原作的典型例子。这种情况并不少见,是译者心照不宣地蔑视外国诗人的结果。常茵楠与沃姆斯利没有意识到,王维如果想的话,他是可以写下“投射着斑驳的图案在绿玉青苔上”这样的句子的。但他没有。
翻译是精神修炼,靠的是译者自我的消解:奔向文本的一种绝对的谦逊。坏的翻译,从头到尾都是译者的声音——即是说,见不到原诗人,但闻译者的聒噪。
1972年
《藏天下:王维诗选》
《鹿寨》 空山:无人得见, 但人语声可闻。 太阳的回光探入森林 闪耀在青苔之上。 ——叶维廉
《Deer Enclosure》
Empty mountain: no man is seen, But voices of men are heard. Sun’s reflection reaches into the woods And shines upon the green moss.
——Wai-lim Yip
叶维廉是批评家,曾精彩论述过中国诗歌对20世纪美国诗歌的重要性。但作为译者,他就有些逊色,可能因为英语是他的第二语言。(尽管有很多人尝试,但离开自己的母语做翻译,通常鲜有成功的。)因此,会出现怪异的no man is seen以及reach into这样古怪的拟人用法。
叶维廉在前两行里追随了王维对“人”的重复(尽管他的persons是men),每行用六个词对应汉语的五字。但不像其他译者,叶维廉实际呈现的比原作少——他把deep(深)与again(复)给抹去了。
叶维廉在这篇译作的后续版本(收录于叶的选集《中国诗歌》〔Chinese Poetry〕,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6年)里,把第一行修剪成完全洋泾浜式的Empty mountain: no man。
1973年
《王维诗集》
《鹿苑》 空山,无人可见 我们只听到人语的回声—— 因光线回返到幽深森林里 青苔顶部再次被点亮。 ——G.W.罗宾森
《Deer Park》
Hills empty, no one to be seen We hear only voices echoed—— With light coming back into the deep wood The top of the green moss is lit again.
——G. W. Robinson
罗宾森的翻译是由企鹅社出版的,很遗憾,它是王维作品在英语世界里传播最广的版本。
在这首诗里,罗宾森不仅生造了一个叙述者,而且让他们成群结队,如同一场家庭郊游。他用了we(我们)这个词,整首诗的基调一下子就被毁了。
对原诗最后一个字(复照青苔上的“上”),罗宾森描述了一个几乎毫无逻辑的画面:你必须得体形极小才能对青苔的顶部有概念。
如果想颠覆认知体系,那就试着大声读读。
1974年
《中国文学》
《狸柴》
空山中,看不到人。 但这里或许有回声交织。 回光 穿过深林 再次闪耀 在深青的苔藓上。
——威廉·麦克诺顿
《Li Ch’ai》
In empty mountains no one can be seen. But here might echoing voices cross. Reflecting rays entering the deep wood Glitter again on the dark green moss.
——William McNaughton
麦克诺顿以汉语地名为诗名,但音译不对——有点像Deer / Beer分不清,鹿苑变成啤酒园。
第一行采用被动语态,几乎是对东方智慧的拙劣模仿。第二行毫无理由地将动作置于 “here”,然后添了一个cross实现自己强作的押韵效果。(其实与moss也不是很押韵,有点累赘。)条件语might匪夷所思(到底有没有回声?)。
最后一个对句破成四行,明显是在尝试图像表现。
1977年
《中国文学:自然诗》
《鹿苑》
荒山上一个人影也没有 然而你可以听到人说话的声音; 森林幽僻的深处, 迷失的太阳光束认出了青苔。
—— H. C. 张
《The Deer Park》
Not the shadow on a man on the deserted hill— And yet one hears voices speaking; Deep in the seclusion of the woods, Stray shafts of the sun pick out the green moss.
——H. C. Chang
张翻译了王维20个字中的12个,其余的全靠虚构。
第一行中的on可能是个排版错误,但也难说。无论怎么讲,那里的影子在干(或者更确切地说,不干)什么呢?只有影才知道。
太阳的shafts(光束)怎么就stray(迷失)了呢?它们怎么就都成光束了?它们怎么就pick out(认出)了苔藓?这动词让人不可避免地想到蟹与田螺的吃法。
简而言之,这是张的诗,而非王维的。(该译本来自一个三卷本套书,出自同一个译者,哥伦比亚大学出版,也是奇怪。)
1978年
《保护全生物杂志》
空山: 看不见一人。 然而——听—— 人语与回声。 返照 穿过幽暗的森林; 再一次闪耀, 在青苔上,天上。
——加里·斯奈德
Empty mountains: no one to be seen. Yet—hear— human sounds and echoes. Returning sunlight enters the dark woods; Again shining on the green moss, above.
——Gary Snyder
肯定是最好的翻译之一,部分得益于斯奈德一生的森林经验——他可以“观照”场景。王维的每一个字都翻译到了,且无任何添加,而翻译又以美国诗歌而存世。
改被动的is heard为主动的hear,很美,但稍有不妥:它营造了一个具体时刻,即当下。以sounds and echoes这两个词翻译第二行最后一个字,同时赋予我们双重含义,无疑是革命性的。译者总是假定一个外语词或句子只有一种读解的呈现,而罔顾一个事实—— 完美的对应是罕见的。
诗的结尾很奇特。原诗最后一字“上”,其他人都解为on,斯奈德却把它拈出来,译为above,并用逗号将它从整个句子中孤立出来。这是怎么回事?推测起来,大概唯有对于石头或虫子来说,苔藓才可以在上面。或者我们看完苔藓后,目光向上,重返太阳:觉悟的垂直性隐喻 ?
对我的疑问,斯奈德写道:“之所以用‘...moss,above...’是因为太阳(日落斜阳,故言‘again’——最后的一道光束)正在穿过森林,照亮了一些树苔(而非在石头上)。我的老师陈世襄是这么理解的,而我的日本妻子第一次读这首诗的时候也是同样的看法。”
重点是,翻译不只是从字典到字典的跳跃,还是对诗的一次重构。如此,无论语言,一首诗的每一次阅读即是一次翻译:深入读者理智与情感的翻译。没有读者是一成不变的,每一次阅读都是不同的。人不能两次读出同一首诗。
斯奈德的阐释也只是一时的,在最新的一刻,这首诗在我们眼前骤然变形。依旧是王维的那二十个字,没有变,但这诗却继续,做着无尽变幻。
[1979年]
本文节选自
艾略特·温伯格/著
商务印书馆 |纸上造物 2019年2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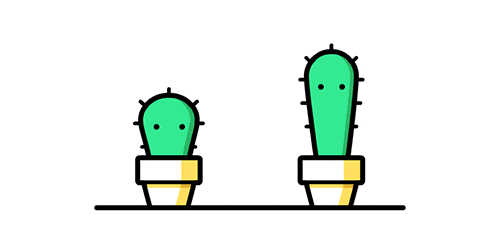

知识 | 思想 凤 凰 读 书 文学|趣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