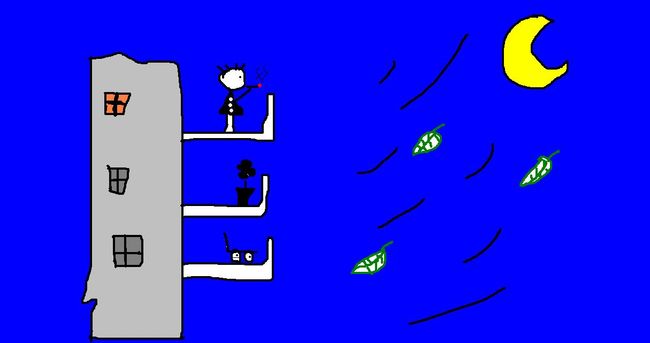Chapter 3酒精与人生没有任何关系,你可以屡屡试图伪装快感,却始终无法长久掩埋睡意
我天生不胜酒力,却热衷于谈论酒力,和不胜酒力的人切磋酒力,就像与ED患者探讨AV拍摄心得一样,挑衅与自我陶醉五五开,总体来讲无聊,细致说开无趣。
至于我的酒力,提与不提就是笑与不笑的区别。由于先天根基的不稳,进而导致了即使后天的钢筋混凝土再牛逼,搭起的也不过是一台只能勉强存放一瓶常温啤酒的报废冰箱。
冰箱第一次插电,是两岁。那时我开裆裤的裆口性感的敞开,犹如夜市中的某个不温不火的档口,路人或急或缓有意无意的从档口或裆口前经过,摸摸小鸟,我们意味深长的会心一笑。
那是一个冬季的午后。冰冷歪斜的阳光将窗棂的轮廓斜铺在钉着薄木板的温热火炕上,一种平淡的错觉弥漫在整个空间。我已经忘记了喝下那口葡萄酒的动机是什么,事实上,关于那时的很多我都从未记得,只是在若干年后的某个巧合看到一张泛黄的照片,上面的我穿着一件泛黄的碎花马褂,将一只泛黄的搪瓷茶缸狠狠的扣在了我自己泛红的脸上。
这台破冰箱,在两岁时第一次插电;而直到我发现那张照片时,这台破冰箱,插过也仅插过一次电。
听说,那个冬季午后的红晕一直持续到了深夜,我趴在窗棂上对着窗外飘雪的世界作出各种撩人而傻逼的姿势,没有目的的去舔舐玻璃,抚摸插销,摧残窗台,我仿佛是一位来自刚果布拉柴维尔的廉价脱衣女郎,缺少的就是一件春光四射的DS演出服和一根坚硬通天的电镀钢管。最终,在漫天飞雪与众人的觥筹交错中,我没有任何动机的开始骚动,接着又没有任何缘由的倒在火炕上,我的下巴上沾满了灰尘,手指间沾满了铁屑,满足的表情与脱衣女郎相映成趣,在一口葡萄酒的催化下,一切随夜入梦。
我相信这个泛黄的故事是有关最为真实的我的最为真实的写照,一口酒所印证的自我果然是没有任何修饰的存在。没有动机的故事不能称之为故事,但这零散的片段却往往是最真实的反应。
那时酒醉后不会矫情书剑恩仇,不会假装迎风流泪,更不会虚伪的胡言乱语。黄色马褂,红色小脸,睫毛闪闪,嘴角弯弯,档口还在,档口大开,小鸟不听话,半夜水潺潺。
原生态。
后来,事情按照“意料之外又情理之中”的节奏继续发展。
与酒精作伴的,一般是香烟。
高中一年级时,一个秋日,以及一场变故后从冰箱冷藏室深处中翻出的香烟。无数个午夜,我悄悄关好阳台的门打开阳台的窗,黑暗中毫无焦点的对焦那只紧攥火机的微微颤抖的手,其似乎和嘴中的那支香烟发生了诡异的共振,使得我根本无法冷静的将烟点燃。
猛吸一口,将脑袋伸向午夜的窗外,微微卷起的头发被冷峻的秋风吹起,是一副极其讽刺和突兀的画面。过去的砖房全都变作了高楼,过去的行道树全部化作了路灯,这个小小的城市缺少了杨树的沙沙声,就像是火机失去了火石一样落寞。窗外居民楼的灯光点点,似乎是在无力的呼应点点星光,顺势将燃尽的烟头从阳台丢下,竟然没有听到一丝跌落的声响,那一点橘黄无声的降落,变色,接着窗子关上,阳台沉默,上床,和衣,等待黎明。
那时的我不否认,我曾经因为一口葡萄酒而迷醉;但我绝对不承认曾有“酒醉的记忆”存在于我的脑海中。香烟不同,第一口烟气进入我的肺部时,我已出生十六年两个月零三天。十六岁,一个不存在任何记忆障碍与成长干扰的年纪,烟气在胸口缠绕的感觉我一辈子都记得——眩晕而窒息,像极了我日后酒醉时的可笑种种。
十八岁。
大学。
在那个燥热的夏天,我用各种酒精来浇灌自己所谓的情绪。可情绪的抒发始终没有持续性,每每想好一肚子话后,伴着一杯啤酒,那些话便又统统退回到马桶中。
直到那时,我才对酒精有了极具意象化的认知,进而我颤抖着将香烟与酒精二者画上等号。
从此,酒醉与香烟就成为了我的生活与文字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二者一旦出现,要么代表生活起了波澜,要么就是生活已太久没有波澜。
值得庆幸的是,十八岁后,就已没有醉过。
我很欣慰,我是一台只能装一瓶啤酒的冰箱。游荡在校园里的这些年,我这台冰箱的电源线难免会被插插拔拔,拔拔插插,可这反复的一插一拔却始终不能对冰箱的本质属性产生任何决定性的影响。
因为我本身就是一台报废的冰箱。
从始至终的一瓶啤酒。
无论是从饭局,睡意,还是年龄,始终就是一瓶啤酒贯穿我所有的主题。之所以没有喝醉过,是因为我总是在喝下一瓶啤酒中的最后一滴后悠然睡去。其实我的脑子还清醒,其实我的嘴巴还灵活,其实我还可以响亮的发出你们想听的音节,也可以精准的接收你们所传导出的声波。只不过,我不想再如此这般从始至终的文艺与虚伪,与其粗鲁的将内裤撕裂于床上,我宁可将本性如桌布一般平铺在酒桌上。
以供各位玩赏。
而且,允许人身攻击。
渐渐,我的伪装被众人缓慢的剥离。酒桌上我的位子在不断的变换,而我始终拎着那一瓶啤酒——就像是小心保护着我晚婚晚育的爱情结晶。那一瓶啤酒仿佛可以催化一滴坠入清水的墨汁,四杯酒的时间便可将整个世界渲染的云山雾罩,黑云缭绕。
当我喝下第四杯以后,我双手平摊在桌子上。邻座的A递上一支香烟,我把它习惯性的别在了耳后。而后又忽然发现耳后的空间已经被眼镜腿占领,于是便只能悻悻的将香烟塞进了双唇之间。
对面的B颤抖着举起了打火机递到我的面前——一个从淘宝聚划算花39.99包邮买下的假货。我想佯装吸上一口,却怎料烟雾似乎和酒精起了反应,二者飞一般的进入,与肺泡开始了亲密的接触。
“我,喝多了。”我又一次把双手平摊在桌子上,索然无味的说。
“我们,嗝,也是。”众人竟然发出了整齐划一的回答,连那声“嗝”都一模一样。
“我是真的。”
“我们也不假。”
对仗工整。
“今天,很开心。”我的双手再次平摊,钢化玻璃被指关节敲打的砰砰作响。
C又抽出一支香烟,我条件反射一般的向地上啐了一口吐沫,当然,他没有看到。
“我两岁的时候,穿着一条碎花小褂,可以不眨眼一口气喝下一大口葡萄酒。”我说。
“还能跳钢管舞。”D补充。
“那是人生的一个美好的开始,如果今天有钢管,我依然能舞。”
服务员敲了敲门,用一堆心管来代替钢管。
“我曾以为我是一棵伟岸的杨树”,我继续。E和F已经等不及,两人一边起身一边旁若无人的解着裤腰带向洗手间走去,“可是他妈的树却倒了。”
“没关系,那树桩上还有年轮。”X清醒的坐在角落,一边摆弄手机,一边说。
“可树桩被铲车铲个稀碎,毛年轮也没有了。”
“那又怎样,”X看了看我,顿了顿说,“你还真以为你是一棵树?”
“我喝醉了,”双手的十个关节,微微红肿,“但我知道,我是。”
那油腻冰冷的钢化玻璃令人有些不安,可我用我所习惯的姿势,趴在上面悄然睡去。
E和F从洗手间回来后,看到了一颗头发微微卷曲的头颅无力的耸拉,微笑。他们晓得,那是我的节奏,从一杯葡萄酒进化到一瓶啤酒的混账节奏。
X搀扶着我往回走。某个明亮的路灯下,他(她、它)狡黠的问我,是不是醉了,我直起身,表情有些悲壮。
“你几时见我醉过?”
“那为何不谈人生?”
“因为啰嗦。”
“那又为何在桌前睡着?”
“因为困了。”
“困了?”
“是的。”我打了一个哈欠和饱嗝儿,“两岁那年的事儿才叫热闹,现在,一看这场景、光景,也就够了。”
“况且,”我意犹未尽,“睡意这东西不比酒精,不是你喝两口热茶就能伪装,手指头压压嗓子眼儿就能解脱的。”
离开路灯的光线,X便无影无踪。
至此,我终可以找到一个灰暗的角落,靠着行道树蜷缩着放声呕吐——眼泪、酸水、鼻涕、污物,统统可以当做由于昼夜温差过大而产生的人体奇异附着物。
脑海中无法回避的浮现出两岁时那张泛黄的照片,幻想黄色的碎花兜兜或马褂。很难得,二十六岁的年纪,还可以下意识的想出“与黄色有关”却丝毫不“黄色”的场景。
我相信那段“黄色”是极为真实的,否则,我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这个机械而伪善的夜晚。
行道树将我扶了起来。
此后,我还要继续蹒跚的行走。
就像是一只徘徊在午夜沙海中,打着钢板倔强蠕动的蜗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