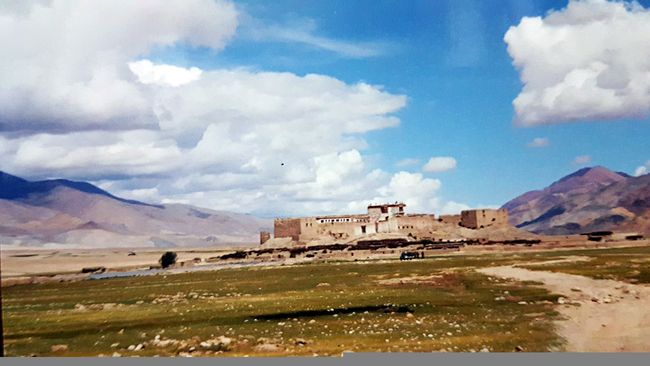喀喇昆仑,我生命里一次难忘的远行……
远去的是岁月,留下的是记忆。一一题记
新疆南缘的昆仑山和喀喇昆仑山脉,我国古籍多把它们统称为昆仑或南山。这两大山脉,都起自帕米尔山结(又称帕米尔高原)而并驾迤东。喀喇昆仑山延入西藏北部,与冈底斯山交接;昆仑山则延新藏地界延入青海、四川。喀喇昆仑山山岩峭峻、巨峰拱列,犹如万笏朝天,群峰海拔均在五六千米以上。主峰乔戈里海拔8611米,为世界第二高峰。昆仑虽比不上喀喇昆仑之陡峭,但山体更为壮阔绵长,其势如巨蟒蜿蜒于亚洲中部,故有“莽昆仑”与“亚洲脊梁”之称。昆仑在新疆境内的山段长1800公里,宽约150公里,山脊高度多在5000米以上,西段还有不少高达7000米以上的巨峰。
我对喀喇昆仑山产生好奇由缘已久。
但令我魂牵梦绕的还是读了报告文学《天界》、《边关》、《神山圣域》,以及看了电视剧《昆仑女神》之后,对昆仑山有了更深刻的印象。
昆仑山在我心目中是一座不朽的雕像。
我之所以敬仰昆仑山,是因为它高大、险峻,充满着神秘与幻想。
我喜欢听人们讲昆仑山的刚直、雄伟,乃至它的粗旷与无情。
我曾经不止一次地期望有一天能亲自拜会昆仑山,感悟昆仑山,感受人们所讲的悲壮与苍凉。
随着我对喀喇昆仑山的渴望与期待,久违了的这个愿望十分浪漫地向我走来一一2001年8月7日,我随原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高原文化工作队演出小分队,冒着蒙蒙细雨,从新疆叶城的零公里出发,沿新藏线向西藏阿里地区开进。
包括我在内,小分队只有五人,三男两女,除我之外,都是演员。可是保障我们的人员和车辆却远远超出我的想象——1名军医,1名带队干部,5名司机,2台越野轿车,1辆牵引车。
我们上山的主要任务是为沿途兵站和边防一线连队、哨所的官兵慰问演出。
这天上午吃过早饭,尽管天上下着毛毛雨,但每个队员的心情非常好,也很激动。因为大家都是第一次上昆仑山,第一次赴阿里高原。
穿过一段比较平坦的公路,汽车犹如一峰负重的骆驼,在崎岖的山路上艰难地爬行。由于汽车颠簸厉害,我们的心情时刻都在发生着急剧变化。大家或兴奋,或叹息;或好奇,或后悔。与我同车的有通俗歌唱演员禹虹、某部新闻干事廖海庭。由于小廖有带车任务,我们乘坐的三菱车就打前阵,跑在前面领路。歌舞团艺术指导、二级歌唱演员庄严与魔术演员闫建荣、舞蹈演员李文娟,以及军医陈涛乘猎豹越野车紧跟其后。
大约行驶了4小时,我们到达走向昆仑山的第一座达坂——库地达坂(蒙古语:冰雪堆积的地方)。这里海拔3150米。由于我从小在家乡那座大山上放牧、劳动,加之后来当司机时开车去过甘南腊子口、四川若尔盖等地,所以,在我眼里,这个达坂海拔不算高,也构不成险峻。因此,面对库地达坂,我还是比较坦然。惟独禹虹由于先一天晚上在叶城多喝了几杯送行酒,加上路途颠簸,在车上难受得死去活来。
为了调整大家的情绪,我们在上达坂前停车休息了一会。期间,其他几位队友下车站在泥巴地里,边就着矿泉水吃着新疆的馕,边望着眼前高高的达坂声嘶力竭的呐喊。我想,他们毕竟是搞艺术的,他们有他们的思维,他们有他们的欲望。我没有随和,只是觉得他们有点神经质,有点小可爱。
爬上达坂,站在山顶,放眼叠嶂起伏的山岗,我仿佛飘在天空,似乎已经触摸到了蓝天,我的情绪好极了,一种既浪漫又愉悦的感觉随之而来。趁着兴奋,我拿起相机,迅速记录下了这美丽的景色。
再往前行,汽车经过艰难爬涉,到了海拔5080米的麻扎达坂(亦称赛里亚克达坂)。这是三十里营房以西最高的一座达坂。下了汽车,瞬间的工夫,我感到头疼胸闷,心跳加快,眼前直冒金花,加上天上飘着稀星的雪花,顿时觉得地在摇,山在动,天在转。
我开始对自己的身体产生怀疑。我更担心其他队员是否还能坚持得住?还好,禹虹因为一路昏迷躺在车上睡觉,并没有完全觉察到麻扎达坂的厉害。闫建荣不知高原缺氧的厉害,竟然在下了车之后继续对着大山吆喝。我不以为然,昏昏沉沉地上前制止了他。从闫建荣黑里透青、青里泛紫的脸上,我发现他有了强烈的高原反应。不一会儿,他便摇摇晃晃,站立不稳,急着钻进了汽车。看来,在这达坂上谁都不能逞能,尤其是初次到昆仑山的人。我本想在这里撒泡尿,但由于晕糊,怕出现意外,还是蹩着上了车。
中午两点多,我们到达库地兵站。迷糊了一路的禹虹被两名战士扶着住进了兵站招待所。兵站官兵热情地接待我们,为我们准备了丰盛的饭菜。吃过午饭,我们在两山的夹缝中,趟着急流,在山沟里继续行军。经过360公里的长途跋涉,晚上8点20分,我们终于到达三十里营房兵站。
禹虹还是发烧不止,昏迷不醒。我们将她送到“喀喇昆仑模范医疗站”一一三十里营房医疗站打吊针。几位队友怕她寂寞,吃过晚饭都去陪她。整整3个小时,谁都没有离开病房。禹虹被大伙的真情感动得热泪盈眶。
三十里营房海拔不算高,3600米,但很闻名,是中央军委命名过的地方,也是昆仑山一带最中心、最权威的军队医疗站。大家熟悉的八集电视连续剧《昆仑女神》反映的就是这个医疗站的事迹。一批批、一代代年轻有为的男医生女护士为了边防将士的生命,无私的在这里奉献着青春,倾注着爱心。据说,山上守防的不少战士耐不住寂寞,还专门找理由请假来医疗站看女兵。
陪禹虹打完吊针,已是深夜11点30分。按照日程安排,今晚我们就在三十里营房兵站过夜。走出医疗站,尽管我们都穿着毛衣,披着大衣,但由于这里缺氧气压大,寒风还是将我们每个人吹得浑身直哆嗦。我没有了欣赏高原夜景的兴趣,也没有睡觉的倦意。尽管很累、很困。
零点以后,兵站停止发电,招待所的宿舍一片漆黑。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我想,这就是高原反应。吃不饱氧气的人们连思维都变得迟钝、浑浊,神经也不那么灵敏。后来,不知不觉地,我好不容易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却被一群可恶的狗叫声惊醒了。透过夜光,看看表,已是凌晨5点10分。我无法再睡下去,索性点着蜡烛看书。7点,当昆仑山还在沉睡之时,我们便起床向多玛兵站开进。
我们计划今天行军480公里。山大沟深,道路崎岖,每个同志都做好了吃苦的思想准备。为了消除疲劳,打起精神,保持乐观,我们在途中休息时统一了思想,提出上车后不能睡觉,要消除上下级观念,消除等级观念,消除男女观念,提倡大家在车上说笑话、讲段子。话虽这么说,可是在我乘坐的车上气氛很难调节起来。禹虹性格内向,不善于交流;小廖初次与女演员同坐一辆车子,加上二十五、六岁的小伙子还没有谈上对象,说话害羞;我更是自以为是,觉得身为一名机关干部怎能在下级单位的同志面前随随便便乱讲话呢?这样的气氛持续了足有1小时,直至我看着小禹、小廖困得都打盹了,我才有意说了几句笑话,刺激他俩也说笑话,但最终谁都没有讲一个笑话,更谈不上讲什么段子了。跟在我们后面的猎豹车,虽然刚开始笑声不断,但趟过红柳滩,18岁的女舞蹈演员李文娟却被颠簸得一路呕吐。同车的庄严高原反应强烈,头疼难忍。坐在车里,他一直紧紧抓着扶手,两腿蹬得嘣直,生怕汽车将自己弹起来。我也未能逃脱昆仑山的戏弄,胸闷气喘不说,脑袋在汽车的剧烈颠簸中像灌了铅似的,闷疼闷疼。
车到死人沟(亦称泉水沟),已是下午3点钟。由于路况太差,我们乘坐的三菱车的保险杠已被颠裂。司机小党心疼地说:“要是在山下,保险杠是永远不会跑断的。”好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山沟里还有一家汽修铺,小党趁我们下车找饭馆吃饭的工夫,抓紧时间对保险杠进行了焊接。虽然错过吃午饭的时间好久了,并且人人肚子饿得慌,但此时将饥不择食用在我们身上似乎不够贴切。当我们找到一家小饭馆就餐时,大家望着一碗碗鸡蛋拌面发呆,谁都没有胃口,没有食欲。李文娟躺在饭馆脏兮兮的床上,铁青着脸,像一具僵尸。在我们的反复劝说下,她勉强吃了几口。那知,刚离开饭馆,她便将吃下去的一点东西全都吐了出来。我在为李文娟的体质感到同情的时候,也为安排她跟小分队一起上山感到内疚和遗憾。小李上山前脸上还是那么天真那么烂漫。现在想起来,让她上山是有点残酷。吐出胆汁的小李身子软得像泄了气的皮球,脸上没有了血色,嘴唇紫得吓人。大伙将她扶上车,车子一跑,她又将头伸出窗外,哇哇地呕吐。坐在一旁的陈医生也许缺少上山的经验,面对如此痛苦的小李竟然束手无策。
离开海拔4700米的死人沟,天上下起了大雨。
汽车在坑坑洼洼的山路上嗡嗡地爬行,我们被颠簸得像厨师炒瓢中上下翻腾的冬瓜,坐也不是,站也不能。
雨过天晴。下午6点左右,我们到达海拔五千多米的界山达坂。我之所以说它为五千多米,是因为界山的石碑上刻着6700米,而也有人说它是6300米,但凭我的感觉,起码在5000米以上。
这里的天湛蓝,这里的云雪白。天蓝得让我惊叹,云白得叫我心悬。
一望无际的昆仑山啊,你使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企盼你,崇拜你,赞美你,歌唱你。为了感受界山达坂,为了证明自己到过界山达坂,也为了在界山达坂留影纪念,我挎起相机,第一个下车走向界碑。然后,其他几位同志跟着下了车。在界碑前合影时,庄严已经蔫得像霜打了的茄子,直不起腰,抬不起头。李文娟更像一只快要死去的羔羊,弯曲着腰,趿拉着脑袋,眼睛可怜巴巴的一闪一闪。禹虹这会儿出奇的机灵,她一会儿做出调皮的姿势,一会儿双手叉腰摆出女中豪杰的风度。闫建荣虽然上气不接下气地喊着头疼,但他在照像时却拉开男子汉的架势,一点都不像有高原反应的样子。应该说,我的体质最好。在给大伙儿一个一个地照完像后,我选了几个自认为得意的角度留了影。之后,我避过大家,在界山达坂撒了尿,以示自己不虚此行——因为我上山前曾听上过山的人说过这样一句顺口溜:“死人沟里睡过觉,界山达坂撒过尿,班公湖里洗过澡,神仙湾上站过哨”。之所以有人编出这样的顺口溜,大概是因为这几个地方非同一般。我想,只要你到了这些地方,并且确实像他们说的那样去做了,你就不一般。
翻过界山达坂,汽车走了多半个小时的翻浆泥泞路,便是行军两天以来最好的国道。
两辆越野车像脱缰的野马,开始在空旷的山沟里赛跑。起初,我们的三菱车一直跑在前面,时速高达130马。猎豹车不甘示弱,加大马力猛追,用了不到20分钟,猎豹绕过正道,从平坦的草地上呼啸而过,猛的超越了我们。
两辆车一前一后,虎视耽耽地跑了将近1小时,我有点后怕,提醒司机小党一边拉响警报,一边放慢速度。猎豹车似乎意识到了我们的暗示,也将车速减了下来。
晚上9点,我们的三菱车安全到达多玛兵站。出乎意料的是,当我们来到多玛兵站时,等候了许久的兵站官兵已经列队敲起了欢迎的锣鼓。我们小分队一个个被感动得流下了热泪,下车向他们敬着军礼走进了兵站。
等猎豹车开进兵站时,我已洗完脸躺在床上休息。忽然,兵站的院子里一阵吵闹声,我赶快起身,走出招待所时,只见两名战士抬着李文娟走了进来。庄严两手紧压太阳穴上的血管,在闫建荣的搀扶下,迈着沉重的步子,遥遥晃晃走了进来。我看事态不妙,赶紧抱来两床被子垫在沙发上,扶着庄严躺下。此时,庄严闭着双眼,只是一个劲地呻吟。我仔细一看,庄严太阳穴两边的血管鼓得很高,像快要迸裂似的。我帮他用毛巾擦了擦脸,将他扶上床休息。
这边的人刚静下来,只听那边的李文娟在屋子里哇哇呕吐。我马上叫来医生,督促他们赶快给李文娟检查身体。就这样,演出小分队狼狈不堪地住进了海拔4300米的多玛兵站。
吃晚饭时,已是夕阳夕照。尽管时针已经指向10点,但是多玛兵站的天空依然晚霞光彩迷人。
也就是在这天晚上,演出小分队的每一个同志都不同程度地演绎了一幕幕令人难忘的故事一一
庄严与我同住一屋。整个夜晚,强烈的高原反应折磨得庄严死去活来。他一会儿痛苦地呻吟,一会儿坐起来骂天,闹腾得我无法睡实。住在邻居屋里的禹虹和李文娟更是彻夜未眠,受尽了缺氧的折磨。李文娟接连打了3小时的吊针,害得兵站和保障我们的医生轮流值了3小时的班。等小李刚刚入睡,禹虹又犯病了。不知怎么搞的,深夜5点多,禹虹上吐下泻,好在她们的屋子里正好住着一位从三十里营房医疗站陪工作组上山的女医生。她们互相照应,互相安慰,总算熬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与军医陈涛同屋的闫建荣反应虽然没有那么强烈,但也十分悲壮。据陈涛第二天早晨讲,闫建荣半夜头疼胸闷得厉害,无法入睡,痛苦地坐在床上流泪,还时不时地自言自语:“我一定要挺住,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上到阿里。”后来我问闫建荣为什么会有这种举动,他不假思索地说:“已经走了多半路,如果因为身体撑不住打退堂鼓,那就太遗憾了。”
这就是我们军队的文艺工作者,一个甘愿忍受痛苦,也不甘心退却的演出小分队。
第二天吃过早饭,队员们一个个像得了一场大病,蔫不溜秋的。但是大伙毕竟亲历了严重缺氧的折磨,知道昆仑山铁面无情,想躲也躲不过。当他们想起自己此行的任务,想起肩上的职责,看到兵站官兵憨厚的神态,都打起精神,主动提出要为兵站演出,也算是对兵站官兵的答谢。
我默认了他们的请求。
演出在兵站小小的篮球场进行。没有音响,他们就利用汽车上的录音机播放伴奏带。4个演员一台戏,唱完歌曲玩魔术,跳了独舞再伴舞。演员演得投入,官兵看得认真,每一个节目都深深打动着兵站官兵的心。
“山与山不能重逢,人与人总会想见。……”随着主持人庄严满怀激情的几句告别词,演员与多玛兵站的全体官兵互赠留言,含泪握别。一个个军礼,一声声祝福,没有豪言壮语,心与心已经沟通,短暂的演出给在场的每一个人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告别多玛兵站,我们在蓝天白云的呵护下,向着下一站——阿里方向开进。
道路还是那么崎岖不平,汽车还是那么颠簸难行。翻过一座又一座大山,绕过一个又一个湖泊,经过3个多小时的跋涉,我们于正午1点钟走进了闻名于世的班公湖沿岸。
这里的湖水清澈见底,这里的湖面波光粼粼。
和我一样,班公湖是演出小分队每个成员渴盼已久的主要风景区之一。汽车沿着湖岸行驶,大家稀奇地睁大眼睛,尽情地欣赏着湖泊。
天蓝湖更美。趁着路过这里的机会,我们将汽车缓缓地停靠在班公湖的码头,大伙或以湖泊高山为背景照相留影,或以蓝天白云为衬托拍摄资料……。一切都是那么新鲜,那么亲切,那么富有诗情画意。
在码头停留了10几分钟,大伙虽然兴致未尽,但为了赶路,都自觉地上了各自乘坐的车子。
汽车继续在布满石头的山沟里艰难地行驶着。
为了保持身体稳定,防止颠簸,我一直紧紧抓着车顶上的扶手,两腿始终没有松驰。
下午两点多,我们到达日土兵站。兵站和通信机务站以及人武部的领导早早的在兵站门口等候,迎接我们的到来。在兵站吃过午饭,我们顾不得休息,马不停蹄地又向阿里方向驶去。途中,我们遇到了几个“全副武装”的或徒步行走或骑自行车的中外旅行者。当汽车行至且坎(地名)时,我们老远看见一个身着红色旅游服的人,他一手扶着带满行囊的自行车,一手缓慢地向我们招手示意停车。走近一看,是一位高鼻梁、蓝眼睛的外国佬。看我们下了车,他嘴里叽呖咕噜地说着什么话。我们听不懂,问他想干什么,他也听不明白。从他甘裂的嘴唇上,我们猜测他可能累了,或者没有了吃的、喝的。于是,我们从车上取出两瓶矿泉水和一块馕给他,他激动得说不出一句话,深深的眼窝里流出了泪水。我们示意他与我们同行,他遥遥头说:“Thank you, Thank you!”
当我们上车回头再看这位外国佬时,他已蹲在原地一边吃着我们给他的馕,一边喝着水。这就是旅游者,一个虔诚的外国探险家。为了寻觅世界屋脊的奥秘,宁肯孤独的挨饿受罪。
还有,当我们经过一段荒无人烟的山路时,发现一位年长的藏族老阿爸困倒在路边,一动不动地蜷伏着。我们扶起他,给他吃的、喝的,他连看一眼都顾不上,接过馕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目睹此情此景,我们为高原的冷漠无情感到无比的心酸。
北京时间19点整,太阳高照,天空明亮。我们在通往且坎边防连的岔路口,与前来迎接我们的阿里军分区政治部侯主任、马副主任会合。50分钟后,终于到达西藏阿里军分区所在地——狮泉河。
这里号称是世界屋脊上的屋脊。海拔4300米。
走进军分区大院,我被眼前的一切感到惊讶——一面几十平米大的鲜红鲜红的版画军旗紧贴分区办公大楼,干净整齐的营院里座落着一幢幢楼房,一排排高大的班公柳在劲风的吹拂下坚强的挺立着……
我们被安排住进了军分区院内的狮泉河兵站。走进招待所,只见楼道里摆放着许多氧气瓶。直觉告诉我:弟兄们,这里严重缺氧。
张主任、马副主任将我们一个个领进宿舍,并且一再解释这里条件艰苦,希望我们包涵。接着,他们又帮我们调试屋子里的氧气,看着我们吸氧,生怕我们高原反应倒下去。
说句真心话,不是谦虚,更不是瞎说,我对高原反应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么明显,那么强烈,那么痛苦。而庄严、闫建荣、禹虹、李文娟就没有我这么皮实。尤其庄严、李文娟反应实在令人担心。庄严铁青着脸,一语不发;李文娟嘴唇紫得像熟透了的葡萄,脸上完全没了少女的美丽。
晚饭前,军分区领导来到招待所看望我们,并与我们一起共进晚餐。席间,雷政委代表分区党委、机关,以及全体官兵,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我们是阿里军分区迎来的档次最高的文艺演出队,也是一支最精干的演出队伍。
晚上,我们还是没有睡好。依然头疼胸闷。
第二天天不亮,我便起床到营区大院散步。由于缺氧空气稀薄,尽管我的心情很遐意,但走起路来还是非常吃力,不敢大步流星,好像也做不到,就像步履艰难的老者。我慢悠悠地转了一会儿,起床号吹响了。和山下的部队一样,官兵们喊着口号开始出早操。看着操场上生龙活虎的士兵,我觉得自己十分渺小,也很惭愧一一同为兵者,我为何这般熊呢?
吃早饭时,军分区领导问我们晚上睡得咋样,我不假思索地说不怎么样。是的,疼不疼,痒不痒,就是睡不实,迷迷糊糊一整夜,你能说我睡得好吗?雷政委感慨道:“别看我们在这里时间长,其实一样睡不好。”他还说:“我们的战士只是习惯了高原,他们的痛苦只有自己知道。”
这天上午10点多,我们来到阿里地区烈士陵园。我们瞻仰了因公殉职的原阿里地委书记孔繁森、进藏先遣连连长李狄三等烈士墓地,为他们祭奠,敬献了洁白的哈达。在烈士墓前,我思绪万千,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为了西藏地区的和平解放,为了西藏人民的幸福安康,多少前辈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如今,为了边防的安全与稳定,为了捍卫祖国的领土完整,我们的边防战士默默地奉献着青春与热血。在我心目中,这些烈士是最伟大的人,这里的将士是最无私的军人。他们的思想境界比这里的海拔还要高。
为了让我们调整心态,养精蓄锐,适应阿里地区的环境,军分区领导没有急着安排小分队演出,特意让我们休息了两天。
8月11日,禹虹和李文娟身体极度疲惫。禹虹因气候不适上火,嘴唇起了许多水疱,卫生队安排医生上门为她俩打了一天吊针。
这天下午,狮泉河狂风怒吼,暴雨足足下了一个小时。晚上9点30分,演出开始。军分区的礼堂内座无虚席。为了防止演员中途出现意外,确保演出顺利,卫生队提前在舞台上准备了两瓶氧气。一切准备就绪后,演出在雄壮的军乐声中拉开了序幕。
为了演好节目,艺术指导庄严既当节目支持,又是独唱演员。舞蹈演员李文娟为了充分展示舞姿,满足广大官兵、职工家属的欣赏需求,一连跳了两曲舞。闫建荣更以坚强的毅力,在此起彼伏的掌声中,坚持表演了30多分钟的魔术。最后,禹虹满腔热情地为大家演唱了《黑不溜秋的你》、《走进西藏》以及《当兵走阿里》等歌曲。面对热情的观众,她越唱越来劲,越唱越兴奋。当她唱完第三首歌曲,准备唱第四首时,坐在前排的分区领导怕累坏了她,劝她不要再演唱时,她却顽强地说:“如果我真的晕倒了,就全当睡着了。只要你们喜欢听,我就要坚持唱下去。”
就这样,4个人的演出小分队竟然在一个礼堂内演出了1小时35分钟,而且节目一个比一个精彩,掌声一次比一次热烈。尤其禹虹演唱《当兵走阿里》时,全场官兵情不自禁地跟着唱了起来——
趟过最后那道冰河
翻过了最后那架达坂
走上世界屋脊的屋脊
爬上高原上的高原
看见了千年翻飞的径幡
就看见了我们的哨所营盘
好男儿当兵就要走阿里
走阿里上高原
缺氧咱就吸口烟
寂寞咱就使劲喊
想家咱就爬高山
月圆看到月牙弯
燃起青春的热血
拥抱高原辽阔的长天
刺刀凿界碑
青春写边关
咱就是阿里
咱就是高原
……
为了表达对演出小分队的谢意,演出结束后,军分区领导向演出小分队赠送了“高原献艺术,阿里见精神”的锦旗。
据军分区的领导讲,4个演员能演这么精彩的一台节目,在军分区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在阿里军分区的几天里,憨厚、朴实、热情的广大官兵给我留下了难以忘却的印象一一狮泉河兵站招待所士官李海岭由于一直在高原工作,脸被太阳晒得油黑发亮。我们每次离开招待所,他都将我们住的房间收拾得干净利索。为了迎来送往,我很少见他闲过,一直忙忙碌碌。当我告诉他晚上演节目时,他并无遗憾地说:“我从来没有看过演出,工作忙,走不开。”说罢,他似乎想起了什么,又好像很难为情。我问他有啥事,他挠挠脖子说:“节目我是看不上了,不过我想跟咱们军区的演员一起照张像。”我觉得小李的要求并不过分,当即答应了他。还有军分区烧锅炉的那个小吴,更是傻得可爱。到军分区的第二天中午,我们被安排洗澡。吃过午饭,小吴来到招待所叫我们,说是水已经烧好,请我们现在就去洗澡。在去澡堂的路上,他非常客气地帮我们拎包,与我们搭话。到了澡堂,他又是帮我们调试水的温度,又是跑前跑后帮我们取拖鞋。等我们洗上了澡,他还时不时地跑进来问这问那,说长道短。说起中央媒体“世纪初年走边关”一行,小吴自豪地说:“他们都来这里洗澡,每个人我都认识。”
当晚,小吴就把陪我们洗澡的全过程讲给他的战友们听。后来我得知,边防上的战士最爱给战友讲从山下来的人们的故事。尤其是与大军区来的人们之间所发生的一切。
从8月12日开始,我们在军分区政治部侯主任的陪同下,先后为扎西岗、且坎、斯盘古尔等边防连队、哨所进行了慰问演出。
首先,我们来到扎西岗边防连演出。该连接到我们演出的消息时,马上向当地几十户藏族同胞作了通报。令我们意想不到的是,该连还派车跑到几十里外的扎西岗武警边防大队,将武警们接来观看演出。得知此事后,我们在路过这个大队时,派廖干事进去打探虚实。见是我们,两名留守战士埋怨着说:“他们都走了,就剩我们两个了。”为了不让这两名边防武警战士失望,不让他们留下遗憾,演员离开扎西岗边防连途经边防大队时,专门来到队部,为两名战士表演节目。两名战士边看演出边流泪。为此,他们感动地说:“我们太幸福了。”
在赴且坎边防连途经该连热琼卡前哨班时,禹虹突然眼睛一亮,看见几名战士站在山头上向我们挥手,于是,她主动提出要上山为前哨班演唱。陪同我们的分区张主任很受感动。他说,难得有禹虹这种乐于为兵服务的精神。在前哨班,我看到每个战士的脸都被强烈的紫外线晒得黑黑的,其中一位看上去足有三、四十岁,我们不大相信,问他实际年龄时,他的回答令我大吃一惊。这名战士结结巴巴地告诉我们说,他是藏族,今年22岁,当兵后一直在连队干后勤工作。其中还有一名小战士不足18岁。他对我们说,由于山上太苦,太寂寞,刚上山那阵子不习惯,成天偷着哭,也想过跑回家,但后来一想,这样做是违反纪律的,不但跑不成,而且还可能要受处分,一狠心,就坚持了下来。
听了这番话,我为自己作为一名军人感到心神不安。
禹虹被战士们的精神感动了。为了表达对战士们的敬意,她为守防战士演唱了3首歌。最后一曲《黑不溜秋的你》,唱出了边防官兵的真实写照。听着听着,战士们都流泪了一一
一条好汉是黑不溜秋的你
上昆仑走阿里靠黑不溜秋的你
鹰飞不过的地方
你爬了上去
树长不活的地方
你活在那里
吃不饱氧气咱就大嘴喘气
看不见人影就大声呼唤自己
高高在上的你呀
黑不溜秋的你呀
越黑爹娘越疼你
越黑姑娘越爱你
……
小分队到达且坎边防连时,庄严、李文娟两名同志就因严重缺氧倒在连队会议室。稍微清醒的禹虹、闫建荣得知还有两名战士在海拔4700米的哨所执勤时,置个人痛苦于不顾,在连队干部的引导下,沿着陡峭的山坡,一步三歇息,爬上高高的哨所,为正在执勤的陈健、雷国平两名战士作专场表演。
爬上高耸入云的哨所,我们仿佛到了天边边。当禹虹演唱《当兵走阿里》时,两名战士感动得直流眼泪。
为了表达对执勤战士的敬意,禹虹忍受着山高缺氧的痛苦,顶着狂风,又接连唱了3首歌,直到实在喘不过气了,她才原地蹲在台阶上歇息。此时,我发现她起疱的嘴唇已经干裂得流出了鲜血。
两名执勤战士紧握钢枪,一边观看演出,一边注视着对面山头上的敌情。
可能因为迎接我们,今天的哨楼换上了崭新的国旗。五星红旗在高高的天空飘扬,格外鲜艳。随着边境浪漫的狂风,国旗在哨塔上发出悦耳的响声,像是专门在为今天的演出伴奏。
离哨楼很近的蓝天白云,宛如一道绚丽的舞台背景,令我们心旷神怡。演出结束后,连队干部告诉我们,禹虹是这个哨所迎来的第一位女性,也是唯一走上哨所的歌唱演员。
短暂的演出给孤独的哨所留下了美好印象。当我们艰难地挪着步子,走下哨所回头仰望时,只见悬在天空的哨所更加雄伟,那面鲜艳夺目的国旗迎风招展,像在恋恋不舍地为我们招手致意。
这天晚上,我们冒着狂风暴雨返回到日土兵站。晚饭后,我们应邀到日土人武部一名藏族副部长家作客。由于当时人多脑子缺氧,我没有记下这名副部长的名字,但我清晰地记得,在他家的桌子上端端正正的摆着南疆军区奖给他的“昆仑卫士”的一块奖牌。从这名副部长黝黑的脸膛上,看得出他为人正直、诚实。起初,我们到他家的目的很简单,只是想品尝当地地道的奶茶。谁知,走进他家之后,我们愣住了——屋子里摆满了典型的藏族家俱,茶几上准备好了大小不一的喝酒用的碗。大的足能盛两公斤酒,小的也在半斤左右。看到这个场面,我有点胆怯。本来就缺氧感到胸闷发慌的我,坐在沙发上一直不敢主动与主人搭话。我希望他们要“攻击”的第一个人不是我。我想观摩一下别人究竟怎么用这样的海碗饮酒。正在我纳闷时,这名副部长提着装满青稞酒的大酒壶,老实巴交地向我走来。他首先给我眼前的大碗里斟满了酒,然后依次类推的给其他同志斟了酒。我担心被灌醉,装糊涂,没有正面看眼前的酒,而是阳奉阴违地巡视着屋子里的摆设。就这,我还是被他“首发命中”。副部长向我献上洁白的哈达,端起那一大碗酒,说了声:“李干事,欢迎你来我家。”然后,他就一语不发,恭敬地将碗用两手托起,站在我面前等候我接酒。面对如此憨厚的主人,我无言拒绝,接过满得外溢的大碗,按照本地人的讲究,用手指轻轻蘸上酒比划了几下,然后硬着头皮,大口大口地猛喝。一碗酒下肚,我已被撑得躬不下腰,靠在沙发上直喘粗气。
一轮接一轮。大家你来我往,不到一小时,已有几个人喝得满脸通红。我想,我们千里迢迢来到这个只有700多人的县城,而且海拔又这么高,人家武装部的领导如此热情,我没有理由拒绝喝酒。只有喝了他们的酒,心里才踏实。这就是我对阿里高原的情感,是对喀喇昆仑的敬意。
在阿里高原,有很多故事令我不可思议,而且最终理解了,接受了。在我看来,高原上的故事很美,只因严重缺氧,这些美丽的故事都被我在阿里、在昆仑山悄悄藏进了心底。
一一女人解手回避旁人,本是天经地义。可是在昆仑山、在阿里,禹虹每次方便都只是提醒我们两眼平视前方,她便躲到汽车尾部解决问题。有时汽车没有熄火,消声气突突地排着废气,将她吹得发晕。她还说:“这里的空气也有污染。”
一一苍蝇本来是人见人烦的东西,可是在高原的兵营,它却可怜得令人同情。当它们闯入你的视线时,你完全用不着计较它们,稀薄的空气会将它们很快窒息,然后,无声地死去,走向另外一个世界。
一一人们知道,狗也是咬人的一种动物,可是狮泉河军营里的那条狗,却也显得过于腼腆和温顺。它饱尝了缺氧的折磨,即使万一得罪了你,你也不忍心为它发怒为它动武。因为能在高原上生存,无论是人还是其它动物,都是那么艰难那么不容易。有一天,我试探着观察这条狗究竟咬不咬人,当我喊着做出打它的动作时,它并没有夹着尾巴逃跑,而是四平八稳地看着我。后来我说起这件事,分区一位领导风趣地说,如果你真地踢它一脚,它最多回过头来看你一眼,因为狗咬人也是要消耗体力的,而且喘气也很困难。我明白了,为了坚持活下去,狗学会了偷懒,学会了与人为善。
一一山上的狐狸也不像内地那么怕人。当我们路过红柳滩时,一只灰色的狐狸发现我们的汽车靠近它缓缓停了下来,它便好奇地跑过来望着我们,直到司机拉响警报,它才懒洋洋地调头离开我们。
……
在阿里,在昆仑山,像这样的故事我耳闻目睹了许多。我之所以对这些故事记忆犹新,是因为我敬畏阿里这块神圣的土地,敬畏这座高原上的高原。在这里,我觉得我的雄心壮志只是一种无助的意念。我承认,在高原,包括我在内,每个人都是最具人性化、最真实的。
当我们完成演出任务向山下撤退时,每个同志对阿里防区、对喀喇昆仑山充满了眷恋之情。大伙儿感慨地说:“如果现在将我留在阿里,我会无怨无悔地干下去。”我相信这不是大话,更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只要你亲历了高原,了解了高原上的士兵,你就会感到自己留在山上完全是一种需要,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奉献。再说,我们在下山翻过界山达坂不久,在一个山沟里目睹了一辆军车被翻的经过。后来我们得知,就在这辆车上,一名探亲归队的战士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我为这名战士感到十分惋惜,同时为他表示沉痛哀悼。
我想,也许他这次回家相好了对象,也许根本就没有来得及考虑这个问题。但是不管怎么说,他已经走了,将灵魂永远地留在了茫茫苍凉的昆仑山。
当我们来到世界海拔最高的兵站——甜水海兵站时,20多名官兵冒着大雨,正在加紧修筑一道桥梁。满身泥巴的站长面对突然到来的我们,不好意思地解释说:“再过几天,这里大雪就要封山。”
走进甜水海兵站,我明显感觉到这里环境恶劣,走起路来有点飘飘然。大伙撑不住,只好躺在床上吸氧。过了大约1小时,兵站为我们准备好了饭菜。由于严重缺氧,大家吃饭时还是没有胃口。为了表示对兵站官兵的感谢,禹虹简单地吃了几口,就悄悄走进炊事班,为战士们演唱歌曲。
看到禹虹乌青发紫的脸,一名炊事兵用怀疑的口气问禹虹:“你真的要唱?”禹虹说:“你们这么辛苦,我不唱心里不踏实。”说着说着,她就唱起了《当兵走阿里》……
离开海拔4890米的甜水海兵站,已是下午5点。这时,我们遇见了阿里军分区政治部司机李亚忠。在阿里时,李亚忠曾开车与分区领导一起陪过我们。今天,他是搭乘一辆地方卡车,准备到喀什接分区1名休假的领导上山。在车上,李亚忠告诉我们,他已服役15年,仅在昆仑山跑车就是200多趟。我问他转业后打算干什么,他说在高原吃惯了苦,准备以后做生意。我说凭你的条件完全可以由国家安排工作。他说在山上得了不少高原病,自己不想给任何人添麻烦。我说这样做你不认为亏吗。他说如果说亏那也不是我一个人。再说,十几年都过来了,与那些将生命献给昆仑山的战友相比,我并不感到吃亏。
……
就这样,我从李亚忠的谈话中,对包括他在内的每一个淡薄名利、不计得失、无私奉献的边防军人更加产生了深深的敬意。
返回的路上,昆仑上还是那么雄伟高大,昆仑山上空的天还是那么湛蓝湛蓝。
我为自己能有这样一段亲历喀喇昆仑山的经历感到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