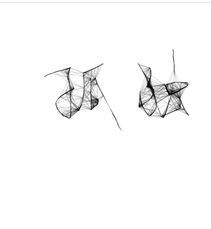作者/不周山(微博:不周山怎么了)
这会是近期最长的一篇,想过分两次连载又想作罢,你若有耐心看完就看完,没有也无甚大碍。这几日翻出这篇反反复复地修改,但最终还是保持了它最初的样子,总觉得是太稚嫩的炙烈,是那种病态少女时期的情感,像一把没有柄的刀,刺痛了别人也划伤自己, 但如若多一份成熟又会显得故意作怪,17岁的时候她不懂这些,即使看着她犯错也只能在平行地岁月里留一声叹息。但这是17岁的绝笔,再提起将是又一个黄桃,又一个自己。希望你们能原谅17岁的黄桃,原谅17岁曾想与世界为敌的自己。
她,可以在午夜独自游荡,不怕空旷的屋子没有光亮,却唯独无法忍受一个人路过黄昏,感受渐变而来的漆暗。
那天,她在豆瓣的一个小组里起了一个线上活动:明天我要去西藏了,一个人。
回复1:呵呵。
回复2:我今天还刚从西藏回来呢。
回复3:你再骗回复可就真懒得理你了。
……
黄桃也已经不记得这是第几次说这些个无聊的话了,她没想过要谁理理她,只是突然又抽了一下,想要矫情一下,大家都是一群深夜独行的夜行人,都彼此了解却从不彼此安慰,他们有属于这个群体的生存方式。不深入,无伤害。
那么一瞬,她忽然想起第一次进豆瓣,一个人翘了晚自修跑去网吧,无意地打开了纯白音乐电台,又无意地进了一个小站,她是那么弱弱地看着电脑屏幕上不断更新的回复,那一次大家好像也是在讨论关于旅行的话题,具体的是什么不记得了,只是当时那种无法形如感觉一直还在,好像暖暖的,又好像凉凉的,这么久他一直把那种感觉定义为自由。她说,这是她唯一可以确定的一次。
凌晨两点零五分,是黄桃最喜欢的入眠时间。她说这个时间把黑夜划分成两半,而她将是最安全的夜行人。我不知道她是怎么算的,我也不想去纠结,她说是的,那就是的好了。
闹钟五点响,黄桃从来没有在八点之前起过床,除非黄亦韦回来,今天就是。
你还知道回来?。
沉默。
不说话?是啊,我是没有外面的女人说话好听,不愿意搭理我是吧!嫌弃我是吧!
沉默。
黄亦韦,我告诉,你别不要脸,找个小三比你闺女大不了几岁,你不要脸我还要呢!
妈,你闹够了没?他犯贱你给他离婚行吗?你别他妈的也跟着犯贱行吗?
黄桃直冲到客厅指着蓬头垢面的妈妈大骂了一句。你们不要怪她,她以前不是这样的,真的。
啪^^
黄亦韦一个巴掌打在了黄桃的脸上。
滚……
她哭?怎么可能?黄桃这辈子最讨厌的就是看到女人哭的样子,绝望的,痛苦的,委屈的,愤怒的……从小到大各种感情的哭泣眼前这个韶华殆尽的女人让她看够了。她说女人哭是这个世界上最让人反胃的事情。
滚就滚,可是,滚远了……
黄桃只穿了一个白色的四角短裤和一个紧身吊带,连外套都没有带,头也不回的走了。
七月的天,除了燥热什么也没有,早上也不例外。那聒噪的声音是蝉鸣吗?好久没听过了,不大记得。
经过楼下花园,黄桃顺便从凉衣绳上取了一件牛仔外衫,好大。明显不是她的,随意,可以出门就好。
十七岁的姑娘,应该是爱美的不是吗?美美的裙子,微微耸起的胸部,第一双粉色高跟鞋……
可是我能说黄桃从来不穿内衣么?她厌恶自己身上任何可以吸引到异性的部位,每晚她都会用白布裹着胸部睡觉,白天再穿上紧紧的抹胸外套一个T恤就好,头发从来没有超过耳朵,黄桃最讨厌的就是家里浴室里那个落地的大镜子,因为洗澡的时候她总能不自觉地看到镜中自己那不断发育的身体,每次都能让她想起妈妈裸着身体在屋里走来走去的场景,后来终于忍无可忍便每次洗澡的时候都将镜子用白布包起来。
黄妈不是不知道黄桃的怪癖,还记得黄妈发现黄桃裹胸时崩溃地表情。她发疯了一样抓着黄桃的头发,扒掉黄桃的裹布并且脱掉自己的上衣,连拉带拽地把黄桃拉到卫生间的落地长镜前,逼着她看镜子里的自己。
镜子里的两个女人,半裸着身子,一个是蜜桃待熟,一个是橘子落地。
黄妈指着自己已下垂的乳房说:这才是女人该有的,你为什么不让它生长?为什么?那是我带给你的,那是我的!
黄桃死死地低着头不愿看镜子,我不知道她是不愿意看自己,还是那个女人。
抬头,为什么不看?看看你那副鬼样子!
黄妈抓着黄桃的头逼她看镜子。
别逼我。
我逼你?好,我就逼你了!
黄妈跌跌撞撞地跑去卧室,拿着一个粉红色的内衣过来。
妈,你干嘛?
穿上,快,给我穿上!
不,我不穿。
黄妈一把将黄桃拦在怀里,想强行给她穿上。
黄桃挣脱来妈妈抓起放在盥洗台上的剃须刀深深地在自己的左胸上划了一刀,鲜血直喷到镜子上,那一刻黄桃看到了缤纷起舞的蝴蝶。
黄妈吓呆了。
原地静待了30秒,以后。
她连忙用手堵着出血的刀口,可是血还是不停地从指缝里涌出顺着黄桃的身体向下流,恍惚间整个浴室里都是血,都是沾染着绝望的血。你看着它流就好像蠕动的蛇,不是红而是,病态的紫。
怎么办?怎么办?桃儿,血,好多血。黄妈看着不断流出的血愈发地不能理智下来,好像黄桃身上的血要流完了一样。
妈!
黄桃将趴在自己胸口用嘴堵着伤口的妈妈推开,顺手拿了一条白色毛巾按在伤口上。
妈,别再逼我,逼我一次我划一次。
转身,离开。浴室里只剩下瘫坐在地上的黄妈。
那之后,黄妈再也没有逼黄桃穿内衣,可是她依旧在换季的时候给黄桃买各种内衣,洗净后整整齐齐地放在黄桃的衣橱里,好似一切都不曾发生过,只是那以后每次也会给她买质地较好的抹胸。黄桃没有阻拦,只要她不再闹腾就好,她想。
前面是个路口,直走是红灯区,还有56秒要等,黄桃想也没有想就选择的平时很少走的左边路口,她想我的人生已经很悲惨了,说不定明天就死在哪个巷口,为什么还要分出56秒给这毫无意义地等待。
从九岁开始,黄桃便活在茫茫的威胁里,面对时不时发疯的妈妈,许久才回一次家的爸爸,嘲笑她的同学和漠视她的老师,她早已习惯到麻木了。
这个时间要去哪里?去学校吗?还是不要了。黄桃一个人沿着马路往前走,路的尽头好像很远很远,一眼望过去看不到末端。很久很久以前,她以为以后就是永远。只要过了今天就会好的,可是她过了无数个今天却怎么也迎不来新的明天。再以后,她也不再希冀,得过且过就好了。
下个路口过了以后应该是有个网吧的,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网吧里空荡荡的,剩下的只是昨晚夜场留下的狼藉。黄桃找个一个墙角的位置。桌子上有半包兰州,应该是上一个机客落下的,黄桃并没有点着只是抽了一根叼在嘴里。突然她想到妈妈一个人脱了裤子蹲在马桶上反复抽烟的样子就干呕起来,于是她连同桌子上剩下的烟一起扔进了垃圾桶并且连吐了两口唾沫。
每次打开电脑,她习惯性的先登上人人,再去豆瓣。人人上好冷清,豆瓣上前夜的欢愉也渐渐的散去。昨晚她发起的线上活动有了几条新的回复,打开一看,是一个叫迟暮的留的。
真的么?我今天也打算去西藏呢!好兴奋,睡不着。
方便的话给我联系吧,我们一起!我从北京出发。
我也是一个人,希望可以遇见你。
回复时间是今天凌晨三点二十。
他也是开玩笑的,对吧!每天想去西藏的人多了,大家只是在一起娱乐假想一下而已。黄桃关了豆瓣,将音量调到最大反复听着一首歌。可是不知怎的,这次她却怎样也无法装作若无其事。
十七岁的少女应该是洛丽塔一样的精灵不是吗?即使没有碎花的白裙子也应该有对美好向往的心不是吗?
这个城市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圈住了黄桃所有的世界,也禁锢了她所有的梦。
每次黄妈犯病黄桃都在心里暗暗下决心:如果她下次再这样我就离开,像爸爸一样放弃她。可是每次平风浪静以后黄妈那歉意的眼神和温柔的亲抚都让黄桃无法拒绝。日子让她渐渐地明白:所谓母女就是一世的缘分,爱你,伤害你,甚至是欺辱你,都带受着,过了这一生。至于下辈子是什么关系,伤害还是被伤害都只留在看不见的未来。
要这样下去吗?就这样一直下去?用他们的错来伤害我?
黄桃愈发的不安,不知怎的她的心再也无法平静,第一次在豆瓣上讨论旅行的感觉再一次逆袭而来,好似什么在胸口燃烧着是她坐立不安。
黄桃,走吧!这一切本就不应该由你来承担。
黄桃,去吧!找回你自己!找回你的生活!
黄桃看到一道曙光,好像回到八岁有笑声的童年。有稻香的野外,有爱的爸妈,还有穿裙子的黄桃。
暖风里一个精灵在奔跑,一步一秒,一瞬一息,风中那摇晃的树叶好似她飞舞的翅膀,她是这灼灼夏日唯一的清凉。她跑在这街道,这梦里。
我要去西藏!
从来没有这么肯定过要去做一件事而且是马上就去做。
黄桃潜伏回了家,蓝亦韦已经离开,黄妈像每次吵完架一样坐在马桶上抽烟。黄桃尽量让自己的步伐轻盈,她只想平静地离开。
黄桃先去黄妈的卧室找出藏在橱柜的银行卡,密码是黄桃和蓝亦韦生日的后三位数。是黄妈告诉她的,她怕自己哪一天无法再醒来会连同密码一起忘了便在一次犯病后把家里所有贵重东西存放的地点和银行卡的密码都告诉了黄桃。
黄桃从来没有想过要动这笔钱,更没有想过会是用它做自己出逃的旅费。想到这里黄桃愈发的紧张,她快步地走向自己的房间简单地收拾一些换洗衣服便匆匆离开。出门之前她又偷偷地站在卫生间门外看了看那个吞烟吐雾的女人说了一声:再见。
就这样离开,毫不犹豫地离开。这一次踏出门的步伐比哪一次都坚定。
黄桃打的去了长途客运站然后坐了最近的客车到青海,在西宁火车站搭上了前往拉萨的火车。上火车的那一刻,黄桃的心瞬间平静下来,这一路是那么顺利好像是一场蓄谋已久的逃亡。
那么一瞬黄桃想起了那个豆瓣上给她回复的朋友,会不会有缘分遇见?她不知。
火车疾驰着,迎面的风击打着铁皮,好像在耳边诉说。青海境内四散的小盐湖像是揉碎的月光,在眼底闪烁。黄桃看着窗外不断流失的风景,没有来得及感伤下一个风景就进入视野,渐入的草原牧场你看到的是养风的孩子在放羊,那种无束缚的奔跑才叫自由。金沙滩的传奇永远留在的最遥远的地方。
火车在托素湖站停留,对面的旅客拎着麻包艰难地下了车留下了两个空位,车子启动没有新的旅客再上车那两个座位还是孤独的空着,黄桃本想挪过去小躺一会,兴奋过后总是会有短暂的疲惫。就在这时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女人出现在黄桃面前,她指着对面的那两个空位试探着问:“请问这里有人吗?”
周围的人各忙各的没有人理会她,她的眼神停留在黄桃的身上企图从她这得到一个回答。
没人。
谢谢。
女人很安静地坐下,一头卷发随意地垂在胸前,是那种暮色的金黄,衬着她白皙的皮肤真好看。坐在黄桃身边的大叔起身应该是要去厕所,衣角不小心碰倒了桌子上的水杯,温度尽消的冷水在桌子上肆溺,那大叔看了一眼头也不回地径直走向卫生间。女人从包里拿出纸巾站起身来,用纸巾一点一点地吸附桌子上的水渍。她的手指又细又长,唯一美中不足的右手中指左侧有一个鼓起的茧子。她的头发在黄桃面前飞舞,几根凌乱的发丝打在黄桃的鼻尖,一股淡淡的烟草味袭来,这是黄桃这辈子第一次闻到的有记忆的味道,是涩涩的甜,她记住了。
收拾妥当以后,便是死寂的沉默。黄桃总是趁这女人不注意时偷偷瞟她两眼。不知为什么,她觉得她好美。那女人只是一直望向窗外,很远很远的地方。
黄桃就这样恍恍惚惚地睡去,梦里她又看到那个蹲在马桶上抽烟的女人,她跑啊跑却怎么也跑不出那烟雾缭绕的空间。她恨,恨到心底。恍惚,她又回到了八年前的那个黄昏,妈妈跪在爸爸的身旁请求他原谅,那是黄桃第一次看到妈妈哭得那么绝望。那也是个夏天,白昼好似有意把岁月拉长,企图帮助那个犯了错的女人留住这最后一丝光亮。那个黄昏好长好长,长的让人顿生厌烦,爸爸终究没有等到迟暮地入袭就摔门而去,只留下离婚两个字。
生活多半是这样的,女人多少能够容忍丈夫的出轨,但是男人却不能容忍妻子的一丝背叛,她的身体和灵魂完全都是属于自己的,那是他的营垒,他的战利品。她可以是他的一部分,但是他必须是她的所有。
离婚?不,我不能离婚!桃儿,桃儿,帮妈妈求求爸爸,妈妈知道错了,我不能没有这个家,不能没有他。
桃儿!
桃儿!
那个黄昏,黄桃一直躲在储藏室里里听着妈妈撕心裂肺地呼喊,微弱的暮光透过那一方窗棂照在黄桃挂满泪痕的脸上。没有人知道她当时那种绝望的恐惧。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黄桃一定不让爸爸去重症监护病房看外婆,那一眼敷衍了爸爸的生活,禁锢了妈妈的一生,更凌乱了黄桃的世界。
亦韦,你一定要答应妈,不能和蓝儿离婚,算妈求你了!
妈,你好好养病不要多想。
你答应妈,让妈走的心安,我就这么一个孩子不能看着她的家败了,妈求求你。
妈!
外婆!
各种检测仪器突然发疯似得响了起来。
我答应您!答应您!
外婆被人推进了长廊尽头的抢救室,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黄妈应该就是在那一晚崩溃的。那一晚的兵荒马乱种在了黄桃的心里。
醒醒,醒醒。
有一个声音在呼喊,可是黄桃却清醒地睡着,无奈地任由梦境来折磨自己,身体一直往下沉,她不再挣扎,只待着梦将自己摔醒。
黄爸做了妥协,外婆离开后他再也没有提出过离婚,可是黄妈却再也无法走出自己涂抹的那片阴霾。
人到底是多可怕的生物,不知疲倦地用自己的错误来惩罚别人虐待自己。黄妈疯了似的活在自己勾勒的故事情节里:丈夫背叛了自己,气死了母亲。
对于一个失了心智的女人,世界就在他的幻想里,没有所谓的事实,事实就是她想的一切。
姑娘,醒醒,别睡了。
那个声音好执着,她一直在呼喊,她知道黄桃痛苦,她想叫醒她。这么多年,每个夜晚黄桃都是在各种各样的噩梦中度过的,每一次的梦靥她都渴望能有一个人能将自己唤醒,直到希望变成绝望,那个渴望的呼唤也没有出现。
姑娘,快醒醒。这次伴随着呼喊的还有摇晃,那股暖流从一个小小的手掌传递到黄桃的血液,冰释了她冻结的血液,也唤醒了她的梦境。
我想她是被这呼唤感动了,八年来黄桃第一次流着泪醒过来。他不敢相信眼角的液体会是泪,她起身跑去卫生间打开水龙头冲洗自己的脸,企图洗掉她流泪的事实。她看着镜中的自己好模糊,暮色四合,柔光照射在镜中上眼睛挣得好吃力。
大戈壁的黄昏那么的长,却是愈发的苍凉,一望过去你可以感受到潜伏在隔壁尽头的黑夜正在躁动。黄桃又把自己的头对着水龙头冲了个彻底。
车还在行驶着,但是速度显然慢了下来,像是已经进入站台了,想想一会儿来来往往的人群黄桃便朝自己的座位走去。
那个女人怎么不在?去卫生间了?下车了?
不知怎的黄桃变得特别不安,好像走失的孩子一般焦虑。车已经停下了,难道她真的到站了?黄桃连忙问坐在她身边的那个大叔,那大叔昏昏欲睡地迷糊着末了才说了一句:下车了。
黄桃哦了一声瘫坐下来,莫名地心痛,没有缘由的。她和这个女人明明连一句话都没有说,可是为什么会这么落寞?
她不是才上车不久吗怎么就这么快下车了?黄桃在心里还想反复安慰自己。
对了,姑娘,这是刚才那个姑娘让给你的。
那大叔拿起放在桌子上的一张素描纸,上面画的是黄桃熟睡的样子,那样干净明朗的样子只是眉宇间满是踌躇。
迟暮!
落款处迟暮两个字深深地刺痛了黄桃的眼。
火车已经缓缓启动了,黄桃抓起自己的旅行包就往出口跑去,列车员已经开始准备关车门了。
不要,没有等列车员反应过来黄桃已经跳下车去。
姑娘!
面对火车上列车员担心的眼神,黄桃回敬他一个抱歉的眼神。火车跑起来了,载着一车人的生命和灵魂。黄桃是这列车的叛徒:没有从起点上,更没有从终点下。注定是匆匆的过客,不留痕迹。
黄桃抬头找站牌,德令哈三个字出现在她的视野里。
德令哈?她为什么要在这里下?这里是她的家吗?
德令哈是个小站,在这里下的人不多,可是稀廖的人群里却怎么也看不到那个熟悉又陌生的身影。黄桃在长长的站台里来来回回地跑着企图在哪个隐蔽的角落可以找到她,可是结局仍是徒劳。黄桃站在原地不再动,看着流动的人群她突然大笑起来,笑自己?笑着笑着便哭了,今天第二次哭,并且是因为同一个女人,黄桃越哭越止不住,好似要把这么多年的委屈都发泄出来一般。这世界早已经没有谁会真的在意她,她知道。
喂,你原来在这里!
这声音,转身,是那女人。黄桃泣不成声地投到她的怀里,那女人显然被她吓坏了,但她没有推开她,只是不停地安慰她是她平静下来。
落日的余辉已经吻着夕阳老去,残光打在黄桃和那女人身上。小小的站台人群散尽,只剩下一地的暮色和黄桃时强时弱的哭声。不知道她哭了多久,只感觉那个黄昏好长好长,她的哭声好远好远。
那个傍晚,她们两个沿着铁轨走了好久好久,在这白日的末迹,斑驳的铁轨,两个陌生的路人拼凑了一次逃亡。黄桃以为她们会一直走下去,走到路的尽头,走到生命的尽头。
黄桃从来没有这么放松地沉醉在暮色里过,那每每黄昏袭来的惶恐不安之感此刻全然消失。黄桃在晚风中奔跑,追赶那隐没的夕阳。
你喜欢暮色?
不!也不是,只是害怕。
害怕?可是此刻的你看着很快乐。
我说因为有你陪着所以没有畏惧你信吗?
嗯?
我害怕看着光亮消失的黄昏,眼睁睁地看着黑夜袭来的感觉让我窒息。你可以预示着一切,预示着美好的消失,预示着希望的幻灭,可是却无能为力。那种已知的绝望让我惶恐到麻木。
你只是太缺乏安全感了,大的变动总会让你有失去感。
是吗?他们都说我是疯子,你会不会也这样觉得?
我?我……不会。
那你会陪着我吗?
那女人的眼神中闪露出一丝慌张。
会的。
以后都会吗?
额,会的。
谢谢你,谢谢你送我的画,迟暮,我很喜欢。
不会,只是感觉你睡觉的样子很美。
……
那个黄昏,黄桃像是开了阀门的流水向那个女人倾诉了所有,她的痛,她的无奈,她的一无所有。她从来没有这么发泄过,从来没有。
那女人一直不语,就那么静静地听着她讲。
夕阳隐没时,她们在走;黑暗袭来是,她们在走;星空闪烁时,她们在走……这世间好似只剩下她们两个,只愿只剩下她们两个。
那以后的种种,黄桃再不记得。那晚上她睡得那么稳,那么安宁,没有梦魇,没有深渊,没有挣扎,没有痛苦。她想着就这样跟着这么女人一直走下去,不管去哪里,只要和她在一起就好。
黑暗早已褪去,戈壁上的早晨愈发温柔,这个世界突然就亮了。黄桃能感受到阳光在一点一点地亲吻自己的肌肤,她不愿睁开眼睛怕一切都只是一个梦。
这姑娘睡的真香。
大概是昨天太累了。
她身上有没有证件。
她随身携带了一个旅行包还没有检查,等她醒来先问问再说。
送她过来的人呢?
昨天晚上就走了。
黄桃听到有各种碎碎的声音,脚步声,倒茶水的声音,私语声。这是在哪里?黄桃懒懒地睁开眼睛,白墙?红旗?警徽?警服?唯独没有那女人。
这是哪里?
你醒了,姑娘。
这是在哪里?迟暮呢?
这里是派出所,迟暮?
就是和我在一起的那个女人。
你是说送你来的那个女人,她昨天晚上就走了。
她走了?她为什么把我一个人留在这里。她去哪了,告诉我。
姑娘你冷静一下。别着急,我们会把你送回家的。
我不要回家!不要回家!
两个民警私语讨论要不要送黄桃去医院看一看。
呵!原来她也把我当成疯子!骗子,都是骗子!
黄桃冲出派出所,在这个陌生的小镇狂奔。她感到眼前的一切都如此地令人惧怖,低矮的房子在嘲笑自己,弯曲的街道在戏弄自己,刺眼的阳光在挑衅自己,挺拔的白杨在藐视自己,所有的一切都黑压压地朝自己袭来,那是一种怎样万念俱灰的绝望。
黄桃怕了。这次是真的怕了。
这个世界怎么可以残忍的若此决绝,怎么可以。
德令哈的民警在黄桃遗落的包里找到了她的证件联系上了黄爸,几个小时后黄爸就赶到了这个小镇。他们在一段废旧的轨道找到了黄桃。
黄爸在一旁不停地感谢德令哈的民警并不停地询问是谁帮的忙报的警。
应该的,是我们镇小学的一个新来的美术老师,对了这幅画《迟暮》是赵老师送给姑娘的。
谢谢,谢谢……
桃儿,快来谢谢民警叔叔。
沉默。
桃儿,我们先去谢谢赵老师再回家。
沉默。
桃儿,以后爸爸再也不会骂你了。
以后?以后是多久?
很久以前,桃儿以为以后是永远。
路过谁以后,桃儿坚信以后就只是明天。
把所有的爱与虚伪停留在明天。
桃儿,以后……
沉默,还是沉默。
这沉默。这沉默的尽头是什么?是一个蹲在马桶上吸烟的女人的背影?是一声划破宁静的争吵?还是……
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夜色笼罩
姐姐,我今夜只有戈壁
草原尽头我两手空空
悲痛时握不住一颗泪滴
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
这是雨水中一座荒凉的城
除了那些路过的和居住的
德令哈......今夜‘
这是唯一的,最后的,抒情。
这是唯一的,最后的,草原。
我把石头还给石头
让胜利的胜利
今夜青稞只属于他自己
一切都在生长
今夜我只有美丽的戈壁 空空
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
——海子
尊重原创,转载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