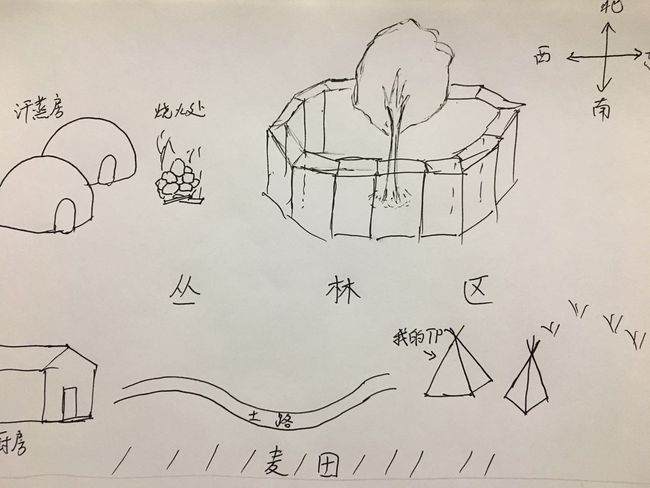- guava loadingCache代码示例
IM 胡鹏飞
Java工具类介绍
publicclassTest2{publicstaticvoidmain(String[]args)throwsException{LoadingCachecache=CacheBuilder.newBuilder()//设置并发级别为8,并发级别是指可以同时写缓存的线程数.concurrencyLevel(8)//设置缓存容器的初始容量为10.initialCapacity(10)//设置缓存
- 系统学习Python——并发模型和异步编程:进程、线程和GIL
分类目录:《系统学习Python》总目录在文章《并发模型和异步编程:基础知识》我们简单介绍了Python中的进程、线程和协程。本文就着重介绍Python中的进程、线程和GIL的关系。Python解释器的每个实例都是一个进程。使用multiprocessing或concurrent.futures库可以启动额外的Python进程。Python的subprocess库用于启动运行外部程序(不管使用何种
- C++11堆操作深度解析:std::is_heap与std::is_heap_until原理解析与实践
文章目录堆结构基础与函数接口堆的核心性质函数签名与核心接口std::is_heapstd::is_heap_until实现原理深度剖析std::is_heap的验证逻辑std::is_heap_until的定位策略算法优化细节代码实践与案例分析基础用法演示自定义比较器实现最小堆检查边缘情况处理性能分析与实际应用时间复杂度对比典型应用场景与手动实现的对比注意事项与最佳实践迭代器要求比较器设计C++标
- 为什么会出现“与此站点的连接不安全”警告?
当浏览器弹出“与此站点的连接不安全”的红色警告时,不仅会让访客感到不安,还可能直接导致用户流失、品牌信誉受损,甚至引发数据泄露风险。作为网站运营者,如何快速解决这一问题?一、为什么会出现“与此站点的连接不安全”警告?浏览器提示“不安全连接”,本质上是检测到当前网站与用户之间的数据传输未经过加密保护。以下是触发警告的常见原因:1.未安装SSL证书SSL(SecureSocketsLayer)证书是网
- 什么是证书吊销列表?CRL 解释
WoTrusSSL
sslhttps
数字证书是安全在线互动的支柱,用于验证身份和确保加密通信。但是,当这些证书被盗用或滥用时,必须立即撤销它们以维持信任。这就是证书撤销列表(CRL)的作用所在。CRL由证书颁发机构(CA)维护,对于识别和撤销已撤销的证书,防止其造成危害至关重要。在本指南中,我们将探讨什么是CRL、它们如何运作以及为什么它们对网络安全至关重要。什么是证书吊销列表(CRL)?证书吊销列表(CRL)是证书颁发机构(CA)
- 有必要获得WHQL测试认证吗,有什么好处?
什么是WHQL认证?WHQL是MicrosoftWindowsHardwareQualityLab的缩写,中文意思是Windows硬件设备质量实验室,主要是对Windows操作系统的兼容性测试,检验硬件产品和驱动程序在windows系统下的兼容性和稳定性。当某一硬件或软件通过WHQL测试时,制造商可以在其产品包装和广告上使用“DesignedforWindows”标志。该标志可以证明硬件或软件已经
- Flask框架入门:快速搭建轻量级Python网页应用
「已注销」
python-AIpython基础网站网络pythonflask后端
转载:Flask框架入门:快速搭建轻量级Python网页应用1.Flask基础Flask是一个使用Python编写的轻量级Web应用框架。它的设计目标是让Web开发变得快速简单,同时保持应用的灵活性。Flask依赖于两个外部库:Werkzeug和Jinja2,Werkzeug作为WSGI工具包处理Web服务的底层细节,Jinja2作为模板引擎渲染模板。安装Flask非常简单,可以使用pip安装命令
- 驱动程序为什么要做 WHQL 认证?
GDCA SSL证书
网络协议网络
驱动程序进行WHQL(WindowsHardwareQualityLabs)认证的核心价值在于解决兼容性、安全性和市场准入三大关键问题,具体必要性如下:️一、规避系统拦截,保障驱动可用性消除安装警告未认证的驱动在安装时会触发Windows的红色安全警告(如“无法验证发布者”),甚至被系统强制拦截。通过WHQL认证的驱动获得微软数字签名,用户可无阻安装。满足系统强制要求Windows1
- 求是网:“内卷式”竞争的突出表现和主要危害有哪些?
加百力
财经研究科技知识人工智能大数据
"内卷式"竞争主要表现为:企业层面的低价竞争、同质化竞争和营销"逐底竞争";地方政府层面的违规优惠政策、盲目重复建设和设置市场壁垒。危害体现在三个层面:微观上导致"劣币驱逐良币",损害消费者利益;中观上破坏行业生态,挤压产业链利润空间;宏观上扭曲资源配置,抑制创新活力。什么是“内卷式”竞争?概括其一般特征,是指经济主体为了维持市场地位或争夺有限市场,不断投入大量精力和资源,却没有带来整体收益增长的
- WHQL签名怎么申请
GDCA SSL证书
windows
WHQL(WindowsHardwareQualityLabs)签名是微软对硬件和驱动程序进行认证的一种方式,以确保它们与Windows操作系统的兼容性和稳定性。以下是申请WHQL签名的基本步骤,供您参考:1.准备阶段准备硬件设备和驱动程序:确保您的硬件设备已经准备好,并且对应的驱动程序已经经过充分的测试,能够在各种配置和环境下正常工作。获取EV代码签名证书:根据微软的要求,驱动程序进行WHQL认
- JSON 与 AJAX
Auscy
jsonajax前端
一、JSON(JavaScriptObjectNotation)1.数据类型与语法细节支持的数据类型:基本类型:字符串(需用双引号)、数字、布尔值(true/false)、null。复杂类型:数组([])、对象({})。严格语法规范:键名必须用双引号包裹(如"name":"张三")。数组元素用逗号分隔,最后一个元素后不能有多余逗号。数字不能以0开头(如012会被解析为12),不支持八进制/十六进制
- 发票合并工具
小朋的软件园
前端javascriptjavahtml服务器
"发票合并工具"是一款专为高效整理票据设计的实用工具,支持将来自不同渠道的发票文件(如PDF文档、各类图片格式)快速整合为排版规范的PDF文件,尤其适用于财务报销场景下的批量票据处理需求。核心功能亮点多格式兼容:无缝导入PDF文件及常见图片格式(.png/.jpg/.jpeg/.bmp),适配多来源发票整合需求。智能布局配置:提供灵活的页面布局选项(每页2/3/4张发票),其中"2合1"模式针对报
- Python Flask 框架入门:快速搭建 Web 应用的秘诀
Python编程之道
Python人工智能与大数据Python编程之道pythonflask前端ai
PythonFlask框架入门:快速搭建Web应用的秘诀关键词Flask、微框架、路由系统、Jinja2模板、请求处理、WSGI、Web开发摘要想快速用Python搭建一个灵活的Web应用?Flask作为“微框架”代表,凭借轻量、可扩展的特性,成为初学者和小型项目的首选。本文将从Flask的核心概念出发,结合生活化比喻、代码示例和实战案例,带你一步步掌握:如何用Flask搭建第一个Web应用?路由
- C++ 11 Lambda表达式和min_element()与max_element()的使用_c++ lamda函数 min_element((1)
2401_84976182
程序员c语言c++学习
既有适合小白学习的零基础资料,也有适合3年以上经验的小伙伴深入学习提升的进阶课程,涵盖了95%以上CC++开发知识点,真正体系化!由于文件比较多,这里只是将部分目录截图出来,全套包含大厂面经、学习笔记、源码讲义、实战项目、大纲路线、讲解视频,并且后续会持续更新如果你需要这些资料,可以戳这里获取#include#include#includeusingnamespacestd;boolcmp(int
- C++ 11 Lambda表达式和min_element()与max_element()的使用_c++ lamda函数 min_element(
网上学习资料一大堆,但如果学到的知识不成体系,遇到问题时只是浅尝辄止,不再深入研究,那么很难做到真正的技术提升。需要这份系统化的资料的朋友,可以添加戳这里获取一个人可以走的很快,但一群人才能走的更远!不论你是正从事IT行业的老鸟或是对IT行业感兴趣的新人,都欢迎加入我们的的圈子(技术交流、学习资源、职场吐槽、大厂内推、面试辅导),让我们一起学习成长!intmain(){vectormyvec{3,
- k8s:安装 Helm 私有仓库ChartMuseum、helm-push插件并上传、安装Zookeeper
云游
dockerhelmhelm-push
ChartMuseum是Kubernetes生态中用于存储、管理和发布HelmCharts的开源系统,主要用于扩展Helm包管理器的功能核心功能集中存储:提供中央化仓库存储Charts,支持版本管理和权限控制。跨集群部署:支持多集群环境下共享Charts,简化部署流程。离线部署:适配无网络环境,可将Charts存储在本地或局域网内。HTTP接口:通过HTTP协议提供服务,用户
- 上位机知识篇---SD卡&U盘镜像
常用的镜像烧录软件balenaEtcherbalenaEtcher是一个开源的、跨平台的工具,用于将操作系统镜像文件(如ISO和IMG文件)烧录到SD卡和USB驱动器中。以下是其使用方法、使用场景和使用注意事项的介绍:使用方法下载安装:根据自己的操作系统,从官方网站下载对应的安装包。Windows系统下载.exe文件后双击安装;Linux系统若下载的是.deb文件,可在终端执行“sudodpkg-
- 【LeetCode 热题 100】24. 两两交换链表中的节点——(解法一)迭代+哨兵
xumistore
LeetCodeleetcode链表算法java
Problem:24.两两交换链表中的节点题目:给你一个链表,两两交换其中相邻的节点,并返回交换后链表的头节点。你必须在不修改节点内部的值的情况下完成本题(即,只能进行节点交换)。文章目录整体思路完整代码时空复杂度时间复杂度:O(N)空间复杂度:O(1)整体思路这段代码旨在解决一个经典的链表操作问题:两两交换链表中的节点(SwapNodesinPairs)。问题要求将链表中每两个相邻的节点进行交换
- Guava LoadingCache
sqyaa.
java并发编程Java知识jvm缓存guava
LoadingCache是GoogleGuava库提供的一个高级缓存实现,它通过自动加载机制简化了缓存使用模式。核心特性自动加载机制当缓存未命中时,自动调用指定的CacheLoader加载数据线程安全:并发请求下,相同key只会加载一次灵活的过期策略支持基于写入时间(expireAfterWrite)和访问时间(expireAfterAccess)的过期可设置最大缓存大小,基于LRU策略淘汰丰富的
- JavaScript 树形菜单总结
Auscy
microsoft
树形菜单是前端开发中常见的交互组件,用于展示具有层级关系的数据(如文件目录、分类列表、组织架构等)。以下从核心概念、实现方式、常见功能及优化方向等方面进行总结。一、核心概念层级结构:数据以父子嵌套形式存在,如{id:1,children:[{id:2}]}。节点:树形结构的基本单元,包含自身信息及子节点(若有)。展开/折叠:子节点的显示与隐藏切换,是树形菜单的核心交互。递归渲染:因数据层级不固定,
- 基于定制开发开源AI智能名片S2B2C商城小程序的社群游戏定制策略研究
说私域
人工智能小程序游戏
摘要:本文聚焦社群游戏定制领域,深入探讨以社群文化和用户偏好为导向的定制策略。通过分析互动游戏活动、社群文化塑造等关键要素,结合定制开发开源AI智能名片S2B2C商城小程序的技术特性,提出针对性游戏定制方案。研究旨在提升社群用户参与度与游戏体验,为社群游戏发展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指导。关键词:社群游戏定制;定制开发开源AI智能名片S2B2C商城小程序;社群文化;用户偏好一、引言在数字化社交蓬勃发展的
- 冒泡、选择、插入排序:三大基础排序算法深度解析(C语言实现)
xienda
算法排序算法数据结构
在算法学习道路上,排序算法是每位程序员必须掌握的基石。本文将深入解析冒泡排序、选择排序和插入排序这三种基础排序算法,通过C语言代码实现和对比分析,帮助读者彻底理解它们的差异与应用场景。算法原理与代码实现1.冒泡排序(BubbleSort)工作原理:通过重复比较相邻元素,将较大元素逐步"冒泡"到数组末尾。voidbubbleSort(intarr[],intn){ for(inti=0;iarr[
- Leetcode 148. 排序链表
文章目录前引题目代码(首刷看题解)代码(8.9二刷部分看解析)代码(9.15三刷部分看解析)前引综合性比较强的一道题,要求时间复杂度必须O(logn)才能通过,最适合链表的排序算法就是归并。这里采用自顶向下的方法步骤:找到链表中点(双指针)对两个子链表排序(递归,直到只有一个结点,记得将子链表最后指向nullptr)归并(引入dummy结点)题目Leetcode148.排序链表代码(首刷看题解)c
- python_虚拟环境
阿_焦
python
第一、配置虚拟环境:virtualenv(1)pipvirtualenv>安装虚拟环境包(2)pipinstallvirtualenvwrapper-win>安装虚拟环境依赖包(3)c盘创建虚拟目录>C:\virtualenv>配置环境变量【了解一下】:(1)如何使用virtualenv创建虚拟环境a、cd到C:\virtualenv目录下:b、mkvirtualenvname>创建虚拟环境nam
- 全面触摸屏输入法设计与实现
长野君
本文还有配套的精品资源,点击获取简介:触摸屏输入法是针对触摸设备优化的文字输入方案,包括虚拟键盘、手写、语音识别和手势等多种输入方式。本方案通过提供主程序文件、用户手册、界面截图、示例图、说明文本和音效文件,旨在为用户提供一个完整的、多样的文字输入体验。开发者通过持续优化算法和用户界面,使用户在无物理键盘环境下也能高效准确地进行文字输入。1.触摸屏输入法概述简介在现代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触摸屏
- LeetCode 148. 排序链表:归并排序的细节解析
进击的小白菜
2025Top100详解leetcode链表算法
文章目录题目描述一、方法思路:归并排序的核心步骤二、关键实现细节:快慢指针分割链表1.快慢指针的初始化问题2.为什么选择`fast=head.next`?示例1:链表长度为偶数(`1->2->3->4`)三、完整代码实现四、复杂度分析五、总结题目描述LeetCode148题要求对链表进行排序,时间复杂度需为O(nlogn),且空间复杂度为O(logn)。由于链表的特殊结构(无法随机访问),归并排序
- 前端项目架构设计要领
1.架构设计的核心目标在设计前端项目架构时,核心目标是模块化、可维护、可扩展、可测试,以及开发效率的最大化。这些目标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实现:组件化:将UI功能封装为可复用的组件。模块化:将业务逻辑分解为独立的模块或服务。自动化构建与部署:实现自动化构建、测试和部署流程,减少人为操作的错误。代码规范化与检查:确保团队协作时,代码风格和质量一致。2.项目目录结构设计一个清晰合理的目录结构对大型项目
- 精通Canvas:15款时钟特效代码实现指南
烟幕缭绕
本文还有配套的精品资源,点击获取简介:HTML5的Canvas是一个用于绘制矢量图形的API,通过JavaScript实现动态效果。本项目集合了15种不同的时钟特效代码,帮助开发者通过学习绘制圆形、线条、时间更新、旋转、颜色样式设置及动画效果等概念,深化对Canvas的理解和应用。项目中的CSS文件负责时钟的样式设定,而JS文件则包含实现各种特效的逻辑,通过不同的函数或类处理时间更新和动画绘制,提
- 高效批量单词翻译工具的设计与应用
本文还有配套的精品资源,点击获取简介: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批量单词翻译工具通过计算机的数据处理能力,大大提高了语言学习和文字处理的效率。用户通过简单输入单词列表到一个文本文件,并运行翻译程序,即可获得翻译结果并保存至指定文件。该工具集成了内置或外部翻译引擎,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实现快速准确的翻译,并可能提供词性识别等附加功能。尽管机器翻译无法完全取代人工校对,但它为用户提供了一种高效的翻译解
- 嵌入式系统LCD显示模块编程实践
本文还有配套的精品资源,点击获取简介:本文档提供了一个具有800x480分辨率的3.5英寸液晶显示模块LW350AC9001的驱动程序代码,以及嵌入式系统中使用C/C++语言进行硬件编程的实践指南。该模块的2mm厚度使其适用于空间受限的便携式设备。内容包括驱动程序源代码、硬件控制接口使用方法,以及如何在嵌入式系统中进行图形处理、电源管理与性能优化。1.嵌入式系统原理1.1嵌入式系统概念嵌入式系统是
- Java序列化进阶篇
g21121
java序列化
1.transient
类一旦实现了Serializable 接口即被声明为可序列化,然而某些情况下并不是所有的属性都需要序列化,想要人为的去阻止这些属性被序列化,就需要用到transient 关键字。
- escape()、encodeURI()、encodeURIComponent()区别详解
aigo
JavaScriptWeb
原文:http://blog.sina.com.cn/s/blog_4586764e0101khi0.html
JavaScript中有三个可以对字符串编码的函数,分别是: escape,encodeURI,encodeURIComponent,相应3个解码函数:,decodeURI,decodeURIComponent 。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它们的区别
1 escape()函
- ArcgisEngine实现对地图的放大、缩小和平移
Cb123456
添加矢量数据对地图的放大、缩小和平移Engine
ArcgisEngine实现对地图的放大、缩小和平移:
个人觉得是平移,不过网上的都是漫游,通俗的说就是把一个地图对象从一边拉到另一边而已。就看人说话吧.
具体实现:
一、引入命名空间
using ESRI.ArcGIS.Geometry;
using ESRI.ArcGIS.Controls;
二、代码实现.
- Java集合框架概述
天子之骄
Java集合框架概述
集合框架
集合框架可以理解为一个容器,该容器主要指映射(map)、集合(set)、数组(array)和列表(list)等抽象数据结构。
从本质上来说,Java集合框架的主要组成是用来操作对象的接口。不同接口描述不同的数据类型。
简单介绍:
Collection接口是最基本的接口,它定义了List和Set,List又定义了LinkLi
- 旗正4.0页面跳转传值问题
何必如此
javajsp
跳转和成功提示
a) 成功字段非空forward
成功字段非空forward,不会弹出成功字段,为jsp转发,页面能超链接传值,传输变量时需要拼接。接拼接方式list.jsp?test="+strweightUnit+"或list.jsp?test="+weightUnit+&qu
- 全网唯一:移动互联网服务器端开发课程
cocos2d-x小菜
web开发移动开发移动端开发移动互联程序员
移动互联网时代来了! App市场爆发式增长为Web开发程序员带来新一轮机遇,近两年新增创业者,几乎全部选择了移动互联网项目!传统互联网企业中超过98%的门户网站已经或者正在从单一的网站入口转向PC、手机、Pad、智能电视等多端全平台兼容体系。据统计,AppStore中超过85%的App项目都选择了PHP作为后端程
- Log4J通用配置|注意问题 笔记
7454103
DAOapachetomcatlog4jWeb
关于日志的等级 那些去 百度就知道了!
这几天 要搭个新框架 配置了 日志 记下来 !做个备忘!
#这里定义能显示到的最低级别,若定义到INFO级别,则看不到DEBUG级别的信息了~!
log4j.rootLogger=INFO,allLog
# DAO层 log记录到dao.log 控制台 和 总日志文件
log4j.logger.DAO=INFO,dao,C
- SQLServer TCP/IP 连接失败问题 ---SQL Server Configuration Manager
darkranger
sqlcwindowsSQL ServerXP
当你安装完之后,连接数据库的时候可能会发现你的TCP/IP 没有启动..
发现需要启动客户端协议 : TCP/IP
需要打开 SQL Server Configuration Manager...
却发现无法打开 SQL Server Configuration Manager..??
解决方法: C:\WINDOWS\system32目录搜索framedyn.
- [置顶] 做有中国特色的程序员
aijuans
程序员
从出版业说起 网络作品排到靠前的,都不会太难看,一般人不爱看某部作品也是因为不喜欢这个类型,而此人也不会全不喜欢这些网络作品。究其原因,是因为网络作品都是让人先白看的,看的好了才出了头。而纸质作品就不一定了,排行榜靠前的,有好作品,也有垃圾。 许多大牛都是写了博客,后来出了书。这些书也都不次,可能有人让为不好,是因为技术书不像小说,小说在读故事,技术书是在学知识或温习知识,有些技术书读得可
- document.domain 跨域问题
avords
document
document.domain用来得到当前网页的域名。比如在地址栏里输入:javascript:alert(document.domain); //www.315ta.com我们也可以给document.domain属性赋值,不过是有限制的,你只能赋成当前的域名或者基础域名。比如:javascript:alert(document.domain = "315ta.com");
- 关于管理软件的一些思考
houxinyou
管理
工作好多看年了,一直在做管理软件,不知道是我最开始做的时候产生了一些惯性的思维,还是现在接触的管理软件水平有所下降.换过好多年公司,越来越感觉现在的管理软件做的越来越乱.
在我看来,管理软件不论是以前的结构化编程,还是现在的面向对象编程,不管是CS模式,还是BS模式.模块的划分是很重要的.当然,模块的划分有很多种方式.我只是以我自己的划分方式来说一下.
做为管理软件,就像现在讲究MVC这
- NoSQL数据库之Redis数据库管理(String类型和hash类型)
bijian1013
redis数据库NoSQL
一.Redis的数据类型
1.String类型及操作
String是最简单的类型,一个key对应一个value,string类型是二进制安全的。Redis的string可以包含任何数据,比如jpg图片或者序列化的对象。
Set方法:设置key对应的值为string类型的value
- Tomcat 一些技巧
征客丶
javatomcatdos
以下操作都是在windows 环境下
一、Tomcat 启动时配置 JAVA_HOME
在 tomcat 安装目录,bin 文件夹下的 catalina.bat 或 setclasspath.bat 中添加
set JAVA_HOME=JAVA 安装目录
set JRE_HOME=JAVA 安装目录/jre
即可;
二、查看Tomcat 版本
在 tomcat 安装目
- 【Spark七十二】Spark的日志配置
bit1129
spark
在测试Spark Streaming时,大量的日志显示到控制台,影响了Spark Streaming程序代码的输出结果的查看(代码中通过println将输出打印到控制台上),可以通过修改Spark的日志配置的方式,不让Spark Streaming把它的日志显示在console
在Spark的conf目录下,把log4j.properties.template修改为log4j.p
- Haskell版冒泡排序
bookjovi
冒泡排序haskell
面试的时候问的比较多的算法题要么是binary search,要么是冒泡排序,真的不想用写C写冒泡排序了,贴上个Haskell版的,思维简单,代码简单,下次谁要是再要我用C写冒泡排序,直接上个haskell版的,让他自己去理解吧。
sort [] = []
sort [x] = [x]
sort (x:x1:xs)
| x>x1 = x1:so
- java 路径 配置文件读取
bro_feng
java
这几天做一个项目,关于路径做如下笔记,有需要供参考。
取工程内的文件,一般都要用相对路径,这个自然不用多说。
在src统计目录建配置文件目录res,在res中放入配置文件。
读取文件使用方式:
1. MyTest.class.getResourceAsStream("/res/xx.properties")
2. properties.load(MyTest.
- 读《研磨设计模式》-代码笔记-简单工厂模式
bylijinnan
java设计模式
声明: 本文只为方便我个人查阅和理解,详细的分析以及源代码请移步 原作者的博客http://chjavach.iteye.com/
package design.pattern;
/*
* 个人理解:简单工厂模式就是IOC;
* 客户端要用到某一对象,本来是由客户创建的,现在改成由工厂创建,客户直接取就好了
*/
interface IProduct {
- SVN与JIRA的关联
chenyu19891124
SVN
SVN与JIRA的关联一直都没能装成功,今天凝聚心思花了一天时间整合好了。下面是自己整理的步骤:
一、搭建好SVN环境,尤其是要把SVN的服务注册成系统服务
二、装好JIRA,自己用是jira-4.3.4破解版
三、下载SVN与JIRA的插件并解压,然后拷贝插件包下lib包里的三个jar,放到Atlassian\JIRA 4.3.4\atlassian-jira\WEB-INF\lib下,再
- JWFDv0.96 最新设计思路
comsci
数据结构算法工作企业应用公告
随着工作流技术的发展,工作流产品的应用范围也不断的在扩展,开始进入了像金融行业(我已经看到国有四大商业银行的工作流产品招标公告了),实时生产控制和其它比较重要的工程领域,而
- vi 保存复制内容格式粘贴
daizj
vi粘贴复制保存原格式不变形
vi是linux中非常好用的文本编辑工具,功能强大无比,但对于复制带有缩进格式的内容时,粘贴的时候内容错位很严重,不会按照复制时的格式排版,vi能不能在粘贴时,按复制进的格式进行粘贴呢? 答案是肯定的,vi有一个很强大的命令可以实现此功能 。
在命令模式输入:set paste,则进入paste模式,这样再进行粘贴时
- shell脚本运行时报错误:/bin/bash^M: bad interpreter 的解决办法
dongwei_6688
shell脚本
出现原因:windows上写的脚本,直接拷贝到linux系统上运行由于格式不兼容导致
解决办法:
1. 比如文件名为myshell.sh,vim myshell.sh
2. 执行vim中的命令 : set ff?查看文件格式,如果显示fileformat=dos,证明文件格式有问题
3. 执行vim中的命令 :set fileformat=unix 将文件格式改过来就可以了,然后:w
- 高一上学期难记忆单词
dcj3sjt126com
wordenglish
honest 诚实的;正直的
argue 争论
classical 古典的
hammer 锤子
share 分享;共有
sorrow 悲哀;悲痛
adventure 冒险
error 错误;差错
closet 壁橱;储藏室
pronounce 发音;宣告
repeat 重做;重复
majority 大多数;大半
native 本国的,本地的,本国
- hibernate查询返回DTO对象,DTO封装了多个pojo对象的属性
frankco
POJOhibernate查询DTO
DTO-数据传输对象;pojo-最纯粹的java对象与数据库中的表一一对应。
简单讲:DTO起到业务数据的传递作用,pojo则与持久层数据库打交道。
有时候我们需要查询返回DTO对象,因为DTO
- Partition List
hcx2013
partition
Given a linked list and a value x, partition it such that all nodes less than x come before nodes greater than or equal to x.
You should preserve the original relative order of th
- Spring MVC测试框架详解——客户端测试
jinnianshilongnian
上一篇《Spring MVC测试框架详解——服务端测试》已经介绍了服务端测试,接下来再看看如果测试Rest客户端,对于客户端测试以前经常使用的方法是启动一个内嵌的jetty/tomcat容器,然后发送真实的请求到相应的控制器;这种方式的缺点就是速度慢;自Spring 3.2开始提供了对RestTemplate的模拟服务器测试方式,也就是说使用RestTemplate测试时无须启动服务器,而是模拟一
- 关于推荐个人观点
liyonghui160com
推荐系统关于推荐个人观点
回想起来,我也做推荐了3年多了,最近公司做了调整招聘了很多算法工程师,以为需要多么高大上的算法才能搭建起来的,从实践中走过来,我只想说【不是这样的】
第一次接触推荐系统是在四年前入职的时候,那时候,机器学习和大数据都是没有的概念,什么大数据处理开源软件根本不存在,我们用多台计算机web程序记录用户行为,用.net的w
- 不间断旋转的动画
pangyulei
动画
CABasicAnimation* rotationAnimation;
rotationAnimation = [CABasicAnimation animationWithKeyPath:@"transform.rotation.z"];
rotationAnimation.toValue = [NSNumber numberWithFloat: M
- 自定义annotation
sha1064616837
javaenumannotationreflect
对象有的属性在页面上可编辑,有的属性在页面只可读,以前都是我们在页面上写死的,时间一久有时候会混乱,此处通过自定义annotation在类属性中定义。越来越发现Java的Annotation真心很强大,可以帮我们省去很多代码,让代码看上去简洁。
下面这个例子 主要用到了
1.自定义annotation:@interface,以及几个配合着自定义注解使用的几个注解
2.简单的反射
3.枚举
- Spring 源码
up2pu
spring
1.Spring源代码
https://github.com/SpringSource/spring-framework/branches/3.2.x
注:兼容svn检出
2.运行脚本
import-into-eclipse.bat
注:需要设置JAVA_HOME为jdk 1.7
build.gradle
compileJava {
sourceCompatibilit
- 利用word分词来计算文本相似度
yangshangchuan
wordword分词文本相似度余弦相似度简单共有词
word分词提供了多种文本相似度计算方式:
方式一:余弦相似度,通过计算两个向量的夹角余弦值来评估他们的相似度
实现类:org.apdplat.word.analysis.CosineTextSimilarity
用法如下:
String text1 = "我爱购物";
String text2 = "我爱读书";
String text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