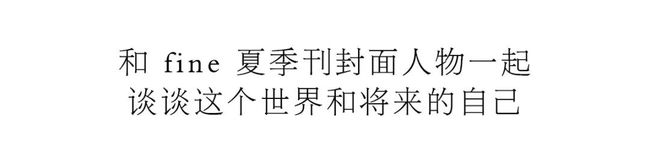fine cover | 华晨宇 “会更好的”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时尚先生fine
(ID:finemagazine)
帽衫 Gucci
运动裤 Ermenegildo Zegna
他有些怯怯地伸出手,轻轻握一握,却没有收回去,指尖冰凉。“实在是对不起……”声音渐渐低下去,几乎被一头蓬乱头发遮住的眼睛盯着地面,仿佛这未抽离的手可以再多表达一分歉意。
他迟到了——前一晚的工作几近通宵,这是一个艰难的早晨。我们一起站在上海近郊的一条小河边,烂漫的夏花丛里有乱舞的蚊蝇,黄梅季未过,雾蒙蒙湿漉漉的空气里笼着不咸不淡的阳光,他显然还没从睡意里完全挣脱出来,像一株无所依靠的蔓藤植物,柔软而倦怠,不知如何是好。
他看起来和周围似乎总有些距离,一种相得益彰、又无需彼此理解的共存。四年前我见过他一次,他正回答着采访的问题,却突然脱下身上的T 恤,然后四下寻找剪刀,专心致志地把领口剪成他想要的参差形状。“是一个会突然遁入自己小世界的人呐”,我还记得当时心里冒出的想法,而一转眼,就看到他正蹲在地上,兴致昂扬地拨开草丛,追踪一只无名小虫的踪迹。
绝大多数人都会不由自主地要求自己在某一个阶段完成某一种成长,先成为被认可的“多数”,再试探自己的棱角被擦亮的可能。但华晨宇简单直接地越过了许多“可不可以”,只遵循自己的节奏和逻辑生长,与众不同,对他而言从来都理所当然,甚至在意识之外。
他身体里似乎有某一部分执拗地停留在了原地,无法被外界改变,更不会被任何事物影响,所以他偶尔的任性和迷糊,与舞台上如入无人之境的自在,都同样顺理成章。他努力从自己的隐秘天地里探出头,寻找一些交融和分享的方式,将来总是会更好的,他知道,如果不追随大流,在隐藏自我之外还有一个选择:边走边唱,走自己的路。
一个无意去了解规则为何物的人,创造了属于自己的规则。
![]()
“相对”
华晨宇最近找到了一个精确的词语来形容自己的状态:相对。“就是对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都可以用相对的视角去看,这让我很轻松,也不会排斥任何一种存在。准确地说,就是接受任何东西,跟人沟通、分享、当老师、上《我是歌手》的比赛……这些对我来说都是可以存在的事情,比较相对。”
他觉得过去有些封闭自己,“很随意”,可他也说不清“随意”到底指什么,或许就是不问世事,“我从小就没有关注新闻的习惯。上学的时候,我用的手机一直都是用几百块的那种,上不了网,我的房间里没有电脑也没有电视,是一个完全与外界隔绝的生活状态。”
他对电子产品的更新换代毫不敏感,一代的速度快过一代,了解之后又要重新了解,实在有点儿麻烦,但一旦入了他眼的新奇玩意儿,他就禁不住去研究。“我喜欢没见过的、好玩的东西,它们也代表我对这个世界的一种好奇吧。”他喜欢电动游戏,继而迷上了VR,“我觉得好神奇,这个世界好神奇”。最入迷的时候,他曾连续几天放不下手,“所以视力越来越差”,因为觉得原本摆放在家里的那张台桌会碍着这个新爱好,就干脆把桌子给扔了。
时代浪潮中汹涌而出的所谓新人新事,他也不怎么关心。“他们总会来,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会这样。我关注的东西、我平时的生活已经够充实了,很多资讯不会进入我的感知范围里。除非真的有一个很好的作品出现,它让我有缘碰到,我会认真看一看,我其实很少上网的。”
他不囤旧物,甚至从来不听自己的歌。“我真的连一张自己的专辑都没有留。我对自己的创作都太熟悉了,任何一个音色、任何一个小小小小小细节我都知道,没有必要再重复。”每一次确认完缩混,他就听完了那首歌的“最后一次”,“编曲编完了,录音录完了,混音也混完了,给我确认了最终版本,我说OK 后,就再也不会听这首歌了。”
除非,它可以“变成很不一样的玩法”,不过在自己的演唱会或是别的场合里重新改编出新版本,他总是感到压力,“歌原来已经很好听了,但又要想出不一样的方式来。比如《异类》可以用一把吉他,或是改成钢琴的伴奏……”
帽衫CHENPENG* X COUNTERFLOW by Li-Ning
相比之下,改编别人的作品更具有挑战性。过去几年里,在《天籁之战》《歌手2018》《王牌对王牌》等节目中,他先后改编过《一人我饮酒醉》《白天不懂夜的黑》《我的滑板鞋》等等作品,赋予了它们全然不同的气质和强烈的个人风格,几乎每一首都会登上微博热搜,又被乐评人拿来细细点评,业内业外,都有十足的关注度。
“改编起来很难,也很好玩,因为你要先理解原版歌曲创作者想表达的东西,找到一个和他(们)的共通点,再加入自己的想法。你首先要了解到这个作品的本质,再加入自己想要传达的东西,你的价值观也好,你想通过这首歌想要表达的世界观也好……应该说是用不同的方式去表现相同的思维。”
今年年初,他在南京的“烎· 2019 潮音发布夜”上与华人编舞家沈伟的舞团合作了《声希》。沈伟曾被美国《华盛顿邮报》评为“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艺术家”,《声希》是他最知名的代表作之一,曾在全球数十个国家演出,每一次几乎都成为当地轰动性极强的“艺术事件”。这部作品以八大山人的“游鱼”为舞台布景,僧侣诵经为背景音乐,舞蹈极缓慢且充满了仪式感,哀而不伤,克制而理性。
当晚会导演把这部作品介绍给华晨宇看的时候,他禁不住“哇”出了声,“很有感觉,沈伟老师怎么能做到这么厉害的?”前一年他和机器人乐队合作过,刚好想再试一些不同的跨界方式,这样的合作简直天时地利人和。“我当时其实有一点压力,就在想如何能把表演变成另一种感觉,但也要很极致。”
思来想去,他觉得无法用歌词这样具象的方式来表述,便用了纯人声吟唱的方式,歌与舞互为映衬又互相对照,如缝隙里丝丝渗入的光。整个作品看起来非常古老又非常未来,似是而非的感觉,被他形容为“黑洞”。“你没有办法去给它一个特别具象化的定义。每个人看那个表演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触,我感觉到的是一个空间,一个黑洞,所以写的东西也在往黑洞上靠,让它的空间具有一种相对感。”
拼色皮夹克Lanvin 衬衫Neil Barrett
他常常会想一些宏大的问题,有关空间,有关次元,开奇奇怪怪的脑洞。“写歌我就要去思考很多人性的问题,思考到最后,就要用我说的‘相对’视角去思考:每件事情你都能找到它的根源,我会去找人类的根源,所有这个世界存在的根源。这个社会为什么会发展到现在,为什么会进阶到这个程度?它都是有根源的。用这种方式思考多了,就会考虑宇宙,再多一点,就会考虑整个次元……越想越大,越想越大。”
想得多一些远一些所带来的并非是缥渺感,“这个世界、这个社会需要这些”,对于无法定夺和张望的将来,他更多抱一种乐观,“这个世界大部分的人都是矛盾的,这是好事,矛盾才可以让整个社会的发展状态越来越好,如果太过佛系、相对视角太多的话,这个世界会倒退。”
看诺兰导演的电影《星际穿越》时,他想,这大概就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未来。基础农作物枯萎病绝,沙尘暴肆虐,人类无法再仰望星空,想象和憧憬也无法自由驰骋,可穿越过星河,依然可以窥见未知星球和黑洞的壮美和神秘。绝望会出现,但总会被希望所替代。
“可能我们要去经历这个阶段,也可能找到一个让自然平衡的状态。”他笑起来的时候有种孩子气,“这个话题好大啊,但那个过程可能和我自己有点儿像,我的意思是,会变好的。”
![]()
“另一个人”
格纹西装、长裤 均为 Alexander McQueen 白色衬衫Dunhill 球鞋Jimmy Choo
我们正一起去往机场,所有人都在庆幸用效率追回的时间,毕竟,第二天他又要在另一个城市完成一堆工作,必须赶上最晚班的飞机。夜色已暗,燥热散去了大半,大家终于可以仔细检查身上各处被凶猛的蚊虫所赐的大包,互相传递花露水。他穿着各式厚实的秋装在草丛里移动了一下午,热得奄奄一息,倒是逃过了这遭罪。此刻他正盘腿坐在椅子上,眼睛盯着前座,恢复了蔓藤植物的状态。
“我超喜欢自然。如果是自己休息的时候,就想去空气好、自然风光好的地方。”他时不时拧一下自己的脖颈后方,艰难地转动一下脖子,让旧伤累累的颈椎调整到舒服一点的姿势。山和海他都喜欢,“它们可以同时存在……也不一定是海,有水就OK了,会让你的感官不一样。”水给予他一种开阔感,有一年住在海边的时候,他写下《寻》,“它就是很开阔的一首歌,是我每天面朝大海时来的灵感。”
和几年前见到的他相比,他更健谈也更善于表达。这种变化多少要归功于他在不少音乐节目中的导师身份,站在一个更客观的角度来看其他的创作者,也让他有豁然开朗的惊喜。“当导师不能说是在教大家,而是分享我的经验和理念。和学生沟通的时候我真的是当成聊天,因为创作人各自会有各自的想法,我也常常在向他们学习。”乐理这些基础知识可以学习,也有章可循,但音乐如何可以做到更好,需要旗鼓相当的交流,“灵魂碰撞”。
《花儿与少年》等综艺节目也让他去了不少陌生的城市,行过万里路,也让他的好奇心有了不同的维度。只是每次到访一个新的地方,他感兴趣的点都会因地而异,“第一次出国的时候,我对马路上的石砖很感兴趣。”他突然停下来,有点儿不好意思地问,“这是不是很奇怪?”接着就回到了当时研究那些花纹的表情,“很多铺在马路边的就是雕刻艺术,走着走着就会看到地上的雕刻石砖。很多路牌也很有意思,用一幅画来讲一条路,特别神奇。”
“我在意的点,有时会很小,有时会很大。”于是问他,身在异地时,除了对音乐的敏感,他最容易被哪种艺术形式吸引?“美食算不算?”他眼睛一亮,“我今年挺喜欢看那种好看的吃的。去年年底我在国外去了一家餐厅,在一间很小的房间里,就我和厨师两个人面对面,他当着我的面现做出每一道菜品,我看到那些精美的食材,那个过程,我……”
他狠狠咽了下口水。
“我觉得这是件很艺术的事情,过程和我做音乐的理念有很多相像的地方。所以突然对这个很感兴趣,很想学一下。”兴致所至,从零开始,但将来可以到哪一步,他求个自然而然,不需要一定把牛角钻出一个洞来。“生活上很多事情我都是特别随意的,‘都行,存在,都可以’。只是做自己音乐作品的时候,必须还是要追求极致。我一直在做当下我觉得最极致的音乐,一到自己的歌,谁也没办法左右我。”
今年11月他即将在深圳宝安体育场开演唱会,开票3 秒后售罄,他曾立下的豪言“自己一定能抢到票”当然没有实现,只能任由粉丝们大张旗鼓地嘲笑。他们摩拳擦掌了一年等待这个时刻的到来,即使每一场的演唱会规模都超过4 万人,胜出者按比例来看依然寥寥,“幸灾乐祸”的背后,是深深的无奈和遗憾。
他们知道,舞台上的华晨宇会成为另一个人,一个每一次都能完全超过他们想象的表演者,他只属于那个时刻,无法复制,不会重来,所以无可替代。每一年华晨宇都花相当长的时间准备演唱会,“每次都想要一种不同的形式,而且每次都会表演新歌。”演唱会超过音乐的表现,需要表演的状态和画面感,去年在北京鸟巢的演唱会上,他尝试了类似“飞翔”的表演。“我们想既然在‘鸟巢’,就可以有一种‘飞’的画面,而且我有一首歌叫《蜉蝣》,很适合在空中飘的感觉,所以我努力尝试了下,不知道能不能吊着唱。”
第一次上去的时候他也有些害怕,倒不是因为悬空的高度,“中间有一个环节我要脸冲着地面,整个人是反过来的,有点儿生理性的不适。”但之后恐惧感便不复存在,“到了现场我就更不怕了,可能台下有人吧,可以吊着唱歌还可以各种玩,感觉挺好。”在震耳欲聋的尖叫声中踏上舞台的那一刻,他心里从来没有紧张也没有忐忑,“就自然而然地上台了”,“我知道台下都是我的人,站上舞台的时候反而更放松更随意,也没有压力。”
![]()
“极致”
华晨宇的现场演唱有许多高难度的音色表现,需要扎实的声乐功底,但他觉得这只是“术”,“它需要基本功,但我私下很少利用它。”写歌的时候,他总有奇奇怪怪的想法冒出来,歌的演绎难度一再被刷新,“为了达到我想要的那种效果,为了达到那个作品的要求,我就会逼自己去唱好这首歌,我的唱功也自然而然进步了,是根据我写的不同的歌来决定的。”每天练声这些在他这里不成立,“我私下很少专门去练习发声。”
曾写过唱不出的歌吗?
“没有,”他歪头想了一下,“我的很多歌曲都用不同的音色来唱,比如《智商250》、《齐天》,包括《异类》这种说唱,我每次都会花很多时间去寻找合适的音色,但演唱上,我都做到了。”
他在大学时组过一支乐队,乐手们各有所长,但都特别注重声音的音色和美感,这让他从另一个角度对音乐的美感有了理解。“比如一个吉他手在弹奏时会用到一个效果器,让吉他变出很多声音。一开始我不懂,觉得几种声音之间似乎没有特别的区别,但吉他手就会为那一丁点的不同找很久。我才知道,那就是做音乐的极致。”
渐渐,他开始尝试把自己的声音当成乐器,实验不同的音色变化。“去年我写了一首《斗牛》,开头用了很低很低的声音来说唱,也是我第一次用这样的音色。又比如我写了一首叫《新世界》的,中间一段我模仿了埙的音色。”人声这个神奇的构造让他欲罢不能,“我既然拥有了那么好的一个武器,就想不断尝试把它玩出不一样的感觉。”
他很喜欢“极致”这个词语,那代表一个终极目标,也是一种态度。但他所定义的“极致”是精神上的追求,无法被一些简单量化的标准概括。“人的音域是天生的,我的声音不可能变得更高或者更低,我只能让它的可能性变得更丰富一些。而且我觉得,你只要掌握三个八度以上基本就OK 了,往再高或往再低,音色不一定好听。”
华晨宇真正拿出来与公众分享的歌,其实只占了他创作的一小部分。“发出来的歌是我愿意分享的,但其实大多数我不想拿出来,因为我觉得那些是写给自己的。”写歌的时候,有时候他想描述一个画面,有时想记录一种精神状态,“感觉不一样,但基本上创作的时候都有画面感。我私藏的音乐很多是情绪类的,但那些情绪也有画面,很抽象,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形容,音乐是唯一的表达途径。”
是与非,好与不好,这些标准的定夺在艺术里模棱两可,他跟着直觉走。“就好比我出的第一首歌《Why Nobody Fights》,它只有一句旋律,一句歌词,你说它能加东西吗?当然能加,但当时我觉得它OK 了,足够了,不要再多了,这样刚刚好。”写歌往往是因为有一个不错的灵感到来,如何衍生和演绎,只能凭感觉,“你觉得到位,就是到位了。”
他的专辑总数不多,没什么计划,也没什么时间压力。“要有计划的话我可能每年都会出,但我是凭感觉写歌的,写完后想一想,要不要发?往往就算了。”他自觉“没有那么多的词汇量”,写不出那种看起来“特别厉害的词”,所以把这一部分的创作交给合适的词人,“我会和他们有精准的沟通,让他们清楚这首歌到底在表达什么。比如《斗牛》那一首,基本上仔细描述了每一段写的内容应该是什么。”
会不会这样的框架会让作词人感觉戴着镣铐跳舞?“不会,精准了方向之后,他们反而会更知道该怎么写,更快,效果也更好。”他没有特别固定合作的作词人,但有几个经常合作的对象,每次写完歌,他心里就有了最合适的人选。“我脑袋里会构建出歌词的方向,然后就会想到这适合谁谁谁的风格,沟通之后会很顺利。”歌名的部分他较随意,写 demo 时取的名字,一般都会成为歌曲的正式名。“《斗牛》《降临》《新世界》,包括以前《寻》什么的,没有词的时候我已经有了这些歌名,而且我很少改,一开始就定好了。”
他不喜欢命题作文,下一张专辑定怎样的方向,用怎样的一个概念先行,都不在他的考虑范围内。“所有你预设好的东西,都不如你当下这个阶段突然来的灵感精彩。那样的音乐才极致,你不知道它会在什么情况下到来,在我心里,没有预兆的东西才是最极致的。”
他的视角一直只限于当下,“往前看,往后看,我好像都没有特别思考过。”他已经记不清五年前的自己到底有什么不同,“但我知道,现在我变得更厉害了。”歌是他的记录,却无法预言他的将来,“每一年我的心态、心性都不一样,写的东西不一样,想表达的也不一样。我没有办法去思考明年我会变成一个怎样的华晨宇,我预估不了将来的自己。”
“应该会更好吧?”他笑一笑,望向窗外。
摄影:Sang Hun Lee
造型:Woo Wu
采访/撰文:李冰清 Lily Lee
策划:王梦云 Mengyun Wang
化妆:邰凌轶
发型:张凡 Bon Zhang
服装助理:李贞贤、翁冰娴、柳树豪
制片 :TJP 新媒体监制:新裤衩 新媒体责编 :Neil 版式: Wendy你可能错过了这些精彩内容......

清华退学记:学霸们的“丛林法则”
我们接近他的生活,看到一个疏离的集体。
更多精彩的Esquire明星内容,请戳
_________________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