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客风云会】郑永年:消费社会不是光让老百姓掏钱
昨天晚上的“侠客风云会”第二期,我们请到了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教授。郑老师长期在国外,能回国与岛友们视频交流,非常难得。我们对谈的信息量非常大,现将部分内容整理成文字实录,与大家分享。
与郑先生对谈提问的,是非著名岛叔无忌;文字整理,岛妹红拂。大家也可以长摁下图,识别二维码进入直播回放,收看昨晚的视频访谈。(友情提示:结尾有料)
本文由“135器”提供技术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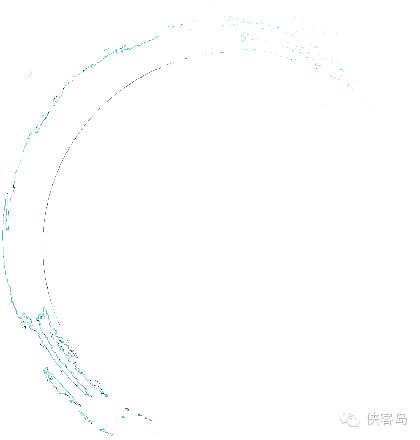
Part 1
无忌:在郑教授您新出的这套书中,我个人认为“重建中国社会秩序”与“再塑中国意识形态”是有高度关联的两个话题,所以今天我们想从这里切入,探讨几个问题。比如说,郑教授的一个观点让我印象深刻:在任何的社会中,权力都可以分为政治、经济和社会三块,政治权力站在哪一边可能会影响国家的秩序。中国社会“失序”风险的根源,就在于这个边界没有理清。那么,您认为这三者之间到底应该存在一个什么样的边界,或者说中国这种“边界不清”的情况下,要如何去理清?
郑永年:通过对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的观察,一个社会的政治权力、经济权力跟社会三方面如果平衡,这个社会就稳定、就发展;一旦失衡,就会出非常大的问题。
我们常说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政府跟社会的关系,但实际上更重要的一块是资本跟社会的关系。政府如果站在资本一边,社会就变得非常弱小;但政府只站在社会一边,经济就发展不起来。所以作为政府,一方面需要资本来推动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要通过对资本的制约、对收入的二次分配,来让社会大众受惠,那么这样就是比较好的平衡,会获得较好发展。政府除了二次分配,还有其他的方法,比如鼓励中小企业的发展,解决就业问题。
从整体的结构上说,中国社会中这三者是失衡的,特别是在地方政府层面,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结合在一起。一旦这二者结合,社会就毫无抵抗力,社会就会暴力化。我的主张就是,真正要减少社会问题,减少社会的暴力,我们要重新使这三种权力处于一种平衡的状态。
本文由“135编辑器”提供技术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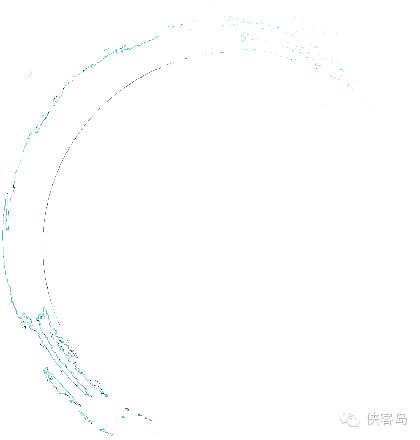
Part 2
无忌:您书中常谈到中产阶级,说中产阶级是一个社会稳定的基石。在中国,您提到,中等阶层还是非常弱小的阶层,很多地方还在破坏中产阶层。
郑永年:亚洲的经济体,日本、“亚洲四小龙”等等,他们在发展中创造了庞大的中产阶级。这些社会,包括台湾、日本、新加坡,这些中产阶级大的社会,往往社会稳定、政府清廉,百姓生活和平。但是中产阶级小的社会,像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就容易有抗议、暴力事件出现。中产阶级大的国家,有抗议也是和平的;而中产阶级小的国家,穷人的抗议是非常不和平的。道理很简单,你自己有车有房,肯定不会烧别人家的车和房,因为你会照顾好自己的财产在先;但完全是一个穷人,就会“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我的观点是,我们国家的中产阶层还是太小。“亚洲四小龙”发展起来后,中产阶层达到百分之七八十,我们改革开放以后,现在也是将近四十年了,但中产阶层还是很小,我们现在贫困线以下人口还有7千多万;如果把贫困标准提高到人均1.25美元一天的话,那会有2亿多人;如果到1.9甚至2美元一天,那以下有三四亿的人口。所以我担心中国中产阶级做不大,社会还是容易不稳定。
那么为什么人家20多年可以把中产阶级做那么大,我们为什么还这么小,我们的财富去了哪里?这就要回到资本权力、政治权力跟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很多研究表明,我们创造的财富里面,经济权力、资本权力和掌握政治权力的比一般老百姓得到的多得多。我们还是要通过培养中产阶层,来实现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否则的话社会很难可持续发展。
本文由“135编辑器”提供技术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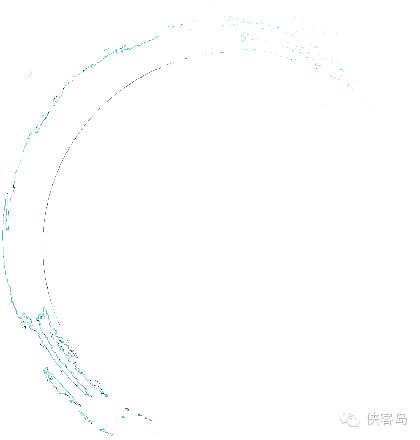
Part 3
无忌:您提到过,阻碍中产阶级发展的因素中,比如住房、医疗等问题,导致了很高的储蓄率,大家都不愿意去消费,阻碍了中国变成一个消费社会。
郑永年:我觉得中国的经济政策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社会政策跟经济政策不分。社会性很强的、不单纯是经济领域的,属于社会保障的部分,包括医疗、教育、公共住房,是不可以随意大规模市场化、货币化的。但因为我们分不清界限,简单地把经济政策应用到这些社会领域,就会出现问题。
1990年代后期开始,医疗成为暴富产业;1997、98亚洲金融危机,很多人提倡我们教育产业化、教育大扩张;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我们最后一个社会堡垒——住房,也失守了,又被产业化。这几块,很长一段时间在中国都是暴富产业,但从任何国家来看,如果这些社会领域成为暴富产业的话,表明这个社会被破坏了,社会会不稳定。这会破坏一个社会的基础。这就产生很多问题:第一,我们消费社会积累不起来。一个人买了房子变成房奴,小孩上学变成孩奴,生了大病可能倾家荡产,在这样的情况下,老百姓哪敢消费呢?所以中国的储蓄很高。中国老百姓不是不想消费,而是不敢消费。所以我在书里说,中国老百姓是“自救”的。
一些西方国家,从比较原始的资本主义转向比较有人性的资本主义,变成福利社会,他们的中产阶级是如何长大的? 一个是通过社会保障,医疗教育这些方面解决好;另一个是劳动工资的增加,使得以前的马克思所谓的无产阶级、工人阶级,转化为中产阶层。这也是西方“二战”以后民主、稳定的基础。中国要是培养中产阶级的话,我想也只能走这条道,日本、“亚洲四小龙”也是这样走过来的。
如果说西方是通过民主、选票的方式,把社会保护好了,那么“亚洲四小龙”不是,他们是政府主动地把社会保护好。如果你不去保护社会,社会就会暴力化。
本文由“135编辑器”提供技术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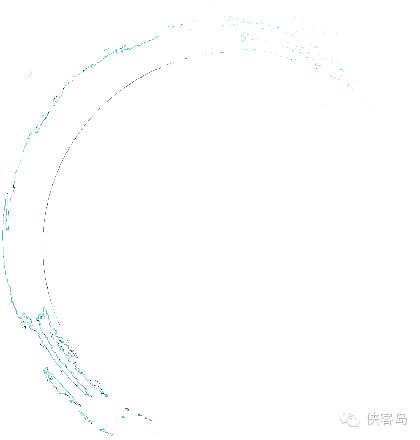
Part 4
无忌:您觉得我们对房地产、医疗教育这些领域的政策,是不是积重难返?
郑永年:已经犯过的错误,不是说不能补救,我是觉得现在要重建中国社会秩序,是有条件的。像是在社会保障方面,任何一个经济体,在经济还没发展的时候,想做社会保障做不了,这些领域都需要很多钱。所以任何一个社会,做社会政策,都要先经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高财富增长,政府已经积累了相当财富的时候,才能做社会政策。我觉得我们中国现在已经到了这个程度了,政府已经有能力去做这个事了。
我们的经济学在这方面有一点问题,老是一种叫老百姓掏出钱来的经济学,这对消费社会理解错了。应该是让老百姓自动的,在医疗、教育、住房有保证的情况下,主动掏钱出来消费。去年的股票市场,我去调查,已经让很多人受了打击;今年的楼市,控制不好的话,又会使大量中产阶级套牢。
就像说去库存,有人说叫农民工来买房子,可是城市有没有准备好接收他们?一个人是不是能成为城市居民,不是买一套房子解决的事,医疗、教育都要配套。中国现在城镇化是53%,但其中只有38%的人具有城镇户口,还有百分之十几还是农民工,这个为什么不去解决它呢?
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多政策,不是为了社会服务,不是为了老百姓的利益,老是考虑政府财政税收,这可能是中国几千年前的问题。就像法家认为要国家富裕,儒家认为要藏富于民,迄今为止还是个遗留问题。我们的经济政策也好,经济学也好,还是没有建设中国自己的经济学。就像亚当斯密《国富论》,实际是百姓的富裕,而不是政府的富裕。
在中国,1994年前倾向是藏富于民、藏富于地方;在1994年后,整个财政向中央倾斜,到今天还是大中央。当然中国这么大的国家,为了国防,中央财政也确实是大一点。但问题是,中央政府还是要承担它的责任。
我一直说,中国还没有“公民”,只有“市民”。因为我们社会保障这些,连省的统筹都没有,最高一级只有市的统筹。北京人走到天津,社会保障都无法共享。但是在美国,任何一个美国人走到哪个州都享受他的权利,因为都是联邦政府统筹。我是觉得,中央要把这种社会的承担做起来,使得我们每个国民,真正成为公民而非一个市的市民。中央政府有财权,但事权在地方政府,地方没钱,这是做不好的。中央只是把钱收起来了,但是总体的统筹没做好。这还是有关部门,没有社会建设、社会保护的概念。
本文由“135编辑器”提供技术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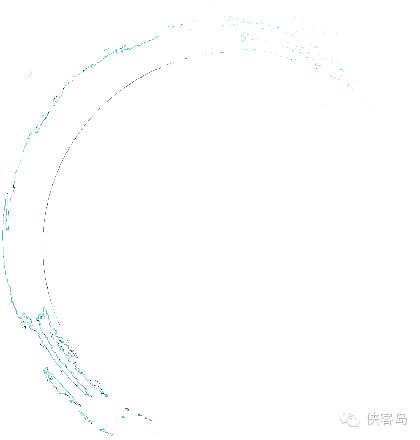
Part 5
无忌:岛友天剑提问说,您曾提到一个观点,大国崛起内部必有健全的国家制度。中国经历几十年的高速发展,经济上无疑是个大国,但综合实力还称不上大国,您觉得在国家制度建设方面,当前最急迫的是什么?
郑永年:国家制度建设上,我的观点是基本国家制度建设在先,民主化在后。历史就是如此,西方、亚洲都是这样。我把国家的制度分为三类,一类是民主化之前必须建立的制度;另一类是只能民主化以后才能建立的制度;还有一种是民主化之前建立,在民主化之后转型。
大部分的国家制度的建立都在民主化之前完成。例如法国的教育制度,也是社会制度了,是拿破仑时代建立的。当然后来有改进,但社会制度的建立和民主化毫无关系,这是政府主动去做的。但是如果基本制度没有,民主化就发生了,这就是非洲,在半殖民后,什么制度都没有,就是现在这种样子。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后发国家,都要先把国家制度建设好,否则很难走下去。一个国家的崛起,是它内部制度建设的延伸,美国在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前,很多制度都建设好了。而苏联,盲目追求外部的崛起,通过军事之类,这是不可持续的,还是内部制度有问题。
中国作为大国,确实要承担区域的责任,但我们要做的要跟能力相配,不可能超越自己的能力做事,强求大国地位是不可持续的,还是先要内部制度建设。那么在内部建设中,哪一块为优先?我就说是中国改革路线图:从经济改革,到制度改革,再到社会制度改革。先发展,再丰富,再民主。经济制度基本建好了,很多方面需要改进,但大的市场制度已经建立;但是 社会制度建设方面,我们才刚刚开始。现在一定要加大社会制度的建设,包括十八届四中全会的“法治”。如果把社会制度和法治建设好了,中国一方面会在实现全面小康后提升为高收入国家,同时也会真正成为一个民主、富强的中国。
本文由“135编辑器”提供技术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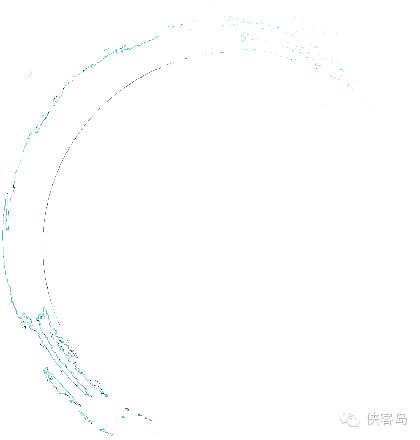
Part 6
无忌:关于政府管理,是不是我们现在很多管理是无效?
郑永年:政府管的少、管得好,这是强政府;什么都管又什么都管不好的是弱政府。我不认为中国是强政府,管的多显得很强,但管不好就会显得是个弱政府。社会要发展,不只是政府的责任。我一直认为,政府要分权给社会,把社会的力量建设起来。政府管应该管的事情,其他下放给社会本身,也减轻政府的负担。
政府一方面要容许社会力量发展,同时政府要监管社会。现在政府还是对社会不信任,所以社会也发展不起来,政府又自己来管,管得不好就会产生紧张关系。
本文由“135编辑器”提供技术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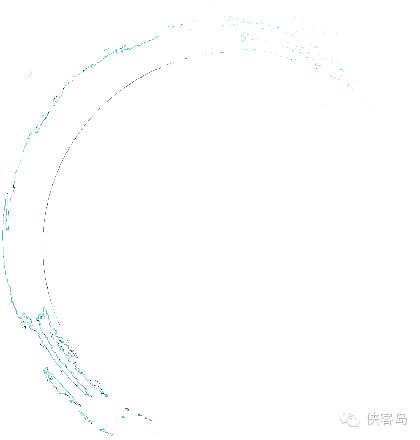
Part 7
无忌:岛友鸿运当头说,郑教授您好,社会危机被说成意识形态的危机,现在国家到底是需要什么样的意识形态?
郑永年:我觉得中国当务之急要树立国家意识形态,现在我们只强调执政党的意识形态,但没有强调国家的意识形态。所谓的对社会来说“意识形态真空”,我看主要是缺少国家意识形态。
那国家意识形态内容是什么?既要有中国的传统资源,还需要全球化背景下面向未来的传统。复兴国学、传统儒学,都不够。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意识形态本身就需要重造。我们现在的国家意识形态很简单。我们的核心价值观需要两种,一种是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一种是共享的价值观。作为全球化的一部分,要跟其他国家有共享的价值观。任何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都由这两部分组成。中国以前就是这样,“三教合一”,中国的文明是学习文明,包容其他文明好的东西,今天也是这样,也是要有开放的态度。
无忌:为什么说要把国家意识形态和执政党意识形态分开?
郑永年:执政党是精英的意识形态,我们十三亿人,接受精英的意识形态,对百姓来说太苛刻了。新加坡也是这样把执政党和国家意识形态分开,前者主要针对党员。
我们中国共产党也是有边界的,除了7800万党员,还有那么多人,还有少数民族,我觉得都要求把执政党的精英意识作为他们的意识形态,还是有困难。
如果有国家意识形态,这个治理成本就低。我们所说的孔孟之道是社会意识形态,皇帝觉得很有用,把它拿过来而已。
我们国家无论是几千年的大传统,还是近代以来的中传统,还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小传统,喜欢不喜欢,都是已经存在的,都跟我们今天的生活相关,发生了的就是已经发生,所以这些意识形态我们都有,不能说只选择一些而把另外的丢掉。现在是怎么把它们包容起来的问题。而且这些不够,还要吸收外面的其他国家的,共同来思考重建意识形态的问题。
注:本文已独家授权海外网刊发,转载请联系15911166061。微信群已满,你可以加岛妹的微信(就是这个号码),让她帮你拖入,注明是想加学生群、公务员群、企业员工群、媒体群、经济金融群还是海外人员群。同时,我们也欢迎大家加入侠客岛微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