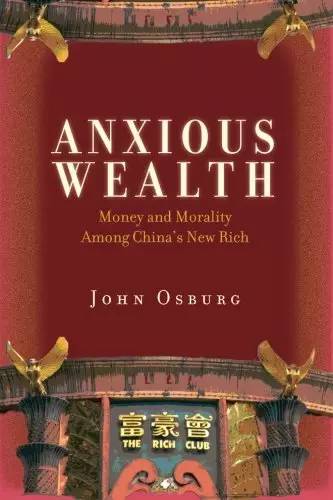为什么中国超级富豪们热衷于将孩子送到国外?| 长报道
▲参加真人秀节目《公主我最大》的Weymi Cho (左)和她的朋友们
温哥华HBIC TV推出以中国女富二代为主题的真人秀节目《公主我最大》(Luxurious Lifestyles of the Ultra Rich Asian),希望借此呈现温哥华亚裔富二代的生活型态。相关宣传影片上传youtube不到24小时,已接近4万5点击率。 一项中国银行与胡润报告的研究发现,百分之六十的中国富人要么正在迁往西方国家的过程中,要么在考虑这样做。中国人正以每年大约450亿美元的速度转移财富。并且不仅是金钱,越来越多他们的后代,也被送往西方国家接受教育、创业和社交。 2月22日,美国《纽约客》刊出了杂志编辑JiaYang Fan的一篇长文《黄金一代》(The Golden Generation)。这篇文章从历史、社会等多种角度解析了中国富豪们的移民热和送子女出国热。她在文中提到,贫穷和落后的记忆在中国人的集体意识中始终存在,「你父母年轻时越穷,他们越想为孩子营造更好的环境。」他们渴望拥有一个受过西方教育的孩子,希望孩子能够接触到自己所无法接触的文化和政治资本。而讨论富二代,是国家在逐步走向成熟时,国民对一国未来精英的忧虑。
编译 | 陈睿雅
来源 |《纽约客》
作者 | JiaYang Fan
1
11月一个清凉的星期天早晨,Weymi Cho驾驶着她的新车来到温哥华市中心,在我住的酒店处把我捎上,这是一辆红色真皮座椅的白色玛莎拉蒂GT跑车。前一天夜里她只睡了两小时。她的公寓新装了一台卡拉OK机,她和一些朋友们整夜唱歌、喝尤乌·里括香槟酒,这处公寓价值四百万美元,可以看到城市的海港。Weymi 20岁,身材瘦削,大眼睛,如瀑长发及腰,在当下的场合里,她穿着一件真丝迪奥衬衫。她有矜持的、近乎贵族般的气质。刚过10点,我们要去购物了。
Holt Renfrew,巴尼斯百货商店(Barneys)在温哥华的近似物,Weymi习惯周末常去的地方之一,尽管她知道其局限性:「它不比拉斯维加斯,那儿明显有更好的选择。」当我们抵达商店,她解释道。Weymi的英语有微妙而明显的口音,当我切换到普通话时她如释重负。她的话语点缀着欧洲品牌名称,被用来充当货币。一个女佣的月工资,可能是一双Roger Vivier缎面高跟鞋的价格。外出一晚会花费掉半只麂皮绒Birkin包。在Weymi的上个生日,三月,不到一个小时,酒水就花费了她大约4千美元——超过两个Fendi手提包。
商店里,Weymi认出了一个以前的同学,她们都曾就读于温哥华的一所时装学院,她在这里当售货小姐。她谈到中国顾客的态度。「他们把这儿当超市,」她说,「一件三千美元的外套就像一盒牛奶。」另外一个售货小姐加入对话,感叹道,这样的挥霍否定了任何排外的意义。Weymi同意。「我甚至不忍直视Chanel包,」她提到一点,「每个人和他们的姨妈如今都有一个boy bag。」
Weymi14岁时搬到温哥华,上寄宿学校。她的家庭在台湾拥有一个成功的半导体生意,她在台湾长大,父母来自大陆。她和姐姐上的是国际学校,为出国留学做准备,整个夏天她在美国或澳大利亚旅行。「我爸爸总是想让我们的英语要好,」她告诉我,「永远是计划将我们送到西方国家。」
去西方国家是很多中国新贵的计划。过去十年,他们席卷而至纽约、伦敦、洛杉矶之类的城市,抢购房地产,引发了关于不公平和全球化财富的焦虑。富裕的中国人成为公众想象力的常客,正如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富人,以及在此之前几十年里海湾国家的富人们。华人在温哥华的存在特别明显,多亏了在环太平洋地区的城市位置,宜人的气候,轻松的生活节奏。中国的新贵们视这座城市为避风港,不仅是他们的金钱,还有越来越多的他们的后代,他们来到这里接受教育、创业和社交。
中国富人的孩子被称为「富二代」。在一个贫穷和节俭曾是常态的文化里,他们的奢侈变得臭名昭著。去年,中国首富之子在网上发布照片,他的狗带着两支金质苹果手表,前爪各一支。网络论坛上,网友们抱怨着富二代「炫耀的并非他们所挣得的东西」,而且「他们怪诞的炫耀对于中国社会的伦理道德观是一剂毒药」。习近平主席提到过「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特别是年轻一代致富思源、富而思进」的需求,而且政府近来为70个富翁的孩子们开办了研修班,让他们接受中国传统价值观和社会责任的速成课。
然而富二代依旧令人着迷。一些最流行的中国电视剧,例如《百万新娘:无悔的爱》,以及《冰与火的青春》——剧情聚焦富二代,他们的爱情生活可以巩固或危害家族财富。还有一档富二代真人秀节目,《公主我最大》(Ultra Rich Asian Girls of Vancouver),Weymi参与其中。
这个由普通话和英语所拍摄的节目,线上播出,被世界各地的中国人热切观看。它记录了6个年轻女孩的生活,炫目的名牌和尖锐的白眼在令人迷惑的快节奏剪辑里展开。女孩们疯狂花钱来证明自己的地位,然后对他人的炫耀表示不屑。第一季结束时,一个女孩被指责为犯下恐怖的罪行——试图用假的爱马仕包和非名牌服装来冒充富家女。第二季在洛杉矶取景,其中的两个女孩正在寻找奢华的别墅。
对暴发户的鄙视态度并不局限于中国,但中国的版本很特别。多亏了共产主义的遗产,几乎所有的财富都是崭新的财富。没有可以模仿的旧贵族,没有如何花钱的模板。我问了《公主我最大》中的一些女孩,作为嫉妒和责难的目标是一种什么体验。「在节目的网络论坛里,人们总是,像是『为什么他们炫耀成那样?』」Weymi耸耸肩,说:「我不认为我在炫耀。我只是在过我的生活。」
▲ 王思聪在微博上发布照片,他的狗带着两支金质苹果手表,前爪各一支
2
购物过后,Weymi和我去到一家高档的泰国餐厅,拍摄节目第二季的最后一集,为了节目餐厅已被清空。我们早早到了,我同节目的创作者Kevin K. Li聊天。Kevin,37岁,生于温哥华的一个讲粤语的家庭,他为这座城市许多的网络节目工作。他告诉我,他曾设想这是一档「富人和名人生活方式」、《长大》,以及《真实主妇》的混搭节目。他说:「我猜测,如果我们好奇这些孩子的豪华生活,那么,加拿大、美国和亚洲的人们也会想。」
演出很容易。Kevin拍了一个简短的宣传片,一个朋友的朋友展示了一系列的包、驾驶了兰博基尼。「一家当地媒体播出后它就像病毒一样传开了。」他告诉我。人们开始用采访请求轰炸他。「富二代的主题现在时机成熟。每个人都会好奇,每个人都有话要说。」
渐渐的,表演的其他成员抵达餐厅——仿佛Helmut Lang,Alexander McQueen,以及玫瑰金iPhone的游行。她们是Diana,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和亚洲研究专业,23岁,在日本、韩国、菲律宾和香港生活;Chelsea是她学校里的朋友,是卡司中唯一的已婚女性,她最近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但看上去苗条无比,她穿着一件粉红色的娃娃裙,覆盖着精巧的羽毛,搭配高耸的Gucci高跟鞋,给人以摇摇欲坠的小鸵鸟形象;Ray,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金融专业学生,她带来同样是富二代的男朋友;Pam,26岁,女孩儿中她年龄最大、最犀利。女孩们等待着拍摄开始,她们细致地察看着每一个人的着装和配饰细节,她们的神态间既有温暖也有竞争,仿佛持续消费的生活培养了一种亲密。
在这一集里,Kevin出场了,他要主导一个关于女孩儿们这一季经历的圆桌讨论。但实际的圆桌是否可取,争论出现了。Chelsea担心桌子会遮住服装太多部分——「早知道我们就在下面穿睡衣了」——但Kevin的眼睛在构图。「我知道你希望的是什么样子,」他同情地点点头,「但我们有六双腿,看起来会很凌乱的。」
这一集从香槟祝酒开始,之后Kevin抛出一系列乏善可陈的问题:Diana为期一天的低预算生活实验感觉如何?(不好。)在洛杉矶选购房屋呢?(很好的别墅,但位置不太好。)Kevin问女孩们和其它阶层的人约会会有什么潜在困难?轻微的暂定后,Diana说:「会很难。我之前做过,它就是」——她花了一秒钟抚平刘海——「就是大家都感觉到尴尬和不舒服。」
这是讨论中不和谐的时刻之一,但摄像镜头以外的交谈更说明问题。某个时刻,Diana并不只对某一个人地宣布道:「我要去修整我的脸。」她听说最近韩国发明了一种整形手术,叫3-D塑形(3-D molding)。无创,各种各样的支架和其他设备用来把脸型塑造成亚洲文化认可的椭圆形。
Weymi帮腔道:「上一次,我和爸妈还有姐姐去韩国,我想做,我爸妈不让我做。」
「这是高科技,」Diana漫不经心地说,「而且很自然。恢复只需8个月。」
我问为什么她这么年轻还要忍受这样的过程,Diana用一种接近于怜悯的困惑表情看着我。
「为了一张更美的脸,当然。」她说。
▲ 加拿大温哥华富二代真人秀《公主我最大》
3
大约1/3的中国财富属于仅仅百分之一的人群。当中国的穷人仍然聚居在世界经济中的发展中国家时,最近一份报道指出中国的亿万富翁比美国更多。杰弗里·温特斯(Jeffrey Winters)是西北大学的一个政治教授:「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构成了人类历史上财富分层最为迅速的出现之一。」他对我说。温特斯,《寡头政治》(Oligarchy)的作者,指出中国是少数国家之一——俄罗斯是另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极端的财富分层在共产主义革命中被消除了,而之后再次出现。正如俄罗斯,中国突然形成的新的寡头政治,意味着那里有许多超级富豪,他们还不熟悉根深蒂固的贵族们悄悄保护财产的方法。「不论文化或年纪,传统的贵族从长久的经验里知道,财富隐蔽、少见是更安全的。」温特斯说。但新贵们,正如托斯丹·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理论,通过炫耀性的消费彰显财富。
一项中国银行与胡润报告的研究发现,百分之六十的中国富人要么正在迁往国外的过程中,要么在考虑这样做。(「富裕」被定义为身家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大约150万美元,这在中国是一笔可观的财富。)中国人正以每年大约450亿美元的速度转移财富。大多数的钱已进入房地产。据美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中国买家已成为美国住房市场最大的外汇来源。
有钱的人因各种原因离开中国。有人担心污染。其他人想为孩子确保一个良好的教育。周雪光是斯坦福大学的社会学教授,他曾在中国获得学士学位,他告诉我:「中国教育系统中的比赛是众所周知的残酷,」他接着说,「好学校有那么多位置,一定程度上,你有多少钱并不重要——你进不去。」不过,对于富裕的中国人,移居国外最根本的原因是,财富在中国岌岌可危。比起焦虑,对国家经济增长的放缓和股市动荡的担忧在加剧。超过一定程度后,没有培养政府官员的支持,或者有时是买通支持,生意很难再取得进步,官员们常常在被竞争对手唆使煽动的情况下被反腐清扫出局。
庄思博(John Osburg),一个在成都常年研究成功商人的人类学家,他告诉我:「担心始终存在,如果与自己关联密切的官员在反腐运动中倒台,他们也会受到牵连,甚至没收财产。还有一个顾虑是,商业竞争对手如果和政府中某些人关系更好,可能运用他们和政权的裙带关系来打压对手。」他知道有人将中国的福布斯年度富豪榜视为诅咒。「在名单上的人们,连续几年来,在一年或两年内出现,然后成为某种犯罪调查的目标,或者在腐败丑闻里被打倒。」他说。
在温哥华,Weymi提到这种焦虑的普遍性:「我有些在上海的亲戚是官员——都是干净的,当然——告诉我他们朋友的故事,他们正为最近的腐败打击力度而烦恼。在中国,重要的不仅仅是你做的,还有你的关系网。」
寻求移民的中国富人数量如此显著,这是第一次。几千年来,统治阶层傲然孤立。「人们现在把中国视作新兴经济体,但是在1810年前,它有两千年都是世界主要经济体。」哥伦比亚大学专攻精英的社会学教授沙姆斯·可汗(Shamus Khan)告诉我。「在此之前,中国的精英非常保守,看待外国人眼光势力。他们认为欧洲的精英是落后人群,觊觎中国文化。」西方人冒险旅行,从中华帝国获得珍贵的商品——瓷器、茶叶、丝绸,而中华帝国视自己为世界的中心。
只有到了19世纪,西方才明显超过中国,特别是军事技术领域。因中英贸易不平等而爆发的鸦片战争,导致了耻辱的失败,以及最终,帝国终结。「中国与全球化的第一次相遇带来了自身的崩溃,此后这个国家从未完全恢复,」可汗说道,「中国新一代精英的出现,恰是中国第二次与全球化接轨,具体维度如何逆转,这会非常有趣。」
▲ 据《2016胡润全球富豪榜》,北京十亿美金富豪人数达100位,首次超越纽约成为世界最多十亿美金富豪居住的城市
4
拍摄后紧接着的Party,持续到凌晨。Ray和她的男朋友指向一个男人,这个男人知道每一个人。他拥有一辆阿斯顿·马丁——这本身不是一个区别,因为他们都在考虑买一辆,但这辆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最新一部007电影里幽灵党同款的阿斯顿·马丁,而且是加拿大BC省仅有的一辆。
这个人是Paul Oei,一个能说会道、满头银发、50岁的人。当我介绍了自己,他立即拍了一张自拍照发到Instagram——这是他惯常打招呼的方式。然后他递给我3张商务名片。第一张确定了他是有机生态中心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和CEO,一个堆制肥料的公司,也是这个节目的赞助商;第二张,温哥华华裔小姐选美比赛的主席;第三张,加拿大Manu移民和金融服务公司的负责人。Oei10年前成立的Manu,提供移民策略、投资和中国公民移民国外如何适应的建议。对于想要在温哥华立足的富二代,他是一个值得信赖的推手和非官方的大使。
Oei说,如此多的中国人想要搬到温哥华,Manu可以容纳更多的潜在客户。「他们毫不犹豫地置业,」他说,「这里非常便宜,比如说,比起纽约、洛杉矶、香港,或日本。首先,购买房地产非常划算,然后,第二,这些人有这么多钱,他们想要多样化,把钱放到安全的国家。」
我问他,他合作的那些人是否可视作中国的百分之一。「我不会说他们是百分之一,」Oei回答,「更多像是介于百分之一和百分之二的。」他的客户往往在地区制造业城市得到了蓬勃发展,而最富有的人来自北京、上海和深圳。「金字塔最顶端有政治支持或联系,」他说,「他们不需要转移财富。」
几天后,Oei带我去最近开在温哥华市中心的一家中国餐厅吃晚餐。停车场里的宾利和劳斯莱斯,以及广阔的海滨景色,给我一流宾客的印象,北京烤鸭,88美元。Oei一边从小陶罐里倒出香菇汤,芳香四溢,一边进一步阐述了那些决定扎根加拿大的中国家庭的目标和态度。初期,他们经常认为这是一个暂时的安排。「当他们到了,最初一两个月,他们想回去,」他说,「这个新世界太无聊了。」转折点通常在一年半以后。「经常是孩子,毕业了,然后他们说:『我爱加拿大。这儿就像天堂——我不想回去。』」
餐厅的老板,胡媛(音),顺便经过我们这桌来跟Oei打招呼。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面颊饱经风霜,举止简洁,她曾是北部城市西安的一个成功的餐厅老板,来温哥华两年了。当我问她怎么决定过来的,她微笑着摇摇头。「我丈夫来温哥华旅行,然后他的哥们儿们把他拽去开放参观日(open houses),」她说道,「接下来我知道的就是,我们在这个城市签约了产权契约。」尽管昂贵,但她没有觉得这是她留在这座城市的承诺。这似乎是针对中国经济变化莫测的保险。
让她思考留下的是她的11岁儿子。她告诉我,他正在参加洛杉矶少年高尔夫锦标赛,她正在计划为了儿子逐渐向东搬迁。胡女士略带几分自豪地解释了她开餐馆的计划,洛杉矶,拉斯维加斯,然后最终,纽约。我问为什么是纽约,她吃惊地看着我:「为了我儿子,当然。东北部是所有顶尖大学的所在地,那是他将来会生活的地方。」
胡女士的当务之急是她这一代人的典型,中国第一波企业家。社会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他们积累了大量资本,足以在一种新的特权氛围中抚养子女,而独生子女政策的遗产,让父母期望的那束目光紧紧追随子女。此外,贫穷和落后的记忆在集体意识中始终存在。我记得Ray曾告诉我:「你父母年轻时越穷,他们越想为孩子营造更好的环境。」声望和实用性的思考刺激了他们渴望拥有一个受过西方教育的孩子。同样相关的还有Oei的观察,他的客户们在中国不是最富或最有关系的人,他们希望孩子能够接触到自己所无法接触的文化和政治资本。讨论富二代,是国家在逐步走向成熟时,国民对一国未来精英的忧虑。
▲庄思博(John Osburg),一个在成都常年研究成功商人的人类学家关于中国商人的著作《Anxious Wealth》
5
在温哥华,我遇到了Andy Yan,他是一个城市规划师,关于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做了大量的研究。我们开车去了西点格雷,最贵的区域之一,它俯瞰布勒内湾。(通常,最合意的房地产在西部,朝向大海,国际货币潮将长期居民推入内地。)这是一个明亮而凉爽的下午,当我们驾驶着经过一个又一个枝繁叶茂的街区,我们见到的仅有的车辆是养护车。「感觉这儿像一个电影场景。」Yan说。我们经过的房屋,是可以看到水的宫殿,呈现出对旧世界的欧洲魅力剪切、黏贴的作法:法式窗户两侧有科林斯柱,覆盖着都铎式的屋顶。Yan指了指站在许多安全门旁的狮子雕像:「这是一个大破绽,主人是中国人。」
Yan生于温哥华,他的家庭来到这里将近一个世纪。他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学习了城市规划,然后在杰出建筑师谭秉荣(Bing Thom)那里得到了一个工作——谭是温哥华本地人,他的家庭最初来自香港,Yan的工作是监测城市房地产繁荣带来的影响。最近一项研究,Yan发现在三大高端西侧街区出售的单户住宅,70%是由中国人购买的。许多房屋的居住者将自己描述为家庭主妇或学生——27%的受访者,其房屋平均价值305万美元。这个发现让Yan将之称为「宇航员」家庭安排。房屋的购买者,通常是丈夫,他们在亚洲生活和工作,挣钱很快,然而他们将家庭成员安置在加拿大,为了将钱转移到社会和政治稳定的地方。Yan为温哥华这样的地方创造了一个短语「对冲城市」:他们是用来防范国内波动的地方。
过去六年,温哥华独栋住宅的价格上涨了75%,平均190万美元。同时,家庭收入中位数几乎没有改变。当地人的经济差距并没有消失。去年,一位愤怒的29岁女人发布了一张自拍,标签是#没有一百万。数百名温哥华的其他市民纷纷效仿。
David Eby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立法议会上是温哥华-灰岬选区代表,他告诉我最近他会见了小区的居民协会。「所有的交谈都是关于大陆的钱。焦虑很多,从某种意义上说,大陆买家购房,但不回馈社区或融入其中。」
压力之下,温哥华市长罗品信,提出了豪宅税和房地产投机税。他建议提高投资性房产空置税,要求对国际投资和缺席的业主进行「更好的跟踪」。但似乎这些措施不太可能实施。房价上涨,普通加拿大人发现自有房屋价值攀升。联邦政府中的许多人,包括总理贾斯廷·特鲁多,主张对具体措施保持谨慎,以免打压房产价值。此外,富有的国际买家意味着更高的税收。「国家对税收上瘾了。」Eby告诉我。
我问谭秉荣相关的变化。房地产繁荣,当然,对建筑专业来说不错,但如今谭快70岁了,发生在他家乡的事情令他困扰。「我生意很好,我在温哥华房地产上赚的钱,比我工作一辈子的都多。」
谭对消费已经有效地代替生产成为温哥华的成长性行业表示担忧。「城市变成了一个旅馆。」他说。他反对——国家授予居留权以换取投资的做法——他称其为「销售国籍」,包括加拿大和美国在内。「我认为任何国家都应该反对这个,因为你不是在购买最好的人,」谭说,「他们不在自己的国家投资。没有归属感。但这是世界趋势。它正在英国发生,正在法国发生,正在澳大利亚发生。任何地方。」
▲ 加拿大温哥华富二代真人秀《公主我最大》
6
共识是富二代正在准备继承父母的事业,但并不一定是这样。节目中的一个女孩告诉我:「我爸爸不愿意让我杀了他辛苦创办的公司。他跟我说:『如果你没有能力来接管,你最好是每月拿月收入,把管理权交给别人。』」父母经常提供给孩子一笔钱,让他们去创办自己的小企业,考验他们的商业才能。Weymi的父母允诺她50万美金,去创办一本介绍奢侈生活方式的双语杂志,杂志会免费发放到高端商店,培养客户的排他性。「我没有计划通过它来挣很多钱,」Weymi说道,「但我的朋友都很同意:这是一个非常Weymi的项目。」Ray的男朋友,虽然还没有毕业,但正计划在温哥华的市中心开一家回转寿司餐厅,父母入股的金额客观。「我计划所有的菜单都在ipad上,不仅可以点菜还可以玩游戏。」他告诉我。
我在节目里遇到的所有女孩,唯一一个有工作的是Pam,她兴致勃勃地在每周70小时的工作时间里挤入3次演出。她是这个节目的制片人,在她叔叔开办的拍卖行里工作,经营着自己的模特经纪公司。一个上午,我陪她从一个工作到下一个。我们在一个临时搭建了跑道的服装店碰面,她正在为一个慈善活动面试模特,然后乘车去了拍卖行。她显然很享受这种节奏。「做朝九晚五的工作,太无聊了,你无法跟人打交道,」她大笑着说,「我最大的缺点是,完成枯燥的任务对我很困难。」她引用了一个成语,虎头蛇尾。
Pam精力充沛。她讲话,常常在英语俚语和满是谚语的普通话之间切换,让人联想到一个分割屏幕上的人。她从哈尔滨来到温哥华,上中学。15岁前,她给自己租了一个屋子。她告诉我:「如果我一直待在中国,我觉得我会被保护得很好。远离我的家庭让我能更珍惜他们的牺牲。」Pam回忆起大学时她等待一笔5万5千元美金的转账。几天后,她打电话给妈妈,妈妈说银行有点小的手续问题。之后,一个亲戚透露了她妈妈的生意濒临破产。「像是,第一次,我真正地了解到我妈妈多么不想要我担心。我不敢想我是多么的粗心啊。」
我们驶入了一个购物中心,在写着「VANDERFUL拍卖公司」的标志牌前停下——「精彩(Wonderful)」和「温哥华(Vancouver)」的双关语。paM带我走进一个陈列室,满是水墨山水画、瓷马雕像、精美雕刻的红木茶几。她是这家公司的营销总监,作为公司商务中唯一的英文交流者,她花了两个月时间把拍卖目录从中文翻译成英文。参观仓库时,Pam指着玻璃柜里的一个小的弯曲竹板,说,这是给书法家休息手臂的。「你称它什么?」她低声说,然后不好意思地说,自己最终用英语把它渲染为「手肘升降机。」「商务翻译,」她点点头,「比人们想象的还难,而且英文词典里不是什么都有。」
这个感叹我常常在温哥华听到,它似乎表达了一种令人羡慕的国家化生存伴随而来的错位。当我们在一个精致的清代柜台前停下来,我问Pam她是否想过在中国工作。她考虑着这个问题,手指在柜子面板上雕刻的孔雀身上移动。
「事实上,我不确定现在我还能完全融入那里,」她慢慢地说,「我缺少父母的中国商业诀窍。西方人都是直截了当。但是,当你在中国谈判条件,重点是没有说出的东西,同时隐藏和暗示你真正想要的东西。在中国,我被对待得像个幼稚的小孩,有时我觉得自己像个外星人。」Pam和很多她的朋友,十几岁就移民,在两种文化中生存。加拿大人,和西方人一般,高深莫测。他们的父母曾希望孩子能拥有的文化资本可以是难以捉摸的。但在中国发生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之时离开中国,让他们在那儿也是外国人。
7
Weymi有一天晚上和我吃晚餐。第一次,她穿着随意——及膝长的羊毛开衫,sensible flats,没有化妆——我们前往一家风格简约的中国餐厅,叫小四川,地点是里士满,遍地是加拿大出生的中国人,和法拉盛、皇后区很像。Weymi驾驶的时候,我问她比起亚洲是否更喜欢温哥华,她说是的。她轻轻敲了一下方向盘,说:「就像这个:当我在这里开车,需要转弯,我打开我的转向灯,然后转弯。这是世界上最普通的事情。而我在亚洲,我亮出我的信号灯,然后人们马上,不是减速,而是全都加速然后拦住我的路。太令人发狂了,然后,一小会儿后,我也变得像那儿的每一个人了。当我在亚洲,我就不打转向灯。我就这么做。你没有办法。」
小四川比名字所暗示的更大。几乎在那儿的每一个人都是中国人,当我们进去的时候,Weymi朝一桌吵闹的年轻人挥手。「在这个小镇上,每个人都认识彼此。」她心不在焉地说。我们点完菜后,她问:「你想看我和贾斯廷·特鲁多的合照吗?」她浏览着自己的手机。「当时他还不是总理,然后我只是叫他一起照照片。我喜欢贾斯汀。实际上,我喜欢大多数的加拿大政客。」但是,她说西方人在一些例如大麻和死刑的问题上太自由了。(中国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处死的人都多,每年超过1000人。)
我们吃的时候,谈话转移到不平等,以及它在中国和加拿大可见的程度。「你去过东哈斯汀吗?」她问,指的是一个相当于贫民窟的临近温哥华的城市,周围是时尚的酒吧和百万美元的公寓。「那就是你看到的极致。但大多数情况下,每个人在这儿的生活都还不错,」她停顿了一下,「至少,比中国好很多。」她回忆起去上海时,误入棚户区,里面是从中国农村来的外来务工者们,然后她谈到中国南方,云南的贫困地区,她妈妈出生的地方。「当我小的时候,我妈妈会告诉我他们以前有多穷,」她说,「那是一种让你恐惧余生的贫穷。」Weymi的外祖母和姨妈洗衣谋生。「她不想像她妈妈或姐姐一样,总是闲言碎语地说着村里比自己富裕一点点的人,」Weymi放下筷子,「这是典型的乡下人的鸡毛蒜皮的小事,但如果她留在那里,那就是她的一生,」她摇了摇头,深呼吸,「我的意思是,你可以想象吗?」